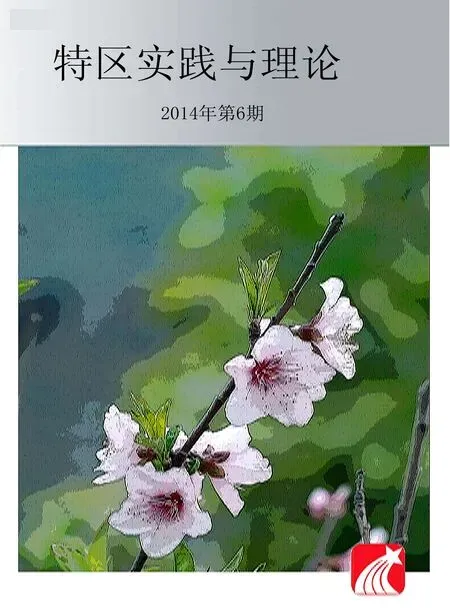城市社區治理中自組織發展的特性分析
胡冰
社會“自組織”是相對于“他組織”的另一種組織化方式,它們的區別在于社會治理系統組織有序的動力不同,社會“他組織”是依靠外部的強制控制力實現社會組織的內部組織化、有序化,而社會“自組織”則是依靠組織內部組織因素的相互認同與協調。社會自組織是人類社會活動的普遍現象,但在社區治理中自發產生自組織的案例還不多見。深圳市龍華新區西頭新村2004年底出現的社區自組織——業主委員會(后來的業主自治委員會)為我們提供一個個案。對該案例的分析研究,有助于我們認識城市社區治理的新途徑以及在我國實現社區自主治理的特殊性。
一、西頭新村自組織的發展過程
西頭新村位于深圳市龍華新區民治街道辦事處上芬工作站西頭社區,占地面積約5萬平方米,共有138棟樓房,出租屋7160間套,居住人口1.83萬。西頭新村的社區治理分為兩個重要階段:
(一)自組織階段
西頭新村,原名“宇豐城”,2002年由宇豐地產公司在西頭股份公司集體土地上整體開發,138棟樓房由來自廣東、湖南、福建等地的人承租,其中廣東省化州籍人士約占40%,業主分別整棟承租,然后再租給外來人口居住。業主、住戶全部由外來人口組成,是典型外來人口組成的城中村社區。
西頭新村所在的民治片區和深圳的許多地方一樣,由改革開放初期的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繼而迅速向信息社會發展,同時積累了大量的外來人口,與原特區內城市管理和社會管理的規范、有序相比,存在巨大差距,轄區城中村外來人口多,居住人員平均文化程度偏低,城市二元結構明顯。多年來,由于管理體制不順,西頭新村成為城中村“臟、亂、差”的典型。小區的惡劣治安和衛生環境導致了房屋出租入住率不到4成,而且租金低。整棟承租者(業主)的收益直接受到嚴重影響。
2004年底,西頭新村業主自發召開全體業主大會,138棟出租屋一棟一票選出了12名業主代表,成立小區認可的業主委員會,并通過了《龍華上塘西頭新村(宇豐花園)業主委員會章程》。2005年至2009年,西頭新村社區完全由業主委員會自主管理。業主委員會按0.3元/平方米向業主收取管理費,用于社區管理和服務的支出,如聘請保安、修理水電、衛生清掃等等。業主委員會成立后,他們向保安公司聘請了15名保安,對小區實施24小時治安巡邏防控,填補了以前小區沒有保安的空白。出資自建社區廣播系統,實時播報小區的生活信息和實時動態,播放防詐騙、防火、防盜等溫馨提示。為社區租戶提供24小時便民服務,居民水、電出了問題能及時得到解決。鄰里糾紛、家庭糾紛,業主委員會積極主動介入調處。業主委員會內部也制定了相關的工作制度,比如,財務公開制度和多人簽名制度等。
自業主委員會自主成立并自主開展社區的管理與服務工作后,西頭新村的治安、衛生等狀況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房屋出租率有所提高。但業委會運作不暢,小區各項建設變化不大,社區治理依然比較混亂。業主收入不多,住戶意見大,造成部分業主和租戶經常到街道辦投訴上訪。
(二)政社互動階段
2009年以來,在街道辦的支持和引導下,西頭新村實行社區自治,采取民主“懇談”、透明化管理、周到服務、增加政府投入、完善設施等措施,實現了環境整潔、治安良好、鄰里和睦。雖然租金比周邊高出約15%,出租率卻達100%。不僅居住在這里的居民不想搬出去,原來搬出去的居民也陸續搬回來,居民家園意識、歸屬感明顯增強。2010年以來,小區再未發生一宗上訪事件。
在民治街道辦事處的指導下,2009年底,138棟業主嚴格按照選舉章程,公開選舉成立了西頭新村業主自治委員會。選舉全程由政府相關部門指導和見證。民治辦事處主動介入,摒棄以前政府大包大攬、效果卻不理想的管理模式,實行簡政放權,旗幟鮮明地支持探索、鼓勵創新、允許試錯;新區綜合辦、社工委、城建局、龍華公安分局等相關部門,也多次深入現場調研,多方聽取意見,全力幫助協調解決創新探索中遇到的困難問題。龍華新區領導多次到小區調研,充分肯定“西頭模式”,要求總結推廣、提升完善。在黨委、政府的引領下,統一了業主、租戶及居民群眾的思想,激發了業主自治熱情,小區內的各種社會力量得以凝聚整合,小區的自主管理走上了規范化道路。
第二階段由于公共部門的介入,解決了西頭新村社區自主治理過程中業主委員會遇到的困難和問題,順利走出了自組織發展的瓶頸,社區的治理上了一個新臺階。西頭新村的建設和管理體現了“政府支持引導、居民自主管理、多方良性互動”等特點。
二、西頭新村自組織發生發展的特點
西頭新村社區自組織的發生、發展有一些自身的特點,既有共性,也有個性。
一是社區的特色。西頭新村是典型的城中村,幾乎都是外來人口,是農村城市化過程中的典型,區域性質的變化與城市文明的差異明顯。這一特色在部分城市帶有共同性。但其管理體制又有特殊性。由于整個社區由工業區轉變而來,傳統的社區治理體系在這里被打亂,沒有居委會,沒有成熟或成型的社區管理機構,這就為業主委員會的自主產生提供了可能性。
二是自組織發生動機單一。由于整個社區138棟樓房全部是外來業主從原工業區管理公司手中承租過來,自組織發起人的動機十分單一和集中,就是利益驅動。雖然嚴格意義上講,所有的自組織都是利益驅動,包括共同價值、社區認同、家園歸屬等等,但西頭新村的自組織發生的動機,經濟利益是最明顯和集中的意志。樓房承租要有經濟效益,一旦經濟利益受損,承租者就會像經營企業一樣,帶有鮮明的利益最大化的沖動。這也正是西頭新村自組織產生的直接動力。
三是自組織發展瓶頸。任何一個自組織都需要經歷發生、維護與發展三個階段。西頭新村的自組織性質的發生完全是自主形成的,但在自組織的維護和發展階段遇到了很大困難。其根本原因是社區治理性質的自組織不同于一般公益性、慈善性組織,它面臨的是整個社區公共事務的治理問題,盡管西頭新村自組織發起是因為共同經濟利益最大化問題,但一旦由一個社區自組織來承擔復雜的社區治理任務時,明顯力不從心。這正是社區治理與企業管理的本質區別所在。
四是公權力的助推作用。西頭新村業主委員會成立以后,雖然做了很多工作,社區公共事務治理也相比之前有了一些改善和提高,但仍然困難重重,社區治理效果不佳。2009年后,民治街道辦事處、社區工作站等公權力部門介入后,社區治理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五是政社良性互動顯威力。公權力介入后,并沒有完全回到傳統的政府包攬的模式,而是繼續發揮了社區自組織在社區治理中的自治作用,但此時的自主治理已經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公共池塘”治理,帶有鮮明的政社互動的特點。
三、社區治理中自組織發展的特殊性
首先,社區治理自組織與其他社會自組織的性質差異
無論是國內國外,社會自組織的種類很多,與其他純粹公益性、慈善類的社會自組織不同,社區治理中的自組織有其特殊性。一般性的社會自組織工作任務比較單一,工作目標清晰,大多以項目為主,從事某一明確的組織活動,比較容易組織和開展工作,效果的評價也比較容易。但社區治理卻十分復雜,幾乎涉及到方方面面。一是社區內的事務繁雜,是一個小社會。它面臨的公共事務很多,管理和服務涉及面廣,涵蓋了社區治安、環境、衛生、人口管理、矛盾糾紛、養老、婦女兒童權益保護等等。二是面臨一個開放的系統。社區治理既然涉及公共事務,它必然要與社區外部已然存在的治理體制發生關系。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社會治理仍然是黨委領導、政府主導,撇開這個外部治理環境是不可能也不現實的。
因此,與其他社會自組織相比,社區治理中的自組織的性質必須是公共事務性的,其目標是多元的,治理方式必須是開放的,政社互動是必然的。
其次,社區自主治理的社會基礎特殊性
西方發達城市的社區治理中自組織的性質更明顯,而且運行順暢,與西方社會的社會基礎有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初形成城市的過程就是一個市民社會與貴族統治者抗爭與分權的過程,市民自治的意識強烈,而且形成了一種市民自治文化傳統。所以現今西方發達城市的社區治理中仍然保持了這種傳統。我國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長期的封建統治使得社會自治沒有空間,盡管也有一定程度的鄉村自治,但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自治,它帶有強烈的宗法、家族統治色彩,是皇權在鄉村治理中的微縮和復制。新中國成立后,20世紀50年代有了城市街道居委會自治的法律規定,但要么被文化大革命徹底破壞,要么被后來的行政化所替代。20世紀80年代出臺了村民自治的規定和法規,農村的自治色彩比城市雖然要濃一些,但也沒有真正實現完全的村民自治。
因此,我國城市社區自主治理可以說是剛剛起步。社區居民的自治意識不強、自治素質不高,自主治理經驗不足等,是當前社區治理面臨的現實狀況。
第三,對西方有關理論的揚棄
社區自組織發展實際上是一個集體選擇問題和自主治理問題。在這兩方面,西方有比較多的研究成果。
大家熟知的集體選擇理論模型有“公地悲劇”、“囚徒困境”、集體行動的邏輯等。“公地悲劇”理論認為,在公共資源一定或有限的情況下,如果每個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結果必然是整體公共資源的退化和集體利益受損。“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個人最佳選擇并非團體最佳選擇。曼瑟爾·奧爾森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也認為,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產生極其有害的結果。以上理論模型均認為,集體中的個人理性選擇必然導致集體的非理性,換言之,社區中的自組織發展是難以想象的。
奧斯特羅姆教授筆下的自主治理是對公共資源的分配與維護,以保證公共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和公共資源的可持續性,增進成員們的福利。在沒有公權力介入的前提下,依據創新制度供給、維護可信承諾和實行相互監督,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公共福利目標。但社區治理不僅僅是資源分配和維護問題,它涉及社區諸多公共事務,涉及社會公平和社會和諧,其社會福利的范疇已經超越了一般意義的利益問題。
集體選擇的悲劇理論關注到每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因素,卻忽略了系統的開放性和信息的流動性,尤其是忽略了人在制度創新上的能動性,將個人的理性與集體的理性完全對立起來。自主組織理論分析了集體選擇的理性可能以及條件,為社會治理中的自組織作用發揮找到了實現途徑,但對于復雜的社區治理似乎并非良方。
西頭新村的案例表明,西方的有關理論在我國有個適應性問題,不能照搬照抄,走中國特色的社區自主治理之路需要符合實際的理性思考。
第四,自主發生、政社互動是現實選擇
從西頭新村社區自組織的發生來看,社區治理中產生自組織是有可能的,但社區公共事務治理依靠社區自組織完全自主治理是不現實的。可行的選擇就是在社區自組織產生后,在實現社區自治與公權力介入之間取得聯系,形成社區自組織的自主治理與公權力影響之間的良性互動。西頭新村后來的發展也印證了這個模式的有效性。西頭新村社區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的資金和政策支持,需要黨委的方針性指引,需要與外部取得可持續的力量。反過來,社區自組織的自主治理力量也是巨大的,它似乎尋找到了社區自治的可能性,西頭新村對走出一直困擾我們的社區治理行政化的藩籬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我們在打破社區治理行政化的實踐中,不能又走入完全去行政、去政府的極端。
城市社區自組織的發生發展在我國還是新生事物,我們應有的態度應該是有所區別,大膽試驗,劃分邊界,各司其職,良性互動。
[1]潘澤泉.行動中的社區建設[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張康之,石國亮.國外社區治理:自治與合作[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12.
[3]吳群剛,孫志祥.中國式社區治理[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11.
[4]劉偉紅.社區治理——基層組織運行機制研究[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0.
[5][美]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6]聶苗.社會“自組織”視閾下黨的群眾工作機制探索[J].傳承,2013(13).
[7]龍太江.社會管理中社會自組織功能的培育與開發[J].領導之友,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