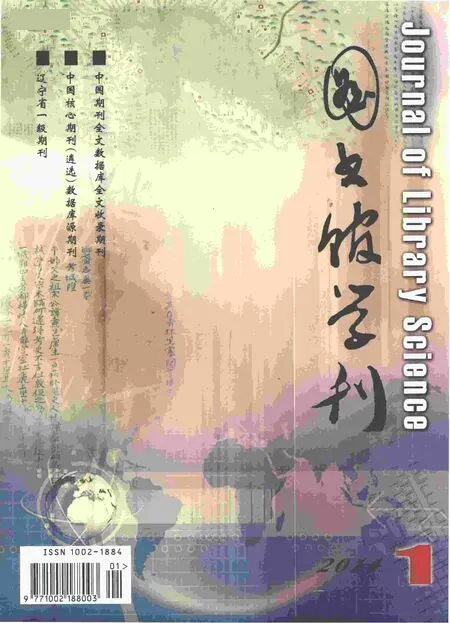圖書館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的版權問題芻論
邢 幸
(許昌市少年兒童圖書館,河南 許昌 461000)
學術界普遍認為,現代意義上的口述歷史文獻活動肇始于20世紀40年代美國口述歷史學之父艾倫·芮文斯(Allen Nevins)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做的具有開拓價值的工作。但是,據我國學者王子舟、尹培麗等人的考證,早在19世紀70年代美國班克羅夫特圖書館(Bancroft Library)就開展了口述歷史業務,是現代圖書館開發、收藏、整理、傳播口述歷史文獻的先行者[1]。20世紀90年代初,口述歷史文獻工作在我國圖書館界悄然興起,特別是2002年“搶救和保護中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工程”的啟動,對這項工作起到了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汕頭大學圖書館、貴州民族學院圖書館、新疆建設兵團黨校圖書館等都開展了口述歷史文獻工作。口述歷史文獻工作滲透著版權保護的思想,而能否在這項工作中落實版權保護的原則,有效地保護版權,成為制約這項工作順利發展的重要法律問題。口述歷史文獻版權保護的具體方法和策略與其類型有著密切的關系,尤其是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的版權問題相對復雜,應是圖書館關注和研究的重點。
1 基于版權的口述歷史文獻類型劃分
1.1 敘述式口述歷史文獻
敘述式口述歷史文獻的形成過程以口述者的“口述”為主,是指口述的動義、目的、主題、結構、內容、表現形式等都由口述者決定,圖書館只起到收藏和管理口述歷史文獻者的角色,或者僅充當“輔助者”的身份。按照《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3條第2款的規定,“輔助者”所做的工作包括為創作進行組織,提供咨詢意見、物質條件,或者其他輔助工作。具體到口述歷史文獻工作,圖書館的輔助性貢獻包括為口述者提供錄音、錄像的場地、設備,提供速記人員,對口述者迎來送往的安排,以及正式口述前簡單的彩排等。依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3條第2款的規定,這些工作不具有創作性,圖書館不能對最終形成的口述歷史文獻主張任何權利,包括版權精神權利和版權財產權利。但是,作為“幕后英雄”,圖書館可以得到口述者,以及其他部門、團體(基金會等)給予的相關物質和精神獎勵,但這不是因為創作活動得到的版權利益回報。對于這種類型的口述歷史文獻,圖書館作為管理者非經授權的隨意處置,或者保管不當,不但可能構成對版權的侵犯,還可能涉嫌對口述者財產權的侵犯。比如,如果口述歷史文獻因為失火、失盜、蟲蛀等原因造成損失,就不僅會使財產權受到侵犯,而且會進一步影響版權利益的實現。
1.2 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
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下,圖書館并非處于配合口述者的“輔助者”的地位,而是積極、主動地介入口述活動,甚至對口述歷史文獻的形成起到控制性、決定性作用。所謂“控制作用”,不是指對口述者口述內容的左右,而是指保障訪談活動的順利完成。正是圖書館對口述歷史文獻工作的主動介入,才使今天看來非常珍貴的許多歷史文獻得以保存[1]。在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形成中,圖書館的工作主要包括:確定訪談專題、對訪談專題進行背景資料研究、尋找訪談對象、設計問題、為訪談者提供清晰的框架,通過機智、巧妙的提問、提示等方式對訪談者進行引導和相關的、恰如其分的干預,以最終獲得更多的信息[2]。在這種情況下,圖書館的工作具有了創作性質,即已經成為口述歷史文獻作者,或者版權人之一。雖然在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中口述者的口述內容仍然是主要部分,但是圖書館的創作貢獻已經不可抹殺。然而,圖書館究竟充當什么樣的創作角色(委托創作、合作創作等)以及創作貢獻的大小,需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圖書館對口述歷史文獻創作活動的實質性參與,使其版權問題變得復雜,而與這類文獻相關的糾紛也最易發生。
2 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的版權歸屬
2.1 口述者與訪談者之間的權利歸屬
Ritchie指出:訪談是雙方共同參與制作的產物[3]。由于在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中,訪談者參與了創作,那么就屬于“合意創作”的情況,版權歸口述者和訪談者共同擁有,即民法理論中的“準共同擁有”。按照《著作權法》第13條的規定,這時口述者和訪談者應共同行使版權,或者只能就可以分割的自己應該享有的版權予以行使,而未經對方許可,不能代為行使其版權。如果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的版權無法分割,那么口述者、訪談者任何一方行使本身享有的版權應征得對方的許可,對方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但是版權行使者應就相關收益向對方分配。另外,在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中是否存在“委托創作”的可能性呢?一般來講,這種情況較少出現在口述歷史文獻的原始創作中。因為,口述者口述的內容始終是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得以存在的主要因素,如果連署名權都能通過委托創作的方式轉歸訪談者所有,那么何來“口述”呢?把訪談者定位為口述者顯然不合邏輯。但是,“委托創作”較多出現于對原始口述歷史文獻的再創作之中,包括改編成文學作品、電影作品、曲藝作品等情況,即便如此,這些衍生作品仍然要為原版權人署名。
2.2 口述者和圖書館之間的權利歸屬
在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創作中,除了訪談者的個人行為外,訪談者通常都是圖書館的委派者,或是圖書館員,或是圖書館以借調、外聘等方式引進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員無論是正式職工、合同工,抑或臨時工,都與圖書館之間存在著勞動法律關系,或者事實上的勞動法律關系,這時訪談者的行為具有職務性。按照《著作權法》第16條第1款的規定,對于職務性的口述歷史文獻,訪談者享有版權(包括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但是圖書館有權在文獻完成兩年內優先使用。在此期間內,未經圖書館許可,訪談者不得把其在口述歷史文獻中享有的版權許可讓第三人使用。但是,圖書館能夠通過約定的方式享有除署名權之外的訪談者享有的版權,圖書館可以給訪談者獎勵。當訪談者的創作行為具有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性質時,那么訪談者個人則不能對口述歷史文獻主張權利,這時精神權利和財產權利都歸圖書館享有(當然不包括口述者享有的版權)。在此情況下,訪談者參與創作的口述歷史文獻相應部分的版權的表現形式由圖書館決定,代表圖書館的意志,并且由圖書館承擔法律責任。
2.3 口述者、圖書館和第三人之間的權利歸屬
“第三人”不是指對口述歷史文獻進行“一般性”使用的用戶,比如外借者、閱覽者等,這類利用不能使口述歷史文獻增加新的價值。“第三人”是指對口述歷史文獻的演繹創作者,這種創作行為通常會產生新的附加了獨創性的衍生作品,比如文學作品、電影作品、曲藝作品,或者譯文、數據庫、多媒體的制作者。按照版權法原理,對口述歷史文獻的演繹性利用必須取得版權人的授權,而口述歷史文獻的版權人可能包括口述者、訪談者、圖書館等主體,從而出現相互的制約性。通常而言,只有各權利主體達成共識,才能對口述文獻的整體版權向第三人許可使用。否則,就只能行使自己享有的版權。由于訪談者與圖書館之間具有隸屬關系,雙方較易達成協議,這樣口述者與圖書館之間的利益平衡問題就成為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演繹創作使口述歷史文獻附加了新的價值,那么第三人與口述者、訪談者、圖書館之間也存在著權利平衡的問題。
3 訪談式口述歷史文獻的版權行使
3.1 厘清相關的版權法律關系
從版權角度認識,口述歷史文獻工作與其他類型的文獻工作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律關系比較復雜,厘清法律關系是科學行使版權,保護包括圖書館在內的相關權利主體的利益,采取正確的版權保護措施的前提,也是防范和化解法律風險的基礎性工作。特別是在產生了衍生作品,版權歸屬發生了變更的情況下,對相關的法律關系予以清晰的界定尤其重要。在正確界定法律關系的基礎上,圖書館應針對具體的口述歷史文獻活動開展法律風險評估,制訂完善的版權管理方案。版權管理方案制訂完畢后,應由圖書館內部專門的版權管理人員,或者外聘的法律顧問、律師,或者高等學校的法學專家等進行審鑒,提出修改意見,力求完善。就目前我國開展了口述歷史文獻工作的圖書館的情況來看,大多數沒有把版權問題放在重要位置來對待,特別是沒有進行事先的法律風險評估,不僅為發生權益糾紛留下了隱患,也使圖書館在版權危機中處于被動地位。
3.2 建立版權管理規章制度
提高版權管理的有效性,不可忽視圖書館制度層面的重要作用。圖書館版權管理規章制度的效力主要及于訪談者和圖書館,而不及于口述者,目的是通過制度的形式使訪談者與圖書館之間的職務創作法律關系,或者法人創作法律關系得以明確,從而對訪談者、圖書館的行為都形成必要的約束。規章制度不僅可以為訪談者、圖書館提供行為規范,避免圖書館內部版權法律關系的混亂,而且對解決許多版權難題非常有利。比如,在口述歷史文獻工作中,有時職務創作與法人創作是難以區分的,如果圖書館直接在制度中規定創作行為都屬于法人創作性質,那么訪談者、圖書館之間的法律關系就非常明了。規章制度建設可以針對重點的、易發生的版權問題進行,也可以按照工作流程建立全面的規章制度,還可以針對具體的任務建立規章制度。這些制度包括《圖書館職務創作和法人創作性質的認定規則》《圖書館法人作品、職務作品版權管理規定》等。
3.3 制定規范性業務操作程序
1968年,美國口述歷史學會出臺了《口述歷史工作原則與標準》,這是世界上第一部較為完整的口述歷史文獻業務操作規范,其中規定了采訪者、受訪者和資助機構的權利、義務以及應當遵循的相關依據。1979年,美國口述歷史學會又制定了《口述歷史文獻評價準則》,此后經過1989年和2000年兩次修訂,現在的版本是2009年9月制定的,即《口述歷史的通用原則和最優實踐》,其中歸納了8條重要原則,包括版權管理原則[4]。2001年,我國四川當代史編委會制定了口述歷史采訪的工作程序與標準,2003年中國口述史研究會在其章程中提出了口述歷史的規范操作標準,2004年首屆中華口述史高級論壇暨學科建設會議討論了口述史的概念、規范、標準、原則等問題。為了保護版權,口述歷史文獻業務操作規范應包括以下主要內容:其一,告知原則,即將口述歷史文獻工作的目的、內容以及版權利用等問題事先告知口述者。其二,原真原則,除明顯的人名、地名、時間錯誤外,圖書館不對口述內容進行改動。其三,補償原則,即口述歷史文獻的開發利用收益應向口述者分配。其四,簽字原則,口述者、訪談者、圖書館應在認同的與口述歷史文獻工作有關的紙面材料上簽字。其五,完整保存原則,把相關的錄音、錄像、協議、會議紀要等資料完整保存,還要寫出階段性、總結性的分析報告。
3.4 注重契約的版權管理功能
從理論上講,有關當事人之間通過談判、磋商,達成契約對版權這種私權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由于法律不完善,加之版權關系較為復雜,所以在口述歷史文獻工作中更應注重通過契約來規范各方的權利、義務,明確違約責任。由于事先沒有簽訂契約導致的版權糾紛,在口述歷史文獻工作中并非鮮見。同樣,因為契約條款規范、明晰,使相關糾紛得以順利解決的例子也并不缺乏。比如,在李宗仁與哥倫比亞大學糾紛中,雙方事先約定用“李宗仁口述,唐納德撰稿”的方式署名,這種約定對法院認定哥倫比亞大學擁有涉案口述文獻的版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口述歷史文獻創作契約應包括下列內容:許可使用或轉讓的權利種類;許可使用的權利是專有使用權還是非專有使用權;轉讓或許可使用的地域范圍、期限;版權使用或轉讓費及其支付方式;糾紛處理程序與辦法等。契約應盡可能把一些難以通過法律、制度界定的問題納入其中。比如,《著作權法》第16條第1款只規定了單位在兩年內的優先使用權,卻沒有規定單位不行使該項權利時版權人利益保護問題,對此問題就可以通過約定來解決。
3.5 加強版權管理人才的培養
口述歷史文獻工作的專業性很強,國外早就開展了口述歷史文獻專門人才的培養。比如,1965年起,美國總統圖書館辦公室就專門聘請訓練有素的職業歷史學家從事口述文獻工作,1968年美國匹茲堡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專門開設了“口述歷史與口述傳統課程”[5]。目前,對從業者專業素質和能力的評判標準也普遍寫入了口述歷史文獻程序規范。在對從業者的素質培養中,不可忽視的是對其版權保護意識、觀念、知識、能力與實踐經驗的培養。當然,要求所有從業者具備版權保護素質是不現實的,也沒有必要,圖書館應抓重點對象,有針對性地培養專門人才。對此,可以學習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圖書館、加拿大蘭加拉學院圖書館等的做法,設置“版權圖書館員崗位”(Copyright Librarian),由專門的版權管理人員來處理版權事務。
[1] 王子舟,尹培麗.口述資料采集與收藏的先行者——美國班克羅夫特圖書館[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2(5):1-10.
[2] 鄭松輝.圖書館口述歷史工作著作權保護初探[J].中國圖書館學報,2010(1):104-110.
[3](美)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資料:實務指南[M].第二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15.
[4] 黃迎鳳.美國現代口述史學考察印象[J].北京黨史,2012(5):57-58.
[5] 陳俊華.圖書館開發口述歷史資源[J].圖書情報工作,2006(6):12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