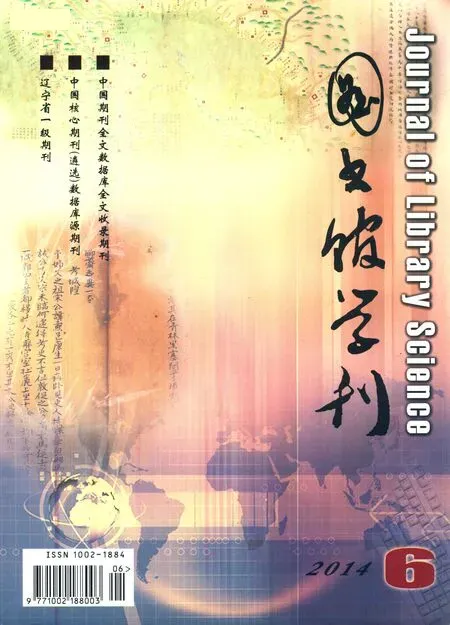辭書編纂中侵犯著作權行為的判斷與防范
彭華杰
(河南省圖書館,河南 鄭州 450052)
辭書編纂中侵犯著作權行為的判斷與防范
彭華杰
(河南省圖書館,河南 鄭州 450052)
相對于其他類型的作品創作,辭書編纂有其特殊性,這給辭書編纂中侵權行為的發現和判斷造成了困難。介紹了界定侵犯辭書版權行為的若干方法,就辭書編纂中防范和遏制侵權行為的措施進行了分析。
辭書 編纂 侵權 版權
辭書向來被視為準據和圭臬。然而,辭書編纂中存在的拼湊嫁接、改頭換面、移花接木等侵權行為卻降低了辭書的權威性與使用價值,敗壞了辭書業聲譽,損害了讀者和辭書版權人的合法權益。對辭書編纂中侵權行為的及時發現和準確識別,是辭書版權保護的關鍵問題之一。基于辭書本身與其編纂過程中利用版權作品的特點,在一些情況下對抄襲等侵權行為的判斷并非易事。雖然經過市場治理與對侵權行為的打擊,侵權之風有所遏制,但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侵權行為并未完全銷聲匿跡,甚至變得更加隱晦。侵犯辭書版權是一種消極的文化現象。所以,有必要以現行版權法律制度為依據,結合辭書版權特點,對辭書編纂中的侵權問題,尤其是判斷侵權的方法和標準進行研究與實踐。
1 辭書編纂中侵權行為認定的受制性
侵權者往往以辭書編纂性質為由,否認辭書具有創造性,進而拒絕承認抄襲。比如,有人認為辭書的主要成分不是著作,而是編纂,絕不能因為辭書中出現相同之處即認定為“抄襲”[1]。辭書的性質指的就是其作品類型——匯編作品,這種作品基于對既有版權資源的二次創作,獨創性可以體現在辭書內容的選擇和編排方式的標新立異。但是,特定領域、特定學科的辭書在內容的選擇上通常都是以“齊全”為收錄目標,這就弱化了其“選擇”方面的獨創性。而為了方便利用,辭書大都是以最為人們熟悉、使用最廣泛的部首法、音序法、筆畫法等編纂,所以其在“編排”方面的獨創性又難以體現。加之為了保障辭書的“工具”特質,編纂規則中一般都有傳承、借鑒、使用已有共識內容的要求,都使得從表面上看辭書的繼承性大于獨創性。辭書的這種特性,也給侵權行為的發現與識別造成了困難。正如有學者所說,辭書的主體是以千百萬計的條目,對每個條目而言,它們是一個知識單元(注音、釋義、舉例等構成),但一般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產權單元。沒有聽說過有這種情況:抄用某辭書的某個條目,便說構成了法律上的侵權行為[2]。
有人認為,辭書編纂是對大同小異的“共識”的表述,也常是生活中本來就有的,編纂者記錄了它而已,因此不屬于創造。即使對它記錄,編入辭書的人,也不能說是他的創造[3]。辭書編纂的確需要使用大量的共識性內容,這是由語言的社會性決定的。辭書編纂中不僅形成了約定俗成的使用共識性內容的規則,而且國家、行業學會甚至以頒布政策的方式將其固定下來,不能做具有“己見”的變通。比如,《漢語大字典》對字形解說和注音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允許有個人的創見,而只能取共識說。如果欲突破成說,自創新義,必須寫出書面報告,由主編批準[4]。編纂辭書要承認共識、尊重共識、表現共識。但是,共識卻不是辭書編纂和詞語釋義的基礎,辭書編纂和詞語釋義的基礎只能是社會實踐。辭書編纂不可能完全建立在抽象的“共識”之上,辭書因其類型性質、收錄規模、讀者對象的不同,對“共識”必定會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在實踐中如何區分“共識”和“己見”卻沒有一致的適用標準。
辭書編纂中對前人辭書的成果和經驗予以繼承和吸收,是形成辭書特征、保持辭書連續性和穩定性的需要[5]。有學者認為,辭書在繼承和創新的關系上,首先應主張繼承。因為,辭書收錄條目數以萬計,不繼承前人成果,只有創新是辦不到的[6]。有人據此特點為抄襲行為狡辯,認為辭書是集大成的積累之作,詞匯是積累,釋義也是積累,把積累下來的東西加工、整理,使之規范化、標準化確定下來,就形成了辭書[7]。法院在相關版權糾紛案件的判決書中也稱:用來釋義的同義詞,在長期使用過程中已趨于固定的關系,不能輕易調換。某些時間詞、稱謂詞、詞義較為簡單的詞,或專業詞的釋義用語的選擇范圍也非常有限,對這部分釋義不應給予版權保護[8]。但是,傳承和抄襲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傳承應該是有增益、有改進、有發展、有鑒別的,應該是一種“突破性借鑒”。有學者認為,可以運用“語言”和“言語”區分的理論對傳承與抄襲進行界定,“語言”具有傳承性,而“言語”則有更多創造性。但是,這種觀點的適用性還缺乏實踐的佐證。
有人認為,辭書編纂中追求表述上的趨同是完全必要的,應該接受這種趨同[3]。之所以有這種觀點,或者是對版權法知識的欠缺,或者是利用辭書中的字形相同、詞性相同、字音相同等特點為侵權辯解。因為,版權法認定的抄襲正是“表述上的相同”。對于同一種事實、道理,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這就是獨創性,是受到版權法保護的智力勞動。基于語言和辭書編纂的特點,不同辭書的部分內容相同、趨同、雷同、巧合難免,但是大范圍的相同就不能用合理性來解釋了。比如,有的釋義、例句長達數十甚至百余字,完全相同,或者對部分進行改頭換面,就只能認為是抄襲。然而,對辭書內容在什么情況下可以相同、什么情況下相同就不合法等問題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司法實踐中并未有共識。
2 辭書編纂中侵權行為的識別方法
辭書編纂盡管有共識性、傳承性、雷同性等特征,但是對詞義的概括、歸納、敘述和表達,對義項的取舍與分合,對例證的安排和選擇都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過程,客觀存在與主觀判斷并非完全一致,帶有明顯的局限性,不能不受個人主觀認識水平、知識結構、學術修養及學術造詣的影響和制約[9]。這樣,就使得一部辭書有了與其他辭書的區別,即獨創性。所以,完全可以通過相應的方法對侵權行為予以發現、識別和打擊。
對辭書編纂中的侵權行為可以采用系統法進行識別。辭書編纂的起始步驟是制定總體方案,包括明確讀者對象、辭書性質、辭書規模;確定編纂方針、編纂思想、編纂特色;確定收詞原則、釋文原則、條目等級;確定配圖原則、附錄內容;確定編排方式、索引內容;確定開本尺寸、裝幀設計;規定力量組織、工作進度等,并以編纂體例的形式予以細化[10]。一部經周密、科學的設計而編成的辭書,其收詞、釋義、書例都體現出全書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看似孤立的一個個條目存在著種種或明或暗的有機聯系[11]。侵權辭書大都是拼湊嫁接、信手拈來之作,不可能有詳細的總體方案,內容也必然是支離破碎、不成系統的。
對辭書編纂中的侵權行為可以采用查源法進行識別。辭書編纂是一個長期的孤心苦詣的過程,編纂者大都留有大量的、原始的材料。比如,英國《牛津英語詞典》最初使用的180萬條例證,是從600多萬張資料卡片中遴選出來的。編纂《漢語大辭典》,頭5年(1975~1979)是成千人專門收集資料,編寫釋文階段還不斷補充收詞,至1984年即已收集近2000種古今圖書中的語言資料卡片700多萬張。正是由于占有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立目才有依據,釋義才有源流,書證才有精心挑選的余地[5]。侵權者不可能提供相關的編纂辭書的原始證明材料。
對辭書編纂中的侵權行為可以采用比對法進行識別。版權法規定,出于非營利性的學習、研究等目的,“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內容是被允許的。法律通常從“量”和“質”兩個方面來界定“合理使用”。比如,王同億的抄襲之作《新現代漢語詞典》的多字條目,有65%以上抄自《現代漢語詞典》及其補編和《古今漢語實用詞典》[12],顯然已經超出了合理使用的界限。即使有的辭書抄襲自他人辭書的部分比例較小,但是如果這部分正好是被抄襲辭書的“實質性部分”,也是一種侵權行為。如果經過比對,一部辭書把別的辭書中錯誤的部分也抄過來,就會弄巧成拙,“自證抄襲”。
對辭書編纂中的侵權行為可以采用答辯法進行識別。由專家組成答辯委員會,以提問的方式就涉嫌抄襲辭書以及辭書編纂中的其他相關知識進行提問。辭書編纂者由于親身經歷了編纂的全過程,因此對辭書編排的動因、總體設計、收詞原則、收詞規模、編纂特色、配圖和體例以及獨創性的體現等都非常熟悉,尤其是會有自己獨特的心得體會,部分成果還會在出版物上發表。于是,在答辯時往往出口成章,重點突出,論據清淅,舉例恰當,說服力強。相反,侵權者由于沒有認真編纂辭書的系統體會,答辯時就會張口結舌,語言干澀,答非所問,露出侵占他人勞動成果的“馬腳”。
對辭書編纂中的侵權行為可以采用時間法進行識別。時光不能倒流,侵權之作總是形成于原作以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被侵權的辭書編纂者能夠舉證其辭書形成、發表于侵權辭書之前,而侵權辭書的編纂者又無相反的證據,則可認定侵權行為成立。但是,界定不同辭書的“完成時間”卻可能成為一個法律技術難題。有學者主張以辭書出版(發表)時間作為判斷侵權與否的時間界限,比如出版社的“收稿日期”,或者合同簽訂日期等。但是,由于我國是《伯爾尼公約》成員國,施行“版權自動保護原則”,作品完成即自動獲得版權保護。從這個角度看,并非首先出版(發表)的辭書就可以排除侵權的嫌疑。所以,“時間法”在特定情況下的適用受到限制,需要結合特定事例具體分析。
3 辭書編纂中侵權行為的防范
解決辭書編纂中的侵權問題,編纂者要提高對辭書事業重要性的認識,增強責任感、榮譽感、使命感。辭書編纂者還要牢固樹立法制意識,尤其是要養成尊重他人勞動、保護知識產權的習慣和覺悟。辭書編纂單位、辭書行業學會應以現行法律法規為依據,結合實踐中的侵權行為及其特點,用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對辭書編纂者開展版權知識教育和版權保護指導。還要注重辭書編纂中版權保護的學術交流,總結推廣先進的、有效的做法。
保護辭書版權,不可忽視辭書編纂單位內部版權制度的約束作用。一方面,辭書本身具有版權關系的復雜性、版權歸屬的多元化特征,版權制度有利于界定辭書編纂中相關主體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另一方面,版權保護制度為辭書編纂者提供了保護版權的具體規則,使編纂者知悉怎么做屬于侵權,怎么做不構成侵權,明晰法律的界限。除了普遍適用的版權制度外,辭書編纂單位還要針對不同的辭書編纂任務,制訂專門性的版權保護規則。
在辭書編纂中應形成保護版權的輿論氛圍,對各種侵權行為應形成社會、媒體、讀者、辭書編纂單位和編纂者合力圍剿的局面。一方面,對侵權行為要及時發現、公開揭露,決不能姑息遷就。另一方面,相關的報紙、期刊、電視、電臺等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應拿出專版或設置專樣,宣傳普及辭書版權知識,介紹侵權糾紛案例,討論重點、難點以及有爭議的版權問題。另外,對辭書的評論要堅持版權保護的正確導向,對存在侵權問題的辭書甚至要當成反面教材來口誅筆伐。
辭書事業的發展在使辭書社會效益得以不斷彰顯的同時,其巨大的經濟效益也被逐步挖掘出來。于是日益增多的出版單位、學術團體、個人加入到辭書編纂的行業,希望能夠從中“分一杯羹”,其中不乏不僅不具備辭書編纂知識,更不具備版權知識,沒有版權保護意識的“淘金者”。于是,編纂出來的許多所謂辭書存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抄襲侵權等問題就不足為奇了。國家有關部門應健全辭書編纂準入制度,并從版權保護角度對辭書編纂質量進行評價和監督。侵權行為是寄生在辭書事業肌體上的“腫瘤”,必須予以割除,行政、司法部門應對侵權者予以法律制裁。
辭書編纂中的侵權問題由來已久,之所以未能得到較徹底的解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法律法規的不健全,對許多存在爭議的問題沒有法律規定,這也成為侵權者為其侵權行為辯護的借口。所以,應針對辭書編纂和版權保護特點,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提高規范的可操作性,避免歧義,同時降低司法實踐中的不確定性。
[1]晁繼周.評辭書編纂中的“抄襲有理”論[J].辭書研究,1996(1):33-39.
[2]曹先攫.辭書的特點與辭書的抄襲[J].辭書研究,1993(1):6-7.
[3]高興.令人遺憾的“思考”[J].辭書研究,1995(6):93-100.
[4]張林川,郭康松.論辭書抄襲[J].辭書研究,1995(5):45-51.
[5]徐成志.論辭書的借鑒和抄襲[J].辭書研究,1994(4):5-15.
[6]董樹人.談談語文詞典的釋義問題[J].語文建設,1999(1):33-35.
[7]張宗培.辭書訴訟何時了[J].中國質量萬里行,1994(3):21-23.
[8]李志江.辭書著作權問題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J].中國語文,1998(1):76-79.
[9]秦珂.辭書編纂問題三辨[J].現代情報,2005(3):152-154.
[10]王岳.談辭書編輯的幾項重要職能[J].出版發行研究,2005(10):39-42.
[11]徐祖友.如何認定辭書的借鑒和抄襲[J].辭書研究,1998(2):31-36.
[12]徐慶凱.抄襲無可開脫[J].辭書研究,1994(1):22-32.
彭華杰男,1961年生。本科學歷,館員。研究方向:知識產權。
G256
2014-04-10;責編:徐向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