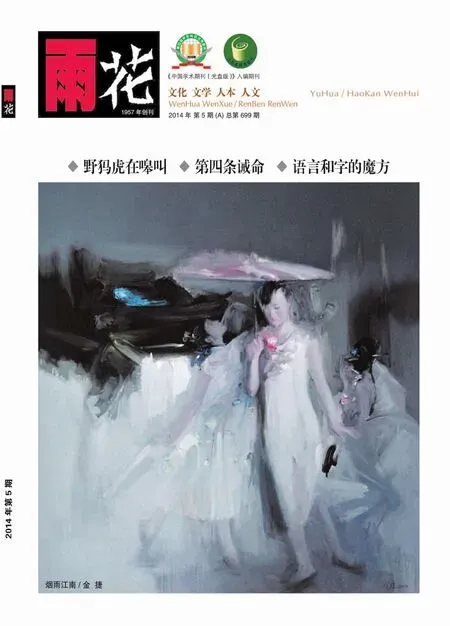隋唐演義
◎劉東衢
隋唐演義
◎劉東衢
原來那臺收音機早壞了。尋找幾天,我們才在一家電子商店里買到那種老式的收音機。大概姥爺是想把從前在鄉下的生活移植到城里。在鄉下,他總是一邊嚼蠶豆喝酒,一邊聽收音機里的程咬金、秦叔寶、裴元慶的傳奇故事,聽他們絕路逢生,聽他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河水流到下游忽然變得柔順、安靜了。兩岸盡是干涸季節才見到的白亮亮的圓石,細沙里裸露出一塊塊淺褐色的云母,宛若孩童的眼神。泄洪閘以下僅剩幾條清亮的小溪,天際處泛著白茫茫的光。陽光曬得石縫脫水,優雅的白鷺孤獨地呆在樹影下,一蹲就是半天。它們大多單獨覓食,除非感覺到了什么,一般而言它們是閑適的,整理羽毛,不必擔心生計。
姥爺退休后,在岸邊一蹲就是一天。水旺的季節,他踩著濕漉漉的月光,肩擔二十只肥嘟嘟的兜網,一臺梅花牌收音機,六節白象電池的槍狀手電筒,一包“麗華”,一盒泊頭產的火柴。收音機里播放評書《隋唐演義》。我那時候上初一,整整一個暑假,我晚上都陪著姥爺在水邊度過,一邊聽《隋唐演義》,一邊計算起網的時間。兜網呈深褐色,是用養蠶的紗網和直徑六毫米的圓鋼制成,上尖下方,中間懸掛豆餅袋子作誘餌。每次起網大都能收獲二兩活蹦亂跳的青蝦。從八點到十點吧,大約能兜到沉甸甸的半桶蝦,有八、九斤呢。姥爺把它們放在竹篩里曬干,拿到集市上賣,我不愿意頂著烈日陪他,一不留神我就逃之夭夭。趕集回來,他責怪道:“這個孬外孫,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我看你長大吃什么。”
很久以來姥爺都珍藏著一只黃梨罐頭瓶,瓶內有幾十顆黃澄澄的子彈。我記得他當年說過,程咬金的斧頭再厲害,也比不過一粒子彈。我和表弟都知道罐頭瓶藏在一只陳年紅木箱里,箱子用紅布包裹。我們扒著窗縫親眼看到姥爺把瓶子放進木箱——也許只是做做樣子——直到他去世,誰都沒見過那個瓶子。我猜想姥爺把它藏在另一個隱秘的地方,他一進城房子就被大舅賣了,后來,原地建成一片新樓,栽下許多冬青樹和梧桐,梧桐樹長得很快,估計現在已經有碗口粗了。房后的水塘也被填平、壓實,開辟成鄉村花園,與園子相鄰的沙土路外邊仍然是從前的莊稼地,不過為了擴大投資規模,一部分玉米地被開發成商業街,雨天街面泥濘不堪,經常有拉磚的驢車陷在里面,很遠都聽到黑驢被鞭打發出的近乎斷氣的嘶叫。商鋪里堆滿鋤頭、木叉、化肥和大肚子雜糧麻袋,有些農戶還在里邊喂雞養鴨,很熱鬧。
不過,這種另類的田園風光姥爺再也看不到了,假如他活著,他會罵罵咧咧,擎著根竹桿,把雞鴨狗貓通通趕到河里。據說,他在鎮武裝部工作時,以臭脾氣出名。他發完脾氣便掉頭回家,連續幾天喝悶酒,如果是周末,他就對我和表弟說:“走,跟我出去轉一轉。”我知道姥爺要去十幾里外的黃草關水庫兜魚,開始幫他準備干燥的豆餅。表弟對兜魚這類枯燥乏味的事絲毫不感興趣,磨磨蹭蹭的,小手背在身后,像領導似地觀看我們綁這個纏那個,系這個扎那個,當準備工作完成,姥爺準備上路時,他問:“有肉吃嗎?”姥爺氣得一聲吼:“有你娘的屎吃!”抬腿朝他的腚踢去,不過表弟十分敏捷,嗞溜就鉆了,再也不見蹤影。
姥爺喜歡走一條偏冷的黃泥路。當時,鄉村公路都是沙土路,汽車駛過塵土飛揚,下鄉等于去一趟揚灰場。黃泥路由沙礓和碎石構成,土少,不沉雨,姥爺說還是學大寨時期修的,我問什么是學大寨,姥爺說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知道,我媽說是吃飯不要錢。姥爺說錯了,那是人民食堂。現在的“人民公社”是一家餐飲連鎖機構,別說免費,連折都不打。我那時想象不出人民公社的模樣,只是覺得這個地方好,起碼有紅燒肉吃。路邊是一個個樣子“革命”的小瓦房,紅磚紅瓦,墻上刷著紅漆標語。丘陵地帶栽種最多的是馬尾松,稀稀拉拉,很遠才看到一棵,像永遠觸不到的戀人。我坐在“大金鹿”后面,腿擔在捆綁成傘狀的兜網上,聽姥爺說,這個地方,叫不動村,逮過一個殺人犯,這兒,叫超產村,他押人待過三天,那兒,有人偷過一頭驢,更遠的那個村子叫石坡村,有個亂崗子,槍斃過十五個土匪。他嗓音洪亮,像擴音喇叭一樣朝四面的田野里送去,溪邊洗衣服的女人都抬起腰看我們,我覺得好狼狽,而姥爺好像回到了他充滿正義、榮譽和激情的青春年代,他記得在這里經歷的每戶人家、每個石磨,每一堵翻過的土墻和每一扇打開的房柵。以前,他身上佩槍,跟同道一塊經過這兒,可現在,他扛著一捆魚網,到這里兜魚。心情的落差常常令他感慨嘆息,搖頭不已。
黃草關水庫面積不大,因在丘陵內部,水質天然,上百年里從未干涸,傳說有許多未曾見過的大魚。看水庫的老頭是姥爺以前一個下屬。烈士陵園在水庫的另一邊,蒼松掩映,莊嚴靜謐。我和姥爺比賽打水漂,中午他要喝三兩,不容我離他半步。這里的水很深,岸陡峭滑,很危險。他把兜到的魚分一半給老友,收拾停當,痛痛快快地上路。經過當年的人民公社,我看到夕陽正把地平線燒成紅彤彤的一面旗幟,連小溪里的水也泛著清冷的紅光,抬頭是無限的暗藍色,高遠而寧靜,我常常抬頭數著云朵,一朵又一朵,我不知道姥爺那時候是不是也這么數過。
脾氣耿直的姥爺幾乎一直被子女認為是冷漠無情的。他的三個兒子都是自謀出路,終日為生計奔波。長女和二女兒隨軍,小女兒當時上初三——那時候我上小學三年級,天天跟她鬧別扭。每次都由姥爺充當調解人:“小丫,你怎么跟小孩子一般見識?你讓讓他不行嗎?”小姨很委屈:“我讓他,他怎么不讓我?我就不讓他。”小姨初中畢業后做過幾年小工,每天吃飯眼淚汪汪,抽泣著,好似受到莫大的屈辱。她向姥爺訴苦:“我長得如花似玉,你為什么叫我干小工?成天和沙灰拌水泥,什么時候是個頭?”也就從這個時候,姥爺開始認真考慮她的工作問題,向領導妥協,退休后讓小女兒接班。三個兒子都有意見。姥爺解釋說:“你們都結婚了,小丫沒結婚。”后來,他們都認定父親并不冷漠,是偏心。姥爺呢,既然妥協了,他就應當遵從這種妥協,否則他連自尊都沒有了。
小姨上班后,聽父親說想兜魚,就托人打制了二十只兜網。兜網打好了,整整齊齊碼在小院子里,姥爺每天瞅幾眼,但并不打開用,他每天都在等待以前的同事和屬下來家里看望他,陪他喝幾盅。在等待來人的空閑里,他一邊聽收音機里的評書,一邊伺弄小小的一塊田地。姥爺的瓦房以前是小學四年級的兩間教室,麻泥地面,楊木三角梁,以扎成綁的蘆葦做頂穹,東西墻各泥一塊黑板,姥爺和姥姥打掃清角落里的蜘蛛網,填實了老鼠洞,可黑板上的粉筆字絲毫未動,過了許多年,我們聚在這里過節,那些字跡仍在。八仙桌以前盛放鍋盆碗筷,漸漸地,擺滿了各種高低不一的白色藥瓶子,屋里久久彌漫著熬制的中草藥味。衣柜旁邊有個小書柜,姥爺眼睛不好,好久不看書了,書頁發黃,受潮脫落,后來就不知所蹤了。電視也看得少,有客人來才打開一會,客人越來越稀少,機殼上覆蓋起一層塵土。酷暑時,瓦房內依然清涼,因為在鄉下生活慣了,姥爺住不慣城里的樓房,沒有土,不接地,又熱,又堵得慌,他又舍不得用空調,家人一打開,他就偷偷關上,他最奢侈的享受是在醫院的臨終病房,中央空調二十四小時開著,他已經沒有力氣了,手臂不能動,對空調的冷風只能聽之任之。后來,他就感覺不到冷風了。
姥爺的那塊田地我至今記得。姥爺的門外是紅石和青磚壘砌的一間院子。東西兩側各辟一塊地,種辣椒、豆角、西紅柿和茄子,每隔幾天姥爺去鎮上的集市,買一斤鮮豬肉,然后去超市買鹽和油。姥姥患關節痛,不能出門,姥爺一出門她就不知道做什么了,直到姥爺提著袋子緩步從集上回來,她才有了主意,繼續做家務。有時姥爺在街上遇到老熟人,免不了被邀請到人家家里吃頓飯,姥爺假意推辭,實際上已經跟著熟人一起走了。回來得晚,姥姥很生氣,姥爺因朋友的酒菜興奮著,陪陪笑,哄一哄,姥姥細問過后才安下心,不再說什么。有一年姥爺栽下一棵櫻桃樹,一棵銀杏樹。三年后,櫻桃熟了,他就讓孫女們來吃櫻桃。櫻桃滋味酸澀,并不適合孩子的味口,她們更喜歡吃薯條果脯。姥爺是離休干部,退休金一上調,姥爺便讓姥姥把兒女們喊來吃頓飯,讓他們也高興高興。那棵銀杏樹六年后才結出稀拉拉幾簇果子,后來結的果一年比一年多,姥爺把它們摘了,晾干,去皮除芽,放在米粥里煮著吃。姥爺去世那年,聽說銀杏樹結了滿滿一樹的白果,深秋時,它仍然翠綠盎然,霜凍那天忽然泛出金黃,晚飯時分,剛起炊煙,幾秒鐘內所有的葉子齊刷刷落到地面上,把兩塊壟地填成一塊金黃色的地毯。
那一年,雨水很少,冬天如約而至。河床里盡是裸露的白石,拖船遺棄在干涸的岔道里。一座花崗巖水壩連接兩岸,保證重型卡車的通過。對面是起伏的茶色丘陵,存水處有許多楊柳掩映的小村莊,取勢自然,歲月的剝蝕令它們顯得困頓疲乏,打不起精神。明亮處,高高的蒿草、覓食的家禽、古跡似的石墻和彎曲發亮的柏油路構成了蘇北的鄉村之美。
老人打發時間的方式是曬太陽,瞇著眼,在溫暖的陽光里昏昏欲睡。不過這種陽光飽滿的日子因冷空氣的南下告一段落,陰云的天氣里,山野和村莊都被蕭殺的霧氣籠罩,這里的寒冷不像北方那樣直接、干脆,它軟綿綿的,好像一直被某個念頭折磨得找不到出路,拿不出辦法。于是,冬季就變得固執,不那么順從了,同時也讓人感覺到可惡,心情糟糕起來。
姥爺在冬季以玩紙牌打發時間。這是一種流行于鄉間的長條形紙牌,黑底紫紋,牌面沒有數字,印有奇怪的彩符,四個人玩,輸贏十多塊錢,是姥爺冬季里溫暖的寄托。隨著年齡增大,他的行動遲緩不便,需要人照料了,姥爺就搬到了小姨家。搬走意味著告別自己生活了近一生的農村,到一個幾乎完全陌生的地方。姥爺的年齡已經不適合從生活中學習什么了,他整天待在家里,靠睡覺、吃飯和看電視度過每一天。他想找人打紙牌,可沒有人會玩那種紙牌,他在城里也沒有朋友。忽然有一天,姥爺對我們說,買臺收音機吧,他想聽評書《隋唐演義》,想聽程咬金的瓦崗軍。
原來那臺收音機早壞了。尋找幾天,我們才在一家電子商店里買到那種老式的收音機。大概姥爺是想把從前在鄉下的生活移植到城里。在鄉下,他總是一邊嚼蠶豆喝酒,一邊聽收音機里的程咬金、秦叔寶、裴元慶的傳奇故事,聽他們絕路逢生,聽他們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但是我們搜索電臺,得到的都是廣告和娛樂節目,有個評書,但不是《隋唐演義》。我們只好買了支帶喇叭的MP5,從網上下載到存儲卡里,想怎么聽就怎么聽。姥爺捧著MP5,感覺這個東東很古怪,以前的收音機有個把手,他拎著四處走,很方便,現在放在沙發上,他聽一會就睡著了。它此后就像一首催眠曲。
最后的兩年里姥爺十分關心自己的退休金。那些數字是他惟一記得牢固的。他擔心自己先走,剩下老伴自己,到時候沒錢看病怎么辦。姥姥一輩子沒工作過,早年哺育六個孩子,他們成家立業,姥姥就為他們照料孩子,直到自己體力不支。俗話說“養兒防老”,事實上他們最后的那段歲月三個兒子基本不在身邊,都是由女兒照顧的。直到住院,兒子們才輪流守在身邊。他們依然為某些久遠的往事爭吵,細到五塊錢的出禮,大到一頭豬,他們都記得很牢,好像是烙在腦子里。
姥爺消瘦,體重減輕,每次都由人抱著去醫院的衛生間。他像個孩子,溫順,無力,柔軟。他不再顯出什么力氣了,只剩下若有若無的呼吸,最后是僵硬。停止了。喪事由活著的人安排,半年后姥姥才得知消息,一天到晚地哭,六神無主,滴水不進。后來稍緩過來,無助地望著我們說:“你姥爺走了,我怎么辦?他走了,我怎么辦啊。”我們安慰她。她似乎沒有聽到我們在說什么,癡呆呆地望著某個地方,好像姥爺會突然從那個房間里走出來,走到院子里,取下墻上的兜網,戴上草帽,把扎綁的兜網套在竹竿上,搭在肩頭,手提著收音機,大踏步地走出門。姥姥仍叮囑著:“水滑,別掉水了。”姥爺大聲回答:“我死不了。”
喪事結束后,小姨把姥爺的衣物送到鄉下。被子、臉盆、鞋襪棉襖、洗漱用品和零零碎碎的小東西都被幾家人分了。一直陪伴姥爺的MP5里拷貝進流行舞曲,放在二舅賣飼料的三輪車上,走街串巷,作吆喝用。沒有《隋唐演義》了,關公戰不戰秦瓊,也與生活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