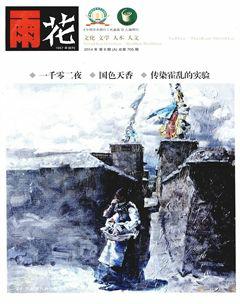密碼
◎漆寧勤
密碼
◎漆寧勤

更多的時候,我們寧愿相信:姓氏的來源關系著基因密碼的承襲。或許,每個生命的朦朧意識里,都有著一種來自遙遠的先祖的記憶和情感,這種記憶與情感扎根在血脈的深處,無比隱秘。
1
晚飯開始之前,本家書華先拋了一堆照片在桌子上,于是大家拿起來輪換著看,一張張湊到眼前仔細辨認那些刻在石梁石柱上的對聯以及以多種不同字體呈現的“漆”字。石碑上的文字告訴我們,它們已經存在350多年了。
但是,現在這些有著350多年歷史的石頭和文字即將消失。有外姓人家要將它們推倒,在它們站立了350多年的土地上新建一座建筑。“外姓人”,書華特意強調了這個詞語。
如果不是因為這件事,自詡關注傳統文化的我,可能還不知道這個小城中有這么一座保存了這么久且與我有關的宗祠。可是我剛剛知道有這么一座祠堂的存在,它就要被徹底拆除了,再不復存在。據說,書華和另外一些族人們阻撓了幾次,終究未能成功。一座供奉著本地漆姓先祖的建筑,就這么在一萬多子孫的眼前被挖掘機推倒,然后重新奠基,成為與被埋入泥土里那些石柱上字體各異的“漆”字再無半點關聯的另一座全新建筑。
如果時間倒退100年,這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一座宗祠,有時候就是一個姓氏在某個地域內的顏面和尊嚴,也是一個家族人心團結所在。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更多的,是利益所在。幾乎沒有誰再理會祖輩相傳的持家規矩,也很少有人再嚴格按照譜牒記載的輩分口訣為新生兒孫取名排輩。
當然,偶爾也會有一些諸如修譜修祖墳、
祭祖建祠堂之類特別的事件突然觸動一下某個族群敏感的群體意識。倡頭制造這樣的事件的人,歷來不缺,即使在完全商業化世俗化利益個體化了的今天也一樣。究其根源,只因為這一大群人有著一組共同的基因密碼和共同的祖先——或者換句話說,有著一個共同的姓氏。
是的,姓氏。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這一直是個人作為社會成員的一個最重要的識別符號。
趙錢孫李,這一個個平常的文字,卻有著綿延千年的優雅和親情。
千年,這其中要發生多少事情啊。一個人擁有了自己的姓氏,然后生下兒子、孫子、曾孫,開枝散葉,一生二(或遠遠不止二,在一代人的繁衍中直接就有了八個十個兄弟)、二生四,經過了災荒、戰亂、病痛、家庭變故,等等。終于,從這一個字詞出發,一路萌生出了一萬或兩萬棵有著同樣內在基因和外在姓氏的樹苗。姓氏,作為每個后代名字的前綴,這是一種標識,如同給屬于自己的物品打上一個烙印。
更多的時候,我們寧愿相信:姓氏的來源關系著基因密碼的承襲。或許,每個生命的朦朧意識里,都有著一種來自遙遠的先祖的記憶和情感,這種記憶與情感扎根在血脈的深處,無比隱秘。
據說,5000多年前,東方部族的首領伏羲就開始正姓氏、別婚姻,形成了最早的姓氏制度和婚姻制度。又據說,秦漢以前,姓和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姓起源于母系社會,所以姓字由女字和生字組合而成,形象說明了早期的姓是跟母親有關的,用來表示母親的血統;氏則起源于父系社會,作為同姓衍生的分支,本來是同姓各部落之間的區分,后來專指部落的首領。國家產生后,不少封地、爵位和官職也成了氏的來源。你為國家養馬,好吧,就叫馬氏;你居住在水城,好吧,可以叫水氏。等等。而封地和官職是可能世襲的,于是氏也就世襲了下來。馬氏水氏的子子孫孫的名字之前就都是馬氏水氏了。而當封地和官職失去以后,氏依舊在,并慢慢演變成家庭的標志。終于有一天,姓氏合二為一,這一個字兩個字所指稱的姓氏,隨著人丁繁衍,世代沿襲。由于姓氏來源的多樣化,到了后來,后代們甚至已經完全弄不明白自己頂著的這一個字兩個字的真正來源和真正意義。一些有心的人,在往上溯源查找自己上代上上代數十代之后,竟然找不到資料,也缺少了明確的源頭指向。姓氏的脈絡,竟然突然就模糊了。人們只知道自己是姓張王劉彭或牛羊朱茍。也好,知道這個就夠了。
2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論語·公冶長》
對于祖輩們在宗祠石梁石墩上刻下的“漆”字,我有著天生的足夠耐心和好奇心。
漆,這個姓氏似乎有些生僻,翻遍歷代的百家姓,即使在第一百位,也找不到它的席位。但是,再往前幾千年的時候,孔子門徒里“七十二賢人”之中,竟然就有三人姓漆雕,占了二十四分之一。正好是一年二十四節令中的一席之地。更有人認為,這三人其中之一的漆雕開,可以躋身孔門的八位高足大儒之一。據說,他潛心鉆研學問,認為有的人性善、有的人性惡,提出了天理和人欲的概念,形成獨特的人性論,在孔門中以德行著稱,很得孔子欣賞。
古籍上記載,這是一個清醒而謙遜的人,孔子曾讓他去做官,而他卻回答“我對做好官這件事還沒有信心”,這種態度讓孔子很高興。
在學術上,性善性惡論讓漆雕開的學說成為了“世之顯學”。《韓非子·顯學》中就說: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韓非
子甚至還認為“自孔子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盂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
文字的記載是我們最大的依憑,但也可能因其語焉不詳而成為我們最大的困惑。
也許正因為“漆”的生僻,到現在我們已經無法詳知它的來源了。有人說是因伯夷叔齊的孫子(神農的四十一代孫)隱居漆水河之東,之后又遷徙到商丘漆園,后人被稱為“漆”姓;也有人說是周文王時對受封于漆沮二水之間的侯王賜氏為漆。又有人說,漆姓確切地說應該是漆雕氏,因周代吳國的開國國君太伯的后代被稱為漆雕氏而得姓氏,直到漢文帝時才由皇帝批準簡化為漆姓。甚至,還有人說,漆姓來源于春秋時期長狄氏的一支鄋瞞族,他們改長狄氏為漆氏。各種似是而非的說法還有很多。
既然孔子的七十二賢徒中就有三個,可以想見,當時同時擁有漆雕氏這個標識的人數當然不止這三人,但漆雕開的兄弟或者父輩似乎都不可考證了。甚至,連“漆雕”兩字在當時到底僅僅是姓氏還是包括了名字的一部分,都有不少爭論。甚至有的文獻說最早當然都是“漆”姓,因孔子七十二賢中有三賢名叫漆雕某某,后人才為紀念而改漆雕為姓氏,直到漢代才復歸單姓“漆”。
爭議歸爭議,按照族譜的記載,全國各地的漆氏子孫還是將自己的祖宗都溯源到了漆雕開等孔子的三個賢徒。這個,是可以理解的。我必須說,我見過最多文過飾非掩惡揚善的書籍當然會是族譜。幾乎每一本族譜的溯源都可以推演到古代的某位賢人、帝王、名臣甚至是上古的名人。沒有誰會去較真,去考證它的真實性。如李姓,溯源的結果必定是唐代皇帝的某支后裔;劉姓,追祖溯源一定可以到達劉邦一代;朱姓,祖宗的祖宗又肯定是可以接續到明代的皇族了。等等。
我似乎從來沒見過一本族譜里面記載著家族里面歷史上不怎么體面或不怎么規矩的人和事。我似乎見到的每一本族譜里面姓氏溯源的終點都在古代某個有名的人物。至于那個人物的姓氏最初又是如何得來的,似乎又都語焉不詳不作重點了。
據說很多一出生就千里遷徙的動物,對出生之地有著天生的記憶,對血脈基因有著天然的敏感。對于姓氏基因的承襲,我寧愿相信,即使幾千年過去了,總還是有一種特定的基因隱藏在我們的身體之內,等待有一天被我們自己激發:哦,原來,我們,都來自遠古某一基因的延續。這也許是現今時代談論姓氏的最主要動因吧。
3
古人的安居,占有土地可能是重要的因素。在大量土地還是荒地的時候,一個人、一家人、一群人來到一個全新的地方,可能憑著勞苦將一片荒地開墾,然后插碑為界,就成了這一家人或者一族人安身立命的領地了。
三百多年前,我的部分族人在本市范圍內又進行了一次短距離的遷徙,從最初在萍鄉聚居的地方來到另一個山村里的龍背嶺下,開始建設屬于自己的房屋。
再次出現祠堂的時候,供奉的主角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從宜豐挑著雜貨擔來到萍鄉的年輕人和他的兒子們了,而是短途遷徙來到龍背嶺定居的祖先甚至是他的兒子孫子們。人的視角和情感總是受限于空間、時間和個體的體驗。
祠堂當然得選一個足夠好的風水寶地,它關系著一族人或者一族人之中某一支系的興衰,人丁、功名、財富、健康,似乎都與這個祠堂相關。
建祠當然得要足夠的財力,一個祠堂的建立往往意味著這一姓氏或者姓氏中的某一支系有了足夠多的人口、財力以及一定的社會資源。很奇怪,僅僅是我居住的這個小小的村莊,三百多年間,就先后有過五六個地域
分支性的漆姓宗族總祠或分祠。需要說明的是,總祠與分祠實際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例如,對于乙地來說,以從甲地來到乙地落腳的某一姓氏第一人為主角的祠堂當然是總祠,但對于甲地來說,這一祠堂卻只能說是分祠。同樣的道理自然也適用于甲地的所謂總祠。
說建祠需要足夠的財力并不僅僅是說建設所需耗費的銀錢。祠堂的建立往往意味著以這一祠堂管轄范圍內同姓子弟為對象的私塾的開設,意味著對同姓族人的扶危濟困,甚至意味著族人權益的維護和與異姓的爭利斗狠。而一個家族的共有財產往往最后體現為宗祠的財產形式。所以,幾乎每一個祠堂都有著自己的產業。這種產業一般是以同族共有的形式存在的田地,然后以每年的田租形成祠堂的財力。有實力的祠堂,就可以由祠堂(實際上是一定區域和宗親關系內的同姓全體族人)出錢,供養本姓子弟讀書或資助進一步求學與獎勵學業有成者。這樣的子弟今后無論走到哪里,還是要念叨著自己是從某某處某某祠堂里出來的。而祠堂的榮光,也往往以出了多少個有本事有地位的文人武人官人商人為衡量標準。昔日,建祠和修譜時提及的理由中經常會有這樣的字句:為免異日或遷徙他鄉,視本族若路人、等骨肉為秦越之亂象……這樣推理,祠堂和族譜就是認親的密碼了。
多年以后,有一個雨天,在某條大街上,兩個素未謀面的人因為不小心踩到了腳而暴怒、謾罵,繼而大打出手。拳打腳踢的間隙,兩個人不經意中都聽到了對方口中蹦出的一些詞語片段,以姓氏為紐帶的基因密碼發生了反應和碰撞,突然就停住了手:你也是某地某村某姓的人?你跟我竟然是同一個祠堂里出來的人?我父親年輕時就離開那個村莊出來謀生了,現在住在某某處,哎呀哎呀,自家人都不認識了,真是不好意思……
這些話語你一句我一句,已經分不清哪一句是誰說的了。總之到了后來,兩個人就停住了手,敘一下輩分,正好是兄弟。也不打架了,相約下回到村里,到祠堂里走走看看,以慰鄉情。轉過身,兩個人都在心里嘀咕:幸好剛才沒有辱罵他的先人,否則不是自己罵自己嗎?
這些從鄉村出走多年,但依舊記掛著自己的祖輩,記掛著與祖輩有關的一切地名的人們,無疑是讓人感動的。而驅使他們這么做的,卻很可能僅僅是因為同一個姓氏,同一組世代相傳的文化密碼。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全部的密碼都只能靠石質的祠堂和紙質的族譜來記載;這全部的記憶,都只能靠石質的祠堂和紙質的族譜來加固。如你所知,祠堂和族譜,這是后人對先人的尊崇,這是兒子對父親的感恩。今后,關于祖輩如何來到這個區域勞作生活,生下若干個兒子,并繁衍至今,又或者是創造了如何榮光的成就,這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宗祠和族譜來紀念和傳承了。一旦連這兩者都徹底喪失,如同我們那個誕生于350年前的建筑物那樣被徹底鏟平,由內在暗語組成的姓氏密碼架構,將轟然坍塌。
這個世界再無所憑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