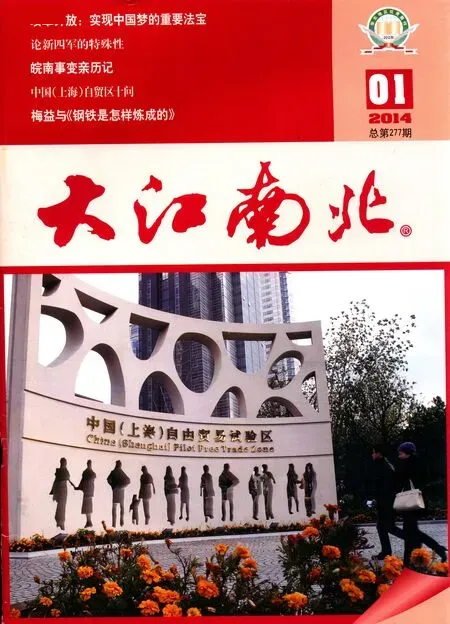坐在方凳上的奶 奶
上海市晉元高級中學高二(1)班 羅欣怡
坐在方凳上的奶 奶
上海市晉元高級中學高二(1)班 羅欣怡

“奶奶沒了。”媽媽的聲音在電話里聽起來沒有真實感。
我掛上電話,到臺盆刷牙。單調的聲音里,我看到那張和藹滄桑的面龐竟那樣清晰地漫上來,像海潮一般沒過了我的眼前。我抬起頭的時候,鏡子里的自己早就淚眼模糊……
我是奶奶最小的孫女。但是很多年來,我甚至不會想起她。與老人的“隔代親”,我只和帶大我的外公外婆才有,與奶奶,除卻血緣的維系,就只剩下逢年過節的探望,也幾乎是走形式的。在一片“叔嬸姑伯”的稱來喚去中,奶奶永遠都是安靜地坐在她常坐的那個方凳上,微笑著看這些名義上來探視她實則只會自顧自聊天的兒女們,這一由她孕育的大家族。
入夜,我輾轉難眠。記憶的碎片總是毫無征兆地浮上來,蠻不講理地在眼前重演。
大多數時候,我和那些“孝順”的兒女一樣,心安理得地將奶奶晾在一邊。坐在方凳上的奶奶雙手交握在膝上,我們都忽略了她那渴望交流的眼神。直到爸爸告訴我和媽媽,奶奶得了阿爾茨海默病(俗稱老年癡呆癥)。
奶奶被告知要搬去養老院的時候,她幾乎是憤懣而無力地吼出了內心的吶喊:“我有八個小孩,憑什么要去養老院?!”
夜半,回憶的寒意滲到了身體的每個罅隙,我裹緊了被子,在黑暗里呼吸。
初一放寒假時,我到奶奶家。進門,奶奶坐在她常坐的那個方凳上,我親切地叫了聲“奶奶”。她慈祥而又滿是皺褶的臉上露出了難得一見的笑容。
“坐,妹妹坐呀。”她忙碌著,硬拽我到里間,搬來凳子,塞東西給我吃。我在她面前坐下,她立即拉著我的手說起話來,節奏不快但鄉音未改,不甚理解的我有一句沒一句地聽著。奶奶13歲就做了童養媳,大字不識一個,可這善良的老人對這樣的生活竟無一句怨言。我們交談了三個小時。
那是我和奶奶唯一的一次長談。也是我對老人的過去了解最多的一次。
夜霧來了。我再無意入眠,索性任回憶恣意馳騁腦海。
奶奶病危的這個月,我到她的病床前看她。此時她已經很久沒有進食了,瘦得不成樣子,呼吸急促。這是我的奶奶嗎?我的天哪!
奶奶得病后,我愈發看清了爸爸的心力交瘁與對人情冷暖的無能為力。我尚未完成學業,他無法全身心照顧奶奶,只有周末到敬老院陪伴奶奶盡盡孝道。可是我,為奶奶做過什么呢?我根本沒有資格評判其他家人孰是孰非。很多時候我捫心自問,我,是一個有良心的人嗎?答案的不確定讓我戰栗得不敢再細想下去。倘若再給我們無數個“假如”,我們會不會依然讓奶奶孤獨地坐在一邊?很多事情,只有歲月的延續才能讀懂。這不是奶奶一個老人的悲哀,而是中國乃至世界千萬老人痛苦。他們看似享受著天倫之樂,其實內心的寂寥好比荒蕪的花園,無人問津,枯葉滿地。
“奶奶沒了。”中國的漢語博大精深,人們從不對親人的死亡直言不諱。我站在奶奶的靈柩前,深深鞠躬。我仿佛又看見奶奶坐在她常坐的那張方凳上,祖孫倆好像還有很多時間對視著聊聊。
時下,一些漸漸富裕起來的家長,對孩子的物質奢求,總是無條件地給予滿足,就連一些收入不高,甚至下崗、內退的家長,在“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思想支配下,寧肯自己省吃儉用,也要傾其所能地滿足孩子的要求。
如今國家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做父母的給孩子吃好點、穿好點、生活上舒適點,這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任何事情都得有個“度”,常言道:“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那些在“慈父善母”用金錢營造的“愛巢”家庭中生活的“少年闊佬”,由于缺少鍛煉,缺乏磨礪,不懂節儉,飽食終日,不思進取,甚至游手好閑,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古今中外,因寵而嬌、因溺愛而毀滅的例子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