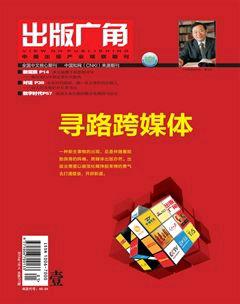漫漫“尋”鹿記
潘飛
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話,要回我們的森林,還有我們自己的獵槍。一想到鄂溫克人沒有獵槍,沒有放馴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夢都在哭!
圣誕節剛過,全世界孩子們的夢里,恐怕還殘留著由八只馴鹿馱著圣誕老人派送禮物的歡樂,還殘留著雪橇車的鈴兒響叮當吧?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民俗或宗教文化中,馴鹿都是與圣潔、吉祥、幸運等寓意捆綁在一起的牲靈。2011年,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某期節目,把“中國最后一個女酋長”,八旬有余的鄂溫克族老奶奶瑪利亞·索和一只充滿靈性的馴鹿請到了演播大廳。那極通人性的鹿兒眨巴眨巴著水汪汪的大眼睛,仿佛天國的使者般,一動不動地站在人群中,兀自端起了貴族式的、優雅的、孤獨的、精靈般的、不容侵犯的“鹿范兒”,頓時就讓主持人李維嘉仿佛受了洗禮般,驟然無語淚奔。記得當期節目播出時,在民謠背景音樂的烘托下,我不僅對這個被外族強大文化異化的民族建立了初步的認識和好感,同時也隱隱地感受到這個老奶奶和她背后的部落、鹿群以及圍繞馴鹿展開的生活,即將和其他消失的文明一樣,瀕臨被吞沒湮滅的邊緣。
這份憂心通過這本《憂傷的馴鹿國》得到了證實。如果說,蒙古族是“馬背上的民族”,那么,鄂溫克人便可以被稱作“使鹿部落”,他們在大興安嶺的密林里按照民族的習慣、信仰、需求一代代地休養生息,馴鹿成了他們的“森林之舟”和精神寄托。然而,2003年,政府以“生態移民”為由,讓他們告別森林,并交出打獵的工具——獵槍,遷移到了官方的新定居點。這對世代習慣靠獵槍自給自足的獵民們來說,不啻于被褫奪了生產工具的奴隸——試問,你如何指望一個被剁去雙腳的芭蕾舞女演員,還能在舞臺上蹁躚如昨?你如何期待一個被奪走鐮刀和鋤頭的農民,還能在秋日的燦燦麥浪里唱著豐收的歌謠?對于沒有經歷“如何成為一個城市居民”等培訓和教育的獵民們來說,他們如何一時之間習慣“被”賜予的新生活呢?通過《憂傷的馴鹿國》,我們只能遺憾地看到:失去獵槍的他們,手無寸鐵,卻不得不陷入了野獸、偷獵者、外人對森林資源涸澤而漁式的掠奪、自居處于“高級文明”的人對他們所認定為“低級”的原始文明的愚笨“改良”之策的重重包圍之中。
不會說漢語的老人瑪利亞·索對當權者的“繳槍之策”發出了鏗鏘之聲:“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話,要回我們的森林,還有我們自己的獵槍。一想到鄂溫克人沒有獵槍,沒有放馴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夢都在哭!”這樣的疾呼代表了一群身份感被模糊,生存權被破壞的異族人的憤怒和不滿。這種困獸猶斗的英勇姿態,我們仿佛也在現世的社會生活中時常觸及——某名人故居的抗拆者、反對開發秦始皇陵的文物專家等屢屢發出這樣的聲音:不動才是最好的保護。
本書的作者顧桃子承父業,扛著攝像機,深入瑪利亞·索老人所在的獵民點,和仍然留守在森林中的鄂溫克人同吃同住,開始了人類學科中的田野調查,用鏡頭記錄下這群正在遭受現代文明蠶食的鄂溫克人的生活原態以及精神世界,于是,便有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紀錄片《敖魯古雅》,以及通過“影像到紙本”的轉換,附生的這本“尋鹿記”。顧桃是一個攝影師,也是個人類學者,他需要藝術呈現,也需要忠實載記,總之,都需要通過肉眼和攝像機來“直接觀察”。本書盡管是微觀世界,瑣碎地包容著他的數篇工作日記,同時,還收錄了對瑪利亞·索、維佳、柳霞、芭拉杰依、王瑛等鄂溫克土著的采訪實錄,就連馴鹿妮亞和獵犬喜力也獲得了代言的機會,使得這本“群像日志”愈發具有了恢弘的史詩氣質,也使得這個《憂傷的馴鹿國》仿佛成了一個人畜平等,與天國打通的理想國。作為社會生態的紀錄者、文化資本的生產者,媒介完全可以作為發揮其特有的社會動員力,形成一種“非暴力式的反抗和對峙”,完成在社會公共領域里的意見抒發和表達,并集結、發酵、放大零碎的觀點,通過意見空間與現實社會的橋接,最終實現輿論影響現實的“反擊”。
重溫本身就是一種與未來反向的尋找,只因“過去”還留著我們未曾發覺,錯漏的各種遺珍。顧桃的“尋鹿記”,不僅是沿著馴鹿的足印,溯找那個即將消逝的森林王國的蹤跡,也是在拉扯住一個只顧往前瘋跑的社會的腳步,建議人們合理并合法地對古老文明/族群加以保護、尊重、合理利用和改造,從而還原一個馴鹿和人共生同榮的美好樂園。這份美好,不應該是虛無縹緲的“天邊”,難道不應是我們日常為之深愛、習慣的“世俗”么?還“槍”于民,難道不就是以“漁”換“魚”,把一個族群賴以生存的技藝、記憶、夢想歸還給他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