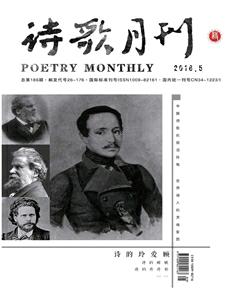群體性突發事件的有限理性分析
季乃禮
摘 要:有關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研究,國內學術界多歸因為非理性行為。而西方學者探討群體性突發事件時逐漸意識到理性與非理性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存在一個中間狀態——有限理性,而且情感與理性也不是矛盾的,情感有時是理性的基礎。在“甕安事件”中,事件的參與者既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成份,群體逐漸把群體性突發事件作為表達訴求的一種最有效的方式,一種滿足其要求的捷徑,即集體性啟發。
關鍵詞:群體性突發事件;有限理性;集體性啟發;甕安事件
中圖分類號:D630.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494(2014)01-0090-05
一、問題的提出
群體性突發事件是近年來中國頻繁發生的一種社會現象,日益引起政府以及媒體的重視。目前學術界對群體性突發事件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解讀:一是從社會治理的角度。有學者認為,群體性事件的頻發與當地的社會治理有關,他們或者歸因于官員的服務觀念淡漠,面對民眾的訴求,不積極做思想工作,工作方式簡單粗暴,片面追求經濟發展,忽略民眾的利益[1];或歸因于改革開放導致的社會轉型,政策不到位,經濟發展程度不高;或歸為群眾的法制觀念不強以及當地的黑惡勢力作怪[2]。從社會治理的角度所歸納、總結的有關群體性突發的原因相對比較全面,但往往忽略了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深入探討。二是社會輿情的角度。輿情是指事件中參與者們已經具有的和圍繞事件情況變化新產生的社會政治態度。在群體事件發生的過程中,群體的政治態度會有所變化,譬如爆發前有情緒的積累,爆發時根據控制方的應對方式不同,有時會加劇,有時則會減弱[3]。
上述研究最大問題是理論研究明顯不足,主要體現為對西方相關的集體行動理論關注不夠。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嘗試著運用西方的集體行動理論,結合中國的國情,對中國的群體性突發事件進行研究。于建嶸運用了勒龐的群體心理學理論來分析,認為群體性事件突發過程中存在著明顯的借機發泄、逆反、盲從、法不責眾等心理[4]。雖然這些研究也認識到中國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一些特征,但由于缺乏理論指導,很難進行深入研究。
另一個問題是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定性存在偏差。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給群體性突發事件定性為“危害”,“對政府管理和社會造成影響。”[1]基本上把這類事件認定為非理性的行為。王來華,陳月生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并概括了群體性事件6個主要特征:導火索刺激,人群聚焦,突然發生,情緒波動,行為沖突和情況多變[5]。于建嶸從參與者心理角度進行了研究。認為事件中的絕大多數參與者與最初引發的事件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主要是路見不平或借題發揮,表達對社會不公的不滿、以發泄為主;有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的行為,不僅給國家、集體和個人造成財產方面的損失,而且會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6]。由此可以看出,他基本上也把群體性突發事件參與者的行為歸為非理性行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國的學者多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衡量群體性突發事件對政府、官員和社會的得失,很少從參與者心理的角度進行考察。而且,他們對參與者的評價相對比較負面,認為這種行為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基本忽略了群體突發性事件中參與者的理性因素。
二、有限理性:群體性突發事件分析的新視角
筆者認為,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參與者既有非理性的因素,也有理性的因素,是一種有限理性。理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自利,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對共同善的追求。只要符合其中一點即是理性[7]。換言之,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選擇個人利益至上,或者選擇集體利益至上都是理性的行為。那么非理性的行為即是在追求個人利益時,做出的決策不利于個人利益,過于關注自己的動機、興趣、精神過程,而干擾了對自己利益的考量,做出有損自己利益的行為,或者說本來追求有益社會或集體的行為,但因受動機、興趣等的干擾,結果卻危害了社會或集體。
西方學者對群體性事件理性與否的探討,體現在集體行動或社會運動理論中。集體行動的理論源于20世紀初期的法國思想家勒龐(Gustave Le Bon)。他認為當一群人聚合在一起時,去個性化、情緒化、非理性化占據主導地位。所謂去個性化,是指群體中的成員往往會失去個體感而淹沒于群體之中,做出一些與個人獨處時不可能做出的反應,甚至與自己個性截然相反的某些行為。所謂情緒化是指群體的行為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情緒色彩,在很多情況下理智往往為情緒所支配。與此相應的是,他們在判斷某事或評判某人時,不能訴諸理智,喪失了批評能力[8]。
勒龐把人們參與運動歸為非理性,注重對人們情感的探討,這種分析模式影響了以后對社會運動的分析。20世紀60年代興起了相對剝奪理論,代表人物有戴維斯(Davis)、古爾(Gurr)等人。相對剝奪感的理論認為,人們的不滿是在比較中產生的,具體來說,在與自己過去,與自己的將來,以及與他者的比較中產生。相對剝奪感越大,產生的攻擊越大,這就是挫折—攻擊機制[9]。
以上的研究基本上屬于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路徑,重視不滿的產生,強調非理性的作用。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有學者對這種研究方式提出了批評,他們注重理性的作用,關注國家和社會結構[10]。最著名的是奧爾森在《集體行為邏輯》中所提出的理性選擇模式。他認為每個人參與集體行為時都是理性的,即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集體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這樣就會出現“搭便車”現象,即個人少付出,甚至不付出。“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者其他某些特殊的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11]這就是所謂集體困境,解決此問題的方法是選擇性刺激,即刺激能夠到達每個個體,真正做到獎勤罰懶。
運用理性進行分析社會運動可謂占據了當今社會運動研究的主流。以美國為例,主要體現為兩大理論:一是資源動員理論;二是政治過程理論。資源動員理論對社會運動的解讀繼承了奧爾森的理論,代表人物為麥卡錫(McCarthy)和扎德(Zald)。他們回答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人們盡管有時懷有不滿,但并不是所有的不滿都轉化為行動。這是因為行動前人們通常要考慮資源的得失(主要體現為時間和金錢)。他們運用市場經濟的供需關系分析社會運動。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被看作是理性的消費者,而社會運動的組織者是供給者,他們提供的產品迎合了參與者的需求[12]。政治過程理論是對資源動員理論的發展,代表人物是查爾斯·蒂利。該理論接受理性選擇模式,認為集體行動有得有失,但在采取行動前,抗議者總要計算自己的付出,以及帶來的利益,然后比較得失才付諸于行動[9]。endprint
以上諸種探討集體行動的研究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即把理性與非理性看作截然對立的兩面,沒有關注到理性與非理性的中間狀態。20世紀70年代以來,認知心理學已經認識到人們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Herbert A.Simon)在70年代末期,發表文章稱政治學的研究應該將認知心理學的有限理性觀點與經濟學中的實質理性結合起來[13]。也就是說,我們在考察政治人的行為時,既要考察經濟學中所提出的人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觀點,也要注意到心理學中提出的人們的理性觀點,兩者結合起來考察政治現象可能更加準確。
有限理性與政治學的結論最好的體現是啟發在政治學中的應用。啟發是一種認知捷徑,能夠把復雜的任務簡單化,它也是一種理性,但是這種理性是有限的,它的作用是避免人們在信息分析中耗費過多的精力。即化繁為簡、有限理性、省時省力是啟發的基本特征[14]。
啟發在政治學中多用于選民的研究,有學者指出,選民在了解和思考政治問題時,運用的思維方式即是啟發[15]。也有學者開始把啟發理論與集體行動理論結合起來。魯爾(James B.Rule)提出了集體行動啟發的概念,即集體行動也會遵循認知的捷徑,集體行動同樣游走于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他認為理性與非理性模式都是理想的類型,只可能解釋某些現象,譬如勒龐等的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群體的情感,以及群體自發的行動;理性模式在解釋參與者的目的方面做得很好。最后他主張兩種模式應該調和[16]。
理性模式與非理性模式的爭論是因為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所致。從集體行動理論的演變可以看出,兩種模式存在明顯的分期,60、70年代以前的理論多主張非理性模式,之后多主張理性模式。非理性模式論者多應用于無組織、群體的自我行動,譬如勒龐就是以法國大革命作為樣本考察群體的心理;理性模式論者探討的多是有組織的集體行動,譬如工會領導下的罷工等,這些行動帶有明確的目的和利益的計算。魯爾的研究還提醒我們,現實中集體行動有可能是理性與非理性的混和,不是單純的理性或非理性。
但魯爾的研究也存在問題,即把情感與理性對立,把情感的發泄看作是非理性的一種體現。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許多學者注意到理性與情感之間的關系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密不可分。許多學者在研究政治認知時發現,政治情感在政治認知的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馬庫茲(George E.Marcus)對情感(emotion)的英文作了如下的解釋:“e”指“to be”,和“motion”結合在一起,意為激勵人們(move people),使人們付諸于行動[17]。麥格勞(McGraw)所說:“在研究人們對政治世界的理解和反應時,如果把情感排除在外,這種研究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們對政治的情感,不管是強弱,也不管是發散的還是具體的,都不可能避免地滲透于其中。”[18]
在此背景下,有學者有意識地把情感、理性同時引入到對集體行動的考察中。卡蘭德曼斯(Klandermans)把不滿看作是一個運動形成的必要條件,只有群眾有不滿,才可能形成共識,最終參與運動。但不滿僅是一個必要條件,并不一定導致人們參與運動。因此還要關注到參與運動得失的考察,即理性的計算。譬如集體的收益,成功的可能性等等[19]。但是卡蘭德曼斯考察的對象多是有組織的示威、罷工,譬如荷蘭組織的反對美國在荷蘭部署導彈的示威,而對群體性突發事件沒有關注。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停留在勒龐的時代,歸為非理性的行動。
綜上所述,對集體行動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定性不僅體現為時代的差異,也體現為研究對象的差異。西方學者近期的研究成果,使我們認識到理性與非理性之間存在著有限理性,理性與情感之間也不是對立的,二者有調和的一面,這點有助于我們對群體性突發事件做出重新的思考。有限理性分析是否適合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分析?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爆發既有非理性的,也有理性的因素,是一種有限理性。群體在與政府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把群體性突發事件看作是一種集體性啟發,即在遇到不滿時,作為影響政府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三、對貴州“甕安事件”的分析
(一)爆發的心理基礎:群體的不滿
甕安事件爆發前,民眾的不滿情緒來自以下方面:對自身地位低下不滿;這種較低的社會地位與相對剝奪感結合使不滿情緒加劇。
2000年至2007年甕安地區生產總值翻了近一番,財政總收入增長近3倍。但礦區民眾的生活水平不僅改善不大反而更加趨于貧困,有的連基本生存都出現了問題。劉子富是這樣描述的,甕安礦產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剝奪了群體的生存權。礦產資源的開發,導致了地面開裂,房屋下沉,賴以生存的水源枯竭,民眾的基本生存條件面臨威脅[20]86。可見,礦區民眾產生不滿情緒來自于生存權的威脅,其產生根源是分配的非正義,即結果的不公。類似問題也發生在移民拆遷等問題上。
對于生活在縣城的民眾來說,他們的威脅則主要是安全。在甕安群體事件爆發前,治安不好是當地人的共識。有的人在家里遇到了搶劫,報警之后,警察卻要求他們打另一個電話。很多人“晚上都不敢出門”,晚上的路邊,“可以見到有人拿著砍刀走來走去的”,小店下午都會很早關門[21]。當地警方對治安案件打擊不力導致了受害者的不滿,縱容了黑社會的形成,在甕安群體事件中就有黑社會性質的“玉山幫”在其中作亂。
甕安民眾在與自己的過去比較中也產生了不滿。民眾的基本生存權在當地礦產資源開發前還是得到保障的,但礦產資源開發后,基本的生存權已經受到了威脅,前后差距明顯。具體來說,他們面臨的威脅或來自于礦業的盲目開采,或來自于社會的治安,這些都需要政府的積極介入才能夠得到改善,但是由于當地政府對這些問題處置不力,有時甚至是不作為,使民眾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失望。
(二)非理性因素分析
甕安群體性突發事件源自于一個小女孩的自殺,最終發展成群體性突發事件。為何小女孩的自殺會成為傳染源?首先,小孩、女孩都是弱者,是人們所同情的對象。李樹芬(即死者)和女伴是在黑暗的晚上與另外兩個社會青年在河邊玩中自殺身亡的,正因為她是一個女學生,其死亡自然首先會使人想到是他殺。警察此后的一系列行為似乎也在印證人們猜測的合理性。警察認定女孩李樹芬屬于溺水死亡,家屬不同意認定的結論。值得注意的,事件之后查明,小女孩確實為溺水死亡,但對于兩次尸檢的結論家屬均不認同。因為法醫所做的工作,家屬并沒有在場,因此家屬懷疑結論的公正性。警察不但沒有很好地解釋,反而與女孩的家屬發生沖突,女孩的叔叔還遭到毒打。endprint
其次,人們缺乏冷靜分析。家屬所提出的主張,看似合理但實際上缺乏有力證據,但由于警方沒有給出很好的解釋,導致謠言滿天飛。譬如有人說,李樹芬的同學王某是縣委書記的侄女,在考試時,李樹芬不把試卷讓她抄,由她請兩個社會青年報復李樹芬;不但死者的叔叔遭到毆打,而且爺爺、父母均被打,甚至,有人傳說她的叔叔被打死。這些謠言是很容易得到證實的,但是人們往往站在弱者的一面而沒有去澄清,輕信了謠言而否定了警察的結論。
小女孩李樹芬的死亡只是群體性事件的導火索,它點燃了群眾埋藏在心里的對當地政府和警察的不滿情緒。此次事件中,每個參與者仿佛都變成了“野蠻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個人的智力水平都降低到了非常低的水平,每個人的理性也完全被對警察的不滿情緒所支配。
(三)理性因素分析
那么甕安群體事件中,群體的參與是否有理性的成分?答案是肯定的。這種理性的成分在事件爆發前后都有所體現。
甕安群眾與當地政府部門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群體性突發事件是最有效影響政府決策的方式。中國的老百姓經常采用的尋找發泄的渠道有兩種:一是信訪部門,向縣級乃至上級的信訪部門反映問題。二是向有關部門反映問題。但這兩條路在一些地方往往行不通。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甕安縣信訪局接待群眾來信來訪共670件,而在“6.28”事件發生前后,僅7、8兩個月,信訪局接待立案的群眾上訪就有600多件。但信訪辦結率卻很低,縣信訪局局長秦綜說:“2006年以來辦結的信訪案件僅122件,辦結率僅為18.2%。”[20]100究其原因,在于信訪部門本身對群眾所反映的問題所涉及的各個部門并沒有相應的制約權力,即使他們走訪一些部門也往往得不到回應。
當然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對群眾的態度。引起當地群眾不滿的,群眾反映問題最多的是礦山的開采。縣、鄉鎮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對這些企業不加管制,導致這些企業盲目地開采,致使群眾賴以生存的水源斷絕,房屋塌陷,農田被毀,環境污染。群眾在向當地政府反映這些問題時,政府能拖就拖,漠然置之。面對政府的不作為,群眾聯合起來與礦業公司進行斗爭,面對礦群沖突,政府明顯偏袒一方:動用公安人員把帶頭的群眾抓起來,然后動用司法機關對他們判刑[20]90。不但在商民的矛盾沖突中,政府明顯地站在企業一方。而且有些企業本身就是官商勾結的產物。甕安縣紀委、縣國土局等有關部門披露,一些黨政干部、公檢法干部用家屬子女名義入股經商辦企業,無證開采相當嚴重[20]102。本來政府應當作為民眾情感的傾聽者,但卻成為民眾情感的壓抑者,這是導致群眾不滿的一個重要來源。
由此帶來的惡果也是非常明顯的:一是民眾把對企業的不滿,會轉嫁到政府身上,政府成為民眾不滿的主要來源地;二是政府在民眾中的威信盡失,使其在說服民眾時無能為力,民眾不是把其作為一個公正的評判者,而是與企業的合謀者,一個自私自利者,公正性的喪失使民眾對官員的解釋始終帶著懷疑的眼光;三是群眾的不滿在政府那里得不到回應,導致不滿的堆積;四是群眾的情緒沒有發泄的渠道,這就導致一時爆發,就可能以突然的形式表現出來——即突發性事件。
在事件爆發過程中,人們沒有相信警察的說法而相信謠言,也有理性的因素。其中,政府和警察平時在當地民眾中的刻板印象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和警察在當地的印象是只是照顧自己的私利,官商勾結。這種負面的印象,在面對模糊性,或者具有爭議性的信息時,人們更多的從警察和政府的負面來理解。刻板印象,往往出現在人們的認知能力有限,同時認知的任務繁重的情況下,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經常采取的一種思維方式,在政治領域經常遇到的是對政黨、種族等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就是有限理性的一種體現,即它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非理性的。
這次事件是以群體的形式爆發出來的,群體是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即沒有領導者,沒有組織性,完全因共同的情感把大家聯系在一起。之所以選擇烏合之眾的形式,也體現了理性的考量:
其一,責任分散心理。沒有組織、沒有領導,這樣使因群體性事件所導致的責任就會分擔到每個參與者個人身上,但是法不責眾又可以使每個人逃避責任的追究。以前的官民沖突中,民眾的代表因與官府的沖突被拘留,甚至判刑,鑒于以前的教訓,使人選擇了烏合之眾的形式。
其二,群體性事件所產生的效力使人們有意無意地選擇了群體性的形式。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官逼民反的觀念,這種觀念已經融化在民族的靈魂之中。全國各地所爆發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所產生的轟動效應,必然會引起各大媒體以及上級領導的重視,從而導致群體的不滿能夠得到滿足,逐漸使人們有意無意地相信,只有群體性事件這一條途徑才有效力。
中國現有的績效評估體制也為這種觀念提出了佐證。中國的官員績效評估中,經濟指標是最重要的指標。但是也有兩個指標是官員不得不重視的,一是社會穩定指標,二是計劃生育指標。如果這兩個指標中任何一個指標不達標,就會一票否決,使政府一年的成績都歸于零。社會穩定指標中,群體性突發事件是最重要的指標。官員對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積極回應,民眾通過群體性突發事件表達情緒的屢試不爽,逐漸起到了心理的強化作用。甕安事件爆發之后,當地的政治生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書記和縣長因此事被撤職,許多影響當地治安的黑社會組織受到了懲治,礦群的沖突也得到了緩和。
四、結語
中國的群體性突發事件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非理性的因素。群體的不滿情緒的出現是群體性突發事件爆發的基礎,群體的不滿可能導致群眾容易相信謠言,不相信政府,以及暴力的行為。這些都是非理性的表現,但是群體性突發事件是群體的訴求得到政府回應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同時因無組織性,參與的群體責任分散,甚至免于受到懲罰。群體性突發事件逐漸成為許多地方群體尋求不滿發泄、問題解決的一種重要的方式。
這就形成了集體性啟發的思維方式,簡言之,在問題得不到解決時,群眾往往把群體性突發事件作為訴求得到解決的捷徑。它是在正規的渠道,譬如信訪、向政府反應問題均無效的情況下,人們所經常采用的一種選擇。因此,要防止群體性突發事件的發生,首先,必須對群體的不滿有所回應,要正視人們的不滿,然后積極尋求解決的途徑;其次,與此相聯系,群體表達訴求的渠道應該暢通。endprint
參考文獻:
[1]史云貴.我國現階段社會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反思與應對[J].政治學研究,2009(2):69-74.
[2]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我國轉型期群體性突發事件主要特點、原因及政府對策研究[J].中國行政管理,2002年(5):7-9.
[3]王來華,溫淑春.論群體性突發事件與輿情問題研究[J].天津社會科學,2006(5):63-65.
[4]于建嶸.社會泄憤事件中群體心理研究——對“甕安事件”發生機制的一種解釋[J].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9(1):1-5.
[5]王來華,陳月生.論群體性突發事件的基本含義、特征和類型[J].理論與現代化,2006(5):80-85.
[6]于建嶸.當前我國群體性事件的主要類型及其基本特征[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 (6):114-120.
[7]Richard R. Lau, David P. Redlawsk. Voting Correctl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3. 1997, pp. 585-598.
[8]古斯塔夫·勒龐.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28.
[9]趙鼎新.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J].社會學研究,2005(1):168-207.
[10]裴宜理.社會運動理論的發展[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6(3):4-12.
[11]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1995:2.
[12]馮仕政.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現狀與范式[J].國外社會科學,2003(5):66-70.
[13]Herbert A.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The Dialogue of Psychology with Political Scienc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79,No2. 1985,pp. 293-304.
[14]Amos Tversky,Daniel Kahneman.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Science,New Series,Vol.185,No.4157.1974,pp.1124-1131.
[15]Paul M. Sniderman; Michael G. Hagen; Philip E. Tetlock; Henry E. Brady, Reasoning Chains: Causal Models of Policy Reasoning in Mass Publ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4. 1986, pp. 405-430.
[16]James B. Rule.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in Militant Collective Action. Sociological Theory, Vol.7, No. 2. 1989, pp. 145-160.
[17]George E. Marcus. Emotion and Politics: Hot Cognitions and the Rediscovery of Passion.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30,No.2,1991,pp.195-232.
[18]Kathleen M. McGraw, Contributions of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o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1, No.4, 2000, pp. 805-832.
[19]Bert Klandermans,Mob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Social psychology explanat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Americal Sociological Review,49.1984,pp.583-600.
[20]劉子富.新群體事件觀——貴州甕安“6.28”事件的啟示[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21]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目擊者還原甕安死亡事件演變到騷亂過程[N].南方人物周刊,2008-07-09.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