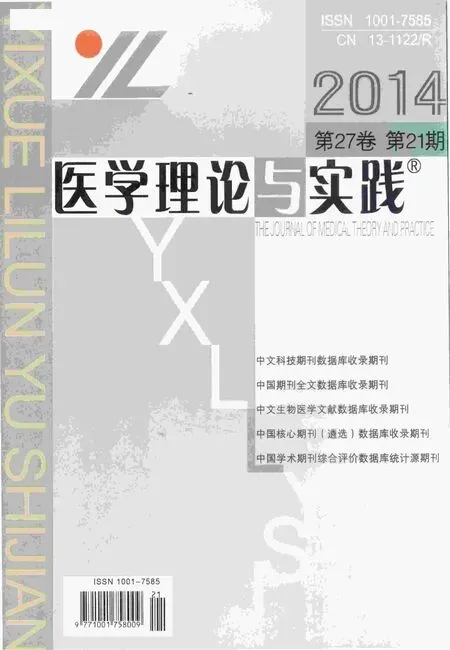頸動脈支架置入術(CAS)后血清WBC、hs-CRP、IL-6變化及臨床意義
阮志芳 何文欽 傅懋林 肖雪玲 解放軍第180醫院神經內科,福建省泉州市 362000
頸動脈狹窄是目前導致缺血性腦卒中的常見病因,而頸動脈支架置入術(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是解決癥狀性狹窄的主要方法[1]。炎癥反應參與動脈粥樣硬化的病理生理過程,而CAS術后,易導致斑塊破裂,雖通過保護傘等“栓塞保護系統”有效解決遠端血管栓塞問題,但狹窄動脈解剖重構及斑塊碎片釋放的炎癥因子進入血循環,可能引起一系列不良后果。因此,檢測外周血中的炎癥指標WBC、hs-CRP及IL-6水平對腦血管事件的評估及預測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通過比較分析CAS術后血清WBC、hs-CRP及IL-6的水平,探討炎癥指標的動態變化在腦血管事件中的臨床意義。
1 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自2012年1月-2013年6月我院神經內科成功行血管內支架成形術治療頸動脈狹窄的患者,術前所有患者通過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頸部血管彩超及數字血管減影(Dig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檢查,確診為頸動脈狹窄,均為腦卒中“責任”血管,病例共入組22例。其中男17例,女5例,年齡(62.1±10.5)歲,體重指數(23.7±2.1)kg/m2。合并有高血壓病、糖尿病、高脂血癥及吸煙等卒中危險因素。入組標準:(1)有短暫性腦缺血發作(TIA)或腦梗死臨床癥狀;(2)采用歐洲頸動脈外科試驗(European carotid surgery trial,ECST)方案,確定頸動脈狹窄程度≥70%;(3)患者意識清楚,肌力≥3級,無精神異常及智能障礙;(4)患者及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5)無嚴重器質性心臟病,肝腎及凝血功能正常。
1.2 CAS方法 采用1%利多卡因局部浸潤麻醉,Seldinger技術穿刺股動脈,成功后置入8F血管鞘,全身肝素化,導絲導引下將8F導管置入頸總動脈,在微導絲的引導下,將腦保護裝置定位于狹窄遠端后釋放,再應用球囊擴張狹窄段后,在路圖下送入自膨式支架(記錄支架的型號),對位準確后釋放支架,復查造影判斷支架成形情況。術中全程肝素化,持續心電監護,嚴密觀察心率、血壓變化。
1.3 標本采集 分別在入院第1天和CAS術后第3天空腹采集2ml EDTA-K2抗凝管1管,促凝管1管;其中抗凝管用于檢測WBC和hs-CRP,促凝管用來檢測IL-6。
1.4 試劑儀器 WBC、hs-CRP采用檢驗科SYSMEX XE-2100血球儀及飛測CRP檢測儀檢測,人血清IL-6試劑盒購于武漢博士德生物公司。
1.5 統計學分析 所有實驗數據用SPSS10.0軟件包處理,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患者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前、后血清WBC、hs-CRP、IL-6水平比較情況見表1。
表1 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前、后血清WBC、hs-CRP、IL-6水平結果比較(±s)

表1 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前、后血清WBC、hs-CRP、IL-6水平結果比較(±s)
?
3 討論
頸動脈狹窄是腦卒中的常見病因,解除狹窄及穩定斑塊是預防卒中的關鍵。頸動脈支架置入術(CAS),由于其創傷小、療效確切,術中通過保護和濾過系統可預防碎裂的斑塊造成腦栓塞,是目前頸動脈嚴重狹窄最常用的治療方法。然而,對于責任動脈解剖重構及斑塊碎裂后釋放的炎性因子可能出現的不良后果一直未受到臨床醫師足夠的重視。
頸動脈狹窄的主要病理改變是動脈粥樣硬化。在斑塊的形成過程中,一直伴隨著炎性反應,如單核細胞在內皮黏附分子的作用下附著于血管內皮細胞表面并進入內皮下轉化為吞噬細胞,吞噬脂質成為泡沫細胞。白細胞(WBC)是一種常見的免疫炎癥細胞,多數斑塊病理研究顯示其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本文資料顯示,頸動脈支架置入術前、后血清WBC水平比較,盡管術后白細胞水平有所升高,但差別無統計學意義,預示白細胞計數在頸動脈粥樣硬化中并非一個敏感的指標,原因在于斑塊僅是局部炎癥反應,而白細胞計數升高多意味著全身性炎癥反應,如感染性疾病。國內李焰生教授等研究認為,相對于白細胞計數,單核細胞比例對頸動脈粥樣硬化具有較高的獨立預測作用[2]。Chapman等[3]亦發現單核細胞計數與頸動脈斑塊及內中膜厚度獨立相關。
既往研究顯示,炎癥標志物hs-CRP是動脈粥樣斑塊穩定性的敏感指標,其水平變化預示著斑塊的易損狀態[4]。本文結果顯示hs-CRP在CAS術前維持在較高水平,術后進一步升高,CAS術前、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hs-CRP始終參與了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發展過程,同時hs-CRP水平越高,預示著斑塊越不穩定,易形成不良的臨床血管事件。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循環血中IL-6水平與顱內大動脈粥樣硬化及腦小血管疾病有關[5]。IL-6高水平與斑塊易損有關[6]。本文資料顯示CAS術前、后IL-6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CAS術后IL-6水平明顯升高,提示IL-6作為一種常見的炎癥因子,是斑塊變化的一個敏感指標,其機制可能是IL-6促進了細胞因子與氧自由基的產生,降低血管內皮細胞一氧化氮的合成。有研究發現,氧自由基的大量產生與內皮細胞功能障礙是頸動脈狹窄血管重建后腦再灌注損傷的關鍵因素[7]。因此檢測外周血IL-6的變化可作為判斷斑塊易損性及CAS術后繼發腦損傷的一項輔助指標。
綜上所述,hs-CRP、IL-6等炎癥因子與動脈粥樣硬化及其斑塊易損性密切相關,對腦卒中的發生、發展及預后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在臨床上,應密切監測上述指標的變化,并將其指導臨床診斷和治療。
[1] Goodney PP,Schermerhorn ML,Powell RJ.Current status of carotid artery stenting〔J〕.J Vasc Surg,2006,43(2):406-411.
[2] 潘元美,李焰生,林巖.炎癥因素與腦梗死患者頸動脈粥樣硬化的關系〔J〕.臨床神經病學雜志,2008,21(3):174-176.
[3] Chapman CM,Beilby JP,McQuillan BM,et al.Monocyte count,but not C-reactive protein or interleukin-6,is an independent risk marker for subclinical carotid atherosclerosis〔J〕.Stroke,2004,35:1619-1624.
[4] Corrado E,Rizzo M,Tantillo R,et al.Markers of inflammation and infection influence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baseline asymptomatic carotid lesions:a 5-year follow-up study〔J〕.Stroke,2006,37:482.
[5] Hoshi T,Kitaqawa K,Yamagami H,et al.Relation between interleukin-6level and subclinical intracranial large-artery atherosclerosis〔J〕.Atherosclerosis,2008,197(1):326-332.
[6] Yamagami H,Kitagawa K,Nagai Y,et al.Higher levels of interleukin-6are associated with lower echogenicity of carotid artery plaques〔J〕.Stroke,2004,35(3):677-681.
[7] Van Mook WN,Rennenberg RJ,Schurink GW,et al.Cerebral hyperperfusion syndrome〔J〕.Lancet Neuro,2005,4(12):877-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