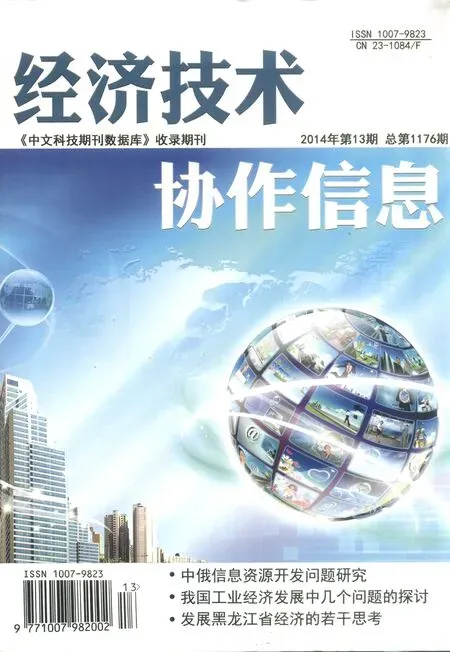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轉型與供求拐點
姜雪玲/哈藥集團制藥六廠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轉型與供求拐點
姜雪玲/哈藥集團制藥六廠
中國勞動市場極為龐大,這主要是以龐大的人口基數作為基礎,但是伴隨著自動化工業體系以及經濟的發展,中國勞動市場無論是結構還還是供求上,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本篇文章主要針對中國勞動市場的結構轉型以及供求拐點進行了全面詳細的探討。
勞動力市場;結構轉型;劉易斯轉折點
一、引言
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由于體制、政策、人口結構等方面所表現出的特殊性,促使中國的勞動力市場與其他資本主義市場之間有著較大的差異性,但是從中國勞動市場以及經濟的不斷發展來看,表現出的相關特征已經基本符合劉易斯二元經濟理論。但是我國國內學者對于中國當前的經濟狀態,是否已經完全達到了劉易斯轉折點,存在著較大的爭議性。下文主要針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轉型以及供求拐點進行了全面詳細的探討。
二、劉易斯轉折點理論
通過現代社會部分勞動極為密集的行業工資、勞動邊際生產率的曲線,可以對劉易斯轉折點理論體系加以闡述。如圖1所示,橫軸代表勞動量(L),縱軸代表勞動的邊際產品(Q)。OW是現代部門的實際工資,0S代表傳統部門的平均實際收入。WN1Q1代表最初階段的剩余,OWQ1L1L代表最初階段支付的工資總額。在這其中,由于現代生產部門在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將一些剩余的資金投資到新資本體系的創造上,那么資本本身持續增加,也就促使邊際勞動生產曲線開始逐漸朝右方進行移動,進而達到N2Q2的級別,而在這一過程中,實際無論是勞動力還是就業數量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此外,現代生產部門在持續加大投資的情況下,使得邊際勞動生產曲線開始二次移動,達到N3Q3的水準,這期間也就僅僅只剩下傳統部門還擁有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這基礎上,現代生產部門也就能夠通過這方面的勞動力優勢,促使生產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達到Q4為止,這一位置是劉易斯理論中的第一次轉折點。此時以往傳統部門表現出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則不再為零,但勞動力逐漸從傳統的生產部門朝著現代生產部門進行流動的過程中,會導致相關機會成本大幅度提升,那么在這基礎上,現代生產部門如若不提升工資,也就無法得到足夠的勞動力。
三、農業發展與劉易斯轉折點
劉易斯模型本身只是對于現代化工業部門所表現出的擴展過程進行了描述,但并沒有針對農業發展詳細的描述,也沒有給出分析結果,而后美國研究學者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上,來對農業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描述,具體如圖2所示。圖2中橫軸OL表示農業勞動量(L),縱軸OY表示農業總產出(Y)。OCPA所代表的,便是農業生產部門呈現出的總體曲線。從這一曲線圖能夠看出,整體曲線是通過兩個不同形狀構成:曲線OCB代表的是農業體系在勞動力不斷增加情況下,其邊際生產率的持續減少;而BA部分的曲線則是完全水培的,這意味著勞動力的持續增長,對于農業產品量的增長沒有直接的關聯,也就是勞動的邊際產品指數為零。那么在這一基礎上,將L1L環節的勞動力從其中完全剝離之后,對農業產品量不會造成直接沖擊,這部分勞動力被稱之為多余勞動力。雖然說L3L1中的勞動邊際超出零,但與平均產量相比較則遠遠不足,這是農業部門存在多余勞動力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說農業部門的工資,并非是通過邊際產量來確定的,而是利用OA/OL來進行決定,這方面的工資也就是一種分享形式存在。也就是說,只要現代部門在進行發展期間,能夠給農業部門勞動力支付略高于平均產量的工資標準,那么就能夠促使大量農業勞動力轉移到現代部門中。

圖2 劉易斯轉折點與農業發展

圖1 勞動邊際生產率與實際工資
但是一旦勞動力轉移達到L1后,如果勞動力繼續轉移的話,農業中勞動的邊際產出大于零,按照劉易斯的定義,可以把B點看成經濟發展的劉易斯第一轉折點,經濟到達這一轉折點后,如果現代部門想繼續吸引農業勞動力,那么現代部門的實際工資就必須上漲,因為該點之后勞動邊際產量大于零,勞動力如果繼續轉移則農業總產出就會下降,農產品價格會上升,勞動力轉移的成本增加,如果實際工資不增加,則現代部門將不能吸收到足夠的勞動力。
由于在L3點之前農業的勞動邊際產量其曲線CBA的斜率小于農業的平均產量(即OA/OL),農業勞動力繼續處于就業不足的狀態。
四、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與劉易斯轉折點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大批農民工向城市流動可以說是舉世矚目,截止2006年,農村外出打工勞動力規模為1.32億人,其中80%進入城市就業。然而我國農民工工資水平低,就業環境差,農民工的權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進入公平流動階段。與農民工相關的政策發生了根本變化,如開始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以及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等問題。與此同時,隨著我國農村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減緩,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幅度減少,21世紀以來出現的“民工荒”已經成為全國性的亟待解決的問題。2010年初的調查顯示,約四成企業用工需求沒有得到滿足。一方面用工需求得不到滿足,而另一方面卻是農民工社會地位得到基本尊重,工資增速加快。
五、結論
綜上所述,大量國內外的研究事實都足以證明,在社會體系中,中等收入的群體發展能夠為社會發展的穩定起到良好的促進作用。并且社會所表現出的合理收入分配格局,應當是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占少數,而中等收入群體占絕大多數的格局。特別是在對于政府、企業、百姓之間進行收入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應當要加快百姓的收入;重點針對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幾個群體之間的關聯性加以調整,加速低收入、中等收入的發展速度。而要達到這一效果,就需要針對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實際情況,構建起一個正常的勞動報酬增長體系,確保經濟得以穩定的發展。
[1]劉洪銀.從中國農業發展看“劉易斯轉折點”[J].西北人口.2009(04).
[2]宋世方.劉易斯轉折點:理論與檢驗[J].經濟學家.2009(02).
[3]李月.劉易斯轉折點的跨越與挑戰--對臺灣20世紀60-70年代經濟政策的分析及借鑒[J].財經問題研究.2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