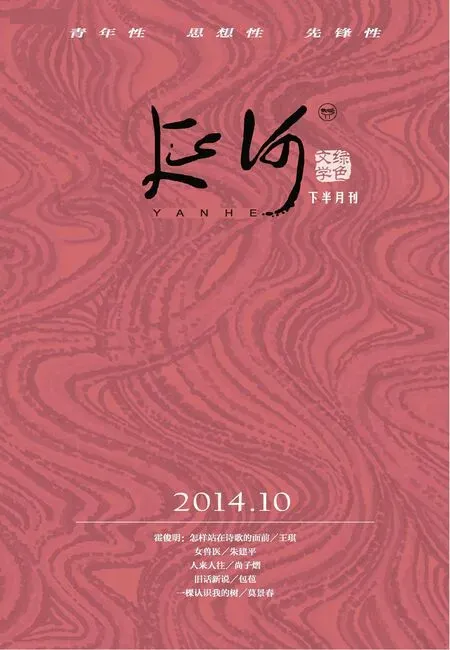筆尖下的家園
◇ 紙墨飛花
筆尖下的家園
◇ 紙墨飛花
1
小麥,是北方土地上最多的生命。
十月,犁鏵聲聲破土,飽滿的小麥種子,就被播進了深軟細潤而又黝黑的泥土里。
過不幾天,小麥就探頭探腦地鉆出來。一粒麥粒,長出來就是一棵小麥,一大片小麥,長出來就是一大片小麥。狀若韭,青綠青綠的。每一棵麥子都很相似,就如同每粒泥土都相似。
轉過年五月,鄉村就像廚房里的那鍋開水,沸騰起來,升騰起來。稻穗,沉甸甸的,在一望無際的田野里,閃著金晃晃的光彩。
爺爺懷抱一管大煙桿,半翕著眼,在田間地頭上,看著身邊蓬勃的小麥,接受著陽光的曝曬。
天氣熱,麥仁就飽滿。小麥拼命地抽穗,拔節,麥芒恣睢地刺著太陽,發出絲絲的聲響。有風吹過,就成排的彎腰,不是你碰著了我,就是我碰著了你,要不,就是你挨著我,我挨著你,嘰嘰喳喳,嘻嘻哈哈。
小麥就是小麥,長大了還是一株小麥。土里土氣的樣子,大大咧咧的脾氣。
過了五月,麥海金浪翻滾,泥土與麥香混合在一起,彌散開村莊特有的氣息。
“蠶老一食,麥熟一晌”。于是,整個村莊加倍忙碌起來。家家戶戶,在磨刀石上磨鐮霍霍,似乎上戰場一般。每天清晨,太陽還沒露頭就要下地,中午麥地里,烈日像個火球,燒在臉上,滾燙滾燙,人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拼命地干,晚上摸黑才回家。小麥一旦成熟,需要趁好天“搶”收,因為麥收的天氣,就像小孩的臉,說變就變。倘若遇到雨天,甚至連雨天,小麥就發霉生芽。一年的忙活就只能落個欠收。割小麥的時候,往往好幾家自發組成一個互助組,今天割這家的,明天割那家的,有割的,有拉麥的,有打麥的,有揚場的,有送飯的,快干,搶干,合干,非常快。麥收開始,人們爭先恐后地向前方移動,鐮刀揮舞,小麥成排地倒下。
鋪天蓋地的小麥,看過了花敗、木榮、果熟、草枯,就這樣,又鋪天蓋地地倒下。
明年,它們還會從土地里長出來,它們不嘆息,不留戀,在鐮刀下歡快地呻吟。
麥垛一個高過一個,歡笑一浪高過一浪。村莊里,開始漾著好聞的新麥的香味兒。
曬谷場上,老牛拉著石磙旋轉,跟著一起旋轉的,是千百農人的日子,是村莊四季的更替,是小麥一樣輪回的生命。
2
爺爺,就是一棵帶芒的小麥。
他的青年,在犁鏵的牽引下漸行漸遠,老年,卻在犁鏵的嘩啦聲中應聲而來。
谷雨還沒到來,爺爺就開始把犁鏵擦拭得雪亮。耕種時,他抖一抖韁繩,蹚出的犁溝,像繩墨拉出來一樣直,亮尖的鐵犁,翻開厚厚的泥土,散發著黑金一樣的光澤。風里雨里,爺爺的目光,隨著犁鏵在歲月里翻耕,滿眼豐收的熱望。
農閑時節,犁鏵就靜靜地掛在屋檐下。陽光撒著細碎的金黃,照在它身上。我會滿心好奇地撫摸著它。兩根粗粗的彎木套在一起,尖尖的犁頭,戴著明亮的鐵鏵,這簡單的犁鏵,怎么就能開墾出那么神奇的土地呢?當我赤腳插進泥土,扶著犁鏵翻起泥土,我就明白了,爺爺與土地,有多么難以割舍;也發現,犁鏵的生命和爺爺的生命也融到一起。因為一部犁鏵,可以犁消歲月,可以犁亮人生,可以犁出一個幸福的家園。
村莊,是真正的家園。在這里,每一葉草,每一棵麥子,從容而生,從容而長。孩子們摸爬滾打在大人煙火紅閃閃的縫隙里,而太陽會無數次從躬耕的脊梁滑落,從穿針的縫隙流過。冬天,天空冷得像結了冰,沒有蝴蝶在花心里睡覺,卻有麻雀在悄悄覓食,一顆老樹,正在發著自己生命的新芽,一些蟄伏的生命,都在雪地里,準備來年的夢想。萬物復蘇的季節,荒蕪蒼涼的土地有了綠意,飄散出獨有的氣息,還有陽光暖暖的味道。鳥兒銜來了一個水靈靈的春天。河水潺潺,流出兩岸的青綠,流出一河的蛙聲。村莊,盈盈地汪在心間,涼風悠悠,送來小麥和青草的香。麻雀把天空壓的很低。一葉犁鏵,舒暢地鉆進黃土。
我的目光在村莊里游移,一只貓,躺在地上,懶洋洋地曬著太陽,那頭老黃牛啊,正咀嚼著嫩嫩的青草,偶爾,還恣意地抬頭“哞——哞——”叫幾聲。蝴蝶,在油菜花里追逐翻飛。半空中懶懶的炊煙,裊裊的,淡淡的。姑娘們被春風吹去了臃腫,一個個明亮鮮艷,風擺楊柳地走在街上,男娃的目光像醉漢,跟姑娘如水的眼神,蹣跚一碰,就有一個動人的愛情故事,隨著草色綠起來了。
在村莊里,我看見過超乎尋常的茂盛,聽見了土地的呼吸,看見了麥香,目睹了五谷豐登。
村莊,在一個孩子的眼里,是黃的。泥土是黃的,小麥是黃的,那一排排斜坡頂的泥屋是黃的,攤在屋頂的掛在墻上的玉米是黃的,就連花盤似的立在向日葵的枝干上的太陽,也是黃的,和土地最近的人,那些耕種土地的人,也是黃的。他們熱愛土地,在麥田勞碌,魂靈也滲透泥土的芬芳,一雙卑微之手,讓家園山清水秀,風生水起。
他們像小麥一秋,看一朵花的盛開與凋謝,一輪太陽的升起與落下,一只鳥的遷徙與回歸,不覺,已是經年。
最后,也像小麥一樣,倒在歲月的鐮刀下,生于泥土,又歸于泥土。

水墨 劉國強
爺爺也是這樣。歲月,是一把無情的鐮刀,割去了他成熟的生命。那葉犁鏵,離開了爺爺,也就離開了泥土,銹跡斑斑,一副老淚橫流的模樣。
人,真的就像小麥,歲月的鐮刀割去一茬,就又瘋長一茬。年年都有人,相繼離去,愈走愈遠。新降生的生命,也呱呱落地,村子并不見荒蕪。
離去的人,像小麥倒在了歲月的鐮刀下,而孩子身上,有剛剛發芽的新鮮氣息。
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
在輪回中,生命永遠鮮活。就像爺爺走在田埂上,我跟在他的后邊,像甩不掉的尾巴。
3
我離開了村莊,那時的我,是綠油油的小麥的模樣。
而爺爺和犁鏵,在我的生命里,漸行漸遠漸無書。
當生命的犁鏵,掀起蜇伏的離愁,思鄉的心如河流,千迴百轉,流淌出一條思鄉之河,流淌著一個尋找家園的靈魂,那人,那小麥,那迷人的村莊,總在魂牽夢縈中。
殘日余暉里,一個人,對著遙遠的天空,心,撲棱棱就飛到了村莊。
村莊,是我人生的起點,也是我精神的歸宿和終點,如果做了失根的蘭花,漂流的浮萍,飛舞的秋蓬,因風四散的蒲公英,我將何處寄托自己的靈魂?
村莊,那是一片只能用心靈觸摸的土地,是我精神和物質上的圣土。天地萬物,一榮一枯,就在不斷的變化更替中,該消亡的消亡,該孕育的孕育。麻雀、谷粒、辭句、陽光與渴望,都是村莊的客,只有土地,才是村莊的主人。
我的生命,是思索與尋找的宿命,它來自村莊,也必將在村莊老去。我的根,深深扎在魯西南的平原,那里是無限美好的精神家園,那里有我童稚的歡樂、有淳厚的鄉情,更有我對生命最樸質的認識和理解,一滴水,就讓小麥有了蔥蘢;一把犁,就讓爺爺的腳步有了方向。
4
我的靈魂,是犁鏵在引路。我把目光,投向田間耕作的黃牛,投向河流繞過的蘆葦蕩,投向落日下的裊裊炊煙,就像一只麻雀,始終不曾遠離曬谷場上的小麥。爺爺的犁鏵透射著我的靈魂。一部犁鏵,可以把耕耘融入生命,可以消磨一個人的一生,也可以打磨一個人的一生。犁鏵,將我和爺爺的生命,深深地連在了一起,兩株小麥,沸騰著犁鏵的熱血,走著相同的路。我無數次在紙上耕耘,把犁鏵,深深地插入泥土,試圖犁過整個春天。我的文字,寫著土里土氣的夢 想,犁鏵閃爍著金色的光芒,穿透泥土,穿透季節,穿透人生和思想。
我的筆尖,注定是倔強的犁鏵,注定躬耕家園的幸福,去尋找生命的依附和歸屬。
家園,如正午的陽光,在我的心中漸漸地濃縮。濃縮了,便落在異鄉,落在筆尖下,落在心里最柔軟的地方。
一片淳樸的土地,在前方守候。我靜坐城市一隅,筆尖,如犁鏵破土,要開墾出一片繁花勝景。
山水走筆
1
生在平原,長在平原,山水常牽絆我的思緒和想象,把我引向蜿蜒的小徑,潺潺的流水,氤氳的云霧和蒼翠的峰巒。
一條蜿蜒小路,被野花熏得醺然,七彎八繞地盤旋向上。千巖競秀,草木飽蘸著蒼黛色,涂抹在藍天白云下。細長的樹枝,從石隙中伸出手,去摘陽光。小舟劃過,一滴水滴撞著另一滴水滴,一浪推著一浪。水波瀲滟,像最醇的青梅酒。
郭熙在《林泉高致》論山水時說:“山以水為血脈,以草木為毛發,以云煙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華,得云煙而秀媚。水以山為面,以亭榭為眉目,以漁樵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漁樵而曠落。此山水之布置也。”
你看,水在山之上為云,山之巔為雨,山之峰為霧,山之澗為泉,山之壑為岫,山之峪為嵐,山之崖為瀑,山之根為潭。水繞著山,山依著水。山因水的滋潤而生機勃勃,水因山的呵護而空靈多姿。
抬頭見山,低頭見水,胸襟豁然,視覺上的無所羈絆,能漸化為心靈的開闊和舒展。
2
山和水,是大自然中兩種迥然不同的形態。
山執著挺拔,志存高遠,簡潔是山的風格,它拔地而起,志在青云;水,暢達柔順,智在深遠。勇往直前,是水的個性,它漫地而游,遼闊浩瀚。
山在淡泊與寧靜中蘊含著深深期冀;水在自然與隨意中隱藏著默默追求。
山是靜止的書,可以培養人的細致和耐性;水是流動的書,可以培養人的靈活和敏銳。
上善若水,無際惟山。兩種形態顯示了兩種生命本質。
山,青云直上;水,迂回滲透。頂天,是山孜孜不倦的追求,并憑執著挺拔表現力度;立地,是水忠貞不渝的理想,且借暢達柔順顯示智慧。山性深邃卻明朗曠達,像極了仁者的不移;水性沉靜卻奔流向前,啟迪了智者的不息。山的哲學意味著仁厚,水的哲學意味著機智,所以,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其實,山和水是一種互補。
山孕育著水,水滋潤著山。山因水而常青,水因山而長流。水瘦,山則窮;水秀,山則明。出山,水則濁;在山,水則清。
林則徐寫過一副寄情于山水的自勉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林則徐的追求是又有水,又有山,既智且仁,既柔且剛。
山無言而壁立千仞,是為無際自高,無欲則剛也。水無形,其至柔而克剛,上潤天,下澤地,其性至靈至堅也。
“人生如山似水。”山使人淳厚,水使人靈秀。人,要既有山的風格,又有水的胸懷。
仁智相輔,剛柔相濟,才更為美妙。
3
山水,賦予了文人不竭的靈感源泉。
謫官隱者,遷客騷人,以山光水影涵容閑情逸志、沉浮悲歡。登高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水,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云之色,其意趣發乎胸臆之中,流乎毫尖之上,溢乎紙絹之外,神韻無窮。地上之山水,畫上之山水,夢中之山水,胸中之山水,三尺絹絲,一方素箋,醇醪的墨香四溢,皴擦點染,濡寫勾畫,收千里于尺幅。地上者丘壑深邃,書上者筆墨淋漓,夢中者詭譎變幻,胸中者舒卷自如。
文人,通過讀山品水,領悟世事的興衰變遷,尋覓精神家園,在盈然中找到自我。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以“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抒發掙脫塵世牢籠回歸田園的自然真淳,臨山恍然,悠悠道出:“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王維在山澗、在松林、在月下、在搖曳的篁竹聲里,尋覓自己靈魂的皈依,深有會心:“興來每獨往,盛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杜甫在春暖花開之季欣賞山水田園景物時,欣然揮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李白卻欣欣自許:“問余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柳宗元被貶官到永州后,也常以山水自娛,到處搜奇攬勝,因山水想得意詩文,寫成著名的《永州八記》。
徜徉于名山大川之中,山可樵,水可漁,藏納于胸,無酒亦當歌。
“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欲問行人去哪邊,眉眼盈盈處。”詩化的山水,就這樣在人心中延綿熨帖了千百年。
4
山水,是中國文人情思中最為厚重的沉淀。
山水,如果沒有卷帙浩繁的詩文作墨,那將是如何的蒼白?
一折山水一折詩,山水隨詩入畫屏。把一卷卷山水詩詞畫軸展開,漸漸鋪展出一條幽深蜿蜒的旅程。
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三峽如果沒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名句,魅力要大打折扣。一片山水,一個地方,只有和文化共生共融,才會顯現出鮮活的生命,蘊含無窮的韻味。
依山走筆,隨水流墨,其實是人在山水之間,在美好的文字之間旅行的過程。
宋代禪宗大師曾提出參禪的三境界: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禪中徹悟,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胸藏丘壑,城市不異山林;興寄煙霞,閻浮有如蓬島。就如,真正的平靜,不是避開車馬的喧囂,而是在心中修籬采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