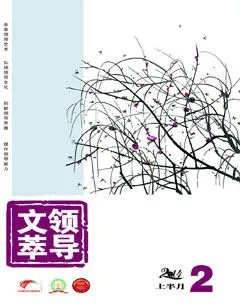我們需要怎樣的交流?
蔡如鵬
知識分子常常不是一個思想統一的階層。就知識界分裂和言論戾氣的話題,知識界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學者江平、杜維明、蕭功秦、許紀霖、魏明倫,對共建理性的言說空間提出建言。
知識界,對于一些最基本的公共話題,似乎完全沒有基本共識。更糟糕的是,在公共平臺上,彼此間的交流充滿戾氣和語言暴力。何以如此?
江平(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我覺得讓知識分子的思想統一是不現實的。但是知識分子應當有自己的表達方式。應當用君子的方式、心平氣和地解決問題,而不是用一些粗魯的方式。
杜維明(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我把學術界、知識界、文化界區分開來,它們的范圍越來越大。學術界的研究越深入,越能不受到外在的政治、商業方面的干擾。這個基礎就成為知識界的認知水平和理性水平。知識界有比較高的水平,文化界的水平就比較好,比較雅。一般的社會都是這樣的。但是,文化的浮躁使得知識界不是很安穩,有很多不健康的情緒,直接影響到深刻的學術研究,我們現在就面臨著這樣一個情況。
許紀霖(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導師):很多話題不能正常討論,而只能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這就使得在表達的時候會產生某種扭曲。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界普遍存在一種戾氣,這種戾氣就是內心充滿著一種不平,這種情緒往往會通過語言暴力顯示出來。
蕭功秦(上海師范大學人文歷史系教授):網絡本身就是一個劇場,它有劇場效應。為了追求這種劇場效應,網民往往會把自己的觀點以最鮮明、最煽情,甚至是最極端的方式表達出來。這種表達能在粉絲中獲得最大的劇場效應,但常把社會上多元化的問題簡單化。簡單化以后就會破壞人們的正常思維,在網絡上人就變得特別簡單化。在網絡上對方就變成一個抽象的符號,抽象地對待對方,就會出現這些問題。
魏明倫(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如今,網絡“約架”,跟我看到的袍哥“教言語”,更和“文革”中的打語錄仗、武斗相似。毫無疑問,這些都是應該制止的。但另一方面,我覺得這又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制止“約架”,但網絡語言暴力是收拾不了的。中國從過去的封閉到現在的開放,網絡有大利也有大弊,人類獲得網絡巨大利益的同時,當然也得為此付出代價。
除了一些客觀原因外,學者個人是不是也應該有所反省?進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識,并改善交流方式?
許紀霖:我發現中國的各家各派普遍相信自己是正確的,自己代表正義,不太善于傾聽不同的意見。我覺得比立場更重要的是你的看法、觀點,而不是以立場和主義來劃線。
江平:現在網上所表現的不同的知識分子之間的爭論,有些已經是屬于缺乏修養。知識分子赤膊上陣,我覺得不太好。知識分子要保持一種知識分子的風度、氣質、語言。在魯迅的時代,再怎么爭論,還是在文章上論戰,不應該以人作為攻擊的對象。所以我覺得對人不應該有成見,對事情可以來論是非。
蕭功秦:中國人的文化思維,從傳統時代到革命時代,都存在兩極思維:正和邪。當一個學者覺得自己是正確的時候,他就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自我優越感,而對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就會定位為道德上的邪惡,采取毫不留情的斗爭的態度來對待。于是產生了一種所謂的斗爭哲學。這種文化思維從傳統時代,到近代、現代,一直長期影響著我們整個的文化。
杜維明:公共辯論,最基本的條件就是必須要突出責任倫理。21世紀我們面臨很多挑戰,有生態環保、有女性主義、有文化多樣性,還有宗教的多元等等,所以在理性之外特別要突出同情,在法治之外還要注意禮讓,權利之外注重責任,個人尊嚴之外還要考慮社會的和諧。
與意見、觀點相左的學者交流,你的交流方式是什么?如果遇到非理性攻擊,會如何應對?
許紀霖:我接觸網絡很長時間了,遇到的非理性評論也很多。這種戾氣我也可以理解,表面上是沖著我來的,其實是把我當作一個符號,當作發泄的一個對象而已。我告訴自己說,在這樣一個不正常的輿論環境里,如果你要成為公眾領袖,一定不要計較這些,這是對自己的一種雅量的考驗。公眾人物付出的代價就是他要有一種心理準備,被傷害的準備。
杜維明:批評有各種不同的程度。對錯對我講起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分析問題的層次,是深還是淺。如果一個人對我的批評很深刻,那我會把它當做一個重要議題來反思。如果根本就是無理取鬧,很簡單,忽視它就是了。
建設一個多元、理性、寬容的社會,從政府到知識界到個人,應該做些什么?
許紀霖:這需要三個方面的努力。一是大環境,需要提供一個自由的、開放的環境。二是每一個參與者要能夠傾聽不同的意見。三是媒體也需要反省,現在媒體有一個不好的傾向,總喜歡有人打起來,然后故意去尋找極端的聲音。今天的媒體和網絡實際上是被市場所操縱的。所以媒體要反省,特別是嚴肅的媒體。
蕭功秦:作為一個正常的社會,不同的多元的思想的對峙和存在是一種正常現象。作為執政者應該把各種思想中的積極因素,吸納到我們的政治愿景當中,實現社會的進步。
杜維明:現在一個新的情況是垂直的關系逐漸變成平行的關系。中國的公共領域長期的情況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大,現在政府已經有意愿要放權。這是要正面肯定的。一個比較進步的、成熟的民主制度,這都是習以為常的,我們正在這樣一個過程中。這個過程需要每個領域,都出現一批有良知有理性的代表。人數不一定需要太多,但公共性一定要強。
江平:我覺得,首先是執政黨要建立一個寬容的氣氛。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每個人也都應該抱著這樣一種心態。寬容是一個社會非常優良的品質。
(摘自《思想理論動態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