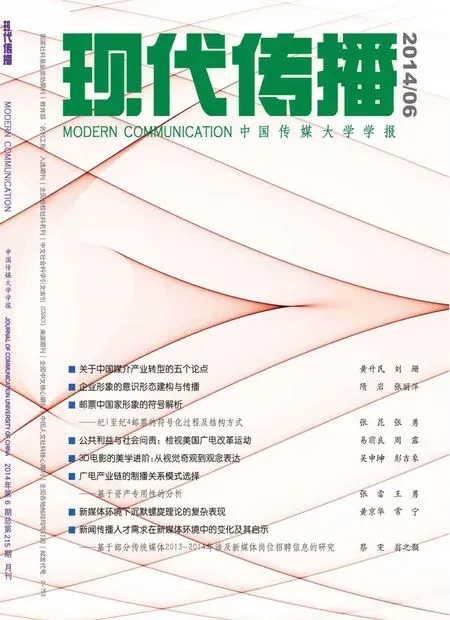演變、轉向與趨勢:新媒體時代下的中國傳播學研究
——中國傳播學會2014年年會暨新世紀的中國傳播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李春雷 陳瑞華
演變、轉向與趨勢:新媒體時代下的中國傳播學研究
——中國傳播學會2014年年會暨新世紀的中國傳播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李春雷 陳瑞華
2014年4月17-18日,由中國傳播學會主辦、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承辦的“中國傳播學會2014年年會暨新世紀的中國傳播學學術研討會”在江西南昌舉行。來自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澳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新聞傳播院所的100多位學者參加了會議。圍繞“新世紀的中國傳播學”年會主題,學者從“中國傳播學學科發展前沿”“新媒體與社會治理”等議題切入,以主題發言、專題講座、專場報告及分組研討的形式進行,形成對當下傳播學研究現狀的系統闡述。隨著新媒體技術催生傳播新事物、新現象、新問題的不斷涌現,如何重新定位傳播學科的社會角色與功能,成為與會學者討論的核心話題。在此次年會中,學者對傳播研究旨趣演變、范式轉向與未來趨勢所做的梳理與反思,不僅是對當前問題的現實應對,更是對中國傳播學科未來發展圖景的勾勒。
一、新媒體語境下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演變
新媒體作為技術存在、社會存在與思維存在,對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與組織結構已然構成深刻影響。上海大學戴元光教授認為,我們現在正處于社會變動的時代,面對不斷創新和變化的研究對象,新媒體將成為人類生存、生活的基本維度,而把新媒體與傳播學有機結合將是全新的研究方向。清華大學熊澄宇教授則認為,新媒介生態已經導致傳播方式的演變與重構,人們對媒體屬性認識由耳目喉舌到人的延伸而不斷深化,媒體自身從新聞媒體向大眾媒體的轉化亦導致傳播內容的分化與深化,傳播方式則由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分眾傳播、交互傳播發展到沉浸傳播,這推動了傳播學理論的思考與創新。易言之,新媒體傳播的交互與共享、沉浸與遙在促使研究者進行反思,傳統傳播學理論已不能適應新的傳播生態,傳播學研究的演變成為必然。
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不斷變化的角色使媒介自身常處于沖突和矛盾中。浙江大學邵培仁教授認為,媒介角色沖突主要體現在媒體事業性與經濟性、行政性與獨立性、政府喉舌與公眾代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中。新媒體語境下,媒介作為政府喉舌與公眾代表的角色沖突愈加明顯。以社會群體性事件為研究對象,上海大學許正林教授發現,微博作為政治表達的新空間正在形成,改變了媒介話語權結構,政務微博、傳統媒體微博、公民微博分別構建政治、媒體、民間三大輿論角色。然而,角色話語博弈容易出現群體極化現象,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現實扭曲的表現。面對新媒體角色沖突的現實困境,促使我們審慎思考新媒體環境下的媒介角色定位。同時,如何調試新媒體時代下媒介角色平衡亦成為急待要研究的新問題。
新媒體改變了傳統信息傳播與共享方式,在更大范圍內實現信息平等與自由。面對新媒體帶來的信息傳播的變化,北京大學陸地教授提出“信息共產主義”概念,認為“信息共產主義”具有人人平等、集體共創共享、信息生產極大豐富、按需分配等特點。當然,新媒體不只促成傳播理論、研究方法、媒介角色的演變,媒介文化演變亦是重要部分。山東師范大學張冠文教授等發現,互聯網信息消費模式對人們行為與價值體系變化、人與社會關系變化、社會思潮與格局變化有重要影響。同時,新媒體和社會文化的解構與重塑之間具有較強關系,中國傳媒大學耿益群副教授等通過探究大學女教師網絡形象的塑造過程,發現網絡媒體存在的問題是導致教師形象偏離的主要原因。
二、新傳播生態催生傳播學研究范式轉向
中國社會已進入關鍵調整期,社會環境的改變促使社會科學由問題研究向社會秩序和社會技術轉變,天津師范大學劉衛東教授認為,傳播學研究首當其沖。傳播學作為平臺態勢將開啟極具實踐操作意義的傳播學學科轉向,即對社會失調、失序、失態、失衡等問題的研究。大眾傳播研究對上述社會問題與傳播現象的思考,彰顯了傳播學研究向新秩序建構、傳播心理調適等范式的轉移,新媒體下社會權力結構去中心化則加速了該轉向。當代中國傳播學研究的時代背景和研究趨向契合了傳播學科轉向,成為構建新社會秩序和規則的重要參照。若以哲學角度思考,傳播學問題研究向秩序建構的轉型呈現“第二哲學”特點,這將成為解釋人類社會普遍問題的傳播觀和方法論。
復旦大學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和深圳大學吳予敏教授以“網絡化社會:中國傳播研究的轉向”為話題,對處于雙重壓力下的中國建制化傳播研究進行專場報告,并以此推動中國傳播學研究的范式創新與轉型。孫瑋教授從傳播主體的視角出發,認為可在兩個方面拓展現有的傳播研究:一是將“傳播”意義擴大,整合、打通傳播學與其他學科隔絕狀態,以增強傳播研究的解釋力;二是開啟被既有傳播理論遮蔽、忽視的諸多研究路徑和議題,如空間、身體及場所等研究路徑。吳予敏教授則發現,當移動互聯網全面進入人們生活后,長期以來沉陷在封閉性很強的“無形的網絡”研究轉向對“強關系”“弱關系”及“結構洞”的分析,如何認識中國式網絡化社會的特點和走向,將成為傳播研究的探尋目標。
黃旦教授認為傳播技術突然進入萬眾矚目的中心,新傳播讓我們反思以往關于媒介的種種理解,重新理解媒介成為傳播研究轉向的關鍵所在。網絡化社會作為嶄新的社會形態,不是以往媒介功能的簡單擴大,媒介認識要跳出工具和功能思維走向關系展現視野,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媒介。謝靜教授以社區傳播為切入點,探討了網絡化社會的復雜連接機制,認為網絡化社會促使傳播學界重新思考各種社會機制與傳播的關系,進而倒逼對傳播本身的反思,推動傳播研究范式的轉向。廖圣清教授則認為大數據、公共傳播構筑了中國傳播研究的新環境,傳播研究需要借鑒新興的(復雜)網絡科學視角,從網絡結構、內容和演化(行為)三個層面對(新聞)傳播領域展開實證研究。
三、中國傳播學發展相關問題及未來趨勢
中國傳播學發展過程中亦出現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鄉村政治傳播在新媒體時代的困境。南京大學鄭欣教授等通過對“送法下鄉”的研究發現,當前鄉村社會法律傳播所慣性依賴的組織渠道形同虛設,并認為農村法律傳播需要立法、司法、行政及民間組織和民間活動等共同努力、改進和創新。江西師范大學邱新有教授等則通過詳盡的案例分析,對民間新聞發布會做了勾勒和描摹,對鄉村社會的信息傳播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上海大學陶建杰副教授通過對新生代農民工信息渠道使用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發現感知易用是最基礎因素、感知有用是最重要因素、使用態度是最直接因素。可見,在新媒體時代下如何提高農村地區傳播效果、促進傳播平等仍面臨諸多難題。
媒介化社會對民眾的社會心理和認同有著重要影響。以社會認同為例,浙江大學洪長暉以湖南桑植白族為調研對象,發現白族存在不同程度的認同斷裂,但以媒介實踐為“軟資源”又在散居情景下重建起作為白族族群的身份認同,“斷裂與接續,成為該民族社區的認同再造的媒介實踐”。毋庸諱言,民眾的社會心理和認同又影響著社會穩定。澳門大學助理教授林玉鳳等通過對澳門幾起公共事件的調研發現,網絡媒體對“官商勾結”“忽視民意”與“公民抗爭”關注遠高于傳統媒體,引起民眾更為強烈的反應。江西師范大學李春雷教授等通過對昆明PX事件的實地調研也發現,新媒體對底層知識青年的記憶打造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不僅能加深底層知識青年與基層政府的群際裂痕,甚至形成對傳統媒體的逆向解讀。
面對現實問題,新聞傳播的理念改變與媒介批評建構等,成為學者策略探討的重點。重慶大學董天策教授從網絡群體性事件出發,認為該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是要突破剛性維穩的思維方式,轉換成探討民主協商式的“公共治理”理念與舉措,從而最終推進當代中國的社會管理創新。對于中國媒介批評方法,上海大學郝雨教授等認為,符合中國媒介批評語境的理論體系尚未確立,而該體系可從中國古代文藝批評特征入手,探析當下媒介批評方法的建構。從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切入,上海建橋學院教師金晶等認為,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傳播學研究理應用來解決中國信息傳播中的現實問題,從而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陜西師范大學裴曉軍副教授認為中國傳播學研究應將社會關系理論引進,可從微觀層面探求受眾與媒介之間的依賴機制,從而調適兩者關系。
四、中國傳媒產業的問題闡述與對策思考
新媒體在業界的繁榮促使學界對其加強研究,學者利用傳播學理論與視角理解并分析傳媒產業成為重要學術的現象。中國傳媒大學《現代傳播》編輯部張國燾主任以“云電視”為研究對象,對當下最為前沿的云電視做了深入剖析,認為其已經成為最激烈的企業戰場,并將在未來成為家庭云生活的中心。他在理論上亦對“電視將死”進行了反駁,電視媒介所擁有的技術紅利、意識形態優勢、技術的完善性、具有的專業性及版權資產都是其未來保持生命力的元素。同時,新媒體的出現對傳媒版權也構成了危機。上海大學鄭涵、趙為學教授以互聯網時代下歐美傳媒產業制度轉型危機為例,認為傳媒新技術與龐大的版權業為人們盜版行為客觀上提供了便利,而社會信息化、休閑化、娛樂化等又從文化需求及其實現方式上推動了盜版浪潮。
新媒體的快速發展與擴張,亦使新媒體運行混亂、內容失控等現實問題日益凸顯。深圳大學李明偉副教授等運用長尾理論對網絡廣告長尾市場進行分析,總結出網絡廣告長尾章魚、蜘蛛、解股模式,并在此基礎上提出網絡廣告長尾治理的制度建議。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任慧博士等基于新媒體語境,深入剖析媒介內容生產與治理機制,在知識治理理念下創新性提出媒介內容治理策略。河北大學陶丹從韓國政府經驗出發,認為我國可采取“倫理教育”與“法律制裁”相結合的方式對媒介內容進行治理,并與經濟制裁、心理治療以及實名制等措施形成綜合防治體系。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新媒體時代下傳播學研究具有反思意識、問題意識,但仍未形成當下傳播學的系統學科譜系。面對社會轉型與媒介化時代的到來,中國傳播學研究唯有銳意進取,確立自身研究旨趣與范式,才能適應本土化問題的導引、秩序的建構,也才能提升中國傳播學研究在國際平臺的話語權。
(作者李春雷系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陳瑞華系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國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