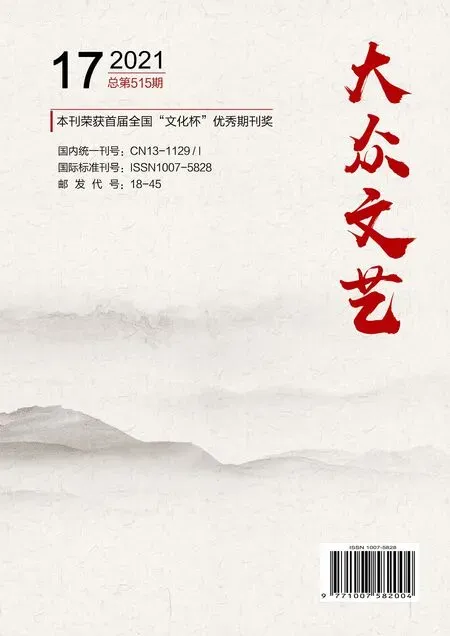論音樂作品中情感性內容的表現
——以聲樂作品《昭君出塞》為例
孫海露 劉子殷 (西南大學音樂學院 404100)
一、音樂是情感表現的藝術
作為中國儒家音樂理論專著——《樂記》,它對音樂與情感的不可分性作了如下論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我們都知道,音樂是人類聽覺系統的聲音效果,造成不同感受的觀眾會產生不同的情感體驗。每個人在生活中必然會產生“哀”“樂”“喜”“怒”等不同的感情,在音樂音響的作用下,人的情感與音樂引起共鳴,產生不同的情感。在這一點上,中外學者都有著類似的體驗和感受。前蘇聯音樂家萬斯洛夫認為,“音樂是一切藝術最接近抒情的”。亞里斯多德認為,“樂調能反映出憤怒和溫和、勇敢和節制以及一切相互對立的品質和其他的性情”。這意味著,與其他藝術比較,在表現多樣性方面,音樂最先是由情感來表現的。我國音樂理論家于潤洋認為,“音樂內容主要是情感內容”。
聲樂作品《昭君出塞》是以歷史故事“昭君出塞”為題材、吸收西方音樂藝術并大膽運用現代作曲技法。這首作品拓展了民族聲樂的表現形式,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傳承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作品中如何表現情感
《昭君出塞》全曲共101個小節,ABA的曲式結構,由d羽調式轉到d商調式再到d羽調式。從歌詞的意境來理解作品:第一部分是序曲,對昭君離開家園的敘述;第二部分是昭君到達匈奴,受到匈奴人民熱情接待,載歌載舞的場景。后面9個小節的“啊”反映出了昭君的內心情感;第三部分是后人對昭君的評說。
音樂是一種處于動態中的音律表現情感的藝術形式。在第一部分中,旋律莊重而深刻,描繪了昭君離別故土的悲痛哀怨之情。前奏一開始就由慢漸快,音越來越密,力度是由弱到強,婉轉的曲調仿佛一下把我們帶到了西漢時代,在前往匈奴的途中,眼前都是戈壁荒漠,人煙稀少的情景。隨著音型越來越密,力度越來越強,突然弱下來,停頓之后,開始模仿起琵琶的聲音慢起漸快,輕起漸強,用最大的音量奏出主旋律。(見譜例1):

音樂與情感是在時間中伸展變化的,二者在運動形態上都存在著上下的起伏、張弛的節奏、力度的大小和色彩的濃淡。這種同構關系為音樂以類比或比擬的方式,模擬和刻畫人物情感活動提供了可能。如第一部分中節奏模仿車輪在行進中發出嘎吱嘎吱的聲響。(見譜例2):

又如第二部分轉到了d商調式,節奏熱情歡快,旋律富有內在動力,表現出一個熱鬧的場面。表現出昭君到那兒后受到了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第一段結束之后,緊接著一段間奏以熱情奔放的快板表現出歡快的氣氛和少數民族比較粗狂的性格特征。這種歡快的節奏,把昭君離別的愁苦心情沖淡。
音響刺激能夠引起興奮度、強度、緊張度的變化,從而引起相應的情緒。音樂可以直接使人產生情緒體驗。表現情緒的能力是音樂超越其他藝術形式的獨特價值所在。而情感中的認知部分并不是音響直接作用的結果,而是聯想的個人經驗和想法喚起情感體驗的產物。
如第三部分中,結構相比前兩段來說稍顯短小,材料在第一部分第二樂句的基礎上作了變化,層次分明,表達了人們對昭君出塞的無限感慨。這部分情緒達到了高潮,音域寬廣,力度達到最強,伴奏織體采用柱式和弦以及八度進行。
三、情感表現的特點
正如人的情感有喜怒哀樂之分,音樂表現的情感也有不同。聲樂作品《昭君出塞》是根據歷史題材創作的一首敘事歌曲。詞曲家經過長期的推敲、斟酌,將自己勾勒的畫面與深刻的情感體驗反映在作品中,把王昭君不惜犧牲自己終生幸福促成民族團結統一,將這樣一段歷史佳話用音樂表現得淋漓盡致。
不同時代及民族的音樂在表現情感上有著相似之處。而在音樂語言和表現方式上又有著鮮明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在不同的音樂傳統中,形成了各自的表現方式。他們在音樂創作活動中,積累了完全不同的經驗。
《昭君出塞》蘊含著豐富的民族精神,詞曲家將其進行再創造,在尊重歷史事件的基礎上,賦予王昭君以當代人的精神,使之意蘊深遠。他鑒戒并吸取了西洋創作理論更好的塑造人物,將敘事、抒情、戲劇完美結合,增強了歌曲的戲劇性效果。他將傳統的歷史題材與現代作曲技法相結合,加強了歌曲的藝術性,使演唱者的表現力更加豐富。《昭君出塞》中塑造的王昭君的藝術形象,將其提升到另一個高度——“慷慨越千年”,與當今社會提倡的和諧發展的遙相呼應。
四、小結
通過對 《昭君出塞》這首歌曲創作和演唱的分析,可以看出:音樂與情感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情感是音樂出現、發展和推動的源動力,音樂因情而生;另一方面,情感通過音樂表現出來應該是自由的、充分的。只有音樂才能完成情感的一系列抒發及表現。二者缺一不可、相輔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