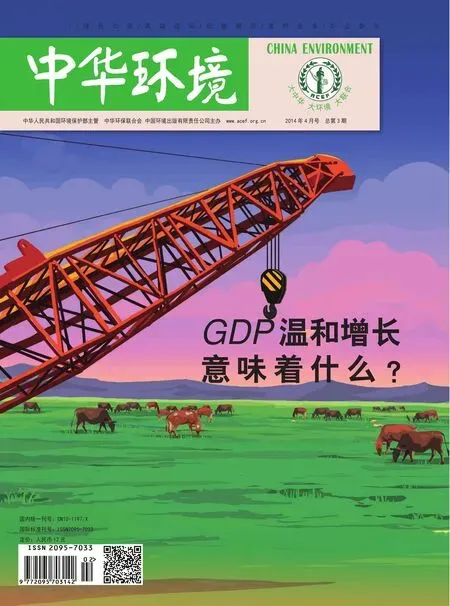解讀環境污染里的經濟賬
周贏
解讀環境污染里的經濟賬
周贏

2013年 4月16日,一場強沙塵暴襲擊了新疆塔克拉瑪干盆地。CNSPHOTO/供圖
進入21世紀,人類進入了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中國粗放式經濟增長所快速創造的GDP,雖使中國人遠離了“饑餓”與“貧窮”,但是自然資源的消耗、清潔環境的減少、生物多樣性的降低、沙漠的擴大化,又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曾經唯GDP的發展模式。我們今天分享了許多發展成果,卻大大降低了環境福利,“一切向錢看”的思想,使我們偏離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平衡點。此時此刻,我們必須使用經濟工具來度量環境污染所付出的代價,找出我們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差距,用更加專業而有效的方式來解決本土的環境問題。
以出口導向式的投資拉動經濟,用資源和環境的過度替代增加GDP,這種低含金量的GDP增長,早就該改變了。
治理投入能否拯救中國環境?
為了將中國從霧霾的困局中解救出來,國務院于2013年9月發布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即國十條)。據悉,“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行動計劃”將陸續出臺,以應對中國目前遭遇的環境危機。
權威人士分析稱,在三大行動計劃中,大氣污染防治國家將投資1.7萬億元,水污染防治將投入2萬億元,土壤防治投資也將達到10 萬億元。據計算,上述三項環境污染治理費用的總和接近13.7萬億元,約為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24%。這個驚人的數字,被很多人解讀為中國經濟發展犧牲環境所付出的代價。
也許我們并不愿意承認,中國步了西方經濟發展的后塵,走了一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治理環境即將付出的高昂費用,已經給我們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亮起了紅燈。
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王玉慶曾向媒體表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世界銀行、原國家環保總局以及一些科研單位曾經分別做過研究。環境損失(財產性損失和健康損失)占中國GDP的比重少則為3%至4%,多則達到11%左右。這兩年沒進行過相關研究,據估計,環境損失占中國GDP的比重可能達到5%–6%。2011年中國GDP為47萬億多,據此折算,環境污染造成損失將達到2.35萬億–2.82萬億元。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將近14萬億元的資金能否拯救中國的環境?
北京大學環境與資源經濟學系主任曹和平教授在接受《中華環境》采訪時表示,關于環境污染的計算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環境污染成本計算包括過程成本和結果成本。“國十條的投入到底是環境投入的一次性成本,還是一次性財政成本?這值得我們搞清楚。實際上它是環境成本中極小的一部分。”曹和平說。
政府部門的預期投入為何是環境成本中極小的一部分?曹和平解釋道,在霧霾天里,霧霾會對人的肺部和身體其他方面造成傷害,這些成本一部分反映在疾病治療的賬單上,絕大部分反映在肺功能衰退和壽命的降低上。對于那些科研和腦力勞動者而言,在高度抽象思考的時候,工作時間可能由原來的8個小時變為6個小時。對于孕婦, 由于難產概率的增高,那么孕產成本就會增高。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這樣的天氣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夫妻爭吵。所以,過程成本非常高。
從GDP的內涵看,經濟學家常常從總需求、總投資、政府支出、進出口等方面進行分析。由于政府支出只是GDP構成的一小部分,所以政府即將支出的治理資金,僅僅是環境污染治理成本的一小部分。
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曾做過相關研究。研究認為,環境污染每制造1塊錢的利潤,卻要花60塊錢來治理,還要花15塊錢去看病。因此,制止環境污染的發生最省錢,污染后才想到治理最燒錢。
“實際上環境惡化會使我們掉進泰勒定義的惡性循環。即環境越壞,污染越嚴重,治理費用越高。”曹和平說。
除此之外,曹和平還對資金使用的效率表示出相當的擔憂。
他表示,霧霾是顆粒性大氣污染,可國十條卻沒有對此進行明確描述。1.7萬億元的治理資金是否符合大氣污染治理的實情,有待檢驗。
2008年,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中國政府出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硬生生地把經濟從衰落的懸崖邊緣拉回。與此同時,有關“4萬億”的各種非議接踵而來。
經濟學界中對此最先持保留意見的是馬光遠,在他看來,4萬億讓中國經濟在結構調整和轉型等方面的計劃被推遲,同時推行的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推高了物價,形成了資產價格泡沫。
向污染宣戰,體現了國家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表明了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堅定決心。但是面對國家如此之大的投入,我們能否吸取此前的教訓,各個相關職能部門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支配方式能否順暢而有效,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地探討。
能源消耗下降能否擠掉經濟虛火?
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工業增長仍然過度依賴物質資源的投入,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會長李毅中曾表示,2012年中國一次能源總消耗折36.2億噸標準煤,約占全球的21.3%,單位GDP能耗是國際的2倍,是發達國家的4倍。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3年我國全年能源消費總量為37.5噸標準煤,相比2012年增速為3.9%。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然而,根據美國媒體的公開報道,中國占世界GDP的比重僅為12%。相關資料表明,中國單位GDP能耗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同時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能源和資源的超常規利用正在制約中國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規劃,使得中國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視我們掉入的發展陷阱。
2014年,李克強總理果斷表示,為治理霧霾,今年能源消耗強度要下降3.9%。據了解,身為中國鋼鐵第一大省的河北,此次為治污提出了5年內削減鋼鐵產能6000萬噸的目標,即砍掉河北省將近20%的鋼鐵產能。一些人士認為這是政府通過宏觀調控擠壓中國經濟發展虛火的表現,是積極的經濟政策。
但曹和平卻給出了另外一個觀點。他認為在擠壓經濟虛火方面,調整產業結構比總量控制要好得多。
“河北省若在一年內,減少1200萬噸鋼鐵產能,雖然對環境起到了保護作用,擠掉了與鋼鐵行業相關的經濟虛火,但是同時也砍掉了好的技術和已經建成的基礎設施和設備。”曹和平說。
今年2月,鋼鐵工業和市場分析公司(MEPS)發布全球鋼鐵產量報告,2013年中國以7.79億噸的粗鋼產量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粗鋼產量的48.5%。根據河北省統計,2013年河北省粗鋼產量為1.9億噸。以此推算,河北省2013年的粗鋼產量占全國粗鋼產量的24.4%,相當于歐洲粗鋼產量的61%,是北美洲的1.6倍、南美洲的4倍、非洲的11.8倍。
顯然,100萬噸的煉鋼爐在總量控制思維導向的影響下,一旦被拖倒,將造成嚴重的資源和技術浪費。這種浪費不僅屬于中國,也屬于世界。
曹和平表示,把資金分給河北,不如讓河北省進行產業轉移,進行結構調整和跨區域的調整。“這比總量控制以降低河北的環境污染要更有效果。”曹和平說。
中國在擠壓經濟虛火的過程中,一定要提高政策含金量。政策與科技同樣重要。

2014年2月27日,河北省霸州市舉行淘汰產能拆除集中行動,對50家排放不達標企業進行了關停或拆除。其中拆除造紙機7臺,淘汰產能1.7萬噸;拆除自制土爐、鍋爐、爐窯12座,年壓減燃煤1120噸。CNSPHOTO/供圖
“像馬達加斯加這樣的國家,沒有一個水泥廠,幾年前還沒有1公里的水泥公路。那邊1噸水泥賣300美元,而在中國1噸水泥才賣300元人民幣。那么為什么不把我們的水泥廠搬到那里?為什么不把產能過剩的行業技術與設備向非洲、拉美、中亞等地方進行產業轉移?”曹和平說。
另外,淘汰落后產能,對當下的GDP影響依然不小。據中國環境科學規劃研究院研究團隊估算,淘汰落后產能將造成GDP減少1148億元,減少非農就業崗位14萬個。
面對總量控制政策可能給河北省發展帶來的不公,曹和平強調,收入補償性的產業轉移優于物理補償性的產業轉移。“河北省應開展基礎能源、重化工領域員工轉業轉產培訓工作,同時啟動環境資源修復工程,讓這些人在這些領域中就業。”曹和平說。
依據經濟學家觀察,在解決中國特殊時期環境污染問題上,經濟結構性調整會比總量控制帶來更多實效,同時也會給社會發展增添更多活力。中國經濟的“綠色化”需要更多前瞻性政策的指引。
正如曹和平所言,中國在擠壓經濟虛火的過程中,一定要提高政策含金量。政策的力量不僅不輸于科技對經濟發展的貢獻,有時候作用甚至會更大。
對于今日中國經濟產業結構的調整,曹和平指出,“單一的國內視野的調整不如全球視野的調整,單一的一個斷面上的調整,不如站在歷史視野下的復合型和體系性調整。”
市場如何控制環境污染成本?
經歷了2013年和2014年的霧霾災難,北京、南京、武漢、濟南、成都、石家莊、烏魯木齊、西安、鄭州被網友公認為是中國霧霾較為嚴重的城市。一份報告顯示,2013年,在被環保部監測的74個城市中,僅有3個城市的空氣質量達標。由于霧霾,一些城市取消了航班,關閉了高速公路,暫停了學校課程。
面對環境危機,如果政府僅僅依靠行政干預和有限的治理資金,去拯救供給14億人分享的環境,似乎難當大任。
經過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和要素配置中已經和正在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明確提出今后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即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對環境資源實行有償使用,通過市場配置環境資源,應成為我國環境管理的重要方向
有關研究表明,政府治理環境的經濟手段如果能以市場為基礎,采用間接宏觀調控改變市場信號,通過利益導向來改變和驅動環境污染者的行為,而不需要全面監督和檢查對象的微觀活動,可以大大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
現在,一些企業擔心履行環境責任后,提高生產成本,拉升產品價格,而失去市場競爭力,惡意偷排漏排。扭曲的激勵機制直接導致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環境成本的失控與膨脹,并大大增加了政府對環境管理的難度。
針對這種現象,曹和平認為,應該在市場中引入“審計模式”。這種審計,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審計”,而是像抽查酒駕一樣的審計,即抽查企業的排污行為。一旦發現企業排污,立刻讓它停產。
“另外,我們還要建立可交易的排污權市場,這是更有效的辦法。”曹和平說。
所謂排污權交易,是指在一定區域內,在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超過允許排放量的前提下,內部各污染源之間通過貨幣交換的方式相互調劑排污量。它是以市場為基礎對污染物排放進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種經濟手段。目前我國已有20多個省份開展了排污權交易政策試點。
排污權交易制度所形成的“倒逼”效應,能夠讓市場更靈活地防止“搭便車”式的環境污染行為。
“假設火電廠每年排污量為200萬噸,在政策要求下預期每年降低1%,20年降低20%。那么火電站就不得不向水電站購買排污權。與其支付高額費用購買排污權,倒不如自己建水電站。”曹和平這樣解釋排污權交易對企業主動履行環境責任的作用。
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在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各個利益主體自然會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根本上對經濟發展起到調節作用。
在曹和平看來,環保部門僅僅向排污企業收取排污費,是一種失誤。
“產值達到百萬元以上的企業都應該具有排污權,按照1元錢1個點計算,就是100萬點。不排污的企業不減點,污染的企業就減點。這樣,從生產到消費,從工藝部門到環保部門,從底層企業到超大企業,從里到外,全民都可以對排污權益進行交換。一年的交易量能達到120萬億–250萬億。”曹和平說。
對排污企業進行懲罰性收費或獎勵來控制污染、保護環境,可有效地減少環境污染行為,更為合理地配置稀缺的環境資源。英國福利經濟學家庇古早在上個世紀就如此論述了經濟對環境污染治理的功能。
從全國范圍來看,數量大、規模大、自發型的排污權交易案例還較少,已有典型案例中實際的交易量主要以SO2和COD排污權為主,氮氧化物和氨氮交易較少。但總體上看,我國排污權交易探索正在逐步深化。據財政部消息,下一步將在全國范圍內推動建立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相關部門聯合起草的工作指導意見已上報國務院辦公廳。
“預防重于治理。”這是曹和平給予環保工作的中肯建議。
由此可見,做事后諸葛亮,計算環境污染的經濟賬,倒不如運用科學手段,事先對自然資源價值進行評估,以提高政府、企業、公眾對環境資源價值的認識。做環境污染的討伐者,倒不如做防御污染的參與者。以市場為媒介,通過經濟手段治理環境,提高企業履行環境責任的意愿,防止環境領域出現“公地悲劇”。這可能才是中國未來從根本上解決環境污染問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