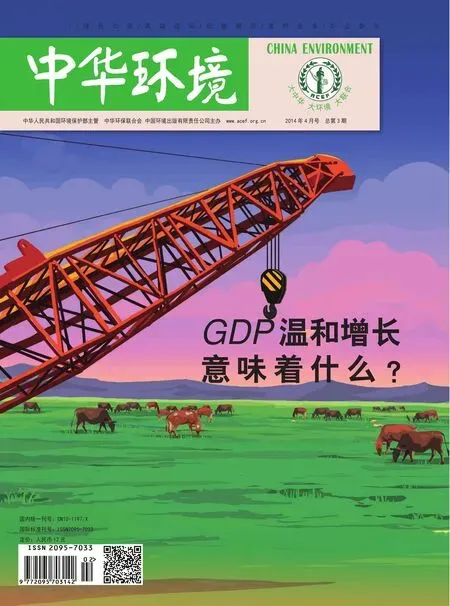守住自然保護的生命線
周贏
守住自然保護的生命線
周贏
我國生態退化已經導致生物多樣性衰退,環境自凈力降低,水資源匱乏,沙塵暴、沙漠化、石漠化、泥石流、霧霾等極端氣候現象以及自然災害日益頻繁出現。每年因為生態退化導致的GDP損失數以億計,嚴重制約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進程。
黨的十八大從“五位一體”總布局的高度提出了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劃定生態保護紅線。這是繼“18億畝耕地紅線”之后,另一條被提升為國策的紅線。其目的就是減少大規模、高強度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開發,遏制生態系統不斷退化的趨勢。
江西、內蒙古、廣西、湖北已被環境保護部列為試點區域。不久前,深圳、江蘇、天津已經率先劃定生態紅線,2014年劃定生態紅線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全面開展。
牢牢把握生態安全底線
今年1月,環境保護部發布《國家生態保護紅線——生態功能基線劃定技術指南(試行)》,標志著生態保護紅線劃定工作進入全國整體推進階段。
1997年,《中國自然保護區發展規劃綱要 (1996—2010年)》
2008年,《全國生態功能區規劃》
2010年,《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
2013年,十八大公報提出建立生態紅線
劃定生態紅線是推進生態文明頂層設計的重要內容,對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自然資源保護意義重大。“生態空間格局的安全和生態系統功能的維護需要紅線來調控” ,環境生態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金鑒明說。
然而劃定生態紅線并非易事。一些環境界學者擔憂,后續的巨額資金和法律制度等能否跟得上?地方政府對紅線劃定的認識和決心又當如何?紅線的劃定范圍、技術流程如何界定?金鑒明也曾經向媒體表示過,如何促使紅線落地是擺在面前的最大難題。
環境保護部根據生態保護紅線提出的背景與發展過程,兼顧資源、環境、生態三大領域的重大問題與保護需求,提出了構建以生態功能紅線、環境質量紅線和資源利用紅線為核心的國家生態保護紅線體系。 有關專家也認為,生態紅線至少要保護三個重要方面,即保護重要的生態功能區、保護生物多樣性和保護生態屏障。
2013年7月,國家林業局啟動生態紅線保護行動,該行動劃定林地和森林、濕地、荒漠植被、物種四條紅線,要求全國林地面積不低于46.8億畝,森林面積不低于37.4億畝,森林蓄積量不低于200億立方米,濕地面積不少于8億畝,治理宜林宜草沙化土地、恢復荒漠植被不少于53萬平方公里,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區嚴禁開發,現有瀕危野生動植物必須得到全面保護。
顯然,保護自然保護地必將在生態紅線落地上發揮重要作用。 在2014年全國政協會議上,一份《關于加強自然保護地管理,有效保護生態紅線》的提案,就提出“守住這些紅線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建立自然保護地”的建議。
直面自然保護地危機
“自然保護地”是國家依法予以特殊保護和管理的各種自然生態區域的總稱,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包括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水源保護區、地質公園、水利風景區、自然保護小區等。過去30年,中國已經建立各類自然保護地8000多個,占陸地18%,涉及2600多個自然保護區、近千處風景名勝區、2700多處森林公園。可以說我國自然資源保護取得了不少成績。
然而我國的自然保護地面積雖大,分布格局卻嚴重不均衡。“我國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護區數量僅占保護區總數的5.8%,面積幾近80%,絕大部分位于西部和北部。海岸灘涂濕地的自然保護地覆蓋率非常低,不足3%,河流自然保護地更是聊聊無幾。”中國科學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說。
此外,一些民間調查顯示,我國不少自然保護區管理水平較低,保護地內各種人類活動無法得到有效控制。“我國的自然保護區雖然數量與年俱增,但不斷被經濟開發和工程建設項目調整、瘦身以至瓦解,有效性不斷降低,保護價值和科學價值正在喪失,一些重要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臨解體的危機。”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國家林業局高級工程師沈孝輝說。
可見,我國自然保護地的保護工作還處于“治理與破壞”相持階段,保護區的發展和建設處于搶救性保護階段。自然保護網絡還不能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
加強自然保護地立法
在2013年中華環保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年會上,民間環保組織對自然保護區“自身難保”的情況進行了討論。諸如神農架自然保護區小水電開發、長江上游珍稀魚類國家級保護區因小南海水電站建設被迫調整、環評公示期施工的遼寧盤錦濱海公路試圖穿越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斑海豹的核心棲息地等等均被談及。本應當做“生態安全底線”去保護的自然保護區,如今顯得有些“沒底氣”。

地處江蘇沿海的鹽城濕地豐富,為了守護“濕地禁區”,江蘇鹽城邊防支隊官兵受命進駐。
相關法律的缺失被指是造成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國只有《自然保護區條例》和《風景名勝區條例》。由于法律法規的缺失,不管是自然保護區和風景名勝區,還是森林公園、濕地公園、水源保護地、地質公園、水利風景區等其他類型保護地,都沒有得到應有的科學保護。
另一個原因就是多部門的條塊分割管理。自然保護地分屬于國家林業局、環保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農業部、國土資源部、海洋局等十幾個部門管理。中國科學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吳金水曾指出,“十幾個部門條塊分割,缺乏信息交流及共享機制,無法從行政角度制定統一的保護規劃并實施有效管理。”
據了解,《自然保護地法》曾一度被全國人大環資委醞釀出臺,但最終還是因為部門之間的利益難以均衡而被擱置。《自然保護地法》隨后試圖為《自然遺產保護法》所替代,但卻被眾多反對聲音叫停。
“《自然遺產保護法》不僅不能幫助解決目前我國保護地體系立法當中存在的問題,反而會帶來更多的混亂。最理想的還是建立一個覆蓋整個保護地領域的基本法,以便建立捍衛中國生態安全底線的長效機制。”解焱說。
2013年,北京代表團向全國人大提交一份呼吁制定《自然保護地法》的議案。該議案建議保留現有多部門管理形式,由環境保護部專責負責統一協調和監管,并鼓勵社會參與自然保護地的管理。
建立國家公園體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劃定生態紅線。堅定不移實施主體功能區制度,建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區定位推動發展,建立國家公園體制。
國家公園是指國家為保護一個或多個典型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為生態旅游、科學研究和環境教育提供場所而劃定的需要特殊保護、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區域。
這一概念源自美國,1872年,美國設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公園,即黃石國家公園。目前,世界上已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近10000個國家公園。
建立國家公園的目的就在于保護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做到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雙贏”。然而,就中國目前情況而言,打破部門利益局限,構建有效率的資源管理與運行體系,保障充足的資金,都被認為是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的難點。
2014年全國兩會期間,《關于加強自然保護地管理,有效保護生態紅線》的提案對此給出了一些建議。提案建議保障每年0.2% GDP以上的經費投入,用于自然保護地體系的保護管理工作,這些經費不能變相用于任何經營投資。經費應主要來自中央和省級政府財政,完善和實施分級管理制度。
“這將成為一項重要的大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可以真正把國家資金和省級的資金更多地投入到我們重點需要保護的那些區域中去。”解焱說。
另外,建立國家公園體制也將對物種保護起到積極作用。對于需要大范圍才能生存的物種來講,孤立的自然保護地無法達到保護目的,如藏羚羊、黃羊、老虎、雪豹、豹、白鰭豚、江豚、大熊貓等。
民間動物保護人士認為,保護一個物種,不能只保護一頭動物,必須要至少保護一個可以長期自我繁衍的種群。
科考資料表明,一頭雌性繁殖虎的領域范圍約450km2,種群的最低數量是15-18只雌性繁殖虎,因此,維持一個東北老虎種群需要的面積,以18只計算是8100 km2。但是我國目前最大的東北虎保護區——琿春東北虎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僅為1000 km2。
延邊州擁有全國50%以上的野生東北虎種群和幾乎全部的遠東豹種群,在中國東北虎和遠東豹種群恢復和擴展中具有最重要地位。若能在琿春、汪清轄區內建設虎豹國家公園,借用東北虎和遠東豹,打出生態延邊品牌,提升延邊整體價值,那里的人民將獲得更多的生態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