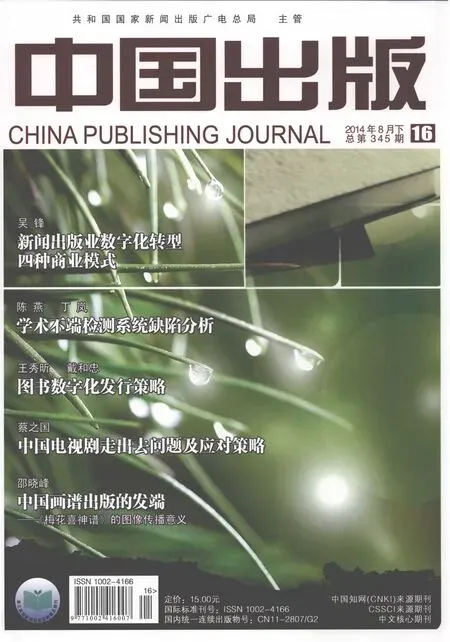中國畫譜出版的發端*——《梅花喜神譜》的圖像傳播意義
文/邵曉峰
南宋宋伯仁繪編的《梅花喜神譜》是我國出版史上最早的木刻畫譜,也是目前發現的第一部雕版印刷的梅花畫譜,共刻有100幅梅花圖,并配以100個畫名與100首五言詩。該譜分上、下卷,按蓓蕾、小蕊、大蕊、欲開、大開、爛漫、欲謝、就實八個梅花的自然開花過程,在畫譜書頁上次第展開。
一、《梅花喜神譜》的出版與傳播
《梅花喜神譜》的誕生離不開宋代出版事業的發展與成熟。自雕版印刷在唐代發明以來,至五代馮道始運用于儒學經典的刊刻、出版與傳播,越來越受到官方的重視。進入宋代,隨著“右文”國策的實行,整個社會對于文化十分重視,文人的地位被升至有史以來的最高,科舉得到了真正的普及,如此一來,對于各類書籍的需要也達到了高峰,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宋代出版事業的大發展。宋代的造紙業發達,以之作為基礎,這一時期的印刷業自然被帶動得欣欣向榮,共同推動了兩宋書籍事業的發展。其中,南宋的印刷業比北宋更有進展,除杭州以外,蘇州、饒州、撫州、婺州、建州、成都等地均成為雕版業、刻書業的中心,兩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區域也成為印刷業的發達地區。甚至與后來的明、清兩朝相比,南宋的雕版書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1.《梅花喜神譜》的誕生背景
雕版印刷術在宋代得到廣泛應用,以雕版印刷復制圖書,體現許多便利之處,如信息容量的規模化、收藏傳播的長期化、適應需求的多元化,而且量大質高、價廉物美、傳播迅速,從而普及教育、造就人才、促進學術發展。雕版圖書之傳播迅速,遠非昔日的寫本所能媲美。它們的廣泛傳播擴大了文人在文壇的影響力,提高了作品的聲譽與地位,造成了士林間的相互傳閱與期待。以東坡詩文為例,北宋元祐年間被下詔禁止,然而“禁愈嚴而傳愈多”、“禁愈急,其文愈貴”,足見雕版印刷對于文化知識傳播之力量之大。雖曾遭禁毀,但是到了南宋,甚至家家均有“眉山書”(見圖1),乃至影響士林,流傳至今,其主要原因即在于雕版印刷出版的發展與傳播。

圖1 南宋寧宗慶元年間(1195~1200年)黃州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在宋代出版史上,像《梅花喜神譜》一樣屬于圖文并茂的著名書籍有,北宋天文學家蘇頌《新儀象法要》,金石學圖譜北宋呂大臨《考古圖》、北宋王黼《宣和博古圖錄》、南宋佚名《續考古圖》,以及建筑圖譜《營造法式》等,它們均通過雕版印刷這一重要出版形式得以流傳后世。
在南宋,雕版印刷已經形成規模與產業,臨安開有很多書鋪,據吳自牧《夢粱錄》記載,陳道人書籍鋪是其中著名的一家。凡經該鋪刊刻的書籍,其中往往標示“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從明代嘉靖年間翻刻的陳道人書籍鋪出版的美術書籍品種來看,當時他的書籍鋪出版有《古畫品錄》《續畫品》《續畫品錄》《后畫錄》《貞觀公私畫史》《唐朝名畫錄》《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益州名畫錄》《畫繼》等自南北朝到南宋的著名美術著述。南宋雕版印刷出版業的普及不但促進了圖書的廣泛普及,而且也促進了《梅花喜神譜》這一類畫譜的有效出版與傳播,堪稱是推動這一時期學術與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2.《梅花喜神譜》版本的流傳
《梅花喜神譜》初刻于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但原刻本已失。目前所見版本是在南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由金華雙桂堂重刻的,但刻工不詳。到了明代,大書畫家文徵明收藏了一部由金華雙桂堂重刻的《梅花喜神譜》,并在其卷首目錄頁上蓋有“徵明”朱文印,在梅圖“麥眼”上蓋有“徵明”朱文印和“文徵明印”白文印。后來,這部《梅花喜神譜》入藏清朝某王府。清初,此譜自王府中散出,先藏于江蘇常熟藏書家錢曾處,后流落北京。嘉慶辛酉年(1801年),藏書家、刻書家黃丕烈在北京文萃堂書肆購得此譜,再三題詠,并邀好友一起賞評。黃丕烈還詳考了此譜的創作年代,說:“卷后葉紹翁跋作于嘉熙二年(1238年),而《吟草》中有嘉熙戊戌家馬塍稿、嘉熙戊戌夏復游海陵稿。嘉熙戊戌、己亥《馬塍稿稿中歲旦》一首注云:己亥嘉熙三年,則嘉熙二年為戊戌,此譜之作當在僑居西馬塍后,以閑工夫作閑事業,意蓋有所感爾。”黃丕烈得到宋刻《梅花喜神譜》之后,陳鳣知道丕烈不僅愛譜,同時喜梅,故在嘉慶十二年(1807年)從杭州姚虎臣家替他購到元至正刻本《梅花百詠》(元代韋珪的詠梅詩集),使之與《梅花喜神譜》形成所謂的“兩梅”。后來,《梅花喜神譜》再傳至于昌遂處,不料昌遂不小心被人騙去此譜,幸虧一年后金順甫幫助將其賺得,仍歸昌遂。再后,傳至吳縣大藏書家潘祖蔭處,后來此畫譜歸祖蔭弟仲午。著名畫家吳湖帆的夫人潘樹春是潘仲午之女,生于光緒壬辰年(1892年)正月十三日,歲逢辛酉,與宋景定刻《梅花喜神譜》的干支正合,潘仲午于是將其作為愛女30歲生日的禮物相贈。吳湖帆夫婦得譜后喜不自勝,遂將所居定名為“梅景書屋”,以示珍重。此譜在梅景書屋寶藏的時間最長,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藏入上海博物館。
《梅花喜神譜》在明中葉以前,不見著錄于各公私書目,到了清代,《梅花喜神譜》漸漸名重于世,多有翻刻,并有多種版本,[1]其中以古倪園沈氏刻本影響較大。大書畫家吳昌碩的詠梅詩《盆盎紅梅》中有“傳家一本宋朝梅”的詩句,可見他也藏有《梅花喜神譜》刻本。
雙桂堂刻本的《梅花喜神譜》流傳至今已為孤本,先后有知名學者、書畫家如錢大昕、孫星衍、洪亮吉、張敦仁、吳讓之、吳錫麟、包世臣、于昌遂、羅振玉等品鑒題跋。在現代出版史上,商務印書館、[2]文物出版社[3]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納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4]先后出版有該版本的影印本流傳于世,本文關于《梅花喜神譜》的插圖即引自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影印本。
3.《梅花喜神譜》的當代研究
當代學界從不同角度對《梅花喜神譜》進行關注、研究,也構成了它在當代傳播、推廣而深入人心的重要形式之一。
對它進行系統介紹與闡釋的有4位學者:曹齊較早對它的來龍去脈以及特點進行了簡介;[5]朱仲岳介紹了其主要內容,作者的生平、個性,它的流傳、影印過程;[6]譚英林分析了它的藝術特點,闡釋了其時代背景,并對它與畫梅藝術的關系進行了討論;[7]傅怡靜論述了它的題名藝術、版刻價值以及詩歌價值。[8]
專門研究其版本的有兩位學者:朱仲岳對《宋本梅花喜神譜》的重刻本、翻刻本作了較為系統的研究與闡述;[9]華蕾研究了清嘉慶間松江沈氏古倪園刊《梅花喜神譜》,認為南宋景定間刻的《梅花喜神譜》是已知最早的翻刻本。[10]
《梅花喜神譜》的題跋也具有研究意義,張卿、呂三川對其題跋進行了研究,指出清代黃丕烈對于《梅花喜神譜》的題跋可視為對畫論文本的修正、補充及考釋。[11]
龐瑾則從書籍裝幀角度對它進行了探討,認為融詩書畫于一體的裝幀形式擴展了它作為書籍的社會身份。[12]
對《梅花喜神譜》所揭示的植物學價值進行研究的有兩位學者:張艷芳通過對畫譜中涉及的梅花開花過程的描述,認為宋伯仁在對梅花的開花物候、繪畫、詩作、文學、梅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系統、深刻的研究,將科學和藝術融為一體。[12]周放探討了畫譜中詩、畫及開花物候之間的關聯,闡述了中華民族精神之靈魂。[13]
《梅花喜神譜》是我國出版的第一部關于梅花的專門畫譜,奠定了后世這一類畫譜的基本模式。它在南宋被私人刊印兩次,說明當時的出版水平是較高的。就畫譜的傳播效能而言,《梅花喜神譜》中的梅花畫法及繪畫模式,對明代劉世儒《雪湖梅譜》、清代王寅《冶梅梅譜》等后代梅花畫譜的編撰深有啟發,乃至于今天學習梅花畫法的畫者以及研究梅花文化的學者均受其影響。
從圖像出版傳播學的視角來看,《梅花喜神譜》豐富的出版歷程與傳播效果與其圖像意義密切相關,這是它能在不同時代為人青睞、得以不斷出版傳播的重要內因。圖像意義的獲取需要借助于現代圖像學三個層次的研究法研究,即通過圖像的描述、分析與詮釋,還原圖像背后的意義。
二、《梅花喜神譜》的圖像描述
《梅花喜神譜》的視覺傳播頗具特色,其版框縱15.1厘米、橫10.7厘米,四周為外粗內細的雙欄,目錄半葉八行,每行書二目。圖版半葉一幅,左二行以歐體字刻五言詩一首,題名橫列于右上,名下為梅花圖。畫譜以木版陽刻,用墨印成,表現出“墨梅”單純樸素的視覺效果。這百幅梅花圖,除蓓蕾四枝及小蕊中“丁香”一枝外,其余每幅折枝表現一朵梅花,形同剪影。又以題名點明梅花的形態,以五言詩延展題名的含義,使畫、題、詩有機地融為一體。
比如,“麥眼”(圖2)之梅圖,屬于蓓蕾四枝之一。單枝斜出,五只蓓蕾猶如剛抽穗的麥粒,十分形象。并配以五言詩:“南枝發岐穎,峻恫占歲登。當思漢光武,一飯能中興。”當讀者翻過一頁,再看梅圖,那些麥粒已經長成了滴溜圓的螃蟹眼珠,故名“蟹眼”。與之相配的五言詩為:“爬沙走江海,慣識風波惡,東君為主張,顯戮逃砧鑊。”再如,“櫻桃”之梅圖,屬于小蕊十六枝之一。其形狀宛如一顆櫻桃,呼之欲出,十分生動。而“孩兒面”(圖3)之梅圖也屬于小蕊十六枝之一,其形狀恰似一張小孩臉,眉、眼、嘴、鼻一一具備,皺著眉頭,似乎是受了委屈,趣味十足。

圖2 麥眼

圖3 孩兒面
三、《梅花喜神譜》的圖像分析
深入的圖像分析需通過對畫譜作者宋伯仁做進一步了解以及分析他自己對畫譜的闡述來進行。
宋伯仁著有詩集《雪巖吟草甲卷·忘機集》《雪巖吟草乙卷·西塍集》,又有《煙波漁隱詞》《海陵稿》《西塍稿》《續稿》等。由于文獻史料中關于宋伯仁的記載很少,故而對《梅花喜神譜》評價甚高的清代文人黃丕烈曾盡全力為其作者宋伯仁匯集各種資料,并為他作了一篇小傳,書于畫譜后。在黃丕烈看來,宋伯仁官雖做得不大,但有慷慨氣節,性格直率,精神氣質如同梅花。
《梅花喜神譜》卷前刻有宋伯仁自序及雙桂堂重刻序各一篇,卷后附向士壁跋及葉紹翁跋各一篇。宋伯仁在《自序》中認為自己之所以能繪出梅花的每個花態,全在于嗜梅成癖,筑圃植梅,實地觀察,久而久之,心領神會。
深入分析這一畫譜,可以發現,以前的書籍插圖多是服務于文字,對文字內容進行進一步解釋說明,而《梅花喜神譜》堪稱一個轉折點,它以圖像為主,文字服務于圖像。《梅花喜神譜》中的圖文形式也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畫,它不把詩句題進畫中,但詩句又是作品不可分離的重要部分。每幅畫的上首均刻有畫題,左側附一首五言絕句,這在當時是一種新創的版畫形式。它的畫題別具巧思,每兩幅為一對偶,如第一、二兩幅,“麥眼”(圖2)與“柳眼”(圖4)相對,展現梅花蓓蕾初露之狀;再如五、六兩幅,“丁香”(圖5)與“櫻桃”相對,展現梅花花色欲現之狀;又如“春甕浮香”與“寒缸吐焰”相對,“晴空掛月”與“遙山抹云”相對,分別展現梅花似放未放、花開爛漫之狀。
四、《梅花喜神譜》的圖像詮釋

圖4 柳眼

圖5 丁香
其中描繪梅花盛開的階段有“大蕊”(花瓣松動,有8種姿態〉、“欲開”(花瓣待放,也有8種姿態〉、“大開”(花瓣綻放,共計14種姿態)、“爛漫”(花瓣盛開,28種姿態),這一階段為梅花綻放的輝煌時期,故作者用姿態不同的58幅圖進行表現,極盡贊美之情。
畫譜每頁畫題的取材內容有五個方面,按由多到少的順序為:動物形象或動態,生活器具,植物形狀,人物及其行為,歷史人物及典故比喻。
盡管是面對單一的梅花題材,作者卻能展開如此豐富的想象,其觀察事物的細致以及審美聯想的廣大,著實令人欽佩。
這一時期雕版印刷術的工藝流程是,需要先寫好書稿或畫好畫稿,選取紋質細密堅實的木材作為原料,按要求鋸成規定大小的木板,刨平,在其上將要印刷的文字或圖像雕刻成反向的陽紋,以之為底版,再在其上刷墨、色,然后利用紙張印刷。印和印刷之間還有區別,若僅是捺印在紙上的,只能叫印,而不能叫印刷。木版印刷是通過馬連[15]一類的印刷工具摩擦紙的背面形成“刷”。而在近現代的印刷中,則是以滾子從背面將紙壓在版面上,這就是印刷的“刷”。沒有經過“刷”這一操作流程的,都只能稱為“印”。盡管雕刻印刷費時費工,但因印刷品清晰,故一直被沿用到清末。除木版外,也有用銅版、石版印刷的。
正是在南宋精湛的雕版印刷的大環境中,《梅花喜神譜》的線條古拙高簡,刻工精妙,運刀如筆,渾厚天成。畫譜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還在于作者宋伯仁是一名酷愛梅花的畫家,并能親自參與畫譜的繪制和刊刻。他先用毛筆畫出原稿,再指導工匠在木板上雕刻,然后印制而成,從而保證了畫譜的藝術質量,這也許是目前發現的畫家親自參與繪制、刊刻、出版的中國最早的一本木刻版畫畫譜。
將《梅花喜神譜》放在更為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查,可以詮釋其蘊涵的象征意義以及背后的深層原因。
表面上,宋伯仁刊刻《梅花喜神譜》是在“閑工夫作閑事業”,但蘊藏在畫譜背后的深層意義需結合獨特的宋代梅文化來理解。梅花獨特的藝術形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國栽種梅花已有3000多年的歷史,在宋代梅花已被賦予深厚的道德內涵,象征堅貞、長壽,與蘭、竹、菊被并稱為“四君子”,與松、竹被合稱“歲寒三友”,梅文化在宋代形成并得到了巨大發展,其燦爛的文化印跡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等宋代詠梅句流傳至今,膾炙人口。
在我國梅花圖像史上,為人熟知、流傳有序的以梅為題材的圖像作品是從宋代開始的,如揚無咎《四梅圖》《雪梅圖》、馬麟 《層疊冰綃圖》、趙孟堅《歲寒三友圖》、趙佶《臘梅山禽圖》、馬遠《梅石溪鳧圖》、徐禹功《雪中梅竹圖》等。揚無咎在仲仁畫梅法的基礎上進行了發展,變水墨點瓣為白描圈線,自成一格,直接影響了南宋趙孟堅、元末王冕等墨梅名家。他逝于南宋乾道年間(1165~1173年),約70年后,宋伯仁《梅花喜神譜》問世。《梅花喜神譜》中采取的手法也是勾勒法,可能是受到了揚無咎派墨梅圖像作者的影響,由于《梅花喜神譜》的繪制要結合當時版畫印刷生產的工藝與流程特點,所以更為簡潔,形成了新的發展。
宋代梅花著述出版的盛況,可從三本專著中看出,即范成大《梅譜》、張磁《梅品》和宋伯仁《梅花喜神譜》。《梅譜》敘述了當時江南所栽植的梅花品種及特點,其所使用的名稱如江梅、綠萼、杏梅等至今仍在沿用;而《梅品》(1185年出版)側重于對不同品種的梅花進行品位的賞析;《梅花喜神譜》則以繪畫配以畫題及五言詩的出版形式呈現給讀者。三部具有經典意義的梅花專著相繼誕生于南宋的50余年之間,絕非偶然!
當時北宋滅亡,南宋偏安,金人虎視,時代因素也許是這三部梅花專著產生的重要原因。當時的文人紛紛以自己擅長的文學藝術形式來表現堅貞不屈、愛國忠君的感情,而梅蘭竹菊等四君子題材更成為當時文人圖像作者喜愛描繪的對象。筆者認為,正是以上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宋代梅文化出版的興盛。
《梅花喜神譜》的每頁插圖簡潔大方,頗有“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之意蘊,這也是受到當時十分昌盛的佛教禪宗思想影響的產物。而且,畫譜中的100首題畫詩多數是借題發揮,藏有深意。如第三部分“大蕊八枝”之一的《琴甲》(圖7)詩云:“高山流水音,泠泠生指下。無與俗人彈,伯牙恐嘲罵。”由初綻如琴甲的一朵梅花而聯想到《高山流水》的琴曲,此詩寫梅之高潔,但無一字言梅,其知音難覓的清高意境,又似乎無一字不言梅,典型地表達了作者壯志難酬、憂國憂民、廣求知音的情懷。如第七部分“欲謝十六枝”之一的《漉酒巾》(圖8)詩云:“爛醉是生涯,折腰良可慨。欲酒對黃華,烏紗奚足愛。”這里作者也沒有一字說到梅花,但是以陶淵明“脫巾漉酒”的軼事來深化梅花的內在品格,以淵明超逸的氣節來比喻梅花清高之品質。

圖7 琴甲

圖8 漉酒巾
宋伯仁在自序中說:“此書之作,豈不能動愛君憂國之士。出欲將,人欲相,垂紳正笏,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宋伯仁的創作意圖是吻合于當時的時代背景的,一部小小的梅花譜竟然與宏大的“愛君憂國”、“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之思發生關聯,這是宋代文人獨特的心境所決定的。宋伯仁繪制、刊刻、出版與傳播此譜之目的,不但叫人終身不忘梅花堅貞剛潔的本性,時時追慕學習,而且可供文人雅士鑒賞怡情,陶冶胸襟。這部畫譜不叫《梅花畫譜》,而稱為《梅花喜神譜》也是具有深意的。為此,清代錢大昕在該譜的題跋中解釋過其原因,即:“蓋宋時俗語,以寫像為喜神也。”至今江浙一帶確實還有稱畫像為喜神的。另外,宋代的“寫像”也叫“寫真”、[16]“寫生”,它們與江浙一帶的“喜神”的讀音十分接近,所以也有可能是方言的“口彩化”形成的這么一個吉祥好聽的名稱。可以想象,宋伯仁陪伴在梅花身邊,細觀精寫,人梅一體,而著成這本入木三分的“梅花寫真集”。
五、結語
在中國出版史研究中,作為畫譜印刷出版的發端,《梅花喜神譜》具有典型性與代表性。它簡潔大方,題、詩、畫三位一體,以物喻人,以物寄情,以小見大,這些均值得我們對它的出版傳播展開追尋與挖掘。另外,圖像得以出版傳播的內在基礎主要在于其蘊涵的圖像意義,從圖像描述、分析,再到圖像詮釋,我們運用現代圖像學三個層次的縱深研究法對此展開研究,不僅嘗試還原了《梅花喜神譜》中蘊涵的圖像意義,也將研究視野進一步打開,為其他更多的中國古代出版圖像研究提供了經驗。
注釋:
[1]例如:《楳華喜神譜》二卷,清代鮑廷博(1728~1814年)據雙桂堂本翻刻,輯入《知不足齋叢書》;《宋雪巖梅花喜神譜》二卷,清代袁廷梼五硯樓藏本,清代嘉慶間松江古倪園沈氏翻刻,中華書局影印;《梅花喜神譜》二卷,清阮元藏本,輯入《宛委別藏叢書》;《梅花喜神譜》二卷,七十二夫容仙館翻刻,清代道光丙戌(1826年)。
[2]《宋本梅花喜神譜》影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
[3][南宋]宋伯仁:《宋刻梅花喜神譜》影印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4]中華再造善本《梅花喜神譜》(函裝二冊)[M].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
[5]曹齊.宋雪巖《梅花喜神譜》介紹[J].美術叢刊,1982(19)
[6]朱仲岳.宋刊孤本《梅花喜神譜》[J].中國歷史文物,2002(5)
[7]譚英林.宋雪巖《梅花喜神譜》的研究[J].齊魯藝苑,1992(2)
[8]傅怡靜.論宋人私刻《梅花喜神譜》的藝術價值[J].中國書畫,2008(11)
[9]朱仲岳.館藏宋刊《梅花喜神譜》及諸版本[M].上海博物館集刊,1996
[10]華蕾.古倪園本《梅花喜神譜》 刊印考[J].圖書館雜志,2010(6)
[11]張卿、呂三川.《梅花喜神譜》 題跋研究[J].泉州師范學院學報,2012(3)
[12]龐瑾.《梅花喜神譜》 :書籍之為藝術[J].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0(5)
[13]張艷芳.《梅花喜神譜》與梅花開花過程及其它[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1(特刊)
[14]周放.《梅花喜神譜》中詩、畫與開花物候之初探[J].北京林業大學學報,2003(特刊)
[15]馬連是一種印刷工具。印刷時,將紙覆在版木之上,以馬連摩擦紙的背面,木版上的圖形即印到紙上。
[16]寫真這一說法在當代中國的流行源于日本,而日本對這一詞匯的運用其實是源自中國的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