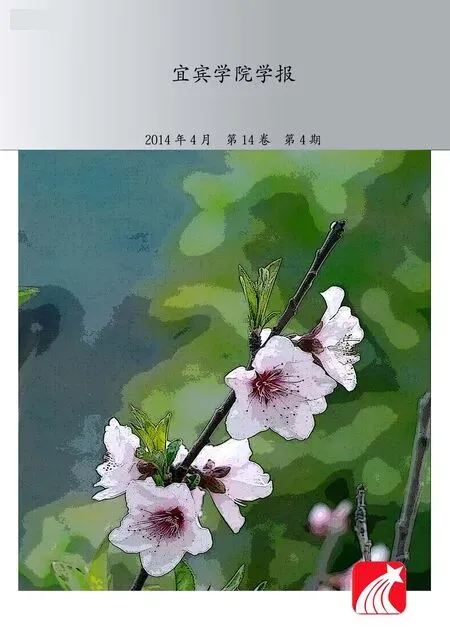《米德爾馬契》體現的女性觀
葉 梅
(安徽師范大學 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8)
喬治·艾略特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一位偉大而奇特的女性作家,她的一生猶如一部跌宕起伏的浪漫小說,讓人驚嘆不已。然而她筆下的女性人物并不像她本人那樣離經叛道,大膽地蔑視世俗規范,女主人公的結局往往平庸而較為悲觀。這一點為激進的女性評論家所詬病。正如凱特·米勒所說,喬治·艾略特“生活在罪孽之中”,一生都在挑戰傳統的婚姻制度,以自己的生活進行“革命”,但她并不贊成女性獨立,在她的作品中也不體現這種主張。[1]94蘇珊·科柏曼的措辭更為激烈:“一想到喬治·艾略特將她的主人公塑造的遠不如她自己本人在生活中那么大膽就不由得感到憤怒。”[2]
然而,無論人們爭論如何,艾略特的女性意識是非常明確的,其主要作品無不體現了女性憑借道德力量和獨特的性格魅力改造男性世界,追求獨立和實現社會價值的意識。在艾略特的筆下,她常將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刻畫成道德力量薄弱,甚至是有某種性格弱點的人物。而女性人物相對高大,作者賦予了她們崇高的品質。女性雖然表面上不得不屈從于男性權威,“但是她們能在有限的活動領域中獲得心靈的成功”[3]。她們往往在男性世界中充當引導者的形象,利用其獨特的女性魅力對周遭的男性產生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女性對男性命運產生引導作用,并以間接的方式引導男性主人公建立起完整的自我。關于女性引導者這一主題在艾略特的小說中非常普遍,如在《亞當·比德》中黛娜對亞當和其弟弟塞斯的引導,《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麥琪對費利浦的引導,以及《織工馬南》中愛蓓對馬南的引導,南茜對高德夫雷的引導等。在其代表作《米德爾馬契》中,艾略特著重刻畫了三位女性引導者的形象,她們分別是多蘿西婭、瑪麗·高思、布爾斯特羅德夫人。
一 理想的執著追求者——多蘿西婭
女主人公多蘿西婭與夏洛蒂·勃朗特筆下的簡·愛有很大的不同,簡·愛來自下層社會,貧窮而無社會地位,且沒有令人驚羨的美貌。而多蘿西婭一出場,作者便賦予她一個中產階級小姐的身份,雖然她也像簡一樣是個孤兒,但是父母留給她的遺產已經足夠她過上富足的生活。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的需要包括五個層次:生理、安全、愛、尊重、自我實現,每當一種需要得到滿足,另一種需要便會取而代之。[4]作為大家閨秀的布魯克小姐而言,她所追求的是較高層次的精神生活,即自我價值的實現。多蘿西婭雖然很富有,但她與當時大多數中產階級婦女追求個人享樂,奢侈的生活不同,她過著清教徒般節儉的生活,對物質的要求極低。她把錢財看做身外之物,并希望通過服務社會來實現女性的真正價值,一心想取得圣女特蕾莎般的成就。在婚前她就獨立開辦幼兒園,擬建村社改善田莊居民的生活條件,還常常出錢資助公益事業,捐助教堂、醫院等。她渴望擺脫中產階級女性平庸無聊的命運,渴望另一半是像胡克、彌爾頓那樣的偉大人物。“我希望嫁的丈夫是在見解和一切知識上都超過我的人”[5]39。她向往的婚姻是那種能夠幫助她“擺脫年幼無知的困境,讓她自覺自愿地接受指導,走上莊嚴崇高的道路”[5]27。當年長她27歲的學者卡蘇朋出現時,她仿佛看到了生活的意義,幻想著與博學的丈夫共同攀登知識的巔峰。但婚后卻很快陷入了理想的幻滅之中,她既不能成為丈夫的助手和精神伴侶,還要受到自私狹隘的卡蘇朋的猜忌。
在卡蘇朋去世之后,經歷現實磨煉的多蘿西婭并未放棄自己的理想。此時的她對愛情婚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與威爾的交往中萌發了愛的激情。為了與威爾結合,多蘿西婭做出了放棄卡蘇朋財產繼承權的決定,這一行為在當時是難以想象的大膽和叛逆。然而威爾并不是一個完美的男性,在W.L柯林斯看來:“拉迪斯拉夫缺點很多,優柔寡斷”[6]。他以自我為中心,崇尚自由,無拘無束,社會責任感較弱。多蘿西婭對威爾的愛源于一種對弱者的同情,當她知道了威爾的身世之后,情感的天平便向威爾傾斜。她把對威爾的愛理解為對抗邪惡的行為,她自己則是“對抗惡的神圣力量的一部分”[5]373。“如果我過分愛他,那么這是因為別人待他太壞了”[5]753,她將威爾置于自己的保護之下,用愛和信任將威爾由一個無所事事的藝術追求者轉變為活躍的政治活動家。可以說,威爾的存在成為多蘿西婭美德的一種補充。[7]100
除了威爾,對利德蓋特以及費厄布拉則牧師,多蘿西婭都伸出了援助之手。當利德蓋特為布爾斯特羅德利用,面臨著身敗名裂的危險時,她以真誠的心關懷他,用坦率的語言安慰她,不但給予他經濟上的援助,還在精神上給他一種信任感,并且四處忙碌為他洗刷罪名。當她了解到費厄拉則牧師的家庭處境時,便努力為他爭取到了洛克伍的牧師津貼,并使他放棄了惹人非議的慧司特牌。多蘿西婭就是這樣一個圣母瑪利亞似的女性人物,自始至終散發著愛的光芒。她向往的是最公正無私的善和正義,具有一種基督徒的博愛精神。“我們活在世上,想到別人的痛苦,那種心如刀割的痛苦,只要我們能幫助他們,我們怎么能夠袖手旁觀呢?”[5]742艾略特試圖通過多蘿西婭對威爾的引導,對利德蓋特,費厄布拉則牧師的積極影響,讓女性盡量發揮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證明自己的存在,實現自己的價值。正如艾略特所說:“她那醇厚的天性,使別人從她對他們的信任中得到了鼓舞,看到了自己的理想,這是女性的偉大力量之一”[5]722。
二 婚姻家庭中的天使——瑪麗·高思
維多利亞時期一位有名的藝術評論家約翰·拉斯金:曾宣稱男人是做事者、創造者、發明者;而女人則是好看的,供人欣賞的,供陳列用的,供贊美吹噓的。[8]瑪麗·高思顛覆了這一傳統看法,她是一位自立自強的新女性,也是艾略特心中完美女性的典范。瑪麗相貌平平,但勤勞、正直、誠實。她做過家庭教師,做過費瑟斯通的管家,但卻不像他的親戚那樣覬覦他的財產。她既沒有像多蘿西婭那樣想入非非,也沒有羅莎蒙德自私虛榮,而是非常理性和實際。她和米德爾馬契市長的兒子弗萊德從小兩情相悅。弗萊德本性善良,但性格軟弱,由于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加之母親過分溺愛,他好逸惡勞,游手好閑,且迷戀上了賭博。他總是幻想著以費瑟斯通姨夫的遺產作為自己未來生活的保障,而不想依靠自己的勞動來生活。瑪麗對他是愛恨交加,她說:“我的家庭是不喜歡向人祈求的,弗萊德。我們情愿干活掙錢”[5]242。在愛情問題上,她也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她希望自己未來的丈夫能夠過自食其力的生活,當弗萊德向她求愛時,她說:“我永遠不會愛上一個沒有男子氣概,不能自立的人,一個游手好閑,蹉跎歲月,指望僥幸得到別人恩賜的人”[5]246。瑪麗將“自立”作為做人的基本準則,并以此來要求弗萊德,表現了她不僅要改變女性自身的現狀,還要改變男性的愿望。由于弗萊德繼承遺產的愿望泡湯,父親逼著他做教士,但弗萊德并不喜歡教士的職業,在瑪麗看來弗萊德的性格以及生活習慣根本不適合做教士,即使勉強做了也不能成為一個好教士,到頭來只能弄虛作假,成為別人的笑柄。于是,在瑪麗的鼓勵下,一直深愛著瑪麗的弗萊德最終違背了父親的意愿放棄了教士的職業。與瑪麗結婚后,弗萊德已徹底改變過去的不良習慣,從事著自己感興趣的農活,最終變成了一個腳踏實地,遠近聞名農業家。
在弗萊德面前,瑪麗似乎扮演的是一位強硬的女性角色,她自始至終保持著女性的優越感。她對弗萊德的理解、指責和鼓勵都是使他最后走向成熟的關鍵。她對自己的父親說“丈夫是較低一級的男子,他們需要別人管束他們”[5]774。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是個成功的女性,因為她不僅實現了自己的婚姻理想,而且在改造弗萊德的過程中實現了她的人生價值。她用她那富含母性的女性之愛以及在任何情況下都毫不動搖的堅定品質,將弗萊德由原來的紈绔子弟變成一個有擔當、有責任感的男子漢。弗萊德的轉變體現了女性的愛在改造男性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這也體現了艾略特不僅意識到女性在經濟上的獨立是實現女性社會價值的重要方面,同時也認識到要真正實現女性的解放,婦女還應擔負起改造受傳統偏見影響的男性,這也是時代賦予女性的使命。
三 完美人格的代言人——赫莉歐
喬治·艾略特的女性主義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她倡導女性應該實現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將力量,智慧與女性的柔和,圓滑以及居家生活的經驗結合起來”[9]。憑借自己的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來影響和改造男性。在小說中作者對布爾斯特多德夫人(赫莉歐)身上的筆墨并不多,但她卻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她是一個普通的并未受過正規的教育的婦女,但勤勞、善良、誠實,為家庭忙碌操勞。在鄰居眼里,布爾斯德太太很得人心,她“一向心地善良,像白天一樣光明正大”[5]。在男人們眼里,她是“溫柔漂亮的妻子”。她一直很信任和尊敬自己的丈夫。當布爾斯特多德在25年前獨吞前妻女兒的遺產而發家的丑聞暴露之后,得知真相的布爾斯特多德夫人并沒有像外人想的那樣離開她的丈夫。相反,她沒有被巨大的打擊所摧垮,而是寬恕了自己的丈夫。聲名狼藉的布爾斯特多德最終在妻子寬容的懷抱中懺悔了自己的罪惡,最終在偉大的女性情感中找到了寬恕。赫莉歐用她那忠于誓言的,仁慈的同情心將她的丈夫從遭人唾棄的恥辱中拯救出來,同時也挽救了自己的婚姻。
根據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學說,即人的心理人格有自我、本我、超我三部分組成。本我代表人與生俱來的各種本能,自我是審慎和理性的象征,它遵循“現實原則”。超我是人格結構中的最高層次,即道德化的自我。[10]當超我戰勝本我時,人作為完整的個體將獲得人格的升華。從表面上看,赫莉歐是男權社會中忍讓順從的女性,在家中丈夫占用絕對的統治地位。但當聲名狼藉的丈夫被擊垮時,她人格中超我的堅強寬容戰勝了本我的軟弱怨恨。她回到了不幸丈夫的身邊,跟他一起承擔恥辱,分擔他的憂慮,談論他的過錯。經歷了人格升華的赫莉歐由兩性關系的弱者變成了家庭的支柱,她身邊的布爾斯特多德先生在她完美人格的映照下反而變得干癟了。
結語
但丁在《神曲》中呼喊道:“永恒的女性指引我們飛升”。這也正好契合了喬治·艾略特的女性觀。在喬治·艾略特這個男性化的筆名之下,作者表面上似乎屈從于男性文化,接受傳統的角色和義務。但她筆下女性人物的經歷本身實際上就是對父權體制下女性命運的解構和顛覆。根據康妮斯的分析,女性反對父權獨裁主要有兩種形式:公然反對當時主流社會的準則和隱秘削弱男性權威。[11]在《米德爾馬契》中,多蘿西婭、瑪麗以及布爾斯特多德夫人即采用了隱秘,間接的方式來削弱男性權威。她們借助男性,用無私的愛和奉獻引導男性,間接地實現自己的價值。在艾略特看來漸漸改變這個世界的正是這種“溫和,間接但卻無可估量的影響”[11]。艾略特讓女性走進社會,不僅向傳統的社會觀念提出了挑戰,而且也是對婦女能夠為社會做出自己貢獻的鼓勵。她通過自己筆下的女性們所做出的成就,以事實說明了婦女不僅能造就家庭幸福,對周遭的男性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也能為社會服務,并從中實現自己的社會價值。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說:“認為那些把婦女發展作為未來希望的人應該為喬治·艾略特立一座豐碑”。[1]可見,艾略特的女性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她實際上促進了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馬建軍.喬治·艾略特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
[2] 弗吉尼亞·伍爾夫.論小說與小說家[M].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94.
[3] Patricia Lorimer Lundberg,George Eliot.Mary Ann E-vans’s Subversive Tool in Middlemarch[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272.
[4] 亞伯拉罕·馬斯洛.動機與人格[M].許金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5] 喬治·艾略特.米德爾馬契[M].項星耀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6] 柯彥玢.威爾·拉迪斯拉夫與窗戶意象[J].國外文學,2010(3):92.
[7] Karen Chase,George Eliot:Middlemarch Landmarks of World Literature[M].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64.
[8] 戴維·羅伯茲.英國史:1688年至今[M].魯光桓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278.
[9] 伊萊恩·肖瓦爾特.她們自己的文學——從勃朗特到萊辛的英國女性小說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100.
[10]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M].高覺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11] 顏蓓蕾.從女性哥特角度解讀《米德爾馬契》[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2012(11):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