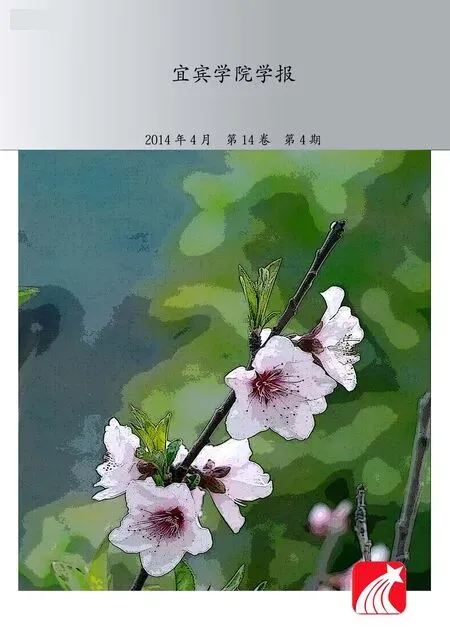崇拜與反抗
——《追風箏的人》主人公對男性權威的態度流變
郭 飛
(黃山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黃山 245041)
《追風箏的人》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賽尼的第一部小說,自出版后,翻譯成多種文字,受到全世界讀者的歡迎。該書,講述阿富汗少年阿米爾的成長故事。他背叛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后來卻又走上救贖之路。據CNKI統計顯示,目前國內有80余篇關于此部作品的研究,它們以身份認同、民族關系、成長小說、生態批評、意象解讀等視角解讀該小說。余剛對阿米爾的身份認同軌跡進行闡釋,他認為,主人公由于身份認同感的缺失從而導致在找尋過程中的焦慮[1];曾萬泉通過分析作品的人物關系來探討阿富汗的民族關系,他指出,小說以人物關系折射出阿富汗民族間的沖突以及不平等的社會階級觀念[2];蔣小慶在其碩士論文中用成長主題探討阿米爾的思想和心理如何在外力的推動下一步步摒棄自私和唯我的道德觀,從幼稚走向人性善良和在邪惡面前不畏強暴而秉持正義的高貴品德。[3]王建榮從民族精神與道德傳承、社會文化變遷與倫理關懷等角度解讀風箏意象,他認為風箏意象具有重要敘事功能,是多元隱喻的載體[4]。但目前國內關于《追風箏的人》的研究與探討主要集中在救贖主題,不少學者從認知詩學、會話分析、親情關系、人性原罪等方面闡述該主題。他們認為,胡賽尼通過小說中人物的命運反映阿富汗社會中因階級、宗教信仰不同造成的友誼與背叛之間的矛盾,為追求人性真諦,個體沖破宗教戒律和社會習俗的束縛,獲得救贖。然而,在成長與救贖中,小說中的“我”與“男性權力”存在密切關聯,這一點,國內研究還未涉及到。主人公阿米爾的背叛、反省與救贖同“我”對男權意識的崇拜、擯棄、反抗一一對應。救贖之路,是對男性權威的態度流變之路。
一 父權崇拜與人性背叛
《追風箏的人》在某種程度上勾勒出一個男權世界,母性缺失是這個世界的典型特征。小說給人印象深刻的女性有四位。阿米爾的母親因生產時出血過多而謝世。“我”從照片上看到“臉帶微笑的媽媽穿著白色衣服,宛如公主”[5]5。寥寥數字,母親的和善、純潔、高貴,令人心生向往。“我”的母親在小說中只作為思念的對象出現過幾次;哈桑的母親漂亮但身份卑微,年輕時放蕩不羈,對自己的丈夫冷嘲熱諷,與當地軍人廝混,最后拋下剛出生的兒子自顧尋歡;“我”的岳母雅米拉,心地善良,喜歡歌唱。丈夫塔赫里同她結婚時,簽署的條款之一就是“她永遠不能在公開場合唱歌”[5]171。第四位女性是“我”的妻子索拉雅,雖出身高貴卻曾跟人私奔,成為難以嫁出去的女子。可以看出,小說中的女性或紅顏薄命,或煙花風塵,或丟失自我,或無法生育,她們都以弱勢的形象出現在阿富汗男人眼中。
相反,塔赫里、阿辛汗等人則扮演著主宰或先知角色,塔赫里傳統、自尊,身上帶有典型阿富汗男人的秉性,他對妻女苛責,不準自己太太隨意唱歌,不準女兒選擇自己喜愛的教師職業;阿辛汗在小說里起著引線作用,出現次數不多,但他已化身為先知式人物。起居室的櫥柜里,有三張照片,其中一張:我還是嬰兒,爸爸抱著我,看上去疲憊而嚴厲,我在爸爸懷里,手里卻拉著拉辛汗的小指頭[5]5。小說開始就通過這一細節隱喻了拉辛汗在“我”生命中的重要作用,這似乎暗示,他是我心靈救贖路上的指引人。多年后,拉辛汗打電話給在美國的阿米爾,“來吧,這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5]186。小說雖未對拉辛汗著過多筆墨,但他卻以男性世界的智者和先知的姿態出現,圍繞“我”發生的一切,他似乎都心知肚明。
小說描寫了阿米爾父親的外形、愛好、性格及關于他的神奇傳說。父親的話題永遠只是政治、生意、足球;父親的綽號叫“颶風先生”,“身材高大……雙手強壯,能將柳樹連根拔起”,“眼珠子一瞪,能讓魔鬼跪地求饒。他身高近2米,每當他出席宴會,總是像太陽吸引向日葵那樣,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5]13這些言辭,無不折射出“我”對父親的仰視及崇拜。甚至,我的夢里都少不了關于父親的傳說。據說父親跟黑熊搏斗過,“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從來沒有人懷疑他的真實性。”“我記不清有多少次,我想象著爸爸搏擊的場面,甚至有時連做夢都夢見,夢中,我分不清哪個是爸爸,哪個是熊。”[5]12政治、足球、黑熊,這些充斥著男人陽剛之氣的符號將父親打造得威武、高大、神氣。此外,父親慷慨仗義,修建孤兒院,每隔一周宴請三十多人來家用餐。在阿米爾眼里,“我對父親敬若神明”[5]31。然而,阿米爾生性懦弱敏感,并不討父親的歡心。父親帶他去湖邊度假,他跟父親說話,父親只簡單“哼”兩下;父親帶阿米爾看比武大賽,“我”看到選手死亡而大哭,父親開車時“沉默不語,厭惡溢于言表”[5]21;父親跟阿辛汗聊天,甚至懷疑“我”是不是他的兒子。父子間的情感失衡,讓阿米爾陷入無邊的挫折感與焦慮中。父親對阿桑的喜愛加深了阿米爾的挫敗感,“我”不明白為何父親會對一個哈扎拉仆人那么友愛而溫和。阿米爾為了讓爸爸只屬于他一人,對父親撒謊說,阿桑有事情不能一起去湖邊。他還恨孤兒院的孩子,希望他們隨父母一起死掉。阿米爾對父親的愛渴望至極,他睡前臆想:“我想起爸爸,他寬廣的胸膛……他身上甜甜的酒味,他用胡子扎我的臉蛋”[5]32。在崇拜父親和得不到父親寵愛的矛盾里,阿米爾設法尋求父親的認同。弗洛伊德認為:“當人失去或不能擁有某一愛戀對象時,為了重新得到甚至長期擁有它,他或許會努力使自己與該對象相似。這便是損失認同。”[6]74母愛的缺失、父權崇拜的冷漠回應,促使阿米爾努力跟父親相似,變得勇敢、堅強。父親在閑談中認為阿米爾能贏回風箏巡回賽,阿米爾立志“讓他看看,他的兒子終究不同凡響”[5]55。弗洛伊德指出:“損失認同常見于遭到父母冷遇的兒童身上,為重獲父母的愛,他們賣力地按父母的意志來表現。父親對孩子怎么要求,孩子就怎樣與之認同。”[6]75然而,正是阿米爾在父權崇拜與認同找尋的糾纏中,他背叛了哈桑。
阿米爾與阿桑將其他放風箏的人斗敗。撿拾被打敗的風箏時,阿桑遭到阿塞夫雞奸。阿米爾站在巷口目睹一切,卻一言不發,他想的是“為了贏回爸爸,這也許是阿桑必須付出的代價”[5]77。阿桑返回時,阿米爾首先關心的是風箏并檢查其是否有裂痕。為得到父親的愛,阿米爾對阿塞夫的罪惡行為只字未提,雖然他知道那是犯罪。在父親溫暖的懷抱里,阿米爾“忘記了自己的所作所為,那感覺真好”[5]78。由此可見,阿米爾對阿桑的背叛皆因他對以父親為代表的男權崇拜而起。父權下的愛與認同激發出阿米爾內心的民族歧視、自私唯我,從而為他日后的內心煎熬與痛苦埋下苦澀種子。阿米爾在日后生活里,他無法忍受阿桑真誠而絕望的目光,無法跟阿桑分享父親的關愛,他制造偷盜假象誣陷阿桑。阿桑父子決意離開,阿米爾并未如釋重負,相反,罪惡感卻加重了。
二 男權崇拜的消隱與自我反省
阿米爾與父親流亡到美國后,他們作為阿富汗人的異域身份凸顯出來。阿米爾和父親住在破舊的民房里,父親在加油站干活,他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臟兮兮的。后來,他們收購舊貨到二手市場去賣。父親曾經的風采與神性不復存在,他身負的男權色彩也一點點消退。“對爸爸來說,美國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5]125父親對阿富汗曾發生的一切耿耿于懷,作為曾是阿富汗上流社會的一員,他為失去的感到痛心,獨自哀嘆:“美國,甚至世界需要一個強硬的漢子。”[5]122言外之意,阿富汗政府當時需要捍衛自己的國家,捍衛以“父親”為代表的一群人的過去。父親無法融入美國社會,他拒絕參加英語培訓班,拒絕接受移民局贈送的食物券,在美國商店,他為對方要查看身份證而大為光火。由此,父親變成一個弱者形象,作為男權象征的他出現垮掉的跡象。美國對阿米爾來說“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5]125。他將心靈上的愧疚淡忘,阿桑不在了,無人跟他爭奪分享父親的呵護與關愛。在處理父親與美國文化沖突時,阿米爾以成人的姿態去解釋、道歉,提議替父親報英語補習班。逃亡美國后,阿米爾全然擯棄曾經對父親盲目的迷戀與崇拜。相反,他開始同情父親。吃飯時,“我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干凈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臟且長滿老繭”[5]126。在得知父親患癌癥后,阿米爾找來《古蘭經》,跪在地上乞求自己不曾相信的真主。父子相依為命,彼此認同。在阿米爾高中畢業時,父親對他說:“我很驕傲,阿米爾”[5]127。父親在阿米爾上大學前為他買了舊汽車。父子深情將阿米爾從父權崇拜中拉出來并讓他體會到人間溫情的寶貴與珍惜。
阿米爾對美國這一異域文化心存熱愛。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嘆不已,城市之外有城市……峰巒之外還有山脈,還有更多城市,更多的人群”[5]132。他認為美國沒有鬼魂、沒有遍地的地雷、沒有阿桑那樣的兔唇兒童、沒有被草草掩埋的兒童,沒有罪惡。“就算不為別的,單單為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5]132阿米爾對的美國欣然接受似乎也暗示著美國的某些諸如獨立、自由等標簽會對其產生影響。小說里,阿米爾在未來職業的選擇上確實表現出獨立意識,他告訴父親將寫作當做未來事業。父親反對,希望他去學醫、學法律。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5]130。這儼然說明,阿米爾已放棄對父權及男權的崇拜,走向獨立。雖然他愛父親,同情父親,但他已跨出擯棄父權的一大步。
阿米爾擯棄父權崇拜的最為明顯例證,就是他愛上阿富汗失足少女且要娶她。索拉雅,塔赫里將軍的女兒,正宗普什圖人。她曾跟人私奔,被將軍拿槍逼回來。在阿富汗,失足少女為人不齒,“自那以后媒人再也不敲將軍家的門了。”[5]137“阿富汗男人,尤其那些出生名門望族的人,都是見風使舵的家伙,幾句閑話,數聲詆毀,都讓他們落荒而逃”[5]143。尊嚴與名譽對阿富汗男性多么重要,這也體現出阿富汗社會的典型男權特色。阿米爾是阿富汗喀布爾屈指可數的巨賈的唯一兒子,母親也是被公認為喀布爾數得上的淑女,祖上是皇親貴胄,他的祖父是一個萬眾景仰的法官。阿米爾也是出生名門。但他擯棄男權意識并為“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5]144。父親病逝前,阿米爾懇求他前去將軍家求婚。新婚之夜,阿米爾與妻子并排躺著,“終我一生,周圍環繞的都是男人,那晚,我發現了女性的溫柔”[5]166。對阿米爾來說,女性或者母性的回歸,無疑了遣散他內心存留的那一絲男權崇拜,他的世界開始平衡。
正是父子間的深情與扶持、美國異域文化的影響及生命中母性的回歸讓阿米爾找到性別情感上的平衡,幫他發現內心的自責與內疚,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消除他曾有過的民族及性別偏見,他對過去的背叛開始自省。父親送車給他的那個夜晚,阿米爾激動而開心,父親提起阿桑,“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堆鐵手掐住了”[5]129。阿米爾開車去海邊,他想起自己曾跟阿桑看海的約定;索拉雅教女仆讀書認字的事,讓阿米爾想起他曾愚弄不識字的阿桑及用晦澀字眼取笑他;索拉雅向阿米爾說起自己的過去,阿米爾“懷疑,在很多方面,她都比我好很多,勇氣只是其中之一”[5]160;新婚之夜,阿米爾尋思阿桑是不是也結婚了;面對索拉雅的過去,阿米爾不在意,他認為他也有過去,且對過去悔恨莫及;出版第一本書后,阿米爾想起阿桑曾說過全世界都會讀你的書之類的話;索拉雅不能生育,阿米爾認為:“也許在某個地方,有某個人,因為某件事決定剝奪我為人父的權利,以報復我曾經的所作所為”[5]183……男權崇拜的消隱及生命里的母性補償在阿米爾的自我反省中起到關鍵作用,阿米爾在自我回歸及周遭溫情的浸潤后發現心靈及人性漏洞,他開始自省,這是他心靈救贖的鋪墊。
三 對男權的反抗與心靈救贖
阿米爾對男性權威的崇拜導致他對哈桑的背叛,那么,自我救贖就意味著回頭尋找這一引發罪惡的源頭,這樣,救贖才具有對精神背叛的等值補償意義。阿塞夫對哈桑的性侵犯行為,這一行為在阿富汗可謂重罪,但當時阿米爾視而不見,也未舉報,父權崇拜是阿米爾冷漠的根本原因。多年后,哈桑的兒子落到阿塞夫手中,成了他的小男寵。如果說阿米爾的父親體現出男權的父性權威,那么阿塞夫則是阿富汗社會中的男性霸權代表。
青少年時期的阿塞夫已暴露出極端分子的端倪。當他提議性侵犯哈桑時,同行的伙伴面帶遲疑,他呵斥他們為懦夫并聲稱哈桑只不過是一個哈扎拉人。在阿米爾的生日會上,阿塞夫能說會道、拍馬阿諛,他送給阿米爾一本《希特勒自傳》,這一細節無疑是阿塞夫未來人生的某種隱喻。阿塞夫還侵犯過他的兒時伙伴——卡莫,卡莫在流亡路上因精神崩潰而死。阿塞夫對法律、教法的藐視可見一斑。
在小說中,阿塞夫是塔利班政府的小頭目,他的所作所為尤為極端。有學者認為:“無論是作為意識形態的伊斯蘭教思想,還是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都發展到了不正常的狀態,而塔利班政權卻繼續把它們視為維持自己統治的合法性資源,并有意識地加以推動,于是塔利班政權開始向極端主義的方向迅速滑落。”[7]34塔利班在20世紀末“把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思想賦予國家意識形態的崇高地位,把自己打扮成復興古老的‘民族’文化和傳播普遍性的宗教價值的角色”[8]143。作為塔利班的一份子,阿塞夫極為殘暴毒辣。他監督部下將犯有“通奸”罪的一對男女活活砸死,而這一切都是在“遵照”真主的旨意。一個為傳播伊斯蘭“宗教價值”的極端主義者,絕對奉行伊斯蘭教法之源——《古蘭經》。該經書在男女兩性問題上,“要求男女平等,這只是伊斯蘭教法婦女觀的終極認識目標,但它降示在封建的阿拉伯社會,它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父權社會,在這種時代,人們的婦女觀深深烙上‘男尊女卑’的印記”[9]。此外,塔利班在1997年奪取坎布爾后頒行了一系列婦女、文化問題的法令,法令在女性教育、婚姻、就醫甚至衣著方式上提出極為苛責的規定。[7]147這是塔利班政府對阿富汗社會男權至上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強化。因此,作為塔利班成員,阿塞夫的男權至上觀念也有跡可循。更讓人痛心的是,哈桑死后,他的兒子——索拉博——被阿塞夫從福利院帶走并將其收為自己的“男寵”,甚至玩弄“男寵”是權貴尤其是民兵領袖們社會地位的象征。
至此,阿塞夫身上體現的男權至上思想已毋庸置疑。可以說,他是阿富汗社會的男性權威代言人。顛覆打倒阿塞夫這一具有符號意義的代言者及心靈之罪的直接肇事者,將成為阿米爾滌清內心罪惡感、獲得內心救贖的唯一途徑。面對阿塞夫,
阿米爾不再如幼時那樣順從忍耐,他選擇對峙與反抗。他跟阿塞夫搏斗,那是他第一次跟人打架。內心充滿恐怖,說話也語無倫次,被對方的不銹鋼圈套擊倒在地,幾近死去,阿米爾躺在地上大笑,內心想著:“心病已愈,終于痊愈了”[5]279。此時,他獲得內心的寬慰與救贖。在阿米爾男權意識的流變里,他逐漸認清父與子的關系,理解親情與善意,擯棄狹隘的民族優越感,最為主要的是——阿米爾因崇拜男權而留下的心靈罪惡,在與阿富汗社會典型男權代表的搏斗中得到清洗與救贖。
結語
《追風箏的人》在救贖主題中還存在一條引線,這就是小說中的“我”與“男性權力”存在關系的流變。“心靈犯罪——反省——救贖”與“男權崇拜——擯棄男權崇拜—反抗男權”這兩條線路彼此交織,互相影響。甚至可以說,阿米爾的救贖就是其自身對男性權威的認識過程。
參考文獻:
[1] 余鋼.身份認同感的缺失及其尋找的焦慮[J].電影評介,2009(5):47-48.
[2] 曾萬泉.《追風箏的人》人物關系隱含的阿富汗民族關系[J].社會縱橫,2013,28(3):259-261.
[3] 蔣小慶.救贖中的成長——從成長小說的角度解讀《追風箏的人》[D].揚州:揚州大學,2010.
[4] 王建榮.《追風箏的人》風箏意象解讀[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8(2):91-94.
[5] 卡勒德·胡塞尼.追風箏的人[M].李繼宏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6] 卡爾文·斯·霍爾.弗洛伊德心理學與西方文學[M].包華富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7] 何明.塔利班的興亡及其對世界的影響[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3.
[8] 艾森斯塔得.帝國的政治體系[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9] 馬東平.論伊斯蘭教法之婦女觀[J].甘肅社會科學,2001(5):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