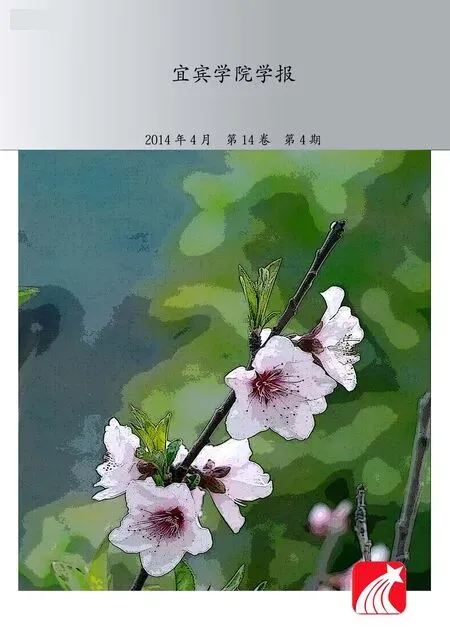白居易的旅游生活及旅游詩
方向紅
(黃岡師范學院 文學院,湖北 黃岡 436800)
唐代文人喜游歷,大多著名文人都有旅游的經歷。中唐大詩人白居易也不例外,他自言“性好閑游,靈跡勝概,靡不周覽”(《修香山寺記》)①。他不僅愛旅游,游歷廣泛,而且所到之處都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旅游詩歌。這些旅游詩是白居易豐富旅游活動的反映,也蘊含著他不同人生階段復雜而獨特的人生體驗。白居易一生主要的旅游活動,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初入仕時期,貶謫江州、量移忠州時期,任職杭州、蘇州時期,閑居洛陽時期。不同時期的旅游詩表現出詩人白居易不同的旅游心態和精神狀態。
一 初入仕途時期:“唯我多情獨自來”
白居易出身仕宦家庭,祖父、父親都是明經科進士。家庭的熏染和環境的影響,白居易少年時代就跟隨父親游歷。貞元九年(公元793年),白居易隨父到襄陽,趁此游覽襄陽的名勝古跡。襄陽是歷史文化古城,有諸葛亮隱居的隆中、羊祜的祠廟、孟浩然隱居的鹿門山等眾多名勝之地。白居易在游覽自然美景、憑吊人文古跡時,詩興大發,寫下著名的《游襄陽懷孟浩然》:“楚山碧巖巖,漢水碧湯湯。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今我諷遺文,思人至其鄉。清風無人繼,日暮空襄陽。南望鹿門山,藹若有余芳。舊隱不知處,云深樹蒼蒼”。白居易用“秀氣結成象,孟氏之文章”詩句高度評價孟浩然,孟浩然一生愛出游,“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經七里灘》),孟浩然的旅游經歷和旅游詩對白居易的旅游活動和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
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二十九歲的白居易一舉中進士,在同榜進士中他最年輕,初入仕途一帆風順。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白居易又以“拔萃”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中“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授周至尉;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拜左拾遺,后任翰林學士。白居易曾無不得意地說:“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貫”(《與元九書》)。從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白居易中進士始到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貶江州司馬止,這十五個年頭是白居易最意氣風發的時期,其旅游詩反映出他的旅游心態總體上是輕松適意的。如《早春獨游曲江》,詩人“散職無羈束,羸驂少送迎。朝從直城出,春傍曲江行”,曲江在詩人眼中景色宜人,“風起池東暖,云開山北晴。冰銷泉脈動,雪盡草芽生。露杏紅初坼,煙楊綠未成。影遲新度雁,聲澀欲啼鶯”,整首詩色彩明快,詩人心境愉悅適意。元和元年(公元805年)白居易任周至尉,這一時期是他旅游詩創作的重要階段。周至對白居易有著特殊意義,給他帶來盛名的千古絕唱《長恨歌》就是他與好友王質夫、陳鴻在周至“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相與感嘆”(陳鴻《長恨歌傳》)而創作。《元和郡縣圖志·關內道二》云:“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周至本作盩厔,山水曲折蜿蜒,風景清幽,名勝古跡甚多。白居易在周至縣很快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詩酒朋友,游遍各處名勝,寫下不少旅游詩,如《游仙游山》“暗將心地出人間,五六年來人怪閑。自嫌戀著未全盡,猶愛云泉多在山”。甚至游興之所致,白居易獨宿仙游寺,如《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質夫不至,獨宿仙游寺》“文略也從牽吏役,質夫何故戀囂塵。始知解愛山中宿,千萬人中無一人”,詩人心境平和,在山水自然中放松身心,悠然享受旅游的樂趣。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白居易因母喪回故鄉下邽守制三年。下邽在長安東百五十里左右,縣尉在渭河以北,渭河南岸有著名的華山。下邽雖是個村戶四五十家的小村落,但山水宜人,自然風光很不錯。白居易閑暇經常游覽,并與當地的村民結下了很深的感情。如《秋游原上》所描寫的“七月行已半,早涼天氣清。清晨起巾櫛,徐步出柴荊。露杖筇竹冷,風襟越蕉輕。閑攜弟侄輩,同上秋原行。新棗未全赤,晚瓜有余馨。依依田家叟,設此相逢迎。自我到此村,往來白發生。村中相識久,老幼皆有情”,儼然一幅人情味十足的鄉風民俗畫。下邽莊暮春的桃花讓詩人流連忘返,“村南無限桃花發,唯我多情獨自來。日暮風吹紅滿地,無人解惜為誰開”(《下邽莊南桃花》)。“唯我多情獨自來”,詩人雖守制遠離官場,但內心對生活的態度是積極奮發的,充滿了對美的欣賞和追求。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白居易與友人游藍田縣王順山的悟真寺后,寫下著名的一百三十韻的紀游長詩《游悟真寺詩》。詩人如導游一般細致描述游覽經過,“元和九年初,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順山。去山四五里,先聞水潺湲。自茲舍車馬,始涉藍溪灣。手柱青竹杖,足踏白石灘”,詩歌篇幅宏闊,精彩紛呈,敘事、抒情、寫景渾然一體。旅游給詩人帶來無窮創作動力,若非切身游覽體驗,詩人斷然寫不出如此感受之深的紀游佳作。
初入仕途的白居易生活順暢,政治熱情較高,反映社會現實的政治諷喻代表詩《新樂府》和《秦中吟》主要作于這一時期,此間的旅游詩無論是描寫自然山水,還是風土人情都充滿著勃勃生機。詩人在旅游中把生命的激情與自然和諧地融在一起,他的心境總體上是愉悅暢快的。
二 貶謫江州、忠州時期:“醉來堪賞醒堪愁”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此次之貶成為他人生的轉折點。白居易被貶江州的直接原因是他上書抓捕刺殺宰相武元衡兇手而獲“越職言事”之罪,究其深層原因,正如他在《與楊虞卿書》中所言:“然仆始得罪于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于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白居易獲罪主因是對當權者腐敗丑陋的無情揭露和批判,導致得罪權臣、積怨甚深。白居易無辜獲罪讓他的心情苦悶到極點,貶居江州、忠州的日子,“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怨恨一直壓在他的心頭。白居易貶赴江州的途中,沿途雖不乏美景佳色,但他途中所寫的游覽寫景之作,無不充滿凄涼惆悵感,如《初貶官過望秦嶺》“草草辭家憂后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須”,流露出詩人面對前途渺茫的孤獨、傷感。《登郢州白雪樓》是白居易經過秦國的故都郢州時,起岸登臨白雪樓所作,“白雪樓中一望鄉,青山蔟蔟水茫茫。朝來渡口逢京使,說道煙塵近洛陽”,登樓遠望,青山綠水,詩人不禁觸目傷懷,掛念著朝廷的安危。白居易抵鄂州時,友人盧侍御、崔評事在黃鶴樓設宴招待白居易,白居易宴會后極目遠眺,頭陀寺、鸚鵡洲的美景盡收眼底,“江邊黃鶴古時樓,勞置華筵待我游。楚思淼茫云水冷,商聲清脆管弦秋。白花浪濺頭陀寺,紅葉林籠鸚鵡洲。總是平生未行處,醉來堪賞醒堪愁”(《盧侍御與崔評事為予于黃鶴樓置宴,宴罷同望》)。詩結尾的“醉來堪賞醒堪愁”是詩人貶謫心境的最好表達,只有在酒中,詩人才能暫時沉醉在山水中忘卻憂愁。
白居易貶謫地江州,唐時屬江南西道,人口稠密,交通便利,被列為上州。江州左倚廬山,又臨長江與鄱陽湖,風景優美,著名的山峰有五老峰、香爐峰,寺觀有文殊臺、東林寺、西林寺等。白居易在無可奈何的逆境中,“從容于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簧、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茍有志于吏隱者,舍此官何求焉”(《江州司馬廳記》)。白居易在《答戶部崔侍郎書》一文中描述廬山“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他直接在廬山興建草堂,開鑿池塘,種植樹木,在世外桃源般景致中忘卻現實的煩惱。白居易的《題潯陽樓》直言對陶淵明的追慕,“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韋江州,詩情亦清閑。今朝登此樓,有以知其然。大江寒見底,匡山青倚天。深夜湓浦月,平旦爐峰煙。清輝與靈氣,日夕供文篇”,但他此時還并未忘懷政治,如《湖上閑望》“藤花浪拂紫茸條,菰葉風翻綠剪刀。閑弄水芳生楚思,時時合眼詠離騷”,詩人以遷客逐臣自居,以屈、賈自況;《春游二林寺》“獨有不才者,山中弄泉石”,直言政治失意;《晚題東林寺雙池》“臨流一惆悵,還憶曲江春”,失落苦悶之情溢于言表;元和十三年,白居易量移忠州,舟行岳陽登岳陽樓作《題岳陽樓》:“岳陽城下水漫漫,獨上危樓倚曲欄。春岸綠時連夢澤,夕波紅處近長安。猿攀樹立啼何苦,雁點湖飛渡亦難。此地唯堪畫圖障,華堂張與貴人看”,詩歌感情惆悵悲涼,詩人一直沉浸在遷客逐臣的失落苦悶中。
江州、忠州之貶給白居易的人生以沉重打擊,詩人初入仕途的積極用世之心在獲罪貶謫后逐步轉向消極避世,早年高漲的政治熱情被無情的現實一點一點磨滅。貶謫江州、忠州時期,白居易登山臨水、尋訪名勝古跡,在旅游中尋找生活的樂,趣化解悲苦的情緒,平息政治的失意,以獲得人生的安慰。
三 任職杭州、蘇州時期:“策馬渡藍溪,勝游從此始”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白居易終于結束了六年的謫遷生涯,回到京城長安。長慶二年,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白居易赴杭州與十年前被貶江州,心境大不相同,“一方面,他擺脫了主上荒縱,朋黨傾軋,政局紊亂的朝廷,不免有一種獲得解脫的愉悅和輕松;另外,他受命出宰的杭州,是一個戶數超過十萬,人口逾五十萬的江南大郡。治所錢塘縣,更是一個物產富庶,交通便利,湖山優美的好地方”[1]。因此,詩人無比興奮地且行且游前往杭州赴任,作于藍溪的五言詩《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最能代表他此時的心境,詩中寫道:“余杭乃名郡,郡郭臨江汜。已想海門山,潮聲來入耳。昔予貞元末,羈旅曾游此。甚覺太守尊,亦諳魚酒美。因生江海興,每羨滄浪水。尚擬拂衣行,況今兼祿仕。青山峰巒接,白日煙塵起。東道既不通,改轅遂南指。自秦窮楚越,浩蕩五千里。聞有賢主人,而多好山水。是行頗為愜,所歷良可紀。策馬度藍溪,勝游從此始。”出守杭州、蘇州時期,是白居易后期生活心情較好的一段時光。蘇杭的山水和名勝,讓白居易流連忘返,其旅游詩洋溢著欣喜、歡快之情。
歷代品題杭州山水名勝的詩作,當屬白居易的作品數量最多,影響也最大。《太平寰宇記》卷九三杭州云:“西湖在縣西,周回三十里,源出武林泉,郡人仰汲于此。為錢塘之巨澤,山川秀麗,自唐以來為勝賞之處。”[2]白居易對西湖景觀有開發之功,他寫下了大量題詠杭州山水的寫景詩。“杭州華麗雖盛于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錢塘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為多……皆錢塘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客子于解鞍系纜頃所見爾。城中之景,惟白樂天所賦最多。”[3]白居易的“繞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余杭形勝》),“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云腳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里白沙堤”(《錢塘湖春行》)等詩句再現了西湖綺麗的風光和詩人愉悅的心境。
白居易杭州、蘇州的旅游詩展示了他后期生活最為愜意的一面,蘇杭的湖山之美,詩酒交游的僚屬都讓他不忍辭別。與早年的旅游詩相比,蘇杭時期的旅游詩閑適有余,政治思想由兼濟轉向獨善。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已年過半百,進入人生的暮年,加上多年的貶謫困頓,白居易雖在職能勤政為民,但他的政治宦情已日趨冷落,縱游山水是他的主動選擇。在休官罷郡時,詩人表現出少有的解脫感,“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游山且看花。自此光陰為己有,從前日月屬官家”(《喜罷郡》)。白居易對朝廷政事、榮辱升遷已日漸淡薄,自然山水在他的眼中是那樣親近、和諧,往日的悲風苦雨已不再讓他系懷。
四 閑居洛陽時期:“眼看筋力減,游得且須游”
白居易文宗大和三年(公元829年)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至武宗會昌六年(公元846年)病逝,一直蟄居洛陽,白居易用他的“中隱”處世哲學演繹著余下十七年的晚年生活。《中隱》是白居易退居洛下不久,對自己心態的生動描述:“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君若好登臨,城南有秋山。君若愛游蕩,城東有春園。君若欲一醉,時出赴賓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歡言。君若欲高臥,但自深掩關。亦無車馬客,造次到門前。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在白居易看來,中隱是對大隱、小隱兩端的舍棄,居官如隱,仕隱無礙,追求無拘無束的世俗快樂。《唐才子傳》描述白居易晚年生活“卜居履道里,與香山僧如滿等結凈社,疏沼種樹,構石樓,鑿八節灘,為游賞之樂,茶鐺酒杓不相離。嘗科頭箕踞,談禪詠古,晏如也。”[4]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
白居易晚年的旅游詩充滿著及時行樂思想。大和四年,白居易因“去年來校晚,不見洛陽花”(《恨去年》)而遺憾,今年“聞道山榴發,明朝向玉泉”(《閑吟二首》),“花寒懶發鳥慵啼,信馬閑行到日西”(《魏王堤》)。大和五年,白居易身體不錯,“不準擬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游春猶自有心情”(《不準擬二首》),天津橋春景“柳絲裊裊風繰出,草縷茸茸雨剪齊”(《天津橋》)。大和六年秋冬,白居易先后游覽嵩山和王屋山,寫有《從龍潭寺至少林寺題贈同游者》、《宿龍潭寺》等多首記游詩。他在詩酒、山水的悠游中消弭對名利的追求,感嘆“七八年來游洛都,三分游伴二分無。風前月下花園里,處處唯殘個老夫”(《老夫》)的寂寞。面對生命的流逝,他極力勸導“眼看筋力減,游得且須游”(《且游》)的閑適享樂思想。晚年白居易心境平靜,悠閑自得的心境反映在旅游詩中呈現出平和之美,如《題龍門堰西澗》“東岸菊叢西岸柳,柳陰煙合菊花開。一條秋水琉璃色,闊狹才容小舫回。除卻悠悠白少傅,何人解入此中來?”
結語
白居易一生熱愛旅游,“忘形任詩酒,寄傲遍林泉”(皮日休《七愛詩·白太傅》)。旅游與詩人結下了不解之緣,旅游是白居易調整生活的重要方式,在旅游中,他化解了現實的煩惱苦悶,享受生命的無窮樂趣,尋求安康長壽之道。旅游為白居易提供了豐富的詩歌題材,他把旅游的獨特體驗寫入詩中,留下了大量膾炙人口的旅游詩。白居易的旅游觀及旅游詩對后世文人的旅游活動及詩歌創作影響極大,晚唐詩人皮日休、陸龜蒙,宋代詩人蘇軾、陸游等都深受其益。白居易的旅游詩,不僅是唐代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古代旅游文學的寶貴資源。
注釋:
①本文所引白居易詩文均出自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1979年北京中華書局版,引文只列篇名。
參考文獻:
[1] 蹇長春.白居易評傳[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4.
[2] (宋)樂史撰.天平寰宇記[M].王文楚,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1865.
[3] 葛立方.韻語陽秋·卷十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166.
[4] (元)辛文房撰.唐才子傳·卷六[M].周紹良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10:1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