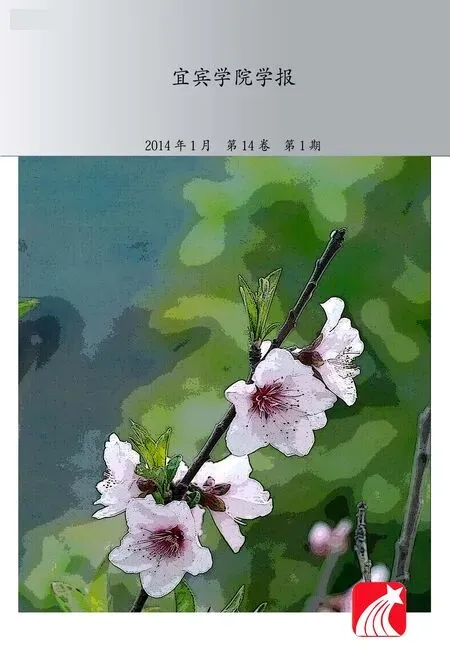近代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研究(1933~1946)
張 偉
(西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重慶 400715)
1899年,世界上第一輛公共汽車在英國誕生。1922年8月13日,上海出現了中國最早運營的公共汽車線路,此路線由華商公利公司開設。路線為靜安路寺到曹家渡外環,全長4公里,不設固定站點,招手即停,就近下車[1]76。這是中國公共汽車事業的開端。
相比之下,由于重慶是內陸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落后于上海、武漢、廣州等城市,重慶的公共汽車出現時間較晚。但是重慶在內陸地區具有特殊的地位。1890年3月,中英簽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重慶成為中國的第20個對外通商口岸,這奠定了重慶在內陸城市當中的特殊地位。從開埠到1929年,隨著重慶經濟的不斷發展、城市人口的逐漸增多和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展,致使原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不能滿足市民和往來商旅出行的需要,重慶的公共汽車事業也由此應運而生。
1929年8月,從通遠門外七星崗,途經觀音巖、兩路口、上清寺到曾家巖的公路建成,重慶的公共汽車通行于此線路。但是此時通行的公共汽車數量較少,并不具有公共交通的普遍性,因此根本談不上公共汽車事業。1933年9月,民生公司創辦人盧作孚以及何北衡、周舊嵐等社會企業家創辦了重慶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這是重慶公共交通史上的大事。重慶的公共汽車事業從此起步。
一 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發展過程
(一)公共汽車的出現
重慶商埠督辦公署時期,在四川軍閥劉湘的得力干將潘文華擔任督辦期間,潘文華效仿東部先進城市建設經驗,提出了他的城市建設方案。潘文華認為“至于城內交通,尤筑公路”[2]528。潘文華看到重慶城內公共交通的不足,認為發展市內公共交通的關鍵就是修筑市內公路。
1927年,重慶商埠督辦公署決定修筑新城區的馬路。1929年8月,通遠門外七星崗,途經觀音巖、兩路口、上清寺到曾家巖的公路建成。該公路全長3.5公里,路面寬度為25米,并規劃有人行道。這是重慶第一條現代意義上的城區公路。爾后,經過十年建設,到1937年底,重慶城區城市道路為21 566米。1949年,重慶則達到了149 904米。[2]474這些城市內道路的建設為公共汽車事業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礎。
1933年,重慶市政府公布《重慶市公共汽車招商承辦條例》,采用招標的方式吸引民間資本投入到公共交通的建設中去,這為公共汽車事業發展募集了大量社會資金,緩解了重慶公共汽車事業創辦之初的資金問題。
在1933年9月,民生公司創辦人盧作孚以及何北衡、周舊嵐等社會企業家創辦了重慶市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起初營業車輛只有一輛,公司資金五萬元。營運客車為從德國購買的一輛奔馳牌柴油客車,營運路線為曾家巖至七星崗路段。重慶第一條公共汽車線路正式營運。后來運營車輛添至5輛。實行分段行駛:由曾家巖至兩路口為一段,兩路口至七星崗為一段,七星崗至過街樓為一段。車票分臨時、長期兩種,“市民極口稱便”。但是最初,本市公共汽車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當中一度停運。[3]142
雖然車輛少,并且中途還出現了停運。重慶公共交通事業就在這樣的曲折中誕生并且不斷發展。
(二)公共汽車事業的發展
1936年,在四川省政府的催促之下,市政府又資助十萬元,市區公共汽車得以繼續運營。1936年2月,四川省公路局將成渝公路收回統一運營,巴縣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經重慶市批準,經營城區至瓷器口段的公共汽車線路。禁止民營公司汽車行駛,重慶的公共汽車業由民營轉變為政府經營。而后,重慶市政府又注入官股40萬元,購買公共汽車八輛,此時營運公共汽車十余部,一路行駛曾家巖過街樓之間,另一路行駛過街樓上榮元壩之間。1937年初,又開通了菜園壩到過街樓的公共汽車線路。此時,重慶市的公共汽車路線發展為三條。
抗戰爆發后,重慶市成為陪都。大量人口和企業內遷,刺激了重慶公共汽車業的發展,同時也為重慶公共汽車業提出了新的要求。到1939年底,重慶市公共汽車股份公司有客車37輛,其中抗戰后新購的為24輛。
1940年5月,市內公共汽車增加到26輛,新開曾家巖到小龍坎的郊區線路。1941年5月,由于物價高漲、管理不善,市政府決定對重慶市公共汽車公司進行資本改組,市政府加入政府股份100萬元,擴充后的公司股本300萬元。股本擴充后,該公司購置新車78輛,加上原有的能投入運營的車輛21輛,共計99輛。調整的公交路線有三路:一路是由過街樓經督郵街、七星崗至曾家巖,全長6.5公里;第二路由過街樓經南紀門至菜園壩,全長5.5公里;第三路經市郊路線,鏈接化龍橋、小龍坎、新橋、山洞至歌樂山,全長三十一公里。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正式發布命令,設重慶市為中華民國的陪都。這為重慶市公共汽車發展提供了機遇。隨著進入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困難時期,蔣介石有感于后方的軍公汽車運輸機構管理混亂,不能強有力而發揮最大作用。蔣介石于1941年3月間主持召開了一次交通會議,作出決定,在軍事委員會下面成立運輸統制局由何應欽兼管。
1941年7月,全國公路運輸軍委會運輸統制局接管,重慶市的公共汽車業務由新成立的運輸統制局重慶市公共汽車管理處進行管理。從最初的民營再到重慶市政府經營,再到此時的國民政府統制局管理。國民政府的重視反映了重慶城市地位的提升以及公共汽車事業在抗戰時期的重要性。
重慶市公共汽車管理處,是在運輸統制局成立后半年內七廠該局管制,以原任車務管理組第一科少將科長黃壽嵩調任公共汽車管理處處長,并由監察處派軍統特務石振江駐該處[4]210。
管理處成立之初,接管車輛共41輛,其中能行駛的僅僅是16輛,行駛干線4條,總長89.5公里。到1944年底,車輛達130輛,其中能行駛的公共汽車為93輛。據黃壽嵩《重慶公共汽車概況》我們可以更為細致的了解此階段公共汽車的營運及發展狀況。
一線路。
市內路線,分普通客車及特別快車兩種,普通客車,行駛于曾家巖至過街樓間,計長六公里半。特別快車,起自上清寺,至儲奇門仍折回上清寺,繞一圈子,計長十三公里。郊外路線其一自七星崗至北碚,長八十三公里;其二自南路口至九龍坡,長十六公里;其三,自兩路口至石橋鋪,計長十三公里。總計郊外路線全長一百零九公里。
二設備。
關于車輛方面,本處現有客車計一百三十五輛,除一部分備供接收南泉土橋二線后用外,現應用之車輛一百零五輛,每日行駛車輛約七十輛,估百分之七十左右。關于修理設備方面,本處現有修理廠一所,保養廠四所。
三業務。
本處車輛,本年三月份之車公里為三十一萬五千公里。至市內方面,前年十二月每日行車十二輛全月乘客五十萬人,最近每日行車三十五輛,每月乘客約一百二十萬熱,可知乘客人數增加二倍半,而車輛增加三倍。[5]
從黃壽嵩的報告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重慶市公共汽車線路、設備和業務狀況,雖然在此階段內公共汽車營運里程、人數以及線路數量不斷增加。全月乘車人數達到五十萬人次,可見公共汽車已經成為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抗戰時期,重慶的公共汽車事業還獲得美國的幫助,凸顯了重慶在戰時的國際地位。美國根據租借法案,曾經供應重慶市公共汽車管理處公共汽車十八輛,除其中一輛由立法院使用之外,其余在昆明裝配車廂后,在重慶市內行駛。[6]援助的公共汽車有十八輛,占當時運營公共汽車數的近五分之一。美國的援助對于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公共汽車事業的衰落及衰落的原因
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的衰落主要表現是營運車輛減少,線路無法維持正常運營。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重慶市政府接管公共汽車事業,該項城市公用事業經營狀況日趨惡化。公共汽車管理處的車輛由戰時的100多輛陸續減少到不足40輛,多條公交線路尤其是市區與郊區之間的線路難以維持正常經營,有些線路無法經營。
重慶市公共汽車事業慘淡經營,舉步維艱。到重慶市解放前,公共汽車管理處每天出車僅10輛到20輛,而且運營路線僅僅市區內和兩石九線等柳條線路勉強維持運營。[4]230重慶市的公共汽車事業已經衰落到了難以維系的地步。
重慶公共汽車業的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乘客減少。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重慶不再是實質上的首都。城市地位下降。城市地位下降直接導致了人口的外遷。黨政軍機構遷回南京,而且一些原來來自沿海的工礦企業、學校也陸續遷回沿海等地,城市人口也相應大量減少。人口減少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戰時避難重慶的難民以及民眾陸續回鄉,這都導致了重慶城市市區的乘客聚減,公共汽車事業收入急劇下降。第二,資金缺乏。在抗戰勝利后至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前這段時間內,盡管中央行政院已不再直接管理該項事業,但并沒有取消在抗戰時期制定的對公共汽車事業的補貼。1946年4月起,行政院取消了該項補貼,這使資金缺乏的狀況雪上加霜。第三,通貨膨脹嚴重,公共汽車公司入不敷出。當時正處于惡性通貨膨脹中,法幣貶值,市內票價一再調高,每站票價曾漲到16萬元,仍然入不敷出,虧空巨大,不能維持營業。管理處長幾次換人,亦回天無力。無可奈何乃將小龍坎保養場的全部財產,以及高灘巖修配廠的舊廢器材,出售與車商。隨即撤銷保養場,裁減大批員工,緊縮開支,勉強維持。不久,又將市區二、四線及郊區全部路線,出包給商車及校車行駛營業。市區只保留一、三兩線,由管理處的幾輛破舊車子繼續行駛,奄奄一息,拖至解放。[7]59第四,經濟崩潰導致對公用汽車的需求減少。抗戰勝利后到解放戰爭前,國統區內法幣貶值、物價瘋漲,各種物資特別是油料也相當緊缺。這是外部經濟條件惡化,直接導致了市民對公共汽車需求的減少。第五,管理不善。無票乘車的現象屢見不鮮,行車秩序時常出現混亂,因乘車或與公共汽車有關而引起的糾紛、打架斗毆的情形也常常出現。管理的落后,外部經濟環境的惡化,是壓倒重慶公共汽車業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 重慶公共汽車發展的特點
第一,特約校車——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的獨創。值得注意的是,重慶市公共交通還有自己的發展特點。針對客運量猛增,公共汽車無法滿足市民乘車的需要的狀況,重慶市公共汽車管理處與1942年1月起,先后與民營的中勝、大中等六家汽車公司簽訂了租車協議,成立了重慶到北碚路線機器區間的6條線路營運。后來校車數量由開始的15輛增加到23輛,重慶市公共汽車發展高峰時的五分之一運營車輛運行在重慶大中院校所在的渝瓷線、渝碚線以及海棠溪至南溫泉重慶至丁家坳、璧山、銅梁等公路之上。
第二,最早的衛星城概念交通——遷建區和主城區之間的公共汽車線路。為了瓦解中國人民的抗戰意志,迫使國民政府投降,日軍對重慶實施無差別大轟炸。國民政府為此采取了人口遷徙計劃,將重慶市區機關和人口緊急大疏散,大批內遷學校、工廠都遷往郊區。為加強遷建區和主城區之間的聯系,重慶開通的公共汽車線路除原開設的七星崗至歌樂山路線外,新增設的線路有:重慶到北碚的渝碚線,兩路口到石橋鋪的兩石線,兩路口到九龍坡的兩九線,海棠溪至南溫泉的海溫線,兩路口到青木關的兩青線,七小線七星崗到小龍坎。陪都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城市公共交通網。這可以說是最早的現代城市發展理念——衛星城交通發展的范本,對緩解大城市交通緊張狀況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三,跳躍式的發展。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公共交通最初是有軌電車。1881年5月16日,世界上第一輛有軌電車誕生。兩年后,1888年,世界上第一條有軌電車線路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里士滿投入商業運營。后來,中國的開放城市上海、漢口、廣州等也先后開設了電車。但是重慶并沒有出現這種公共交通方式,而直接發展了公共汽車,這中間出現了一個斷層,出現跳躍式發展的現象。出現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地形方面的原因,重慶是山城,城市發展比較分散,而且市內道路較為狹窄,不適宜電車的運營;經濟發展方面的原因,雖然重慶自開埠以來,經濟迅速發展,但是相比上海、廣州和漢口來說,經濟還遠遠落后于這些城市,經濟落后,缺乏建設資金,因此辦理電車事業自然也是非常困難的;政治方面的因素,劉湘統一四川前,四川和重慶地區深陷地方軍閥混戰泥潭,這必然破壞了社會事業的正常發展,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開始城市建設事業也只能是癡人說夢。
三 影響重慶發展公共汽車事業的因素
縱觀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發展,重慶城市規模的擴大、市區人口的增加是刺激公共汽車事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對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給公共汽車事業發展提供了發展條件。重慶大轟炸是另一個影響公共汽車事業發展的不確定因素,導致重慶公共汽車事業出現與其他城市不同的特點。
第一,城市規模的擴大。重慶城市規模的擴大表現在城市空間的不斷擴展,也就是城市占地面積的不斷擴大。開埠以前,重慶的主城區位于兩江環抱的半島上,依山傍水而建。城區面積不但狹小,而且城內街道布局凌亂、狹窄,缺乏規律,市內的道路的落差較大。如南北向的街道大都依山而建,靠階梯連通。再如市內道路狹窄凌亂。“全城依崖為垣,彎曲起伏,出處現出凹凸,陜西、督郵各街,僅寬10余尺。其他街道尢窄。[8]26這很不利于市內人員和物資的流動。
1921年,四川軍閥劉湘設置重慶商埠督辦于重慶,任命楊森為督辦。楊森提出了自己的城市拓展方案。楊森想“先開辟北岸,擬自江北縣城外打魚灣,下至唐家沱一帶,沿江筑堤三十里,以為輪船泊步,原有舊城商店、堆棧悉令他悉以整齊之”[9]。后來按照此計劃,新區建設和舊城改造陸續開展。1922年7月,劉湘與賴文輝、鄧錫侯之間的軍閥戰爭爆發,劉湘兵敗,督辦楊森敗走宜昌。自此城市建設史上的第一個拓城建設就此打斷。直到1926年5月,劉湘重新占領重慶以及川東,城市建設又回到了正規上,城市真正的拓展由此開始。
到30年代中期,城區又從臨江門、通遠門、南紀門一線向西不斷擴展,曾家巖、兩路口、兜子背一線成為城區,面積增加近兩倍。這就為城市的進一步打下了基礎,同時也積累了城區建設和拓展的經驗。而此時江北區從有當時的“四川內地的小日本國[10]”之稱的日本租界也拓展到了南岸區的彈子石、玄壇廟、海棠溪、瑪瑙溪、南坪、銅圓局以及王家沱一帶,并且被設置為市內第六區。人口已達64 512人。
1940年,重慶西郊地區劃為重慶市直接管轄。根據相關資料統計,1940年底,重慶由原來的六區擴展為六區,此時的城市面積達到了328平方公里。[11]1157
1941年,重慶市設立了歌樂山區、瓷器口區和石橋鋪區三個行政區。至此,重慶市城區在西部和南部地區的城區擴展至此。
隨著城區的拓展,舊的城市交通工具已經不能滿足城市發展和人員流動的需要,新的交通工具也應運而生。滑竿、轎子被新式公共交通工具人力車和公共汽車所取代,重慶的公共交通業事業也隨之建立,并不斷發展。公共交通事業與城市規模的擴大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城市規模的擴大是公共交通產生和發展的原因,但同時城市規模的擴大,又促進了公共交通事業的發展。
第二,人口內遷導致的市區人口的增加。重慶在抗戰以前,市區人口只有四十萬,但是抗戰爆發后,經過幾次移民潮,到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之前的1946年,重慶的市區人口達到了124萬[12]。人口翻了三倍多。市區人口的增加,再加上市區空間的擴展,導致市民公共交通需求的增加。這既給公共汽車業發展提供了廣大的客源,同時也對重慶公共汽車事業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三,重慶大轟炸是重慶發展公共汽車事業的不確定外在因素。1938年到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實施了長達五年的無差別轟炸。[13]4重慶大轟炸不僅造成城市市民的大量傷亡、成片的城市建筑房屋淪為瓦礫,而且也對重慶城市公共汽車的正常運營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重慶大轟炸對重慶城市公共汽車事業的破壞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區道路的毀壞,二是對客運車輛及對公司房屋的轟炸破壞。在日機發動對重慶城區密集性大轟炸的過程中,城區道路毀壞相當嚴重。公共汽車公司不得已改變了自己的經營時間。由于日機一般在白天轟炸,所以公共汽車公司不得不放棄了它們出行的高峰時段,避免在白天運營“據重慶市政府訓令: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本年七月有一訓令,‘該公司七月十九日呈擬房屋汽車被炸請設法救濟一案’”[14]。據統計,在那段時期內損壞的公共汽車中大多都直接或間接與日機對重慶城區的轟炸有關。
敵機還對公共汽車房屋或售票站點及車輛修配廠房等地方的轟炸。“在新市中四路一三零號,六月十二日敵機襲渝被炸,除廚房一隅外,所有全部房屋暨一切用具陳設物品以及五金器材損毀,是日停廠待修之車計三十四號、二十八號、二十二號、十九號等四車亦被炸毀。
“商公司”乃將原中四路三零號院內職工宿舍作為臨時辦公地址。后于本月八日轟炸波及房屋損失一部,器具全毀,并將停車待修理之八號、十八號客車兩輛,卡車一輛被毀。再六月二十六日開往防口口之卡車一輛及二十八日開往通遠門外交消防總隊借用之卡車一輛亦被炸毀。公司在此一月中兩次被炸,房屋毀壞、車輛損失玖輛,數字實足,現正著手統計清算之中[14]。
公共汽車被炸,市區道路被毀,運營時間改變,公司房屋及車輛修配廠房被炸。不僅造成了公共汽車公司的巨大財產損失,同時對公共汽車的整體運營、車輛的維修都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從而使原本運營狀況都顯得十分緊張的局面更加艱難。
參考文獻:
[1] 虞同文. 上海公共交通的由來[J]. 交通與運輸,2012 (4).
[2] 隗瀛濤. 近代重慶城市史[M]. 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
[3] 王瑞芳. 近代中國的新式交通[M].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 楊實. 抗戰時期西南的交通[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
[5] 黃壽嵩. 重慶市公共汽車概況[J]. 交通建設,1944 (7).
[6] 美租借法案下供應我公共汽車十八輛 [N].中央日報,1943-08-05.
[7] 王立顯. 四川公路運輸史 [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8] 潘文華編.九年來重慶之市政(第一編)[Z].1936.
[9] 向楚. 巴縣志(18)[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 .
[10]重慶日租界的發展[N].新蜀報,1931-10-21.
[11]周勇. 重慶通史[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 .
[12]程朝云.戰時人口內遷與重慶[J].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2卷,2002.
[13]西南師范大學歷史系,重慶市檔案館. 1938—1943:重慶大轟炸[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14]重慶市檔案館.關于重慶市公共汽車股有限公司房屋汽車被炸損失慘重請求救濟的呈、指令[Z].民國檔案,全宗號 0053.目錄號 0012.卷號 00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