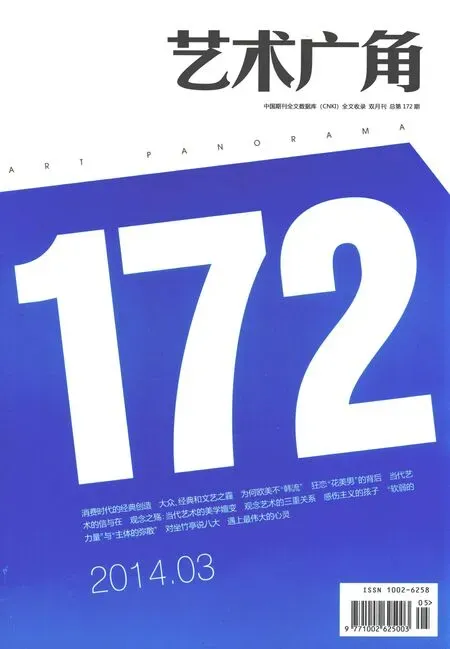感傷主義的孩子
——周云蓬的寬度和限度
劉大先
感傷主義的孩子
——周云蓬的寬度和限度
劉大先
1994年,大學畢業、不愿意接受社會福利的盲人周云蓬開始了自己的流浪歌手生涯。這個節點性的時間,正是中國城市民謠興起的時候。從中國當代音樂譜系來看,城市民謠的興起是搖滾樂剩余力量流散的結果。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興起到上世紀90年代初期極盛而衰的中國搖滾,本來是在文化匱乏中渴求信仰與思想,進而以西方搖滾形式在既有的意識形態和價值系統中撕裂而出。然而,一方面,90年代本土政治與經濟發生轉型,進入所謂后革命時期,讓搖滾的反叛性內涵消弭于無效;另一方面,全球性的資本與信息,帶來更為多元主義的文化選擇和價值取向。應和著城市化的進程,校園民謠轉而向都市民謠發展,這是民族與民間的音樂傳統反哺于現代西來流行音樂形式,兩者相結合的產兒。最主要的是,城市的發展也給周云蓬這樣的歌手帶來生存的空間。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下,才能更準確地理解他的歌、文和人。
周云蓬一開始是以流浪歌手身份出現的,而此后這變成了他的形象,因為這個形象本身充滿了可以滿足都市文藝愛好者有關異域、遠方、江湖的種種想象——他們自己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做到的事情可以通過心向往之的方式在這樣的形象中找到落腳點,所以這種形象本身就具有了消費的價值。而他又是以盲人身份出現,更因集體記憶的積淀而為這種形象增添了傳奇性的色彩。
盲人為樂官,是古典中國的傳統,《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其中的演奏人員有“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而《周頌》中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可能在當時人的心目中,瞽者被認為不受目迷五色之惑,而更方便以精神溝通天地人神。春秋晉國的盲臣師曠更是在擅琴鼓瑟之余大治晉國,《左傳》記載楚國進攻晉國時,師曠說沒有關系,因為他在演奏北方音樂和南方音樂的對比中,聽到“南風不競,多死聲”,因而楚必無功而返。音樂在這里就具有了神奇的預示功能,其根底里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所以后來就會出現《毛詩序》中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風采樂,因而就成為君主了解民眾俗情的重要途徑。“古人將歌謠稱為風,也許不僅是因為歌謠像風一樣風靡大地,感人至深,更是因為歌謠也像風一樣,有一定的季節性,隨四時光景的轉換而流轉。歌為生命的心聲,生命在不同的季節有不同風格,因此,不同的季節就有不同的歌聲,歌發四季,四季如歌。”(劉宗迪《古典的草根》)民謠中包含著民間的智慧和民眾的心聲,直至今日也依然被認為是不悖的真理。
從西方來看,也有類似的文化原型。古希臘的史詩據說就是盲人荷馬的杰作,15、16世紀彈著琉特琴的游吟詩人也是歐洲文化中的常見形象。“這些大地上的游吟者,游走在村落間,歌唱在人群里,身份更接近于說書藝人。他們不專事于寫詩,節律性的長短句只是方便吟唱的必需。他們也不專事于記敘歷史,說歷史、傳信息、談論時事變故,是說書娛人混飯的本錢。民謠藝人們著眼于生活,以敘事為主體,把唱歌當說話,包容了生活的全部內容。……游吟者不只是游吟者,還是民間詩人、酒徒、信息傳播者、諷喻現實的小丑、助興人、詩誦家、史詩雜匠;由于傳布廣遠,全憑口耳相傳,有時同一首歌流傳的版本多達一百多種。”(李皖《多少次散場,忘記了憂傷》)游吟者的后代在今天就演化成周云蓬這樣的民謠歌手,他們是口頭文學在當代的遺留物,一項卑微、似乎在大眾傳媒興起中已經奄奄一息,卻終究因應時變、默默前行的文化遺產。
周云蓬在一篇名為《民謠是什么》的短文中對自己心目中的民謠做了一個詩意的描繪:它是單車上的純真戀情,是千辛萬苦尋找失蹤兒子的父親偶爾一次的回到自我,是漫無目的的疲憊旅途中的一次迷失……
是你騎自行車,在夢里。
你老百姓今天真高興,蹬呀蹬,
左手扶著車把,右手拄了一根盲杖。
實際上,你根本沒看過自行車,你走路還得人領著呢。
你也沒坐過飛機,在夢里,飛機上有個售票員,在座位間走來走去,她讓大家買票。
你也沒親近過女人,
在夢里,她是早上剛出鍋的煮雞蛋,
你吹著氣,小心地一片一片撥開,
先是指甲蓋大的熾熱軟潤,
然后逐漸擴大,
越來越燙手,
越來越不敢撥。
這種詩意化的描述往往遮蓋了民謠和民謠歌手背后的艱辛旅程,當然,也可以視作是一種生活審美化,在歌謠中超拔世俗煩冗生存狀態的努力。周云蓬對此心知肚明,事實上他自覺地把自己與小河、萬曉利、野孩子、趙牧陽等人的音樂稱為“新民謠”。在《江湖夜雨十年燈——關于新民謠的孩提時代》中,他回顧2005年小河在798策劃的一場民謠音樂會,第一次冠名為新民謠,以區別于當年的校園民謠。2006年,張曉舟在深圳體育館組織“重返大地——2006中國民謠音樂周”。2007年,“迷笛”音樂節設立民謠舞臺,人氣和主舞臺不相上下。同年,萬曉利獲得華語音樂傳媒大獎“最佳民謠藝人獎”,打破了港臺藝人對此項獎的壟斷。這一系列事件在很多民謠歌手和聽眾那里也許不過是無數文娛事件在新世紀的經濟繁榮中獲得生存空間擴展的證明,而周云蓬則把其中美學自覺的訴求點化了出來。
經過大約十年的北京與異地游唱生涯,周云蓬已經小有名氣。他連同“新民謠”對校園民謠的替代性登場,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宏大敘事式的對抗性政治幻覺的完結,新經濟模式下被侮辱與損害者的表達欲求,文化多元主義狀態的興起……還有不可忽視的是,“它得力于互聯網的自由傳播,人們對于宣泄自己心理訴求的渴望,以及平易近人的現場音樂的回歸,仿佛多年前的天橋撂地,梨園捧角兒。”技術帶來的變革,既是新語境中音樂方式的內部轉型,同時也是亙古不變的“歌永言,律和聲”的當代變體,甚至連接受方式從本質上說也繼承了先輩的傳統。
在《瞭望東方周刊》的采訪中,周云蓬清晰地剖析了新民謠與高曉松等人的校園民謠的區別:新民謠帶有強烈的草根性與社會現實感,因為“我們更多是在城市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環境中掙扎的人。”對校園民謠,周云蓬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所有的人都是不變的三拍子,好像校園民謠就是青春氣息這點東西。其實它沒有反映出真正的校園。”其實,早期大陸校園民謠的歌手比如老狼也時常是周云蓬聯袂演出的伙伴,他之所以這么說,是有一種長久底層生活賦予的底氣——無疑,至少從經歷上來說,他接觸的社會廣度和思考的深度已經大大越過了校園和青春的體裁,夾雜了民謠傳統的積淀、搖滾樂的殘余、通俗流行樂的營養,因而不免氣盛言宜。
在一首叫做《不是詩》的詩里,周云蓬給自己勾勒了一幅肖像:
我在中國的最底層
在人最多的地方
喝最便宜的啤酒
詛咒塔尖上的人
和虛偽的光
我的情人是個丑姑娘
她只上過小學
我是個快四十歲的中國男人背負所有免費的公廁
所有不衛生的熟食攤
所有痛苦的公共汽車
所有麻木的黑白電視
所有口蜜腹劍的主持人
十三億潮濕的軀體
就算我是最下面的一塊磚
即使如此
就算這樣
這是多年流浪生涯淤積的意象和情緒,同時在極端意義上也構成了新民謠歌手的心理群像。豐富的經歷造就了源自個體經驗的詩歌,體現的是彌漫在底層空間的普遍性情感,對于命運的逆來順受和敞開懷抱矛盾性地交織在一起,對于集體性公共話語虛偽的憤懣最終溶解在不屈服的姿態之中。有時候這種個體經驗會導向更為宏闊的社會層面,它顯然是間接經驗的轉化,比如《中國食物鏈》:
一個香港佬
在深圳包了個年輕女人
女人抽空愛上了一個來自山東打工的小伙子
小伙子把得來的港幣寄給留在家鄉的姑娘
姑娘把一部分錢分給整天喝酒的弟弟
弟弟在盤子里夾起一塊排骨
丟給跟他相依為命的短腿狗
狗叼著骨頭舍不得吃
把它埋在樹下
一只螞蟻爬上骨頭
發愁
盤算著
要叫多少螞蟻來
才能把這塊大骨頭搬走
極簡主義的詞句將社會層級結構觸目驚心的利益與關系網絡呈現出來,以至于形成了類似民族寓言式的漫畫場景。零度情感的抽象抒情,在客觀主義中把態度和判斷留給了受眾。但是這種抒情固然可以引發同情共感,卻不可避免要走向感傷主義。在各地的巡演中,周云蓬屢次倡導痖弦作詞,李泰祥譜曲,齊豫原唱的《四匹馬》:“誰在遠方哭泣呀/為什么那么傷心呀/騎上金馬看看去/那是昔日。 誰在遠方哭泣呀/什么那么傷心呀/騎上灰馬看看去/那是明日。 誰在遠方哭泣呀/為什么那么傷心呀/騎上白馬看看去/那是戀。 誰在遠方哭泣呀/為什么那么傷心呀/騎上黑馬看看去/那是死。”昔日、明日、戀與死,唯獨缺乏的是“今日”和當下的生活,他在為失去的黃金歲月(如果有的話)而哭泣,為不可知的未來而憂慮,為愛高歌,為死痛心疾首,但是找不到今天的出路。就像崔健那張具有象征意義的專輯《無能的力量》這一名字所暗示的,這種尷尬局面是上世紀90年代之后歌者的普遍經驗。歌者的無能為力不僅在于主體力量的卑微和弱小,更在于整個社會語境再也不能把集體性的共鳴轉化成有效的政治能量。像那首最為著名的《中國孩子》,周云蓬只能把社會新聞作為集錦一般直白地唱出來,“不作中國人的孩子”,也僅此而已。因為無法擺脫既定的命運,社會差距造成的失落感,與自然生理的缺陷,讓他特別敏銳與感傷。他從自己身體的局限和經驗的齟齬中,感受到整個社會的痛感,由身體的殘疾引申到世界的殘疾,那些黑窯工、失蹤的人、失業者、喪失現實和精神上雙重家園的游民……就是他的同路人,他同他們齊步而行,一路嗟嘆呻吟,終究不知所終。這是種并無獨特之處的多愁善感,是我們時代無權無勢者真切的現實與內心。
周云蓬面對的是整體性消解后的破碎時空,他所鐘愛的詩人海子,止步于九十年代的門檻。“詩人之死”具有的象征意味在海子之死中達到極致,詩歌作為立法者的地位讓位給了更加繁復的社會過程,與詩學社會的終結并生的是經濟學社會的誕生。在這種轉型里,“詩人何為?”用周云蓬的話說,他們只能“坐在路邊小聲自語/這世界不好/不幸福。”這已經是近乎撒嬌的做派,卻連撒嬌的對象都找不到了。回憶圓明園的盲流生活時,周云蓬不無尖刻地反思了原先不切實際的理念:“那時大家談得最多的藝術家是凡·高,因為通過傳記知道他很窮,而我們也很窮,起碼在這一點上我們等同于凡·高,但貧困不等于偉大的藝術,很多藝術家陶醉于自己的悲劇命運中,他們事實上愛的不是藝術,而是貧困,愛上了虛妄中的悲劇英雄。”而“我只有埋頭于生活里,專注地走一步看一步。音樂不在空中,它在泥土里,在螞蟻的隔壁,在蝸牛的對門。當我們無路可走的時候,當我們說不出話的時候,音樂,愿你降臨。”從藝術的虛幻回歸現實的生活,好在還有音樂,搖滾的政治激情和詩歌的超驗想象結合起來,讓民謠歌手得以安身立命:“生活是清醒的水,歌聲是如夢的酒。生活是直覺的自由,歌聲是幻覺的蜃樓。這些有著世界上最壯麗的傷口的人,在幻覺的導向下,讓傷口流成了一首澎湃的歌。”《新疆西游記》中,周云蓬寫道:“音樂應該是那種可以消除人與人之間恐懼的最好的鑰匙”,這是無奈的選擇,也是必然的選擇。
其結果是在周云蓬的吟唱中,盡管有批判,但是批判的對象是個無名的實體存在,一種抽象總體,就像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讓批評者無從入手,甚至批判本身也會被納入到它的邏輯結構之中。周云蓬在這里顯示了他的狡黠,就像他的朋友說的,他很少會對人對事做出個人化的評論,這可能是混江湖的基本生存智慧。排除這種誅心之論,周云蓬的身體體驗會影響到他對于歷史和現實的理解方式。他的心意中理想的民謠應該避免“民間”與“官方”或者類似結構上的二元對立,無疑是從另一面體現了他內在的欲求:以個人幸福、個體反思、美學趣味去疏離社會化敘事。
《聲音與憤怒》的作者張鐵志認為,大陸有必要出現憤怒、抗議型歌手。周云蓬在這一點與他發生了分歧,他反而認為此類音樂越少越好:“我更主張大陸出現小花小草類似卡奇社、蘇打綠這種。像大陸這種土壤,就別老出現很大氣、很公眾型的歌了。我們的根源在于缺少個人主義,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公民社會的土壤,而不是又出現一個偉人、英雄。”他提出要警惕社會議論式的歌曲,這種歌固然因為扣著熱點與焦點話題與情緒,容易獲得熱烈的反應,但公眾的心態比較復雜,很多時候不過是借歌曲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躲在安全的文本帷幕之后發泄浮皮潦草的情緒。所以,當憤怒成為一種常態和姿態,就容易陷入到被外在事物左右的陷阱,很容易喪失自我。“我首先看重的是音樂的審美,而不是過分應景。所以也警惕自己不能進入一種公眾的慣性中。音樂的本身就是音樂,其他像公眾性、教育性、道德性,都是附帶品。像詩歌本身就是詩歌,它可以承載道德,也可以不承載,但第一性是詩性的。音樂也是這樣,不能把它淪為一種工具……我們現在貶低小清新,你可以不喜歡,但應該尊重他們。他們培養了一個大批個體的土壤,有這個土壤,將來我們才可能唱我們自己的歌。”自我的反思和包容的心態,表明了他的自覺和自知。
到這里周云蓬的音樂理念已經清晰地凸顯出來:“人生如果不是作為審美對象,它便毫無意義。”“歌就是一個副產品,那么多經歷,那么多故事,最后變成一首歌,但它們的目的并不是變成一首歌,它們是沒辦法了。你要知道那些經歷是為了一首歌,你非氣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寫。你會想,別寫那首歌了,寧愿經歷好一點。都是陰差陽錯,一種情緒,漚著,排泄不掉。”歌永遠只是生活的一個部分,這其中并沒有值得自豪的資本或殉道式的悲壯。這并不是新鮮的觀念,然而周云蓬很巧妙地將其表述出來,表述本身的修辭性賦予了陳舊思想以華麗的外衣。陳舊并非必然意味著過時,因為民間的時間給予生活以無限性,從而讓其具有了命運的形而上意義。周云蓬對于文字的精煉把握,讓他從眾多民謠歌手中脫穎而出,如果通讀、聆聽他的所有作品,就會發現他是個一流的詩人,僅《不會說話的愛情》就足以超越大多數所謂的詩人;他也是個二流的評論者,因為他雖然有關懷,卻囿于身體和學識的局限,只能停留在普通民眾的見解,而不具備真正知識分子的洞察;他更是三流的歌手,雖然他以此身份為名,但樂器、演唱和應對聽眾的技巧只能說差強人意。從《牛羊下山》《清炒苦瓜》里的曲目可以看到,周云蓬的總體風格是淳樸天然,他往往采用橫云斷峰、戛然尖新的意象呈現法,突出細節,又不同于口語詩,與其他敘事性較強的民謠相比,他更注重抽象的抒情。但是藝術或技巧上的粗糙并無關大局,內心體驗的豐富才更重要。
從周云蓬的寫作和歌唱乃至“在路上”式的生活方式中,可以看到許多與上世紀60年代全球性“反文化”的互文性。就像“垮掉一代”的那一撥毀于瘋狂的天才,“我到處走,寫詩唱歌,并非想證明什么,只是我喜歡這種生活,喜歡像水一樣奔流激蕩。我也不是那種愛向命運挑戰的人,并不想挖空心思征服它。我和命運是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們形影相吊又若即若離,命運的事情我管不了,它干它的,我干我的,不過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罷了。”早先的“無因的反抗”或者激進的訴求已經消弭于無跡。他的自我想象資源源于日常主義的經驗,也終于此。這個置身事外的形象證明周云蓬像他同時代的無數文藝青年一樣,其思想來源因為被大眾媒體泛濫地放大而變得膚淺和扭曲。但是也無法證明下面的表述全然虛偽:“克爾凱郭爾把人生分為三種境界,即:倫理的,審美的和信仰的。我但愿能置身于審美的光明中。我是一個殘損的零件,在社會精密的大流水線上派不上什么用場,那就做一個玩具,有朝一日交到一個窮孩子手中。這正如莊子所喜的:無用者大用。于我而言達不到一定的速度,是無法克服重力的,飛翔僅當那時才成為可能。我的愛尚且不夠,因此病苦還不夠深邃。”這里分明回響著塞林格筆下那個麥田的守望者的聲音。
這種選擇其實是城市民謠的宿命,因為鄉土之根已經斷絕,而周云蓬這樣在衰落的工業區長大的孩子從來就無法吟唱出美妙的田園牧歌。“無用之用”是從堅硬壁壘中鑿空混沌,抒泄郁結,以文化上的象征價值獲得世俗社會中殘存的驕傲。他的受眾顯然不是農民或者農民工,而是城市小資、文藝青年,因而事實上缺乏廣闊的傳播場域。
敏感、細致、細膩、明心見性式的審美追求,讓周云蓬具有極強的感受力。同時,也注定他逃脫不了題材狹窄、格局仄小的窘境——外在的不可為使得他不得不向內轉,只是訴說自己的故事。作為個人最真實的理想狀況是求得一個“希臘小廟”式的烏托邦,那個《青春療養院》中的大理,就像童話《小王子》里的國王、銀行家、點燈人……每個人守住的一個星球,回憶過去,自言自語,半夢半醒。在評論“野孩子”樂隊主唱張佺《伏熱》時,他寫道:“一次古老民歌精神的靈魂附體,用石頭花兒作比喻,首先要放下爭奇斗艷的心,孩子和大師才有的思路。民歌幾千年,就是個保守的賦比興,信手拈來,又無比恰當。像陜北民歌中的‘山坡坡’,‘淚蛋蛋’,一切外物都成了親娘老子婆姨孩子。”這種保守主義式的思路不獨是他個人的傾向,也是新民謠總體的取向。周云蓬歌曲中難得歡快跳脫的《兩只山羊》就是典型的西北農民的調調,不過大多數時候他的演唱都可以尋到循規蹈矩的蛛絲馬跡:他的聲線本來寬厚高亢,但是演唱中總是壓抑著,克制、低回、憂傷,從來沒有越軌的嚎叫和歌哭。
然而,話又說回來,每個人都不是一座孤島,周云蓬幼年生活過的鐵西區和成年后游歷過的每個角落都是一塊完整的大陸,他在說自己的故事,也是在說一個群體的故事。“道路死在我身后,離開河床誰更自由……我不要清醒的水,我只要暈眩的酒”。沒錯,真是“幻覺支撐我們活下去”。我想,這可能與他的肉體缺陷有著直接的關聯。他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并且熱情擁抱它:“蛇只能看見運動著的東西,狗的世界是黑白的,蜻蜓的眼睛里有一千個太陽。很多深海里的魚,眼睛蛻化成了兩個白點。能看見什么,不能看見什么,那是我們的宿命。我熱愛自己的命運,她跟我最親,她是專為我開,專為我關的獨一無二的門。”能夠窺破命運的殘酷,還能夠坦然面對甚至升華,周云蓬至少是個充滿勇氣和智慧的人,難能可貴的還具有黑色幽默的特質,像《如果你突然瞎了該怎么辦》中設想的無數可能性,手把手教導如何與厄運相處。而如果世界突然瞎了該怎么辦呢?周云蓬會回到自己的內心。
回到內心往往意味著最深刻的洞察和最蒼白的退縮。“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盲人影院。周圍是空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座椅,屏幕在前方,那不過是一片模糊的光。我們在黑暗中誤讀生活,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只有想象它真實如流螢,在我們的現實和夢境里盤旋閃爍。一個現實的人,也就是一個抱著自己冰冷的骨頭走在雪地里的人,而想象是我們的裘皮大衣,是雪橇、篝火、是再也無法看到的屏幕上的春花秋月,最后,等著死神,這個領票員,到我們身旁,小心提醒說,電影散場了。他打著手電筒帶我們走出黑暗。”生命的領票員其實就是自己。有時候,這種逃遁帶有莊周式的機智,在日常中能直達自我滿足、醍醐灌頂的頓悟。《那些租來的房子》記述他的租房之旅,而結尾就像一個蘊積力道的太極高手,筆鋒一轉,“還有一個租來的房子,是本人的身體。俗話說,眼為心靈之窗。我這個房子,窗戶壞了,采光不好。找房東理論,我膽子小不敢。那只好在里面,多裝上幾盞燈增強照明。其實,總是亮堂堂的,也不好,起碼擾人清夢。坐在自己黑暗的心里,聆聽世界,寫下這些文字。字詞不再是象形的圖畫,而是一個個音節,叮叮咚咚的,宛如夜雨敲窗,房東就是命運,誰敢總向他抱怨?有地方住就不錯了,能活著就挺好了。等我離開這間房子,死亡來臨時,那將是又一次嶄新的旅行。哪兒都會有房東,哪兒都會有空房出租,流浪者不必擔心,生命也不必擔心死亡。我將死了又死,以明白生之無窮。”他的寬廣之處在于能從一己身體出發對更廣大的社群有理解的同情,而其限度也正在于無法走出骨子里的感傷,雖然時不時他會用調侃來進行化解——這種調侃也帶有無助的凄涼感。
我最初是因為聽到《九月》才開始接觸到周云蓬,一個行游四方的高大盲人吟唱憂傷的歌曲,正足以滿足柏拉圖所謂人們非理性中的感傷癖和哀憐癖。在脆弱的夜晚,悠長緩慢的吟唱帶有迷幻式的沉溺感。不過,我清楚,在冰冷的工具理性主宰著的功利社會中,濫情主義會成為它吊詭的另一面,因為個體在這樣情感已經淪為商品的社會中無力自拔,只能尋找一個虛幻而脆弱的情感投射物。尹麗川曾經寫過一段炫麗的文字介紹周云蓬和他的伙伴們:“他們不是精英,不是杰出青年,不是勞動模范,不是政客,不是知識分子,不是文化人,不是頻頻奔赴威尼斯的藝術家;他們是民間藝人,是城市和村莊的流浪者,靠手藝吃飯,為自己創作,為普通人獻藝。他們跟藝術潮流之古典、前衛沒什么關系,跟包裝、商業也沒什么關系。他們自得其樂,自食其苦。他們不想改變這世界,更不想為世界所改變。”然而,我想說的是,這個世界處處充滿荒誕,評價對象時中肯的言辭,一不留神就可能變成反諷。
劉大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民族文學研究》編輯部副主任,從事文學、影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