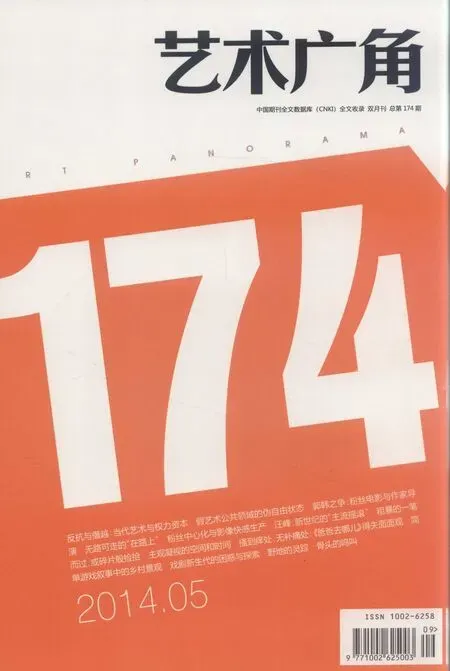搔到癢處,無補痛處:《爸爸去哪兒》得失面面觀
邵楊
搔到癢處,無補痛處:《爸爸去哪兒》得失面面觀
邵楊
《爸爸去哪兒》,無疑是這一年來中國電視屏幕上最具有話題性的文本之一。一檔節目要被認證成“最好看”“最精彩”“最有誠意”“最有創意”都存在難度,這些定語本身都出于主觀判斷,涉及態度、口味、立場和喜好,難免變得見仁見智、眾口難調。唯獨“最具有話題性”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和一種已經發生的狀態——無論這個社會有沒有因為它而變得更好,至少因為它而變得更加熱鬧:該節目的開放式結構和場景任務的變換、帶有反差感的嘉賓選擇與拼盤式人物性格設定、戲劇性和紀實性之間的兩難與搖擺、對教育理念和家庭生活中各種現實困擾的復現和延展,它的爆笑、飆淚、溫情漫溢、角色逆轉,它的自黑與自曝、積極與消極、引導與誤導、正常與非正常、底線與無底線,無一例外地儲備和提供了大量的爭議空間和討論余地,時時地騷動著這個迫切需要談資的時代。最終,除了作為一個慣性選擇而持續霸占周五晚間的遙控器,作為一個網絡熱詞而刷爆了微博微信朋友圈,它更具有了一種文化學、倫理學、大眾心理學層面的樣板個案價值。透過它,我們似乎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電視的成與敗、媒介的得與失、觀眾的愛與恨,乃至,當下中國的需要、希冀和無助。
《爸爸去哪兒》與社會文化的性格契合
作為歐美最風行的節目模式之一,西方的戶外真人秀一直以來均以野外競技和生存權的角逐作為核心內容,以封閉的空間、嚴苛的賽制、殘酷到不近人情的淘汰機制,催動選手在規定情境下與隊友競爭、與自然搏斗,不斷探求體能和意志的極限。很顯然,這種把“誰將被誰排擠出局”作為主懸念的、讓饑餓疲憊創傷和勾心斗角伴隨始終的重口味取向,并不適用于中國觀眾所習慣和渴求的那種溫情、和諧、積極、健康、正能量的審美,也不吻合中國觀眾對于電視的休閑、娛樂、精神療愈的定位(中國觀眾對腹黑與厚黑的圍觀欲求都由宮斗、家斗、職場、商戰等電視劇所承載,對于“真人”這個層面,他們還是愿意相信人性本善)。所以回溯中國電視綜藝的發展史不難發現,在《爸爸去哪兒》出現之前,戶外真人秀在內地的收視業績幾乎是一地雞毛:2000年之后,央視、廣東衛視、四川衛視和貴州衛視等制作機構,以《閣樓》《幸存者》《荒野生存》等外國成功范例為樣板,先后推出的《生存大挑戰》《走入香格里拉》《奪寶奇兵》《金蘋果》等節目,不是迅速邊緣化到無人問津的地步,就是在不斷的自我游移中淪為廉價的游戲和博彩,最終無一例外地慘淡收場。湖南衛視已經堅持到第八季的《變形計》是個例外,但它更偏向于苦情化宣教和治愈,不適合承擔黃金檔的綜藝要求。
相比之下,《爸爸去哪兒》節目模式的原產地是一衣帶水、同歸東亞文化圈的韓國,可說是戶外真人秀在東方倫理的改寫和糾偏下,完成的一次重新自我塑型,在多個方位上都呈現出更貼近中國人思維模式和精神氣質的狀貌。第一,參與者從個體變為父子,參與內容從生存比拼變為組團旅行,天倫之樂、情感交流、互幫互助取代了封閉空間內的道德觀察和人性實驗,回歸到溫暖的生活細節,這體現了儒家文明對家庭的絕對重視。第二,保留一部分戲劇性虛擬設定和競爭關系,但無關乎你死我活的是走是留,也并不進行成績統計和優劣評選,每一場游戲的輸贏充其量只能決定當晚烹飪的食材是否差一點、居住的房屋是否小一點,這種無傷大雅的玩笑和喜感貫穿始終,吻合亞洲觀眾的輕口味愉悅和休閑娛樂訴求。第三,節目主體從普通人變為明星,一方面,褪下光環洗盡鉛華的平凡生活場景,滿足了后起商業國家里大眾對于成名者的習慣性趨奉與好奇心;另一方面,在與歌唱表演競賽統統無關的洗衣做飯帶孩子中時時暴露的失措和無奈,又在心理上拉平了觀看者與被觀看者的雙方在社會階層上的差異,符合國人最偏愛的“公子落難”“屌絲逆襲”“草根的大腕化和大腕的草根化”等來自身份錯置的快感。第四,在傳統父權社會里,父親是名義上的一家之主,是威嚴、權力、決斷、歸屬的象征,而母親總是與家庭、子女、日常起居綁定更多的一方,當二者在節目中完成任務逆轉,當母親缺位之后,父親回歸家庭,這種反差感足以轉換成節目的新意與創意。
不止于此,當《爸爸去哪兒》從韓國進入中國之后,某些更細致、更貼合、更接地氣的改造仍在繼續將其拉近中國觀眾的心理需要:其一,從一個父親帶兩三個孩子變為一個父親帶一個孩子,匹配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現象,更容易觸及到分享、謙讓等個人品德的養成;其二,相較于原版較為緩慢的劇情設置和強烈的綜藝形式感(三天兩夜一次任務,分兩期播完),湖南衛視版明顯更注重節目編排和節奏的緊湊性(兩天一夜一次任務,分三期播完),敘事重點也從溝通、交心、分享、體悟轉移到搞笑、哭鬧、撒嬌、安撫這些比較直觀的沖突上,降低了參與孩子的年齡(韓版的兒童都比較大,最小的也已經六歲),這種簡單、明快、對情緒的直接撩動,顯然與本土觀眾群體年齡跨度大、女性居多、知識水平相對偏低的特質有關;其三,中國地域廣大、幅員遼闊的特點也給拍攝制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環境便利性,從燕郊農村到西北沙漠,從云南苗寨到威海小島,從江南古鎮到東北雪原,視覺上的奇觀性和陌生化效應,乃至“飽覽祖國大好河山”的自豪感,無疑也很對國人的胃口。
必須提及的還有《爸爸去哪兒》登陸中國屏幕的時間點:一個若干檔“某某好聲音”“某某最強音”扎堆混戰的夏天剛剛過去,演藝類、歌唱類選秀造成的審美疲勞和內耗透支了觀眾的熱情,整個電視業仿佛置身于群雄逐鹿后百廢待興的迷茫中,急需更清新、更鮮活的血液補充進來,急需挖掘和捕捉一個新的潛在熱點。而2010年之后,80后初為父母、二胎政策引發關注、第四波生育高峰如期而至、“小兒難養”成為無數家庭最集中的困惑與焦慮——孩子正在不可逆轉地重新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心。與之相比,由于長期以來的偏見和盲視,也由于低齡參與者在電視拍攝制作中存在著太多不確定性,中國電視屏幕上的兒童形象始終都是缺位的、偏狹的、符號化的,或至少是被動的、機械的和沒有存在感的:孩子們或者在少兒節目中擔任被教育、被規訓的對象,或者在家庭劇中扮演婆婆媳婦爭吵角力的觸因。是以,當《爸爸去哪兒》第一次將這個群體作為情感寄托中心、故事推進中心和精神傳導中心,放在前所未有的突顯位置上,試圖用孩子身上天籟般的善意、博愛和赤子之心作為價值旨歸的時候,一個巨大的空白被填補了。一個新的、低齡的、天真爛漫的興奮點,用各領風騷數百年的改朝換代,和王侯將相本無種的不拘一格,再次拯救了中國電視。
當然,作為孩子們的監護者,明星父親們才是這檔節目實際上的決策領袖。需要看到的是,近年來以《藝術人生》《魯豫有約》為代表的名人訪談的社會影響力正在急劇萎縮,尤其是大量曾經在這類節目中談過道德操守的巨擘出了道德問題、秀過夫妻恩愛的大腕出了婚姻問題之后,觀眾對于這種端坐演播室里聲淚俱下的撫今追昔越來越失去興趣和信任。于是,明星們發現,在這個推重真性情的時代,自我形象營銷和商業價值提升的最佳模式,已經不再是談話節目里干巴巴地講述“我很厲害”,而是去戶外真人秀節目的田間地頭表演一幕幕“我很能干”,再不濟,“我很可愛”甚至“我很呆萌”也可以被接受。
于是,當戶外真人秀以“先韓國再中國”的逐步趨近完成了戰略調整和本土改造,輔之以恰當的時代背景和公眾焦慮,瞅準了節目開播時機,呼應了明星曝光需要,這一切條件都聚合在《爸爸去哪兒》身上時,它已經變成了一枚精準的針灸,不偏不倚地扎在了那個最準確的穴位和神經元上,立即釋放和激活了整個軀體的內循環。
如果我們細心的話,還不難發現在這檔節目和這個社會、這群觀眾之間,其他一些更加復雜也更加微觀的同呼吸共命運,確認了它們的性情相投:
我們總在說,電視業需要創新,需要自我變革和探求新的可能性,于是,以《爸爸去哪兒》為契機,我們看到了一種主持人角色的變化——劇情內置而非舞臺司儀型(那個總在頒布任務又不斷易裝的村長李銳);看到了即使在紀錄型節目中,人物編劇的作用依然在不斷強化;看到了700比1的樣片成片比幾乎顛覆了中國電視界對于剪輯的認知;看到了40個以上的機位設置、200人的制作團隊和航拍器、直升機的使用在刷新電視節目“大片化”的定義;看到了字幕組的價值前所未有地凸顯,那些“屏幕上的文字”不再是人物語言的機械重復而是對劇情的推動、對笑點的總結、對亮點的提醒。
我們總在說,市場需要從成功的電視節目里獲取資源和衍生價值,于是我們看到,《爸爸去哪兒》以生活細節而非技能比拼傳達的成長性、伴隨性,造就的觀眾情感的黏著度和忠實度,太適合灌注在一整條產業鏈之間:春節期間《爸爸去哪兒大電影》的票房奇跡、同名手機游戲首日下載量破300萬、幾個孩子都在小小年紀接下了巨額廣告訂單、網絡播出權實現天價售賣、拍攝地靈水村在今年五一正式升為3A景區對外開放,這一切都太符合消費社會娛樂至死的邏輯——對某個經過檢驗的優質資源,做毫無保留地反復挖掘和毫無顧忌地蜂擁而上。
我們需要無微不至的暖男,于是我們找到了張亮(這是中國第一個沒有通過任何具體專業才藝展示,而在綜藝真人秀里用性格和家務紅起來的明星)和黃磊;我們需要不會老去的帥爸,于是我們找到了林志穎和陸毅;我們覺得女孩子應該美麗善解人意如天使,于是我們找到了Cindy和多多;我們覺得男孩子應該堅毅甚至粗糙,于是我們找到了石頭和費曼;我們轉念一想,女孩子胖一點丑一點其實也很可愛,于是我們找到了王詩齡和Grace;我們轉念一想,男孩子柔弱一點愛哭一點其實也很招人疼,于是我們找到了Kimi和楊陽洋。
當所有隨時升起的愿景,都能在這個標靶式的節目里找到落點和對應,你只能說,它確實搔到了這個社會和這個文化的癢處,讓人愉快而且舒暢。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癢點和痛點是否吻合?穴位和病灶是否匹配?取悅和治療能否并軌?那些被滿足的愿景是真實的還是錯覺?那些愉快和舒暢,又是否絕對積極、正確而且健康?
《爸爸去哪兒》對社會焦慮的療救無力
筆者以為,《爸爸去哪兒》以及在它的引領和垂范中前赴后繼的《爸爸回來了》《媽媽請回答》《爸爸聽我說》等親子類節目,按照內涵上、立意上的由低到高,其實可以達到五個層次的效果:1.圍觀孩子賣萌;2.兩代人的溫情對話;3.集體追懷童年和歲月;4.感悟成長和評估教育理念;5.用童心反哺和療救成人世界。
如果以此作為評價標準的話,目前,賣萌和溫情較為飽滿地鋪展在整個觀看過程中,童年與回憶若隱若現,教育理念大多是網友和評論家們一廂情愿的過度解讀,而來自童心的反哺,很遺憾,至少我沒有看到,或者說,我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面。
因為涉及育兒,有體驗有感受有經驗有教訓的人太多,隨意一個細節(比如前往拍攝地的途中,車上有沒有裝安全座椅)都可以被拿出來指摘把玩;因為孩子們和父親們性格反差大,酷愛抱團相斗的粉絲心態可以得到非常便捷的滿足;但如果這種簡單無害的討論和各有所愛的取舍都會被演繹成殺氣騰騰的對立,那這個節目所燭照出的,恰恰是整個社會對于童真的遠離,或者說,是在那些稍縱即逝的童真面前,整個成人世界的自卑、自戀和自虐。當孩子們在菜市場因為幾塊錢的使用而產生的分歧,招致微博上排山倒海的“黃磊父女滾出節目”的聲討;當吳鎮宇和兒子間的雙語對話被網友們斥為“崇洋媚外”或“裝X秀優越”;當天天被封為“是非精”、多多被指責“太做作”、王詩齡和貝兒被貼上“沒家教”的標簽;當許多人以一幀一幀截圖的方式,在不厭其煩地堆疊出制作方的黑幕,論證任意一對星爸萌娃表現自己打壓別人的心機;當那么多人因為各自喜歡的孩子不同就急不可待地惡語相向彼此詆毀……我不得不說,以這個節目為契機,這個社會正在暴露它最病態的東西。一檔以和睦和諧為主要氛圍的節目,并沒有在外部社會生產制造出和平與和解,相反,它對于戲劇性和可看性的過度追求,在某些場景里的選擇性呈現和刻意引導,放大了不必放大的,卻又未曾避諱應該避諱的。這一切錯位和誤區,把“話題性”極端化為一場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口水鬧劇,這鬧劇里的暴戾乖張,早已與人們曾經期待過的那個屬于童真的世界相距千里。
尤其是,這種過分強烈的目的性和節目效果壓倒一切的思路,在第二季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和肆無忌憚。如果說一年之前還有許多人欣賞和陶醉于每個兒童帶著羞澀、忐忑甚或是害怕參與節目的那種“璞玉感”,眼下的這些孩子,似乎對于節目意味著什么已經具有了明確的感知力和較為鮮明的配合意愿,不介意時時刻刻把自己的性格特質與行為特質極端化。
就像已經被很多教育專家和兒童心理專家所指摘過的那些細節一樣:為了所謂的“分享”考驗而故意讓某些孩子的碗中沒有早餐,是一種制造不信任感的欺騙;換爸爸過夜會造成界限意識甚至倫理意識的混亂;父親易裝嚇唬孩子容易留下心理陰影和創傷;隨意尋找小鎮居民配合表演電視劇橋段顯得肉麻、低俗且居高臨下。
只要看看《爸爸去哪兒》第一季在各大視頻網站里被替換上的那些狗血標題:黑米天天友情觸礁、田雨橙與王詩齡閨蜜變情敵、小小志偷瞄王詩齡放羊、三娃虐戀、小情侶鬧翻分、Kimi詩齡戀情告吹……就不難發現,它幾乎繼承了中國傳統育兒經里最不科學與讓人反感的部分——拿著孩子保媒拉纖、隨意打擾孩子的精神空間、“推己及人”地揣度孩子的心理、八卦孩子的純潔交誼、有意識地哄騙孩子說出“我喜歡某某某”這樣的話并自鳴得意,所有這些背后,是對孩子的工具化、奇觀化、成人化甚至物化。
即使放低要求,暫時無視這些文化偏執和倫理偏差,僅僅退回到“教育孩子”這個技術性的層面上,《爸爸去哪兒》又果真具有示范效應嗎?性別認知是人格塑型過程里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認知,爸爸媽媽作為兩個近在咫尺的性別樣板,基于不同性別特質給予孩子的引導和反饋,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孩子的一生。而父親在育兒行為中的缺席導致中國孩子長期以來受到的女性化溺愛、嬌寵和過度保護,早已引起了廣泛的憂思,所以,節目能將爸爸拉回到孩子身邊,強調男性親人對于孩子生活的有效參與、有效干預,原本是很具有價值的初始創意。但遺憾的是,在我們目前看到的整個內容設計上,“爸爸”的形象顯得異常模糊和混亂。一方面,作為籠統的“家長”,他們仍以說教者的身份反復強調著懂事、謙讓、感恩、樸素、勤勞這些并不新鮮的美德,盡管這種強調被節目組設計成一個個具體的場景,并伴隨以某種平等和親切的溝通;但相比另外一些更加具有視覺煽動力的吃苦受虐、闖關斗力內容,這些溝通顯得那么的走過場、那么的草率、那么的刻意和那么的不充分,而且永遠只有一種結果:孩子懂得了一個道理,孩子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孩子接受了新的觀念,孩子開始了變化和成長。在一個重建孩子主體性的節目中,孩子依然只有被說服的權利(只不過說服的方式更和風細雨一點),我們支配孩子、規訓孩子的企圖和決心,原來從未改變。另一方面,因為“教育”環節的輕描淡寫、一廂情愿和可視性不足,爸爸到底應該如何更好地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這種參與招致的抵觸和困惑如何解決,不能解決的部分又如何懸置和規避,這些本該更具有挑戰性、建設性和可視性、話題性的內容,被忽略于“好看第一”的原則下。從第一季到第二季,整個節目的內容設計幾乎越來越與親子成長無關,而是更加趨向于肢體層面的耍寶,趨向一種“爸爸”生存技能、表演技能、體育技能的大考驗。做飯、捕魚、爬樹、劃船、投籃、泥地足球,這種奶爸版的“野外大競技”的確妙趣橫生,讓人忍俊不禁,但在爸爸們的笨拙、滑稽、狼狽、萌態百出面前,那些和我們一樣拍著手咧著嘴看熱鬧的孩子,究竟獲得了什么積極意義(除了節目組反復渲染的“爸爸為了你什么事都愿意嘗試”的心靈雞湯之外),確實很值得懷疑。
這便是今天《爸爸去哪兒》的角色和屬性:它成功地找到了中國觀眾最需要的噱頭和彩蛋,摸出了中國電視的命脈和成功訣竅,呼應了絕大多數網絡時代和娛樂時代的特定性情,從而準確地搔到了社會的癢處;但它自身的浮躁與浮夸,它價值觀上的混亂,它骨子里所受的成見和偏見的根深蒂固的影響,它對于集體無意識的無力和無感,最終決定了它停留的位置,也只能是娛樂大眾、提供虛擬的滿足,它并沒有治愈社會的痛處,充其量,它只是反映和反饋了它們。在這樣的癢處和痛處里,它天真著當下中國的所有天真,沉重著當下中國的所有沉重。
邵 楊:文學博士,供職于浙江大學城市學院傳媒與人文學院,研究方向為當代影視傳媒與動漫文化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