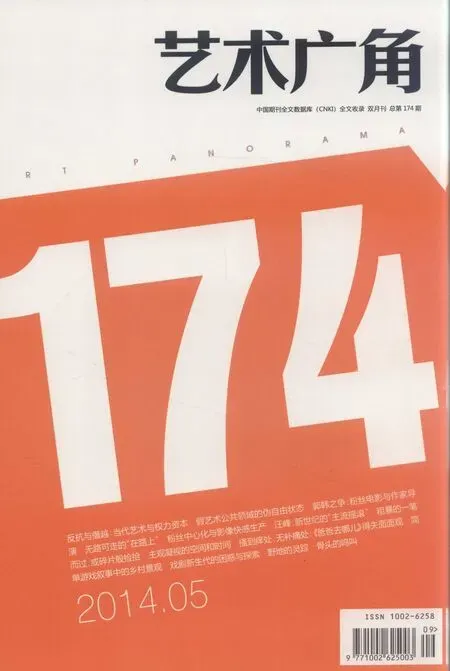戲劇新生代的困惑與探索
陶慶梅
戲劇新生代的困惑與探索
陶慶梅
青年人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在很多時(shí)代都被人們關(guān)注。人們總是對(duì)青年人有著這樣那樣的期望,期望他們的創(chuàng)作能夠推陳出新,在新的時(shí)代找到藝術(shù)的新樣式、回應(yīng)新問(wèn)題。最近幾年,從以孟京輝領(lǐng)銜的北京青年戲劇節(jié),賴聲川主持的烏鎮(zhèn)戲劇節(jié)的“青年競(jìng)演單元”以及田沁鑫的“新寫作計(jì)劃”等等,可以看出,著名戲劇導(dǎo)演也紛紛將目光投向70后、80后的青年創(chuàng)作群體;與此同時(shí),越來(lái)越多的青年戲劇導(dǎo)演,如黃盈、趙淼、王翀、李建軍、周申等等,也在努力適應(yīng)市場(chǎng)規(guī)則的同時(shí)努力追求帶有個(gè)性特色的表達(dá)方式。隨著這些年輕的戲劇導(dǎo)演逐漸進(jìn)入觀眾的視野,進(jìn)入市場(chǎng)的角逐,進(jìn)入藝術(shù)的探索,人們對(duì)這樣一批年輕的戲劇導(dǎo)演充滿好奇,當(dāng)然,也不免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夠如他們的前輩導(dǎo)演一樣推陳出新,賦予當(dāng)代戲劇新的面貌[1]。
對(duì)當(dāng)代青年戲劇人的理解與認(rèn)識(shí),不可避免地是在比較中獲得的。這種比較既包括他們之間的互相比較,也包括和60后的導(dǎo)演十年前的作品相比較。我自己更感興趣的是將當(dāng)前的青年戲劇與十年前的青年戲劇做比較,嘗試?yán)斫猓诓煌臅r(shí)代,同樣對(duì)于時(shí)代變化最為敏感的青年人,他們的創(chuàng)作有什么樣的不同?為什么會(huì)出現(xiàn)這樣的不同?
在縱向比較中認(rèn)識(shí)青年人的戲劇
如果我們將如今在戲劇舞臺(tái)上非常受關(guān)注的年輕導(dǎo)演(他們基本上是70后、80后)的作品與孟京輝、田沁鑫、牟森這些60后戲劇導(dǎo)演上世紀(jì)90年代大約同樣類型的作品相比較的話,很容易發(fā)現(xiàn)這二者的差異。我選了三組進(jìn)行比較。
比如在民族化方向的實(shí)踐上,我們可以將田沁鑫1997年創(chuàng)作的《斷腕》與黃盈2011年創(chuàng)作的《黃粱一夢(mèng)》略做比較。《黃粱一夢(mèng)》的題材來(lái)自唐傳奇,導(dǎo)演黃盈也試圖在現(xiàn)代劇場(chǎng)中以中國(guó)戲曲的表現(xiàn)方法呈現(xiàn)中國(guó)故事的韻味:在舞臺(tái)上有一名身著中式服裝的敘述者,不時(shí)地在舞臺(tái)上喂喂魚缸里的魚;主要演員是戲曲演員(其他非戲曲演員顯然也受過(guò)一定的戲曲表演訓(xùn)練),在步伐、身段上都有著戲曲演員的一些特點(diǎn)。不過(guò),《黃粱一夢(mèng)》最為別致之處應(yīng)該是導(dǎo)演在舞臺(tái)四周放置了幾個(gè)電飯鍋,鍋里一直在煮小米飯。等到演出結(jié)束(大約90分鐘),小米飯也煮好了,觀眾可以和演員一起分享小米飯。也許導(dǎo)演是希望觀眾在看完戲后重新體驗(yàn)一下什么叫榮華富貴不過(guò)是黃粱一夢(mèng)而已吧。
應(yīng)當(dāng)說(shuō)黃盈導(dǎo)演的《黃粱一夢(mèng)》是有自己的創(chuàng)意的。只是,這些小的劇場(chǎng)創(chuàng)意在舞臺(tái)上都是獨(dú)立的,彼此之間沒(méi)有呼應(yīng)。因而,它們并沒(méi)有構(gòu)成這部作品完整的、獨(dú)特的舞臺(tái)敘述方式,更不用說(shuō)美學(xué)風(fēng)格了。
我們?cè)賮?lái)看一下田沁鑫1997年的處女作《斷腕》。《斷腕》取材于遼國(guó)蕭太后述律平的故事。在這部根據(jù)歷史記載中幾段話鋪陳出的作品中,田沁鑫沒(méi)有用任何的戲曲演員,舞臺(tái)上也沒(méi)有特別強(qiáng)調(diào)“中國(guó)元素”,但卻以簡(jiǎn)潔的舞臺(tái)敘述創(chuàng)造了民族化的美學(xué)表達(dá)。
《斷腕》與中國(guó)戲曲最大的相似性,就是舞臺(tái)是空的。年輕的田沁鑫導(dǎo)演,以電影蒙太奇的技術(shù)手法(述律平的老年與少年的不同場(chǎng)景,竟然同時(shí)呈現(xiàn)在一個(gè)舞臺(tái)上),以現(xiàn)代舞演員的身體造型(舞蹈演員金星為《斷腕》的舞臺(tái)營(yíng)造了獨(dú)特的雕塑感),在這樣一個(gè)空的舞臺(tái)上創(chuàng)造了自由的流動(dòng)時(shí)空,也創(chuàng)造了獨(dú)特的中國(guó)美學(xué)韻味。這樣一種美學(xué)上的創(chuàng)造,在今天看,仍然是獨(dú)一無(wú)二的。黃盈的《黃粱一夢(mèng)》與之比起來(lái),就顯得過(guò)于小巧別致,缺少對(duì)于傳統(tǒng)美學(xué)方式深切的領(lǐng)悟。
如果說(shuō)民族化的努力需要更多的經(jīng)驗(yàn),那么,在戲劇與影像等當(dāng)代藝術(shù)的結(jié)合上呢?這些年,王翀與李建軍在這方面都走得很激進(jìn)。王翀?jiān)凇独子?.0》中直接讓攝影機(jī)入場(chǎng),將現(xiàn)場(chǎng)表演與攝影機(jī)同時(shí)拍攝下的場(chǎng)景,并置在一場(chǎng)演出中;李建軍在《美好的一天》中讓二十幾位群眾演員陸續(xù)坐在臺(tái)口,同時(shí)講述自己的一天,觀眾則是人手一個(gè)調(diào)頻器,可以根據(jù)他的喜好選擇他要聽的那個(gè)演員的講述;在舞臺(tái)后方,一個(gè)爐子在靜靜地?zé)_水……
這些時(shí)髦的劇場(chǎng)藝術(shù),在年輕的戲劇導(dǎo)演手中,的確也已經(jīng)玩得像模像樣——而且,只要愿意,你還可以給這些表演負(fù)載很多的意義。只是,在我看來(lái),這些作品,比起牟森在上世紀(jì)90年代創(chuàng)作的《零檔案》來(lái),就顯得機(jī)敏有余、力量感不足。在《零檔案》的舞臺(tái)上,并不完備的影像技術(shù)、帶有工業(yè)化氣息的鼓風(fēng)機(jī)以及鍛壓機(jī)壓榨出四濺的蘋果汁液……這些,讓整個(gè)舞臺(tái)洋溢著叛逆青春的能量。
此外,在舞臺(tái)敘述方式上,年輕的導(dǎo)演又走了多遠(yuǎn)?孟京輝導(dǎo)演的特點(diǎn)之一就是不按照傳統(tǒng)的、所謂“現(xiàn)實(shí)主義”的敘述方式來(lái)做戲。比如《戀愛的犀牛》,明明與馬路的愛情是故事的主線,但這個(gè)愛情故事是經(jīng)過(guò)多重?cái)⑹鐾七M(jìn)的:這里面明明與馬路愛情故事是主線索,馬路個(gè)人的故事(馬路與犀牛)以及馬路的朋友們插科打諢分別又是兩條敘述線索,這三條不同的線索同時(shí)推進(jìn),共同成就了馬路與明明各自對(duì)于愛情——也是他們對(duì)于自己所堅(jiān)持的信念——的決不妥協(xié)。黃盈2007年的《未完待續(xù)》可以說(shuō)是發(fā)展了這種舞臺(tái)敘述方式:他比孟京輝走得更遠(yuǎn)一點(diǎn)的是,演員的表演也作為一種手段進(jìn)入舞臺(tái)敘述之中。演員們不僅用自己的身體“再現(xiàn)”了各種場(chǎng)景,而且整個(gè)舞臺(tái)始終以演員的表演來(lái)構(gòu)成,充滿動(dòng)感。但以成熟的舞臺(tái)敘述手段完成的《未完待續(xù)》,作品中對(duì)于情感的表達(dá),卻異常的溫和;缺少《戀愛的犀牛》中寬闊的社會(huì)視野,也缺少馬路與明明的愛情關(guān)系中蘊(yùn)藏著的決不妥協(xié)的緊張感。
因而,或許可以這樣描述兩代青年戲劇導(dǎo)演的差異:當(dāng)下青年戲劇導(dǎo)演的作品在總體上都還算精致,有創(chuàng)新,有突破。只不過(guò),對(duì)于這些精致的新人新作,我總有些淡淡的失落:年輕的戲劇導(dǎo)演們?cè)谛问缴舷矚g一些別致的創(chuàng)新,但這些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并沒(méi)有在戲劇的整體表達(dá)上構(gòu)造出強(qiáng)大的力量。因而,年輕戲劇導(dǎo)演的作品,無(wú)論在內(nèi)容上還是在情感上都比較溫和,即使他們“想和這個(gè)世界談?wù)劇保哺嗳缋罱ㄜ姷摹睹篮玫囊惶臁纺菢樱⒁獾氖遣蹲饺藗兩娴臓顟B(tài),而并不呈現(xiàn)自己的態(tài)度。
我在對(duì)比中表達(dá)了對(duì)于青年戲劇創(chuàng)作的些許失落,失落是因?yàn)樽鳛榕u(píng)者,我固然有我自己的態(tài)度、立場(chǎng)與偏好,但也并不是要以此來(lái)否定青年人的戲劇創(chuàng)造,而是想探究這一代人創(chuàng)作上的特點(diǎn)是怎么樣的?以及,他們?yōu)槭裁磿?huì)形成這樣的特點(diǎn)?
當(dāng)下青年戲劇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
要認(rèn)識(shí)當(dāng)代青年的戲劇創(chuàng)作,首先還是要理解他們創(chuàng)作的整體環(huán)境。
對(duì)于孟京輝那一代導(dǎo)演來(lái)說(shuō),他們年輕時(shí)生活、經(jīng)驗(yàn)的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國(guó)社會(huì)面臨著激烈的轉(zhuǎn)型變革的時(shí)代。隨著計(jì)劃經(jīng)濟(jì)解體而逐漸生長(zhǎng)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正在緩慢而堅(jiān)定地重新塑造著中國(guó)的社會(huì)格局。具體到戲劇創(chuàng)作來(lái)說(shuō),以牟森、孟京輝、田沁鑫為代表的那一代戲劇作者,可以說(shuō)面對(duì)的幾乎是一個(gè)荒蕪的戲劇市場(chǎng)——過(guò)去在院團(tuán)戲劇生產(chǎn)機(jī)制下老的戲劇市場(chǎng)正在萎縮,而一個(gè)新的戲劇市場(chǎng)尚未形成。因而,對(duì)于牟森那一代人來(lái)說(shuō),或者是完全放棄市場(chǎng),赤裸地呈現(xiàn)自己的表達(dá),游走于國(guó)際戲劇節(jié),仰賴國(guó)際戲劇節(jié)的生產(chǎn)機(jī)制;或者是迎難而上,赤手空拳地在國(guó)內(nèi)創(chuàng)造一個(gè)新的戲劇市場(chǎng)。牟森選擇了前者,孟京輝和田沁鑫則選擇了后者。而當(dāng)70后、80后年輕的戲劇導(dǎo)演登上戲劇舞臺(tái)的時(shí)候,新的戲劇市場(chǎng)已經(jīng)初步成型:就在孟京輝、田沁鑫們打拼出一個(gè)新的戲劇市場(chǎng)之后,商業(yè)戲劇迅速跟進(jìn),不斷擴(kuò)展著這個(gè)新的戲劇市場(chǎng)。于是,以1999年孟京輝的《戀愛的犀牛》為標(biāo)志擴(kuò)張出來(lái)的戲劇市場(chǎng),經(jīng)由戲逍堂、雷子樂(lè)、李伯男在2005年以來(lái)近十年的開拓,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然逐步成型。大致說(shuō)來(lái),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孟京輝、田沁鑫這一代導(dǎo)演可以說(shuō)占據(jù)著這個(gè)戲劇市場(chǎng)的高端——所謂高端的意思不僅是他們的戲劇演出票房一般都不錯(cuò),而且他們?cè)谧髌凤L(fēng)格上可以更多元、更異質(zhì)一些,也可以不按照市場(chǎng)的預(yù)期,冒一些票房的風(fēng)險(xiǎn);大量的商業(yè)戲劇則構(gòu)成這個(gè)市場(chǎng)的低端——所謂低端的意思,是他們的票房保證他們可以持續(xù)在戲劇市場(chǎng)的生存,在風(fēng)格上基本上是以?shī)蕵?lè)、搞笑為基本方式,內(nèi)容上則基本以青年人的感情生活為主要題材,比如李伯男的《嫁給經(jīng)濟(jì)適用男》《隱婚男女》等劇,基本上就是以崔民國(guó)與張靜宜這對(duì)年輕男女的愛情、婚姻、事業(yè)不同階段的故事組成的一個(gè)系列。
在這樣一個(gè)現(xiàn)階段相對(duì)成型而且還相對(duì)穩(wěn)定的戲劇市場(chǎng)上,這些年輕導(dǎo)演在市場(chǎng)上存活既容易,又不容易。
說(shuō)容易,是因?yàn)橄鄬?duì)于市場(chǎng)上這些流行的作品來(lái)說(shuō),像黃盈、王翀、趙淼這樣的導(dǎo)演,處理同樣的題材,一般都會(huì)比市場(chǎng)上通行的作品質(zhì)量要高,因而他們也較為容易在這個(gè)寬闊的地帶找到自己的市場(chǎng)。比如黃盈的作品《未完待續(xù)》、趙淼的《狂人未愛狂想曲》,同樣都是寫青年人的愛情,但這兩部作品在表演方式與舞臺(tái)語(yǔ)匯上,無(wú)疑都要比商業(yè)戲劇更豐富,也因此這兩部作品在市場(chǎng)上的口碑與票房都很不錯(cuò)。
但是,正因?yàn)樗麄兇婊钤谕|(zhì)化的商業(yè)戲劇與孟京輝的多元戲劇風(fēng)格之間的地帶,而這個(gè)地帶又非常開闊,他們又很容易就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他們反而容易失卻當(dāng)年孟京輝他們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勇氣。大多時(shí)候,他們都是在小心翼翼地適應(yīng)著這個(gè)由他們上一代開拓的市場(chǎng),保護(hù)著自己在這個(gè)地帶的位置。而年輕一代作品中洋溢著溫暖、別致的格調(diào)、缺乏振奮人心的力量,是不是正因?yàn)樗麄內(nèi)鄙倜暇┹x那一代導(dǎo)演在一無(wú)所有中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天地、要與周遭環(huán)境“死磕”的魄力呢?而是不是也因?yàn)樗麄兲^(guò)呵護(hù)他們?cè)诩扔惺袌?chǎng)中的位置,輕易不去刺探這個(gè)市場(chǎng)邊界,因而,21世紀(jì)以來(lái)我們所看到的劇場(chǎng)突破,仍然是他們的前一輩完成的——比如孟京輝的《兩只狗的生活意見》、田沁鑫的《青蛇》、牟森的《上海奧德賽》,他們通過(guò)自己的這些作品,完成的既是對(duì)自己的突破,也是對(duì)當(dāng)下舞臺(tái)表達(dá)邊界的拓展。
或許,在這樣一個(gè)既有的戲劇市場(chǎng)中生存是這一代青年戲劇人的宿命——他們不是孟京輝那一代人,不面對(duì)上一代的社會(huì)條件,你無(wú)法要求他們同樣具備赤手空拳打天下的勇氣和力量。那么,他們還有沒(méi)有可能在既有的市場(chǎng)框架中,在藝術(shù)上創(chuàng)造新的風(fēng)格、新的表達(dá)呢?或者說(shuō),他們?cè)谒囆g(shù)上又應(yīng)該克服什么樣的難題呢?
藝術(shù)史的不同命題
生長(zhǎng)在什么樣的時(shí)代是沒(méi)法選擇的——你不能希望年輕一代和60后分享同樣的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
從藝術(shù)史的角度來(lái)看,這兩代人面對(duì)的藝術(shù)上的問(wèn)題也是不太一樣的——相同之處是這兩代人都要回應(yīng)西方藝術(shù)的現(xiàn)代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的挑戰(zhàn)。對(duì)于孟京輝那一代導(dǎo)演來(lái)說(shuō),更重要的命題在于回應(yīng)現(xiàn)代主義,而對(duì)新一代戲劇導(dǎo)演來(lái)說(shuō),現(xiàn)代主義戲劇觀和后現(xiàn)代主義戲劇觀,他們幾乎是同時(shí)遭遇的。
對(duì)孟京輝那一代來(lái)說(shuō),與其說(shuō)是在回應(yīng)現(xiàn)代主義戲劇觀的挑戰(zhàn),不如說(shuō)現(xiàn)代主義戲劇觀是通過(guò)“誤讀”來(lái)對(duì)抗已經(jīng)很脆弱的“傳統(tǒng)”戲劇觀。在中國(guó)特殊的語(yǔ)境中,成長(zhǎng)于上世紀(jì)80年代的60后導(dǎo)演是在傳統(tǒng)現(xiàn)實(shí)主義(暫時(shí)這么稱呼)與現(xiàn)代主義的撞擊中逐漸成熟起來(lái)的。在上世紀(jì)80年代的思想躁動(dòng)中,現(xiàn)代主義給了他們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思想資源、藝術(shù)資源。同時(shí),他們也經(jīng)歷了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帶來(lái)的精神、思想上的陣痛,經(jīng)歷了從狂歡到壓抑的巨大失落。這種強(qiáng)烈的心理沖擊與現(xiàn)代主義思想、藝術(shù)資源的互動(dòng),成就了他們?cè)谖枧_(tái)上的大破大立。
不過(guò),在我看來(lái),也不用夸大現(xiàn)代主義對(duì)于孟京輝那一代戲劇導(dǎo)演的作用。現(xiàn)代主義給了他們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武器,但其實(shí)他們未必要真的理解現(xiàn)代主義戲劇觀的內(nèi)容。很大程度上,他們是在對(duì)現(xiàn)代主義的誤讀與挪用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戲劇語(yǔ)言與戲劇表達(dá)的。最典型的就是孟京輝的《等待戈多》——那種砸碎玻璃的做法完全是在表達(dá)演出者內(nèi)心深處對(duì)于社會(huì)的嚴(yán)重不滿。貝克特那看似不明不白的臺(tái)詞,他們也未必明白,但他們很清楚他們就要用這誰(shuí)也不懂的臺(tái)詞來(lái)挑釁傳統(tǒng)戲劇的直白。牟森對(duì)于格洛托夫斯基的推崇——雖然他運(yùn)用格洛托夫斯基的訓(xùn)練方法演出了《彼岸》——并不構(gòu)成他作品的美學(xué)底色,真正讓他走向世界的,還是與他合作演出的那些土生土長(zhǎng)的藝術(shù)家自身所具備的能量,以及他個(gè)人對(duì)于工業(yè)化舞臺(tái)表達(dá)的著迷。
反觀現(xiàn)在的青年戲劇導(dǎo)演,他們成長(zhǎng)的90年代、投入創(chuàng)作的21世紀(jì)初,已經(jīng)是市場(chǎng)化高歌猛進(jìn)的時(shí)代,他們只有適應(yīng),沒(méi)有跌宕起伏的深刻挫折。而他們投入創(chuàng)作時(shí),現(xiàn)代主義已經(jīng)用不著再和傳統(tǒng)撕扯,而是一種現(xiàn)成的、正確的甚至“落后”的思想資源。在他們走向舞臺(tái)的時(shí)候,“后戲劇劇場(chǎng)”之類后現(xiàn)代戲劇讀物,也已經(jīng)成為他們的精神指南了。因而,我們看到他們吸收了現(xiàn)代主義的一些理念,也很時(shí)髦地運(yùn)用后現(xiàn)代的理念對(duì)自己作品進(jìn)行多義性的解釋。但如果說(shuō)孟京輝那一代人對(duì)于現(xiàn)代主義可以一知半解地以誤讀來(lái)進(jìn)行創(chuàng)造,今天的年輕導(dǎo)演,在缺乏與傳統(tǒng)或者社會(huì)相對(duì)抗的緊張感的刺激之下,再對(duì)于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戲劇觀夾生著運(yùn)用,就會(huì)出現(xiàn)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狀況:個(gè)別的靈光一閃很多,技術(shù)上成熟也很常見,但整體上的舞臺(tái)美學(xué)迄今仍是破碎的、實(shí)用性的。
如今,在全球化已經(jīng)如此成為我們的生活事實(shí)的狀況下,在我們的年輕導(dǎo)演如此頻繁地出國(guó)演出、交流的情況下,在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生進(jìn)入歐美院校學(xué)習(xí)戲劇的情況下,我們面對(duì)的問(wèn)題,首先不再是誤讀,也不應(yīng)該是夾生著把現(xiàn)代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戲劇觀的教條隨手拿來(lái)解釋自己的作品,而是要真的理解現(xiàn)代主義和后現(xiàn)代主義。如同青年導(dǎo)演周申在創(chuàng)作話劇《驢得水》的體悟:我是真心地想做一個(gè)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作品,但是,當(dāng)我想完成人物的心理轉(zhuǎn)折時(shí),我必須把時(shí)空推到變形,因而,荒誕就自然地產(chǎn)生。也就是說(shuō),我們?cè)趧?chuàng)作的過(guò)程中,要消化掉西方的各種主義,而不是迷信,也不是僅僅把它當(dāng)做闡釋自己的作品、讓自己的作品顯得有“深度”的工具。
理解只是在祛魅,理解之后是要回應(yīng)自己的問(wèn)題。無(wú)論現(xiàn)代主義還是后現(xiàn)代主義,都是回應(yīng)西方戲劇自身的問(wèn)題。中國(guó)當(dāng)代戲劇起步很晚,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本就基礎(chǔ)薄弱,現(xiàn)代主義在誤讀中被囫圇吞棗,后現(xiàn)代就已經(jīng)如約而至。其實(shí)在我看來(lái),說(shuō)“后現(xiàn)代的戲劇觀”也許并不那么準(zhǔn)確,“后現(xiàn)代”不過(guò)是把現(xiàn)代主義的戲劇觀更向當(dāng)代藝術(shù)甚至行為藝術(shù)的方向推進(jìn),有自己的戲劇主張,但很難說(shuō)這些主張就真的能經(jīng)得住實(shí)踐的檢驗(yàn),成為能量充沛的理論。但我們的年輕導(dǎo)演可能還是比較愿意癡迷于“后”這樣一種時(shí)間感,認(rèn)為“新”的就是好的,至少新的就是“酷”的。其實(shí),對(duì)于我們的青年導(dǎo)演來(lái)說(shuō),玩起“后現(xiàn)代”一定不比當(dāng)下西方戲劇導(dǎo)演差多少:比如說(shuō)黃盈在2014年的最新作品《語(yǔ)文課》,演出中的許多部分就是由觀眾參與一起完成的。這種取消演員與觀眾的距離、觀眾參與演出的后現(xiàn)代式樣的劇場(chǎng)實(shí)驗(yàn),在年輕導(dǎo)演那里可以說(shuō)是得心應(yīng)手。問(wèn)題是,這種得心應(yīng)手的劇場(chǎng)游戲在什么意義上可以與我們當(dāng)下自身的經(jīng)驗(yàn)勾連起深沉的聯(lián)系?這種劇場(chǎng)實(shí)驗(yàn)如何可以逐漸找到我們的舞臺(tái)敘述方式?
其實(shí),一些年輕導(dǎo)演也在探索。同樣是黃盈,他已經(jīng)模模糊糊地意識(shí)到現(xiàn)代主義或者后現(xiàn)代主義的不足,意識(shí)到要用自己生活的經(jīng)驗(yàn)與生活的方式進(jìn)入劇場(chǎng)。他的《黃粱一夢(mèng)》未嘗不包含著這樣的努力。只是,要消化一種異質(zhì)文化,再要將自身的經(jīng)驗(yàn)創(chuàng)造性地呈現(xiàn)到現(xiàn)代劇場(chǎng),這必然是條艱苦的道路,不是討巧地在劇場(chǎng)內(nèi)裝置“小米飯”就可以完成的。
我們期待著年輕的戲劇導(dǎo)演在這條道路上不斷前行。
注釋:
[1]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在商業(yè)戲劇中打拼的青年導(dǎo)演也是青年導(dǎo)演群體的一部分。但商業(yè)戲劇的導(dǎo)演有兩個(gè)問(wèn)題,一是商業(yè)戲劇的青年導(dǎo)演的作品同質(zhì)性比較嚴(yán)重(比如李伯男的系列作品),二是商業(yè)戲劇的導(dǎo)演往往受制于作品出品方的市場(chǎng)定位(比如“麻花”系列)。因此,本文在分析中暫時(shí)不涉及這一部分導(dǎo)演,但這并不表示商業(yè)戲劇青年導(dǎo)演不重要——只是對(duì)他們的研究、分析與批評(píng)應(yīng)該是另一種評(píng)價(jià)系統(tǒng)。
[2]這里講的戲劇市場(chǎng)主要還是以小劇場(chǎng)市場(chǎng)為主。這也是因?yàn)榇蠖鄶?shù)的青年戲劇導(dǎo)演的作品還是以小劇場(chǎng)創(chuàng)作為主。大劇場(chǎng)的戲劇市場(chǎng),要稍微復(fù)雜一些。
陶慶梅:文學(xué)博士,現(xiàn)為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所副研究員,從事當(dāng)代戲劇評(píng)論與戲劇研究工作。著有《當(dāng)代小劇場(chǎng)三十年1982-2012》《剎那中——賴聲川的劇場(chǎng)藝術(sh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