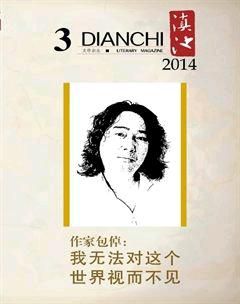我無法對這個世界視而不見(創作談)
包倬
我想先說說我的父親。他是一個嚴父。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他似乎覺得可以在我身上延續他的未竟夢想,于是,對我的嚴厲超過了我的弟弟和妹妹。這對我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過度的期待和壓力,讓我長期感覺心里壓著一塊石頭。他念過小學一年級,靠著一本《新華字典》,硬是把自己鍛煉成了能夠識文斷字的人。他對文字,有著宗教般的崇敬。而這種崇敬,自然也影響到了我。我在上學之前,很希望自己會寫字,寫出那種密密麻麻的繁復的文字。可是,我發現自己那時學到的都是一些筆劃簡單的文字。
我父親是對我寄予厚望的,但我的成績并不容樂觀。我嚴重偏向于語文,數學一塌糊涂。我和我的語文老師親如父子,和我的數學老師卻如仇人一般。我父親其實也一樣,只會讀寫和算賬。他始終是個傳統家長,覺得我不認真學習,辜負了他的期望,于是對我非打即罵。壓力之下,我學會了撒謊。而撒謊,編織一個場景,編織一個故事,而且要符合大人的邏輯,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謊撒得好,瞞天過海,謊言被揭穿,棍棒相交。我和他在長期的撒謊與揭謊中,鍛煉了自己的虛構能力。
是的,有時候,我甚至認為,寫作,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撒謊。并且要沒有漏洞,不被揭穿。
有了壓力,自然需要發泄,我只能寫出來。我在十六歲的時候,曾經動過寫長篇的念頭,我想寫一個少年被家庭壓力逼死的故事。當我構思那個故事的時候,我躺在大涼山的一間潮濕的黑屋子里,淚流滿面。后來,我找到了逃避壓力的方式,離家出走,遠走高飛。我已經離開故鄉十五年,這些年,無論我遇到什么樣的困難,我都沒想過要躲回故鄉。這種和故鄉的長期疏離,讓我時刻懷想那些人和事。
當我某天在外面的世界稍有喘息的機會,我自然想到了讀書。那一年,我漂到了云南的一個小縣城。蝸居在一間出租屋里,我幾乎借遍了那個小縣城的租書店里的文學著作。那一年,我二十來歲,我懵懵懂懂開始了寫作,并且虛構了一個故事,寄給了《短篇小說》雜志,發表了。
在我的處女作中,我的父親以一個望子成龍的慈父形象出現。有意思的是,自從我開始發表小說,我父親就再也沒有管過我。他開始承認,自己老了,他聽憑我構建自己的世界,不再加以干涉。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我逃離故鄉,其實就是躲避我的父親,但當我開始寫作,我發現他是我無法繞開的形象。到目前為止,我的小說中,幾乎都會下意識地出現“父親”。在《獅子山》中,“父親”是一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的人,這篇小說里其實是有兩個“父親”;在《百發百中》中,“父親”的形象更為明晰;在一個尚未發表的小說《命命》中,“父親”是一個為了呵護兒子想要變小,去陪著孩子一起成長的形象;在小說《根種》中,寫的就是父子之間的對抗……當然,作為一個家庭的成員,“父親”是無法繞開的,但作為寫作者,這么些年來,我其實一直沒有走出“父親”所給我帶來的心理陰影。
不要給孩子恐懼,這是一個育兒常識。而我,是那種從小生活在嚴父的恐懼中的人。這種恐懼,讓我膽小、怯懦,并且心性敏感,過早學會了察顏觀色。而敏感和富于觀察,又是寫作者必備的東西。如今想來,也算是不幸中的幸運。
即使是在一個關于城管的小說中,“父親”的形象仍然掩藏其中,只不過這一次,他是作為配角出現。《蚍蜉》這個小說,來自于我對這個世界的粗淺理解。時代在向前發展,發展中矛盾重重。城市要井然有序,城管應運而生;而底層的人們要吃飯,要為了生計,背井離鄉,于是有了小販。關于城管,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大家對這個群體的感覺也都大同小異。充斥于媒體的負面新聞,讓人麻木。但是,我想這只是新聞的表象,造成這個現象,尚有深層次的原因。事實上,城管和小販,都是底層,這是底層之間的相互傾軋,這才是最悲哀的事。
凡事不能一概而論,這是個簡單的道理。即使是在城管這個隊伍里,也絕對有良心未泯之人,既同情弱者,卻又迫于職業的壓力而不得不去做出違心的事情。于是有了“小武”這個人物。他自身的無奈,以及想要蚍蜉撼樹的勇氣,其實只是人性的微光。當然,這種和世界的對抗,也有其一己私利,這同樣是人性。事實上,我并不想尖銳地對抗,但我不會妥協。我想從小武的個人命運,甚至是小聰明、小私心中凸顯當下小人物的普遍悲哀。這個有著對抗性的小說,讓我在寫作的時候,小心翼翼,仿佛一個走鋼絲的人。這種顧慮,讓我在寫作的時候有束縛感,也許會讓讀者意猶未盡。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無法對世界視而不見。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寫作過程,而不是刻意為之,因為只要我們寫,我們寫下的都是這個時代的人物。而人物,總會置于某個背景下,正如一個演員,只要他表演,他的腳下就是舞臺,他的身后就是幕布。《蚍蜉》中的小武,城管臨時工的身份只是一件外衣,這在某種層面上,其實是出于情節的需要。我無意去批評城管,人性中的善與惡,其實都跟環境密不可分。來自小武身上蚍蜉撼樹的舉動,無疑會遭到失敗,這是日常邏輯。關于這個人物,我可以對他加以很多修飾語,悲哀、勇敢、愚蠢、倒霉、天真……但這些所有修飾,都在指向人性的復雜性。
關于小武,他是我們自己,也是我們身邊的人,我期望寫出某種感同身受,寫出一個時代背景下的小人物命運。而這種螻蟻般的命運,只能潛藏于文學作品中。這,可能是文學作品之所以存在的價值之一。
寫了十年的小說,一直處于邊緣狀態,寫一篇創作談,對我來說,比寫一篇小說還難。感謝《滇池》厚愛,讓一個憑感覺寫作的人,有機會去回溯這些年的創作歷程。但愿這樣的回溯,不會太貽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