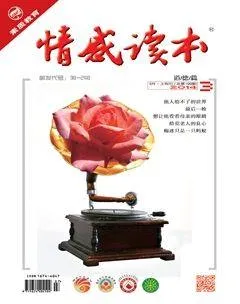父親在101國道上增了一條斑馬線
西城雨
有時(shí),
我會(huì)猛然想起,
也許老天爺再次賦予我生命的原因,
是不忍傷害這個(gè)單純又渴望我回到他身邊的父親。
沉睡三個(gè)月后奇跡般蘇醒
哪一種死法最幸福?在我看來只有一種——睡著離開人世間。
2012年夏天,我在廣州市第三人民醫(yī)院睡了一個(gè)很長很長的覺。努力睜開雙眼的那刻,床頭邊有張臉湊過來,滿眼驚訝、懷疑、激動(dòng)……這是誰啊?我覺得腦子一片混亂,什么也想不起來。“醒了!乖兒子,你終于醒來了!”哦,這是父親。
父親慌里慌張地出去叫醫(yī)生。我看看四周,斑駁的白墻,強(qiáng)烈的燈光,刺鼻的藥水味……正當(dāng)懷疑自己是否病了時(shí),聽到旁邊有人說,“奇跡啊!昏迷了整整91天,竟然醒過來了。”“他們家終于有個(gè)盼頭了。”
醫(yī)生來了,翻開我的眼皮看了看,對(duì)我說:“張眼,閉眼,抬手……”我一一照做。最后醫(yī)生說:“嗯,是醒過來了。恭喜你呀!”父親的眼淚淌了下來,顫抖地握著醫(yī)生的手,不停地道謝。
“我兒子醒了,醒了。”……父親打了一個(gè)又一個(gè)電話。下午,我的身邊圍了好多好多人。一個(gè)個(gè)問我:“認(rèn)識(shí)我嗎?知道我是誰嗎?”一個(gè)個(gè)都眼淚汪汪。我記不起來,只能茫然地?fù)u頭。我只記得那個(gè)抱著我大哭的女人,是自己最親的母親。
“沒關(guān)系,出車禍的人都是這樣的。”親戚們勸著,“對(duì)啊,慢慢來,不要急,醒過來就好,醒過來就好了。”爾后終于聽明白,自己是出了車禍。
我沒有以最幸福的方式死去,老天爺給了我又一次重生的機(jī)會(huì),將我從鬼門關(guān)丟回了人間。
必須道歉說聲對(duì)不起
病情好轉(zhuǎn)一點(diǎn)后,父母把我?guī)Щ丶爷燄B(yǎng)。可剛回家的那段時(shí)間,父親天天不在家。我問母親,母親總是說:“去交警大隊(duì)了。”“去干什么?”
“去抓那個(gè)肇事逃跑的司機(jī),給你討回公道!”父親回家的時(shí)候,就帶回來各種各樣的人。
有時(shí)候是警察,有時(shí)候是記者,有時(shí)候又是無關(guān)緊要的什么人。我總覺得很煩躁,我討厭那些人可憐我的眼神。有天我聽到父親說:“他躲起來了,有人說可能去鄉(xiāng)下了。”
母親說:“那可不行,你一定要找到他。醫(yī)院里的醫(yī)藥費(fèi)還欠著呢!”
“嗯!”
父親出門了,一去就是一個(gè)多月。回來的時(shí)候,他衣衫襤褸,風(fēng)塵滿臉,手里還緊緊拽著一個(gè)人,那個(gè)人也同樣狼狽不堪。父親把那人拉到我的面前:“說吧,快點(diǎn)!”
那個(gè)人愣愣地看著床上的我,神情復(fù)雜,張了張嘴卻吐不出半個(gè)字。
我茫然地看著,不知道父親要那人說什么。父親扭頭望向我:“兒子,這個(gè)人就是撞你的司機(jī)!就是害你躺了91天,現(xiàn)在還不能走路的人!”
我聽得出怒氣在他胸腔內(nèi)燃燒。父親對(duì)著那個(gè)人怒吼。那個(gè)人又走近了一步,低著頭。他嘴巴終于張開了,顫抖地說了一句:“對(duì)不起!”
話音剛落,他便猛地跪在地上失聲痛哭。
父親似乎更來氣了,拽起那個(gè)人:“誰讓你跪著了,男兒膝下有黃金。你有點(diǎn)骨氣沒有?”尷尬的氣氛僵持了許久,那人吃力地站起來深深鞠了一個(gè)躬,轉(zhuǎn)身跌跌撞撞地走了。
母親疑惑不解:“怎么讓他走了,錢要到了嗎?”
父親搖了搖頭,“他沒錢。”母親一下子大哭了出來,對(duì)著父親又踢又打,“你這個(gè)沒用的人,你千里迢迢找到他,就讓他說一句對(duì)不起就算了?你到底有沒有為兒子想過?”
父親悶聲說:“兒子治病的錢我會(huì)賺到,用不著你擔(dān)心。”
這以后,父母親三天兩頭地吵架。父親的脾氣也越來越暴躁,有時(shí)候誰也不愿意搭理。后來父親才告訴我,那人家里很窮,有一個(gè)兒子,比我小兩歲,是個(gè)殘疾人。來城里是跑業(yè)務(wù)的,肇事的大眾車也是臨時(shí)租來的。
父親又說:“我不讓他賠,但是我必須讓他向你道歉,這是他一個(gè)男人應(yīng)該承擔(dān)的責(zé)任。兒子,你要記住,一個(gè)人做錯(cuò)了事情要敢于面對(duì),這才是真正的男子漢。”
血濃于水的呼喚
回想起來,在我的記憶中,從小我只愛依戀母親,不喜歡父親。父親是個(gè)脾氣很執(zhí)拗的人,他永遠(yuǎn)愛給我買鮮艷的亮色衣服。只要我出門,他就要我穿亮色衣服。一直到上初中,無論怎么反抗,父親依然頑固不化,有時(shí)候真覺得自己被約束過頭了,連穿衣服的自由都沒有。
2008年,我和朋友一起做生意,資金周轉(zhuǎn)不靈,在最艱難的時(shí)候向父親求助,父親卻沒有伸出援手。那次以后我和父親之間本就不親密的關(guān)系冷到了冰點(diǎn)。
時(shí)間是支隱藏在歲月深處的鎮(zhèn)靜劑。誠然,從前總覺得父親對(duì)我不好,但現(xiàn)在想想,我又何嘗不是一直忽視父親,甚至沒有對(duì)父親認(rèn)真笑過,也從來沒有用親熱的語氣喊過一聲爸爸。一有什么事情第一時(shí)間找母親,父親于我而言仿佛就是個(gè)陌生人。自從我車禍之后,連一向勤勞的母親都不得不承認(rèn):“這段日子最累的就是你爸了,你出事以后,他就把醫(yī)院的走廊當(dāng)家了,每天吃睡都在那里。那時(shí)候還是春天,醫(yī)院的花崗巖地板冰冷冰冷的,你爸困極了就在地上睡。”
我很心痛:“他怎么不回家睡呢?家和醫(yī)院很近啊。”
“他怕你醒過來看不到他會(huì)害怕,他想第一個(gè)看到你醒過來啊。”
更令我難受的是,醫(yī)院有規(guī)定,重癥室的病人是不能隨便探望的。父親為了時(shí)刻了解我的病情,連重癥室里打掃衛(wèi)生的師傅都打點(diǎn)好了。每次師傅打掃出來他就上前尋問情況。
師傅不懂病情,就把從治療儀器上看來的數(shù)字(血壓、心跳等等)告訴父親。父親更不懂,記下來跑去問醫(yī)生。一次又一次,醫(yī)生被他問得煩了:“你兒子醒過來的幾率極低,即使脫離危險(xiǎn)期,以后90%也是個(gè)植物人,除非奇跡出現(xiàn),你要做好心理準(zhǔn)備。”
父親好像聽不懂這些,不管醫(yī)生怎么說,他總是執(zhí)拗地堅(jiān)持著:“他是我兒子,我最了解他,能不能醒過來我自己知道。”
我這才恍惚憶起,原來沉睡的3個(gè)月里,“夢(mèng)中”那個(gè)呼喚的聲音是父親在一遍遍喊我:“兒子,醒來吧。快醒來,爸爸等著你呢。”endprint
“兒子別睡了,這么貪睡,對(duì)身體不好啊。”
老父親的脆弱,有時(shí)真的比新生的嬰兒更讓人心疼。
父親執(zhí)意畫斑馬線
在家療養(yǎng)期間,父親有天下午興沖沖地對(duì)我說:“兒子,我要為你做件事。爸爸要讓他們?cè)谖覀冃^(qū)門口畫上一條斑馬線。”
母親告訴我,我出車禍的地點(diǎn)正是在小區(qū)門口的國道線上。聽說,在我之后依然有人不斷地在同一地點(diǎn)發(fā)生車禍。
父親認(rèn)認(rèn)真真地在家寫申請(qǐng)書,說是要交到縣政府。他文化程度不高,寫起來很費(fèi)力,寫了撕,撕了又寫。他一邊寫一邊感慨:“要是你病全好了,就可以幫爸爸寫了。”
好不容易寫完了,父親請(qǐng)內(nèi)行的人來看。那人看完了說:“你這樣不行啊,得有數(shù)據(jù)。這條路上有過多少場(chǎng)車禍,傷亡的人有多少。斑馬線不是你說要畫就能畫上的,政府不會(huì)因?yàn)槟阋粋€(gè)人就給畫一條啊,這有規(guī)定的。要不然不都亂套了?”
內(nèi)行人幾句話就把父親兩天的勞動(dòng)成果給否定了。
父親又跑去交警隊(duì)要求幫忙,好話說盡,人家還是把他趕了出來。
他不服氣,厚著臉皮去求人,終于有人同意幫父親,找來了數(shù)據(jù)。父親激動(dòng)地念給我聽:“2006年交通事故202起,18人死亡,68人重傷……這么多人都在這條路上遇難了啊,幾家人受得了啊?”
當(dāng)天中午,父親沒睡午覺,刷刷刷地把申請(qǐng)書寫好了,拿著申請(qǐng)書就挨家挨戶串門,要小區(qū)所有人簽名支持。
很多人勸父親,“你不要白花力氣了。政府、交通部門豈能聽你一個(gè)人指揮?”父親搖頭,“不,我一定要討個(gè)說法,我不能讓我兒子就這么白白地被撞了。”
沒有人可以拉回發(fā)了瘋似的父親,他片刻不休、馬不停蹄地又跑開了。整個(gè)小區(qū)6棟樓,300戶人家,接近1000人。父親一個(gè)一個(gè)找上門去,從1樓到10樓,有的人白天在晚上不在,有的人晚上在白天不在,父親就白天跑晚上跑,第二次,第三次……父親這一跑就是整整10天,連夢(mèng)里也嚷嚷著讓人簽名。還好小區(qū)的人多數(shù)都知道畫上斑馬線對(duì)他們也有莫大的好處,父親最終獲得了多數(shù)人的支持。
皇天不負(fù)苦心人,半個(gè)月后,父親把那張寫滿名字的紙給我看,“兒子,你看,這是大家對(duì)我們的支持。爸爸不是一個(gè)人在作戰(zhàn),而是整個(gè)小區(qū)的人。畫上斑馬線以后,大家就不用擔(dān)驚受怕地過馬路了。”我看著馱了背的父親,忍不住拍拍他的肩:“爸,你休息休息啊……”
男孩穿得鮮艷并不可笑
申請(qǐng)書終于交上去了,父親松了一口氣。我拉著父親坐在身邊,心平氣和地聊天。我們聊車禍,聊小時(shí)候,我突然問父親:“小時(shí)候,你為什么老是要我穿亮色的衣服。我那時(shí)候可恨你了,一個(gè)男孩子穿得那么惹眼,會(huì)讓人家笑話的。”
父親停了話,愣愣地看著窗外:“馬路上車來車往,太危險(xiǎn)。穿著亮色衣服顯眼一些,司機(jī)就能注意到你。想不到還是出了車禍,爸還是保護(hù)不了你……”
隔天,父親滿臉笑容地對(duì)我說,“兒子,爸帶你下樓去看看。”我坐在輪椅上,父親在后面推著我。一出小區(qū)大門,就看到馬路上雪白的斑馬線,在陽光下耀眼極了。整個(gè)小區(qū)都轟動(dòng)了,大家都跑出來看,看到我和父親,大伙都拍起了手。
父親在眾人的歡呼聲中俯下身來,用消瘦的尖下巴頂著我的頭,雙手環(huán)抱著我。我抬頭看著滿臉皺紋蒼老的父親,淚水滂沱……
有時(shí),我會(huì)猛然想起,也許老天爺再次賦予我生命的原因,是不忍傷害這個(gè)單純又渴望我回到他身邊的父親。
如今,那條101國道線上新添的斑馬線,所有人都叫它“親情斑馬線”。
林冬冬摘自《華夏關(guān)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