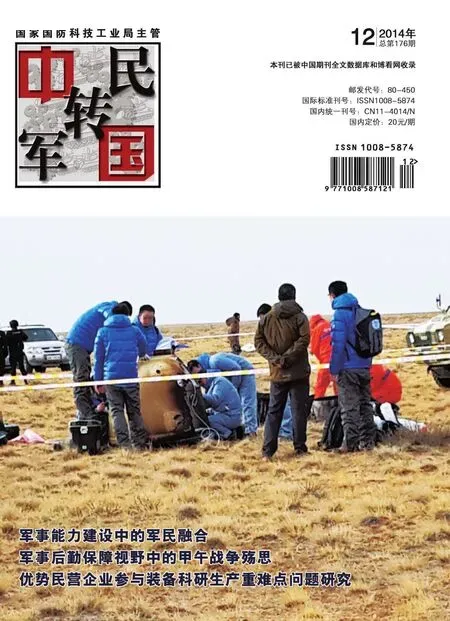離職退休以后
——我的軍工生涯(十)
■ 懷國模
離職退休以后
——我的軍工生涯(十)
■ 懷國模
到2012年我已步入八十高齡,回顧我一生的軍工生涯,能親歷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創建、改革與發展,是我的榮幸。在漫長的道路上個人能為之盡一份微薄之力,為筑起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添磚加瓦,終身無憾。我要感謝培育、幫助、關懷我的人,實在太多太多。

1997年7月15日曹剛川主任、李繼耐政委與我談話,傳達軍委已下達我的離職命令。7月18日開了科工委常委會議,正式宣布我免職事。至此我的軍工生涯已告結束,從那時算起,至今又已過15年(注:成稿時間為2012年),但仍心系國防科技工業。幾十年建立起來的深厚感情,使我難以割舍軍工情結,在思想上并未完全告別軍工。還經常利用各種機會到各地的軍工廠、所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些情況,也向中央和有關領導反映一些情況和建議。
總結過去,思考未來
1997年下半年,離開工作崗位以后靜下心來,回顧過去,思考未來,寫了幾篇稿子。關于國防科技工業改革與發展的思考之一《制定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國防科技發展戰略迎接新軍事革命的挑戰》,思考之二《抓住機遇搞好國防工業的戰略調整》,兩文均列入1998年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年會論文集。并送劉華清、張愛萍、鄒家華、曹剛川、李繼耐。思考之三《適應新的形勢,把軍民結合推向新階段》,經呈送鄒家華副委員長,他隨即批請吳邦國同志參閱。
1997年5月應國家科技部要求,由我牽頭組織“軍民兩用技術產業化發展研究”,經過擬制項目建議書,于10月召開課題組第一次會議。參加課題研究的有王峰、劉林山、李蔭濤、劉永恩、鐘家雪、朱榮桂、歸永嘉、王雨生、李鷹翔、侯印嗚、劉路弘等同志,他們對軍轉民情況都比較熟悉,經過研究討論、到基層調研、起草研究報告、聽取各軍工集團公司領導和專家的意見,反復修改報告,于2000年5月結題。請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鄧壽鵬、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周叔蓮、國防科工委副司長陳根甫等同志組織評審組評審,認為課題研究“總結了國防科技工業改革開放20多年來軍轉民的發展歷程,提出了發展軍民兩用高技術產業的框架體系和建立技術創新體系等建議,具有創新性、綜合性、系統性、戰略性和前瞻性,對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和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具有決策參考價值。”研究報告呈送鄒家華同志,7月4日他作了批示:“在這樣比較深的研究的基礎上,能否和國防科工委商量把軍民兩用技術落實到目前還缺乏能適應市場需要的產品的軍工廠去,幫助他們開發產品,適銷市場,提高效益,扭轉虧損。使這個研究成果產生積極的效果。”
2000年3月,我出席總裝備部科技委年會,作了《新世紀武器裝備發展戰略若干問題的思考》的報告。
2000年12月,我在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第3屆學術年會上作《經濟全球化與軍民兩用高技術產業化》的報告。
2000年我寫的《發展軍民兩用高技術實現國防科技建設新跨越》登載在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將軍文選》上。
2001年12月,應邀在上海交通大學作《展望21世紀國防科技發展》的報告。
2003年7月應軍事科學研究會之邀,寫了《世界新軍事變革對我國武器裝備發展的啟示》。刊登于《中國軍事科學學會通訊》2003年第3期。
2003年10月在浙江工程學院作《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歷史回顧與未來發展展望》的報告。
2003年12月在中國軟科學研究會年會上作《加強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雙向轉移,發展軍民兩用高技術產業化,推進寓軍于民新體制》的報告。
2004年4月在中國民用工業企業技術與產品參與國防建設研討會上作《加強軍用技術和民用技術雙向轉移,發展軍民結合推進寓軍于民》的報告。
2005年10月在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召開的“國防科技與國防安全”研討會上做《抓住機遇,深化改革,促進國防科技工業不斷發展》的總結性發言,刊登在《軍事經濟研究》2006年第1期上。
2005年12月在第5屆中國軟科學學術年會上作《論國防科技與國家利益》的報告。
2006年6月在國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作《對自主創新的幾點認識》的報告。
2006年9月在國家信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作《關于我國國防工業發展問題的探討》的報告。
2006年10月寫了《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促進武器裝備建設》。
2007年12月10日,在《科技日報》舉辦的“學習錢學森創新思想,培養領軍人才”的專題研討會上,作《培養創新人才,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發言。
對核工業發展方針的幾次建議
在我國經濟技術還很落后的情況下,毛主席、黨中央英明決策自力更生研制兩彈,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上世紀八十年代,核工業實現了保軍轉民的戰略轉變。進入二十一世紀,在新的歷史發展時期,核工業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發展戰略,爭取更大的進步,發揮更好的作用。作為一個曾在核工業戰線工作多年的一員,始終關心和思考這一問題,即使在退休以后,還多次向中央提出建議。
2003年5月,我向鄒家華同志寫信,呈送核工業幾位專家寫的《世界核能的爭議與我國核能的未來》研究報告,信中提出“過去由于我國經濟能力有限,采取‘適度發展核電’的方針;從長遠看,作為我國能源發展的戰略方針,核電應當加快發展”。經鄒家華同志批請曾培炎副總理,轉報溫家寶總理。得到他們的重視,責成國家發改委研究。于2003年8月函復,認為“所提建議對我國核電自主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時間到了2004年9月,國家已確定積極發展核電的方針,但因對核電發展選用何種堆型有不同認識,新的核電站遲遲未開工,我對此深感憂慮。9月7日約請核工業集團公司科技委副主任郝東秦談談情況,核工業集團公司黃國俊副總經理也來參加。大家深感核電的發展是國家戰略問題,需要引起高層決策的進一步重視。經過幾天的思考,我寫了對核工業技術發展戰略的幾點建議。提出我國核技術工業的發展,應當統籌解決軍用和民用兩方面的需要,要把核電事業的發展作為我國能源戰略的重要組成。并提出了三點建議:
一、核電站的發展從技術水平到建設規模要有一個深謀遠慮的長遠規劃。
二、核燃料和元件后處理的生產規模,要與核電站的建設同步發展。
三、大力加強核科學技術研究,保持領先地位。
報告經鄒家華同志于9月22日批請曾培炎副總理并溫家寶總理閱示。溫總理于10月1日批:“所提意見值得重視”,曾培炎副總理批:“請汪洋、尤權閱報黃菊同志并發改委、國防科工委。”

2008年1月4日到核工業集團公司與于劍峰副總經理、科技委郝東秦副主任、劉建橋秘書長討論在國家重視核電發展的形勢下,如何發揮核工業集團的技術優勢,建設軍民結合型核工業體系。在總的認識上大家比較一致,于劍峰表示為了推動核工業建設的發展,支持開展課題研究。于是開始了《建設軍民結合型核工業體系發展戰略研究》的課題研究。課題組由我牽頭,參加人員有糜振玉(原軍事科學院副院長)、李鷹翔、郝東秦、劉建橋、劉林山、劉潔、嚴叔衡、白云生、吳瑾等,研究報告在研討過程中,聽取了原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原國防科工委政委伍紹祖,以及核工業部老領導劉杰、蔣心雄、趙宏、彭士祿等同志的意見。于8月完成了最后修改稿。報告提出“核科技工業承載著持續鞏固發展我國核力量和加快推進核電產業發展的雙重歷史使命。面向未來發展要建設軍民結合、寓軍于民、科學高效、協調順暢的核科技工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建設軍民結合、科研生產結合、產業上下游結合、體系完整、相對集中的自主創新型核科技工業體系”。提出了軍民結合型科技工業的發展目標和思路和若干措施建議。經伍紹祖同志寫信,呈送李克強副總理。李批請張德江副總理并發改委、能源局研閱。
編寫國防科技工業發展歷史經驗的書刊
國防科技工業的發展歷史,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由國防科工委副主任謝光組織科技部專門成立編研室編寫過《當代中國國防科技工業》卷。后來又由我和辦公廳編研室組織各軍工部門和民口軍工辦(局)編寫各行業的軍工史。這些都是比較系統的歷史敘述。在我退職以后,深感改革開放時期國防科工委在加強技術基礎、預先研究和軍民結合方面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和實踐,積累了許多寶貴經驗,值得后人借鑒。如果不及時總結、記錄,將來有可能散失。于是萌生了組織寫書的想法,得到了技術基礎局局長安衛國、副局長王峰(后任總裝電子信息基礎部副部長)的大力支持。
2001年元月,開始組織編寫國防科技技術基礎管理叢書《軍工產品質量管理》、《軍用標準化》、《國防計量》,負責編寫組的分別是周星如、孔憲倫、郭群芳,他們都是當時質量管理、軍用標準化、國防計量的組織者。在首次召開的會議上,我談了編寫叢書的指導思想、大綱要求。參與部分章節的編寫,對全書進行校閱修改。經過多次討論,到2002年底三本書經審改定稿,交國防工業出版社刊印發行。
2003年7月,又開始了技術基礎后三本書的編寫,即《國防科技情報》、《國防科技成果管理》、《國防專利》。于2005年5月刊印發行。這六本書均由劉華清同志作序,鄒家華同志題寫書名。
2005年組織編寫并出版《中國軍轉民實錄》,系統總結軍轉民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鄒家華同志作序。參加本書編寫的還有王峰、宮宏光、劉林山、方海鷗、劉潔、安衛民、李錦程、廖懷峰。
2009年寫了《歷史性跨越——親歷國防科技工業改革開放的回顧與思考》,于2010年由國防工業出版社出版。在這本書中記述了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到1997年,在國防科技工業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作為一個親歷者,撫今追昔,把我參與和經歷的一些事情寫下來,并盡可能地把歷史背景、決策過程、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和解決辦法的探索過程寫下來。既是作為歷史的記載,也是為后來者提供一些借鑒。
回訪各地軍工廠、所
離職以后,利用各種機會到各地軍工廠、所走訪。先后多次到陜西、甘肅、四川、重慶、遼寧、吉林、黑龍江、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內蒙、天津、江西、安徽、江蘇、浙江、上海、山東、廣東等地。雖然我已不在位,但所到之處,都受到各省國防科工辦和廠、所的熱情接待。省科工辦的領導專程陪同,所到廠、所都不忘記當年在困難時期給予的支持鼓勵,那怕微薄的幫助。
2002年我同王峰、金擊強(原航空工業部民品司司長)到哈爾濱飛機公司,見到郭景山副總經理。他深情地回憶起當年為上民品微型汽車生產線,到我辦公室申請外匯資金支持,得到解決,離開后高興得流下眼淚。現在看到他們生產的松花江微型汽車已成為全國知名產品,民品的發展也支持了飛機研制條件的改善。對于他們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軍民品齊發展深感欣慰。
四川長虹機器廠原是生產飛機雷達的工廠,單一的軍品生產使工廠處境困難。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靠國防科工委上收的外匯支持,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彩色電視機生產企業,產品行銷國內外,看到工廠欣欣向榮,感到由衷高興。重慶長安機器廠原是生產小口徑艦炮的軍工廠,現在已經發展成為現代化的汽車生產工廠。這是兵器工業實現軍轉民的一個突出典型。
2010年我借到上海參觀世博會之便,參觀百年老廠江南造船廠搬遷到長興島的新廠區。由老廠長陳金海陪同介紹當年搬遷之艱辛,現已建設成為世界一流的現代化造船廠,令人振奮。
2011年9月,應陜西省政府和國防科工辦邀請我和原國防科工委幾位老同志重訪陜西的部分軍工廠、所。陜西省歷屆主管軍工的副省長婁繼偉、劉春茂、龔德順、崔林濤等熱情地和我們聚會。省科工辦領導張濤、趙西林、蘇文山陪同參觀。所到之處看到一片片新廠房拔地而起,安裝了現代化的設備,完全改變了過去數十年老廠的形象。我深有感慨地說:“這次陜西之行,回想過去,看到了陜西軍工面貌大變的今天,也看到了充滿希望的明天。”
各省國防科工辦為交流工作經驗,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每年都要輪流在一個省召開科工辦主任聯席會議。我過去在位時因工作忙沒有機會去參加,退下來以后,他們還盛情邀請我去參加。我先后于2003年、2004年、2007年、2011年到遼寧丹東、湖北武漢、甘肅蘭州、江西景德鎮參加聯席會,見到了一些還在位的老主任,也認識了一些新上來的主任,倍感親切;同時也了解了許多新的情況。
這里不再逐個講述我在新世紀走過的軍工廠、所給我的感受。總之,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經過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防科技工業實行改革開放、戰略調整、艱苦創業、不斷進擊,已經進入欣欣向榮充滿生機活力良性循環的發展階段,這是幾代軍工人奮發圖強、艱苦努力、夢寐以求的理想。
感恩
到2012年我已步入八十高齡,回顧我一生的軍工生涯,能親歷我國國防科技工業的創建、改革與發展,是我的榮幸。在漫長的道路上個人能為之盡一份微薄之力,為筑起保衛祖國的鋼鐵長城添磚加瓦,終身無憾。我要感謝培育、幫助、關懷我的人,實在太多太多。
首先是養育我的父母。我的父親懷寶汝,生于小康之家,早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教育系,畢業后執教于蘇州、紹興、嘉興等地的中學。抗日戰爭爆發后轉輾來到上海,與旅滬浙江教育界同仁在孤島創辦浙光中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淪陷,學校被迫停辦,舉家返回嘉興。他安于清貧,淡泊一生,從不趨炎附勢結交權貴。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十分重視對子女教育,把培養子女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作為自己的責任。不論家庭經濟多么困難,都盡力使子女能受到高等教育。在工作和家庭負擔沉重的情況下,晚上還抽出時間輔導我們學英語。他對子女最深刻的言傳身教是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克勤克儉、關心他人、報效國家。我的母親陳學珊,出生于書香門第,知書達理,終身安于操持家務,為全家生活辛勤操勞一生,但從不愿為自己的事情麻煩別人。在對母親的最后告別儀式上,我弟弟國楨寫的挽聯:
淡泊有真諦一生勤勞含辛茹苦持家
平凡見深情終身儉樸養兒育孫成材
充分表達了我們對她一生的涓念哀思。
還要說的是要感恩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對我的培養教育。上海交通大學是我國創辦歷史最悠久、辦學水平最高的幾所現代大學之一,尤以培養理工科人才著稱,有“東方MIT(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之美譽。從建校之日起就高揚“救國、興國”的旗幟,把為國家、民族培養優秀人才為己任,形成了“起點高、基礎厚、要求嚴、重實踐、求創新”的辦學傳統。交大不是象牙塔里的課堂,而是具有革命歷史傳統的學府。解放前夕,交大學子把生死置之度外,追求真理,勇敢地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作斗爭,學校享有“民主堡壘”之稱。
在學校短短幾年的學習生活,使我初步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健康的思想、道德品質和人格。朱物華、蘇元復等學高為師、身正為范的師長學者,治學嚴謹,親自為我們講課,給我們打下了良好的學業基礎。我住宿的西齋門前,樹立“飲水思源”的校訓紀念碑,在我心中永遠建立起難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在我的一生中遇到過許多令人至今懷念的老領導、老同志。在我還涉世不深缺乏工作經驗的時候,引導我走向人生,幫助我培養我增長才干,做一個有益于國家人民的人。
前面提到過鞍山鋼鐵公司的領導王玉清、王金棟、李力、計晉仁等是我的帶路人。后來在二機部劉杰部長、張漢周局長,到國防工辦的劉柏羅副秘書長、二局陳一民局長,以及后來的方強主任、洪學智主任、周一萍副主任等等,都對我有很大幫助,他們出以公心,為黨愛護培養年青干部,使我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逐步成長。
要特別提到的是兩位尊敬的領導,慈祥的長者。
一位是鄒家華同志,他在1973年批林整風以后調任國防工辦副主任。至今算來我們認識已有40年。當時成立國防工辦黨的核心小組,我們同為核心小組成員,差不多每個星期都在一起開會。在當時的政治氣候情況下,反對無政府主義,反對派性,我們息息相通。我們共同承受“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壓力。特別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對江青借寶雞212廠氣浮陀螺事件攻擊國務院不支持自力更生的事件,他實事求是地向中央寫報告,說明沒有壓制自行研制的情況。
在工作中他作風民主、循循善誘。他在擔任國家計委主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對科工委的工作非常支持,有事要向他請示匯報,總是很快得到安排接見。有一次到他辦公室匯報工作時談起我與計委國防司一位領導在具體工作上有一些不同意見,他馬上打電話找到這位同志說:“在具體業務工作上你們沒有國防科工委清楚,要聽國防科工委的。”
在他擔任副總理期間,每遇到外地調研視察,經常通知我跟隨他去(曾到過陜西、四川、遼寧),有關國防科技工業的情況,要我發表意見,更多的是聽他的指示和教誨,使我深受教益。他退了以后,我每年都去看望他,他非常關心國防科技工業的情況,有時還提出問題,我當時不能答復的,回來向有關同志了解后,向他報告。有一些值得參考的意見建議,他都批請國務院領導參閱。
還有一位是劉華清同志。早在1964年我到國防工辦工作時,他是國防科委副主任,我們同在旃壇寺大樓辦公,但沒有直接接觸。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1970年,他當時作為海軍造船工業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負責人主持召開051艦研制生產協調會,我作為國防工辦派出的代表參加會議。當時一些造反派打著反對以生產壓革命的旗號,態度囂張,但他耐心地做說服教育工作,給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在他擔任總參謀長助理、科技裝備委員會副主任、海軍司令員期間,工作上時有接觸。后來他擔任軍委副秘書長、軍委副主席直接主管國防科研生產和武器裝備期間,更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得到他的言傳身教。
他為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對工作實事求是,對同志平易近人堪為楷模。他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后,每個星期要打一次橋牌,我做他的搭檔,我們的接觸仍較多。在娛樂中,更是一位慈祥的長者,平等待人而從不以勢壓人,打輸了一笑了之從來不發脾氣,從不埋怨對方。2006年9月25日他和夫人徐宏霞專門請軍工部門的老同志攜夫人在軍委八一大樓過國慶中秋,飯后照相留念。以后我還經常去他家看望,他雖然話不多,但總是很高興聽我們說話,臨走時送我們到門口,笑著向我們敬禮告別。2011年元月12日他在301醫院彌留之際,我去醫院,看到他躺在床上已不能睜眼說話,但十分安祥。我敬愛的老領導、尊敬的長者走完了一生。他的高風亮節,堪為楷模。
在我退休以后,我的妻子劉惠瑗還在工作崗位上從事繁忙的建筑設計,不管工作有多忙,在生活上對我無微不至的照顧。她支持我寫這本書,承擔起一切家務,使我能集中精力寫作。我的秘書戚太友,承擔了全部書稿的文字打印工作。我感謝他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