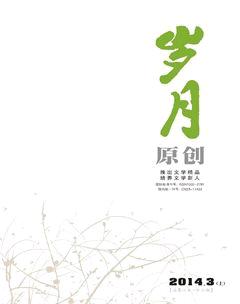鄉下的慢節奏
余世磊
時間像根松緊帶,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即使很短的時間,但若在鄉下的手中,總會被拉得老長老長。
閑回鄉下,啥事都不用管,放心地睡吧。一覺醒來,一方穿黃衣裳的太陽,爬上我的床來,仿佛要借我的床,再睡個回籠覺。沒有鐘表,不知道是啥時,也不去管是啥時。穿衣起床,媽媽這才洗凈鍋臺,還沒正式做早飯。不著急洗漱,先到村里轉上一圈,逗逗鄰家乳兒,看看莊稼花兒。太陽已經升起很高了,根據以往的經驗,知道時間肯定不早,開始有了些關于時間的意識。突然,聽見一聲公雞鳴,長長的,由低音向高音,在高音處,又急速地滑落下來。隨后,幾只公雞也附和起來,此起彼伏。雞鳴總是與時間有關,這時候的雞鳴表示什么?我不知道。真的,這些雞鳴,把我剛剛才有了些的時間意識,又給弄散了,弄亂了。
看幾家屋頂上,已經有了炊煙。炊煙也是有性格的,有的是急性子,有的是慢性子。常常,急性子的炊煙已經散盡,慢性子的炊煙還沒有升起。炊煙急,人不急也不行,有人還在山上放牛,有人還在田里薅草,把飯弄熟了半天,還是吃不成,都成了剩飯了。其實,我說的那炊煙的急性子,也只是相對而言,急不到哪里去。總要等到村里人家前七八后吃完了早飯,早晨才能算過去,是上午的時光了。
如果在農閑時節,生活的節奏就更散漫了。春節我回鄉下過年,吃罷早飯了,去邀堂哥一起給姑母拜年,堂哥的門還關著,一家居然還在睡覺。把堂哥喊醒,堂哥說,又不是去趕考,急個什么?人在鄉下,生活得久了,那種散漫就浸沒了一個人,滲入到骨子里頭。不自覺的,走路的步子放慢了,對事物的思維也變緩了。像我住在城里,也擺出幾分臭清高,從來不去人家串門,極度瞧不起某些人,但回到鄉下,常常,信腳,便走進了村里一戶人家,逗逗他家的小兒,聊聊些可有可無之話,一坐便是半天。
鄉下的午飯相對也會推遲,大約要到一兩點的光景,這樣一個漫長的上午,能做多少事情呀!可以到離我家十里的巖上,去砍一擔柴,砍柴間隙,如果在春天,還可去尋一把蘭草花;如果在秋天,還可去摘些野柿子之類。挑柴而歸,路上歇上幾陣,到家日頭尚在頭頂;如果把手腳放麻利一點,不去尋花采果,路上少歇一陣,砍上兩擔柴也可;像我大哥身體特好,做事雷厲風行,甚至可以砍上三擔柴,不過,那是他年輕時候的事情了,現在年過半百,不行了。如果是個巧婦,一個人,可以揉出一百多斤油菜籽;可以打滿滿一擔豬菜;可以挖兩畦地,施上肥,再種上蘿卜;如果有幫手,可以舂出一斗米的糯米粉,過年前做年粑……
而在城里,一個上午我能做些什么?不過看兩張報,喝一碗茶,或者向領導匯報一項工作,或者把一篇公文擬個開頭;或者幾個人七嘴八舌,開一個毫無意義的會議……看看表,又到了下班的時間。
夏天日子長,一個上午,不遜于冬天一日。午飯后睡上一覺,也可算一個短夜,又可避開炎夏的烈日。睡至日頭偏西,起床去割稻、薅草,傍晚再摸點黑,也不比上午做的事少。這長夏一日,可以分成兩天了。
天陰、雨、霧或雪,不見太陽當空,亦不見日影移動,便連個大概的時間也估不準確了。要么,把時間估得太早,要么,把時間估得太晚。看家家屋頂的炊煙,雖然往日里升起時前七八后,但也不會相差太長的時間,至少分得出一日三餐。而在這樣的天氣,就完全亂了套,從早到晚,都在人家的屋頂上冒著。我媽媽去鋤紅薯地里的草,直到半下午方歸,用茶泡點剩飯,當作午餐,雖然讓肚子受了委屈,心卻喜這一天做的事真不少。鳥雀也把時間弄糊涂了,在暗淡的天色里早早歸來,少了它們的唧唧喳喳,村子里顯得安靜了許多。直到夜幕籠罩,三三兩兩的燈火差不多同時亮起,才把這亂了套的時間重新校正,找回那份失落了的生活的節奏。
最怕是這樣的冬夜,外面下著冷雨,無人來串門,一個人枯坐,電視里又沒有什么好節目,百無聊賴,不如早早上床,偎進被子里。睡了長長的一覺,醒來,但聽村里人語、狗吠、電視聲,知道這夜還早著呢。年輕人會睡,上了年紀的人就再也睡不著了,不知何時才盼來天明。
城里的一天,太陽升起來,滋溜一下,便從東滑到了西,了差事似的。鄉下的太陽不是這樣,在巴掌大的一塊天上,老不急的,遇云要到云中去串串門,遇鳥要和鳥拉拉家常,感覺過了很長時間,才挪移了一丈來路。有時,空中無云,也無鳥,太陽也會分神、發愣,忘了走動。夏日正午的某一刻,時間仿佛靜止了,蜻蜓停在籬笆上,一動不動。風也像凝固了,風中的小樹,一直保持剛才被風吹斜的狀態。人在閑時,尚可看看書,串串門,無事找些事做。牛也想出去走走,可是,一根繩子將它系住了。從秋到冬,牛的日子就有些難捱了,只能臥在牛欄里,把干稻草吃進去,又吐回嘴里咀嚼。看這時牛的眼睛,是憂郁的,灰暗色的,渾濁的。終于,等到春暖花開,有田可耕,再看牛的眼睛,是歡樂的,明亮的,清澈的。
我回鄉下住一日,再回到城里,感覺就像住了兩日,甚至更長時間。真的,在鄉下過一輩子,抵得上在城里過兩輩子、三輩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