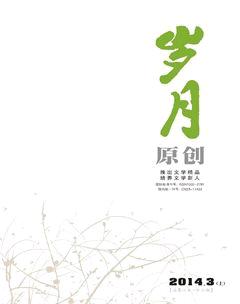對人間煙火,守望著生命的風景
邢海珍
曹立光就是“荒原狼”。近些年來,這位名為“荒原狼”的詩人以其強悍的詩風出現在我視野的地平線上,他的詩和詩人的這個筆名一樣,帶著一種野性的沖動和生命的張力,其中不無自然的新鮮和原色在。《北緯47°》是他的第一本詩集,這是詩人耕耘多年之后的收獲,是他在發表了大量作品、創作進入了較為成熟時期的一次階段性的總結。
在黑龍江的詩人群中,“荒原狼”曹立光已是赫赫有名的一位。多年來他對詩歌執著、癡情地追求,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的作品,不斷有各種獎項收入囊中,影響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在詩人的筆下,故鄉小興安嶺注滿了詩的深情,那里的土地、河流、草木、云霞都被人性和詩情的靈光所普照。一個離開故鄉的人,心里永遠裝著故鄉,他的詩從懷戀和反思中表達著詩人的赤子情懷。在詩集的后記中,曹立光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此刻,當我在臺燈籠罩的鍵盤上,敲擊出這些和小興安嶺有關的文字時,我在內心深處得到了一種寬慰和滿足。不為別的,只為我是一個有故鄉的人,我是一個有根的人就值得了。等老了的時候,和妻子一同回去,在湯旺河邊蓋一間樺樹木刻楞,親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聽風,聽雨,聽松濤,閑看吃飽草的馬兒甩動尾巴,累時煮一鍋星星共品夜的清涼,與來訪的親人在天狼星的守護下,詩意地棲居。”其實作為詩人的曹立光,重要的不是他“等老了的時候”能否回到故鄉的土地上“詩意地棲居”,而是寫詩的當下心系故土的一種精神返鄉行為。這樣的懷想和思戀就是詩人的真性情,他寫出的詩才能有情懷有境界。毫無疑問,詩人曹立光深愛著自己的故鄉,是小興安嶺這片神奇的土地賦予了他詩的靈感,他的詩思開闊而渺遠,像山泉宛轉回環,像澗谷幽謐深邃,像霧嵐飄逸空茫。他的詩多是短制,或以情致見長,或以靈性取勝,詩人著力提煉語言和詩意的純度,讓自我內在的心性在直覺的境界中快捷而強烈地突顯出來。在這首《一些草》為題的短詩中,詩人寫下了這樣十個短句:“送走白露/陽光從流水深處/伸出手來/掐掉黃葉、花朵和風/包括鮮活的生命/”我不是以精選的方式引述此詩,而完全是以抽樣的方式把它提取出來,這樣或許更能體現一種代表性。詩寫得簡潔、干脆,語體樸實自然,但又是平中見奇,警策而有深度。詩人寫“一些草”在嚴酷的現實中與命運抗爭,白露、秋分天氣轉冷,自然界中的“草”由綠變黃,那些葉子、花朵及“鮮活的生命”將走向悲劇的時刻。關注事物最微末的部分,去發現事物本質中被人忽略的微妙內涵,含淚的秋分,被空白壓低的土地,寫草的生命動態,“招展良知與信念的旗幟”,“一次次彎下腰來”,經驗性的內容不是直白地表現出來,感性和理性含而不露地詩化為意象的存在。在曹立光的這一本詩集中,像這樣的詩不是特例。
在哲思追索和生命探求的詩學本質意義之上,作為一個詩人又必然尋找一種感性世界里有關個人化的“個在”的身世與角色的內容,這當然是藝術創造前提下所不能忽略的。曹立光對于鄉土的關懷,讓故鄉的具象性事物進入藝術化的情感世界,從根本上說是真實的生命歷程、是靈與肉深切體驗和感悟的一種過程性的足跡。當一個人以其真實身份的角色返身回到詩中,它便是詩的血肉精魂和根性所在,詩意的本身便不再是凌空蹈虛之物了。在《我寫下》一詩中,詩人有這樣的表述:“在一卷風濕的陽光中,我寫下/湯旺河白紙的青春和黑字的履歷/懷揣火苗,在生活的低處/隨時保持自己的堅硬和清白/簡單愛,好好活著/學習流水的從容和落花的無畏/讓這個我所經歷的人世/因為我寫下的每一個字而顫栗”在這樣一首宣言式的詩歌中,詩人以一條故鄉的河作為感性的精神依托,表達了一個平常的人努力追求的人生與生命境界,白紙黑字,流水落花,保持了與土地有關的質樸和本色。在“生活的低處”不斷砥礪自我,“簡單愛,好好活著”,并“隨時保持自己的堅硬和清白”。語言平實,但詩意的境界卻高拔向上,詩的余音讓人體味不盡。“湯旺河”是與家鄉有關的標志性意象,它自然也是詩人身份與角色的佐證,對于整個詩意的拓展有一種固定性意義。這實指的事物當然不僅僅地只局限于一條河流的本身,在詩中是與人的生存和命運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的。
著名詩歌理論家沈奇在評述先鋒詩歌話語取向的《“說人話”與“說詩話”》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論述:“為此,以伊沙為代表的更年輕一撥的先鋒詩人們,針對惟美惟雅只說‘詩話的詩壇積弊提出詩人也要說人話,要言體及物,力圖讓詩變得有血有肉,有生命痛感和生活氣息,不再那樣濫情矯情和偽貴族氣,實在是又一次革命性的進步。我們曾將詩作為向廟堂獻禮的祭品,后來又將詩局限于精神后花園中的散步,總之轉來轉去,總轉不出高蹈酸腐的調調。現在終于有一只年輕的手,將詩拽回到我們生存的現實、生活的大地和日常生命狀態中來,讓它說點人話,多點人氣,變得更堅實、晴朗和親和一些,甚至性感一些,不失為對積弱甚久的中國新詩,一劑‘壯陽補鈣的良藥。”(《沈奇詩學論集[卷一]》第31—32頁,中國科學出版社2008年1月)當然,曹立光還不屬于伊莎那樣的先鋒詩人,但他的詩歌寫作中涉及的“人話”和“詩話”的問題卻有著必須面對的共同性。曹立光的詩是從自我生命的特定角度來實現詩歌說“人話”和“言體及物”的轉型目標,他選擇了與他生命攸關的故土,選擇了養育了他陶醉了他的山川河流及與此相擁的風物景觀,從中汲取藝術的汁液和元神,進而生長出自己詩的血肉來,讓詩有了“生命痛感和生活氣息”,他也是用自己這只“年輕的手”,“將詩拽回到我們生存的現實、生存的大地和日常生活狀態中來”。從這個角度說,曹立光的詩也同樣有著掃除積弊、增加詩的新質的先鋒性,不過他的先鋒性不是割斷傳統的臍帶,而是強化了傳承的基因,他的詩更多的是溫情和靈性。
包括鄉愁鄉戀在內的鄉土情懷,是詩歌寫作的永恒的題材,好像哪一個詩人也無法不被童年和親情所吸引。慣常的鄉情的書寫也當然地存在著一種難度,古往今來,詩人們都在這一領域里反復詠唱,今天怎么能唱出別一番情調和韻致來,實在是要費些力氣的。在這一點上,曹立光的基本策略是深入到故鄉的細節中去,找到生命本質和生命張力的契合點,并從中加大思辨的力度,引導經驗和理性進入直覺的空間和抒情的渠道中來。讀《永翠河畔》這樣的詩,可以感受到細節之中所含納的情感的魅力:“一根看不見的繩子/拴著奔跑的云/“滴溜溜”的鳥鳴/滑過山坡,草就綠了/穿過幽谷,花就紅了/此刻,患關節炎的石頭,舉著風/把蝌蚪吹成青蛙/把少女吹成母親/把炊煙吹成家/香椿炒雞蛋,青絲變白發”。“永翠河”可能是詩人故鄉的一條河,詩人深情灌注其間,以風物和景致的具象性構成了自然而優美的詩意情境。這樣一條河邊,無數詩的細節抽出了詩性的內核,不經意的筆致刷新了流水的生命過程。“奔跑的云”被“一根看不見的繩子”拴著,“鳥鳴”是動態的,“滴溜溜”地“劃過山坡”“穿過幽谷”,草與花便獲得了鮮活的生命。詩人寫“風”被“石頭”舉起,而“石頭”是“患關節炎的石頭”,包含了故土上生存的痛感,引導著詩意朝著特定的方向前行。“吹”是由“風”而生長的一個特殊的動詞,形成了生存的詩意風景,也率性地提示了生命演進的過程。詩中的生活場景描述,有強烈的主觀性,“頂天立地”的水,是一種精神的象征,在“食草的牛們”的眼里,“彩霞出嫁”有著豐富的詩性內蘊,是對故土之河的一種特殊的寄情方式。endprint
一個優秀的詩人,可以選擇人們通常習見的題材來表現自己內心的情志,但詩人的寫作又可不必為題材所局限。曹立光寫故土情思,我想這只是他詩意抒寫的一個基點,一個感情表達的平臺,其實他的詩性疆域早已溢出了鄉土和親情的框架,進入了更大的、更有深度的情境之中。人性深度的體驗、生命的靈性和感悟為某一題材注入了更充分的活性,使那些具象的事物在詩人的筆下產生了更大的張力。正如曹立光在詩集的《后記》中說的那樣:“詩歌,就在這時候照亮了我黑暗的生命。就像我內心的森林搖曳著生命的葉片,在時間的河岸,寧靜自在,熱烈而淳樸,以原始的自然風貌存在著。這時,就有一種力量驅使我的筆墨成為文字。我覺得自己在逐步告別郁悶和酸楚,慢慢向一個光明的山頂前進。那一刻,我對自己和詩歌有了更多的奢求。我難以覺察隱藏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似乎也說不清楚,但我可以覺察到詩歌的存在:如我身體里的那條叫做母親的河,無聲而親切地注視著我,并且時時刻刻校準我內心飛翔的方向。”從鄉愁、鄉情這個深切而具象的門走進來,詩人曹立光的心靈以其極大的敏感度邁向了情境的縱深處,生存和生命的感悟在故鄉土地的觀照中呈現出更為悠遠博大的氣象。在題為《守望生命》的詩中,詩人寫下了這樣的句子:“真的羨慕飛蛾,/他們生來/就注定是一團火,而所有的火/都必然成為路。就像/鳥,追逐天空;雨,追逐閃電/黎明劃破黑暗/慶幸,我在黃昏的皺紋中/終于讀懂了生命,那流失的寸寸光陰/就是我默守的良心和擔當/一生一世,咬緊牙關永不放棄”。詩人對生命的認識和理解或許和懷鄉的題材沒有太大的關系,是許多更為廣博的空間里的諸多自然意象如“飛蛾”“鳥”“雨”“黎明”給詩人以啟迪,“默守的良心和擔當”,“咬緊牙關永不放棄”,一生一世的守望,生命在覺醒中獲得了靈感和悟性。像這樣的詩,從中可以看出詩人對于抒情性的重視,還保留了詩歌傳統中較為鮮明的傾訴式表達特色,形成了一種流暢自如的描述性,使詩的境界與主體心靈達成了某種高度的契合。他的詩中雖然有著較強的“及物性”,但總體看與先鋒詩歌的“敘事”方式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詩中的鮮明的情感脈絡使諸多具象的內容成為不容質疑的心靈訴說的載體。
對于詩歌文體來說,“抒情”有時被狹義化了,讓人們誤解了對文體具有主導性的話語方式,以為那些強化感情的特殊修辭手段就是“抒情”,而把其他方式都排除在抒情之外。其實,詩的抒情是文體的常態,具有極大的開放性特點,是以巨大的包容的可能與詩歌共生。曹立光的許多詩中有明顯的“敘事”因素,但這些表達的基本形態還是一種情感的流動,而不是“事”的過程延伸。
在《敘述中的當代詩歌》一文中,詩論家姜濤說:“敘事性首先是作為對80年代迷信的‘不及物傾向的糾偏而被提倡的,與其說它是一種手法,是對寫作前景的一種預設,毋寧說是一次對困境的發現。較之于自我表露的諸多花樣,中國詩人處理現實的能力要遠為遜色,敘事發生在寫作與世界遭遇時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而正是困境提供了創造力展開的線索。”(《巴枯寧的手》第156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其實,敘事性并非與詩的抒情相悖,而是抒情的一種必要的方式。曹立光的詩中較好地吸收了“敘事”的營養,讀來擲地有聲,有了充分的“及物”的現實性。在《母親》一詩中,有這樣的句子:“三歲扶著藥罐站起/八歲搖搖晃晃上學/一九五三的夕陽/像張漏風煎餅/掛在光禿禿/榆樹之上/十四歲下地扶犁點種/十八歲在灶口前清點口糧/高粱米飯熟了一鍋又一鍋/日子總是喊餓”這些敘事性很強的句子,是曹立光抒情詩中不能缺少的因素,對于詩人藝術表現的個性是重要的。詩以簡潔敘事方式陳說著母親人生艱難的一種過程,雖是“事”性因素,但情感的表達是極為充分的,其本質還是抒情,這與詩歌文體本身的出發點有關。抒情可以有許多方式,曹立光的詩游刃有余地駕馭了敘事性,他的詩更顯充實厚重。當代許多先鋒意識較強的詩人們在這方面表現的優長之處,是詩歌寫作應當學習的。
在詩歌寫作中,敘事性所說的“及物”其實是對具體事物和具象內容的重視。一個詩人的實際生存景象、生活經歷的記憶是重要的,詩中任何細節性描述,其實都是經歷表象和心靈虛化的再造的過程。曹立光的許多詩都可以看到人間煙火的景致,能夠在近距離的觀照中找到自我情懷抒寫的熱點。《雨落黃昏》一詩是如此表現生活直覺的:“蒿草之上是如芒的歲月/搖晃的麥田邊,蟈蟈/抱著炊煙的大腿/在日子的飯碗上,守望黃昏”。
詩人面對黃昏,寫下的是具體、感性的生活現象,這里的人生經歷和感悟都化為血氣十足的細節,現實的過程性充滿了歷史感,落日和灶膛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嘆息,詩在變形的物象中使感情的流水曲折有致。這樣的詩是直覺的,但又不是把不加改造的生活事物及過程性呈現出來,是生命體驗深度的詩性表達。《雨落黃昏》是情境的言說,在生活的表現和細節的描寫方面,它有別于散文,不可否認地包含著象征和隱喻的因素。比如說“在日子的飯碗上,守望黃昏”,比如說“虛幻似的彩虹”、“千年的鳥巢”,都暗示著生活和命運某些深度的東西。我想,詩是無法逃離象征和隱喻的,包括那些生活流口語化,或者反詩反文化的新派詩人,也不可能完全擺脫能指和意象的多義性可能。象征和隱喻是詩的文體宿命,你可以玩弄不同的形式和手段,但不可能最終離棄。
曹立光的詩的深度還在于他能以達觀的心態來表現生活和人生的悲劇性。他的關于故鄉山水的詠唱,不是田園牧歌式的,他把困境和苦難的人生情境納入了一種詩意的氛圍中進行深入的思考,在真善美中提升人性人情的品位和質地。像《雨落黃昏》這樣的詩在涉及苦難的情懷表述時,就有一種充分的曠達、開闊之美,不是那種悲觀的調子,是超然中的大氣,是真情流露,讓人感受到生命的沉郁之美。《日子頭上的喜鵲窩》也是這種類型的詩作:“喜鵲叼著彎曲的夕陽/突然出現在西山口,那棵/曾見證過/王大小子初戀的歪脖榆樹上/戴在日子頭上的喜鵲窩/年年漏雨,年年翻修/兩根年老多病的榆樹杈兒/令多少外出打工的眼睛,哭紅黎明”。詩人寫平常的生活,時光在不經意中流逝,許多離家在外的人為生存忙碌著,人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覺中自然地衰減著,正如樹上的喜鵲窩“年年漏雨,年年翻修”,以及“兩根年老多病的榆樹杈兒”,都隱含著一種人生的無奈和傷懷的感嘆。但詩人在抒情的過程中并非是一種灰暗的看世界的方式,而時時表現出一種從容和自信,讓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詩人王鳴久在《詩懸》中說:“詩無力消弭世界的苦難,但它可以以其真善美的光芒燭照人類認識自己,反省自己,清潔自己,改變自己;引導人類在直面苦難時,不茍且,不沉淪,不絕望。最終擺脫了苦難,也就擺脫了罪惡。”(《中國詩人》第84頁,2011年第五卷)在生存的現實中,詩人曹立光雖然不無感傷甚至哀婉的情愫,但他卻能以自我充分的內在精神的陽光照亮生活,照亮他筆下的事物,進而以詩意的真善美照亮心靈世界,因此他的詩有了一種與光明心性有關的亮色。
《北緯47°》是詩人曹立光這個“荒原狼”的第一部詩集,它帶給我們的是這位并不陌生的詩人對于人生世界、故鄉土地的深切而充滿命運色彩的情感剖白,其中生命的活力雖不無直面人生的痛感,但基于積極的生存信念和對于未來的矚望,他為人們留下的是他作為一個詩人的美好的記憶和從容舒放的詩意情懷。
人生的過程遙遠而漫長,我們只是對曹立光這位還很年輕的朋友寄以厚望并祝福他在詩的路上大踏步地走下去,不斷地找到自己的芳草和綠洲,寫出更讓人心儀和情動的美好詩篇來。我想強調的是,詩之路難行,但你只要選擇了這條路就只能無畏地走下去,風光無限處就在你的前方。曹立光的詩歌寫作追求處于一種強勢狀態,大門已經打開,朝前走就是了。在對生命風景的守望中,我們看見親切的炊煙正裊裊升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