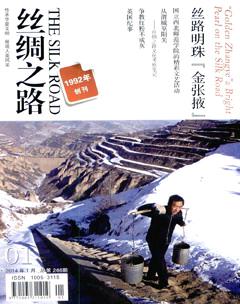耿派藝人楊金民
牟豪戎
耿忠義(1884~1947)乳名福保子,甘谷安遠鎮人,幼年在蘭州學藝,先學旦角,后攻生、凈,30來歲便已技藝超群,生、凈俱佳,名聲大震,成為與麻子紅(郗德育)并駕齊驅的杰出秦腔表演藝術家。因而,蘭州早年就有這樣的順口溜:“牙古子的包子,馬保子的面,福保子的生凈,八娃子的旦。”這就是所謂的“蘭州四絕”。前兩句指蘭州的兩種名特飲食,后兩句說的是享有盛名的兩位秦腔藝人。八娃子,名史月卿,是風靡一時的旦角演員;福保子即耿忠義。
耿忠義雖然和甘肅前輩秦腔名家“福慶子”(張福慶)、“十二紅”(李奪山)一樣,也是一位生、凈兩門抱的杰出人才,但由于他繼承了花臉名宿唐待招(唐華)的表演藝術,并吸收甘肅前輩秦腔名家的藝術優長,經過自己刻苦鉆研和精心創造,因而他的花臉戲成就更為突出,標志著甘肅秦腔凈角表演藝術達到新的高峰。他的花臉戲演的多是古老的甘肅秦腔傳統劇目,代表作有《火焰駒》、《白逼宮》、《黃花山》、《五岳圖》、《鴻門宴》、《虎囊彈》、《馬芳困城》、《老君堂》、《游西湖》、《破方臘》、《黃飛虎趕駕》、《斬侯英》等。服飾、裝扮、造型是典型的甘肅風格。他的臉譜筆鋒凌厲,色彩鮮活,神采飛動,性格鮮明,既不同于京劇臉譜,也不同于陜西秦腔臉譜,是甘肅特有的“耿家臉譜”。他化妝起來就像一尊神,創造的人物大多帶有神氣。
他演花臉講究神采氣度,注重扎勢亮相的雕塑感和造型美,著重通過工架造型塑造藝術形象,偉岸嚴正,氣象恢宏,器宇不凡,蘊含豐厚。即使是繁復的戰斗場面,也只是簡約地走走過場,擺幾個雕塑感很強的不同姿態的架勢,就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創造。例如,他演《黃花山》中的聞仲時,頭戴紫金冠,身穿黃金靠,足蹬黑厚底靴,畫黃臉,泰山眉,兩頰畫幾筆腮紋,額頭畫一天眼,用三角形黃表罩著,上唇及鼻翼兩側抹黑,鼻尖如峰,戴黑三須,兩耳橫插鬢毛,后肩背扎墨綠墊肩,肩頭扎成兩朵花,后背掛一五彩繡球,手執雙锏,锏上扎幾束黃表紙花。這一造型威嚴震人,常在觀眾中引起轟動。他出場后,一個前弓后箭的架勢就贏得了全場的熱烈喝彩。同姜子牙對陣開打,打一個回合,擺一個架勢,就這樣擺三五個富有雕塑感的架勢,便把莊嚴肅穆的聞仲的藝術形象樹立于戲曲舞臺之上。又如他演《白逼宮》中的曹操,大白臉上勾勒三角眼,兩頰略點油漬,歪戴黑相帽,身穿紅官衣,腰懸寶劍,怒沖沖拔劍入宮,提袍頓足,氣焰逼人,大吼一聲:“魏王進宮來了!”將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奸相形象及其精神狀態刻畫得入木三分。
耿忠義的藝術風格,雖然是大寫意,寥寥幾筆就能立顯人物的神韻,但有時為了細致地表現人物的精神風貌和性格特征,也會細密點染,刻畫入微,妙趣橫生。如他演《白逼宮》中的曹操,在逼死皇后以后,奏稟漢獻帝:“西涼馬超造反,請主家定奪。”此時的漢獻帝已魂飛魄散,曹操便代傳圣旨:“曹操聽旨:西涼馬超造反,命我卿帶兵征剿。勝了加官進爵,敗了嘛……也就敗了!嘿嘿!”他在“嘿嘿”大笑時,用左肘將漢獻帝一捅,然后說:“有道的明君呀!”便大笑而跪拜謝恩。這樣的口吻和小動作刻畫出了曹操的奸猾、狡詐。當他欲出宮門時,突然警惕起來,便說:“觀見漢家文武以在宮門擺來擺去,莫非有害操之意?咹呔,說什么有謀操之意,兵權現在我手,誰敢加害于我。待我大喊三聲,看他們哪個膽敢近前!”說完轉身拔劍,面對宮門大喊:“嗚呀呔!魏王出宮來了!”神色俱厲,不可一世,一副飛揚跋扈、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梟雄嘴臉,活靈活現,神態逼真。
耿忠義的表演動作經過精心加工提煉,沉穩有力,美觀大方,簡潔明快。再繁重的表演,往往也只是三五下,但卻鞭辟入里,精彩傳神。特別是他善于運用急緩適度,長短適中,富有美感節奏的“三”來表演,不僅渲染了濃烈的環境氣氛,而且也勾勒出人物的精神氣韻。例如,他演《火焰駒》“傳信”中的艾謙,先是一把火鋪路,人物隨火出場,用揚鞭、勒馬、抽馬、踏四角的舞蹈動作,表現出為拯救被陷害的李彥貴母子,晝夜兼程,去北國給李彥榮傳信的急切心情。然后唱:“胯下的火焰駒四蹄生火,耳內里忽聽得風號葉落。就地下塵土起一片烈火,眼看看加一鞭越過草坡!”緊接著連抽三馬鞭,隨鞭連放三把火,右腿抬起再放一把火,又從背后向頭頂放一把火。在滾滾火焰中,低頭將羅帽絨球甩在前額,列勒馬架勢,火爆熾熱,形象鮮明,突現了艾謙這位濟人救難的英雄壯士的焦急心理。這“三鞭子”是出了名的,蘭州就有“耿家的三鞭子壓了天下”的贊語。再如《破方臘》中的方臘為向梁山泊好漢示威,一上陣捅三桿子;《老君堂》中的程咬金為活捉李二王,猛向廟門劈三板斧;《游西湖》中慧娘與裴瑞卿眉目傳情時,賈似道的三看;《白逼宮》中尚方寶劍懸掛宮門時,曹操的三拜;《五岳圖》中面對定神針時,黃飛虎的三退。這都是運用“三”的表演特技刻畫人物的典范之作。
耿忠義創立的耿派藝術獨具特色,膾炙人口,影響廣泛,是甘肅秦腔的瑰寶,因而后學者眾多。但由于耿忠義的藝術造詣太深,那種獨特的神韻和品位一般人難以掌握,所以多數后學者只能演個別的耿派劇目,也只是略具形貌而已,能達到形神兼備者為數更少。若從演出耿派劇目數量之多、研習耿派藝術時間之長來看,楊金民可算是耿派藝術比較全面的繼承者。
楊金民是陜甘馳名的秦腔旦角演員楊金鳳的胞兄,原籍陜西武功,生于1918年,父親是個搟氈匠,因生活所迫,幼年時隨父親輾轉流離落戶寧夏。因為自幼喜愛秦腔,1933年,與胞妹楊金鳳到靖遠丁振華班學藝。他的啟蒙老師是秦腔老藝人霍振川,先學小生、須生,后專攻花臉。年長后常和胞妹楊金鳳一起在寧夏銀川、中衛及甘肅靖遠一帶演出。1941年,楊金鳳到蘭州靖正恭、王正端主辦的眾英社演出,逐漸走紅。后來楊金民也到蘭州,對耿忠義的精湛演技崇拜得五體投地。1946年,他參加了由平涼的平樂社來蘭組建的精誠劇團。這個劇團當時領銜主演的著名演員有靖正恭、劉易平、高希中、楊金鳳,除了這幾位名家的拿手戲外,演出的多是以生、旦為主的易俗社劇目,如《軟玉屏》、《奪錦樓》、《雙明珠》、《人月園》等,花臉的戲很少,楊金民能夠露臉并通過演出提高自己的機會并不多。加之自己嗓音欠佳,于是他深刻地認識到,要想在蘭州的戲曲舞臺上站住腳,必須向耿忠義學習,走著重以臉譜、工架、造型塑造人物形象的藝術探索之路。于是,他便到耿忠義所在的文化社參加演出。
文化社是一個歷史悠久、具有深厚甘肅秦腔傳統特色的藝術團體。耿忠義是其臺柱式的人物,當時已屆晚年,表演技藝依舊爐火純青,每當演出,全場轟動。在文化社,甘肅派代表人物還有岳鐘華。他是在其姐夫、甘肅前輩秦腔名宿“十二紅”(李奪山)的嚴格教誨下成長起來的藝術全才,腹笥淵源,功底深厚,年輕時演文武小生,中年以后演須生和花臉,在觀眾中聲望很高。岳鐘華精于甘肅秦腔臉譜的繪制,諳熟甘肅秦腔戲路的底蘊,因而也能演耿派路數的花臉戲。他面頰瘦小、身材較矮,為揚長避短,不演《白逼宮》中的曹操、《游西湖》的賈似道,但演《黃花山》中的聞仲、《火焰駒》中的艾謙、《破方臘》中的方臘、《五岳圖》中的黃飛虎,形象矯健挺拔,別具風采。我曾看過他與耿忠義合演的《雙火焰駒》,兩個艾謙你出我進,紅火熾烈,各顯其能。耿忠義沉穩凝重,以聲勢壓臺;岳鐘華干凈利落,以情采取勝。楊金民到文化社與耿忠義、岳鐘華同臺演出,增長了見識,受到了熏陶。他虛心向耿忠義學習,也向岳鐘華請教,細心琢磨,刻苦鉆研,逐漸熟悉和掌握了耿派表演藝術的路數。因此,在耿忠義謝世之后,楊金民便陸續演出耿派花臉戲,成為文化社一直到后來的蘭州市秦劇團挑大梁的主要花臉演員。
40多年來楊金民持之以恒地研習耿派藝術,比較成功地演出了《火焰駒》(艾謙)、《白逼宮》(曹操)、《五岳圖》(張奎)、《游西湖》(賈似道)等耿派劇目。他演的這些耿派戲我大都看過,有幾次精彩演出,讓我印象深刻,至今記憶猶新。
1948年,在鹼灘文化社劇場,岳鐘華主演《三闖碧游宮》,飾廣成子,楊金民配演靈寶天尊,工架穩健,氣度宏偉,具有耿派風范,頗得好評。1952年,在馬坊門文化社劇場,楊金民與岳鐘華聯袂演出《五岳圖》,岳鐘華飾黃飛虎,楊金民飾張奎,竟然應對裕如,沉穩大氣,令人贊嘆。1957年,在教育館文光社(文化社與新光社合并后的社名)劇場,楊金民與“十二紅”(李奪山)的哲嗣李化仁聯袂演出《五岳圖》,李化仁飾黃飛虎,他飾張奎,二人配合默契,功力悉敵,受到熱烈喝彩。1964年,在教育館蘭州市秦劇團(文光社升格的國營劇團)劇場,楊金民與薛志秀聯袂演出《白逼宮》,薛志秀飾漢獻帝,他飾曹操,二人各展其能,相映成趣,受到觀眾歡迎。
對此,蘭州的秦腔觀眾是認同的。例如,原甘肅省委副書記聶大江,2005年夏在蘭州大學專家樓接受了《鑫報》采訪談到秦腔時就說,他于20世紀50年代曾看過楊金民的《白逼宮》。曹操相帽歪斜,一手提袍襟,坐在椅子上蹬腿亮靴底的表演,形象威嚴神煞,風格粗獷豪放,呈現了與京劇迥然不同的藝術特色。他完全被楊金民創造的充滿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鮮明的民間審美情趣的曹操形象所吸引。他說,從這時起便深切地感到秦腔是埋在黃土里的明珠。這么好的戲曲藝術如果得不到保護,那就是對文化的輕蔑,也是對廣大人民群眾的不負責任。
更為難得的是,楊金民能夠堅持運用耿派藝術手法,塑造不同類型的舞臺藝術形象,使人物顯示出耿派的神韻。比如他40多年來飾演的《鍘美案》中的包公、《玉虎墜》中的馬武、《潞安州》中的金兀術、《四進士》中的顧讀、《闖宮抱斗》中的殷紂王、《葫蘆峪》中的司馬懿、《逼上梁山》中的高俅以及現代戲《杜鵑山》中的毒蛇膽、《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都具有突出儀態神氣、注重工架造型的耿派表演藝術特征。唯其如此,甘肅戲曲評論家范克峻在《甘肅秦腔表演藝術的特征》一文中,稱楊金民為甘肅派的優秀者之一。
我因從小跟大人看戲成了秦腔迷,幾十年來樂此不疲,但是最愛看的還是大氣磅礴、蘊含深厚、具有甘肅古老風格特色的秦腔戲,所以對耿派藝術非常仰慕。因此,早在1961年,我便以自己粗淺的認識撰寫了《漫談耿派藝術》,發表于《甘肅日報》。1985年,秦腔已開始不景氣,我出于對耿派藝術的珍視,就如何繼承和發揚耿派藝術的問題,走訪了已退休在家的楊金民。他充滿深情地對我說:“耿忠義確實不簡單!他的許多戲、許多表演程式和技巧,是咱們甘肅秦腔的獨特創造。比如蘭州觀眾交口稱贊、至今念念不忘的‘三鞭子、‘三桿子,確實受看,堪稱絕招,陜西秦腔是沒有的。”說到這里,他乘興拿起一個雞毛撣子,就地表演起《火焰駒》來。只見他神情專注,揮鞭策馬,唱“胯下的火焰駒四蹄火,耳內里忽聽得風號葉落”,表演扎勢亮相、馬后三鞭、甩羅帽一套程式,讓我再次領略到了耿派藝術的風采。他談了很多,表露了對耿派藝術瀕臨失傳的憂慮,讓我深受感染。隨后,我撰寫了題為《耿派藝人談耿派》的專訪,發表于《甘肅日報》。在此前后,我因參與主持當時舉行的甘肅振興秦腔的演出活動,面請他參加演出,他出于對秦腔發展前景的關切,慨然應允,不顧年老體衰,除演出耿派名劇《火焰駒》外,還飾演了《闖宮抱斗》中的殷紂王、《葫蘆峪》中的司馬懿、《六部大審》中的刺客石龍,舉手投足,典范猶存,以富有耿派神韻的表演,受到觀眾的好評。
楊金民是繼承、延續耿派藝術時間最長的繼承者,也是最后一位繼承者。1992年,他不幸病逝,人琴俱亡,耿派藝術也就灰飛煙滅而絕跡舞臺了。
歲月如梭,轉眼20年過去了。楊金民逝世20周年之際,我在2012年12月28日的《蘭州晚報》,發表了題為《憶楊金民先生》的短文,以文中最后一句話作結:“楊金民先生是一位誠實的人,勤奮的人,他把一生獻給了秦腔事業,我們不能遺忘這位耿派藝術的繼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