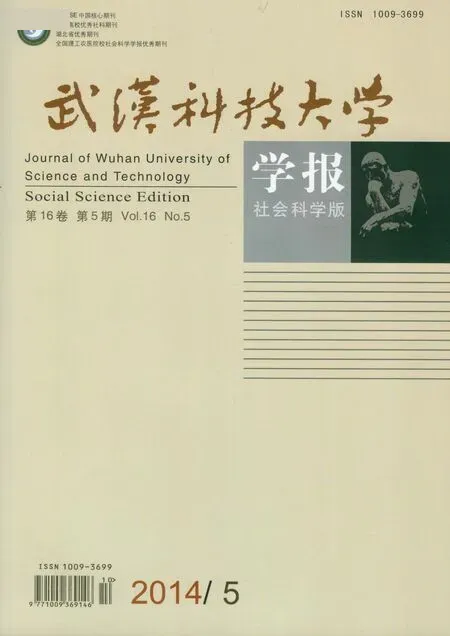想象力與超越
——從想象力看康德與海德格爾的超越概念
帥 巍
(武漢大學 哲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2)
在哲學史上,亞里士多德將想象力定義為“一種根據現實地發生的感知而形成的與感知相似的運動”[1]。康德也將想象力視為“在對象不在場時在直觀中表象對象的能力”,這當然是與其認識論密切相關的。可以說在傳統哲學中“想象力”是一個與感知、與人的意識和心理以及與人的認識密切相關的概念,因而主要是與心理學以及與認識論相關的概念,但想象力與形而上學的超越性的本質關聯卻鮮有人問津,更不用說它與人的生存——與此在的本質關聯了。
康德區分了兩種想象力,即經驗性的再生想象力和生產性的先驗想象力,先驗想象力在康德那里是溝通知性與感性的中介,只有以先驗想象力為中介,現象才能被統攝為概念,概念也才能運用于現象,同時也就是說只有在先驗想象力這個中介的作用下,純粹知性概念——范疇才具有其合法的運用,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康德的認識論與其先驗(Transzendenz或譯超越、超越性)哲學也正是借助于先驗想象力(及其產物——先驗圖型)才能得到合理的說明。但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先驗演繹中將先驗想象力看作從屬于知性的一種感性認識能力,這樣康德的先驗(Transzendental)哲學就只是以知性范疇作為現象或存在物的超越性的可能性條件的一種本質性或形式的超越論哲學。
在海德格爾看來,康德在進行形而上學奠基的過程中得出一個令人“陌生的”的結果,那就是先驗想象力并非作為從屬于知性的一種能力,而毋寧是知性與感性的共同根源,但康德為了維護其“先驗邏輯”的優先地位而在這個“根源”面前退縮了。海德格爾認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根本不是尋求認識論的知識,而毋寧是尋求存在論的知識,因此,作為認識論意義的先驗想象力實際上是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論想象力,這種超越論的想象力不僅顯示為知性與感性的共同根源,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物(現象)得以被領會的發生境域——時間性,正是它將超越形象了出來。而這種時間性的境域正是人的生存(Existenzial)境域,此在也就是一種出-離自身的實存性的超越性,而非對于存在者的超越(存在者存在或得以被認識的可能性條件)。可以說康德和海德格爾對于先驗想象力的兩種不同態度決定二人對于形而上學或哲學的“超越性”的不同理解,也就是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導致了康德傾向于認識論的先驗哲學,而海德格爾傾向于生存論的存在論的超越論思想。
一、形而上學的兩種超越追問方式
“形而上學”(Metaphysics)這個詞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實際上是他的“第一哲學”,它是研究“作為存在者的存在者(to on hei on)”或存在本身的科學,Metaphysics這個詞的詞義為“物理學之后”,這個詞的前綴(Meta-)本意為“……之后”,因而它是指研究物理世界背后不變的原因或根據的科學,由此可以說Meta-本就有著超越的含義;海德格爾也認為 “在古希臘文中,meta意為‘越出’,‘超出’。對這樣的在者的哲學發問,就是meta ta physica;問出在者之外去就是形而上學。”[2]18按照傳統的觀念,“ ‘在的問題’就是對在者本身的追問(形而上學)。但是從《存在與時間》的想法來說,在的問題就是:對在本身的追問”[2]20。可見,在海德格爾那里形而上學則是對存在本身的追問。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形而上學就被定義為研究 “存在者是什么?”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又可以分為 “什么存在”(to ti estin,was-sein,拉丁文為essentia,本質)和“如此存在”(hoti estin,wie,拉丁文為existentia)兩個問題,與這兩個問題相應,形而上學的 “超越”(Transzendenz)也可以分為“什么存在”的本質意義上的超越與“如此存在”的實存意義上的超越。“什么存在”的超越是向本質(essentia)方面的超越,即是作為“先驗之物”(das Transzendental)或先驗性質(Transzendentalien)的超越,而“如此存在”的超越則是指存在者如何存在的 “實存”意義上(existentia)的超越。
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兩種實體(Ousia)——海德格爾認為應將之翻譯為在場或在場者,即第一實體和第二實體,第一實體是指個體事物,如個別的馬;第二實體是指個體事物的屬性,如(馬的)白色。在海德格爾看來,“第一位意義上的在場乃是在hoti estin[如此存在]中被表達出來的存在,即如此-存在(Dass-sein)、existentia[實存]。第二位意義上的在場是在ti estin[什么存在]中被追蹤的存在,即什么存在(Was-sein)、essentia本質”[3]。可以說,在亞里士多德這里,實存意義上的超越作為第一實體是高于本質意義上的超越的。
在康德的先驗哲學中,Transzendental(通常譯作先驗的或超越論的) “并不意味著超過一切經驗的什么東西,而是指雖然是先于經驗的(先在的、先天的),但卻僅僅是為了使有關經驗的知識成為可能的東西”[4],而且他 “把一切與其說是關注于對象,不如說是一般地關注于與我們有關對象的、就其應當成為先天可能的而言的認識方式的知識,稱之為先驗的”[5]19。而先天的知識或先驗哲學也就意味著“并非不依賴這個那個經驗、而是完全不依賴任何經驗所發生的知識”[5]2。由此,可以說康德的先驗哲學是關于對象的先天可能性的認識方式的認識論哲學,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關于對象的存在論的哲學。按照本質與實存兩種意義超越的劃分,康德的先驗范疇大致可歸入本質上的超越,因為這些范疇還只是先驗自我進行聯結、綜合和統一表象以形成知識的固定功能,它們還只是經驗和關于經驗對象的知識的形成的可能性條件,它們只是根據判斷表而形成的固定功能,而并無實存性的超越特征,也就是說,它們與先驗主體的實存或存在方式還不是直接相關,而只是派生的先驗主體聯結表象的方式或形成知識的條件。因此,它們還算不上第一位的實存性的超越。那么是否就意味著康德的先驗哲學與存在論毫無關系或者說康德的先驗哲學從根本上講就只是一種本質性意義上的超越哲學呢?
二、本源性的超越與認識論和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論想象力
眾所周知,傳統形而上學是“純粹的、理性的關于存在物‘一般’和存在物主要領域中各個整體的知識”[6]6。而海德格爾認為傳統形而上學對其主張的觀點缺乏某種有說服力的證明,因此需要對形而上學的內在可能性條件進行探索,而“形而上學奠基在整體上就叫存在論的內在可能性的開顯”[5]8。所以,對形而上學的奠基就是要對存在論的內在可能性進行追問,即是要對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進行追問。“那使得與存在物的關系(在存在物層面上的知識)成為可能的東西,就是那對存在法相的先行領會,就是存在論的知識”[5]7。
在海德格爾看來,“舉凡有存在物知識的地方,存在物知識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有某種存在論的知識存在”[5]9。所以,他認為《純粹理性批判》與“知識理論”毫無關系即是說與認識論毫無關系,如果非要說它是一種知識理論的話,那么它就應該是一門關于存在論的知識理論。而且“倘若知識的真理性在于知識的本質,那么,先天綜合知識內在可能性的超越性疑難就是在詢問存在論的超越之真理的本質”[5]13。海德格爾甚至認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從整體上看就是圍繞超越問題的一個問題圈”[7]210。為了進一步理解超越,從而獲得一種源始的、奠基性的“超越”概念,以及對Transzendental(Transzendenz的形容詞形式)一詞在不同哲學家那里的含義和在不同的哲思境域中應該如何翻譯它進行說明與澄清。我們需要對形而上學的基礎進行追問,海德格爾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①海德格爾的《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即《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王慶節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年版。見文后參考文獻)。本文采用學界對該書書名的慣常用法:《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中就是要通過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解釋為形而上學的一次奠基來展開一種基礎存在論的觀念。而《純粹理性批判》在海德格爾看來也就是一門關于存在論的知識理論,并且“為形而上學奠基是作為對純粹理性批判來進行的”[6]9。因此,形而上學的奠基就與“純粹理性批判”、與存在論知識關聯起來。最為重要的是“存在論的知識就是要將自身表明為把超越形象出來的東西”[6]114,由此我們需要跟隨海德格爾對于康德“存在論的知識”進行的探究,以便獲取對超越的根本的意義。
因此,為了將超越“形象”出來,就需要對(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進行探究,即是要對理性自身、對人的認識活動的一般本質進行考察。“形而上學奠基的基源(Quellgrund)是人的純粹理性,由此,理性的人性化,也就是說,理性的有限性就在根本上成為奠基之疑難索問的核心”[6]17。由此,人性化的理性或有限的理性就成了首先需要進行批判的對象,海德格爾認為在康德那里,“人類的知識有兩大主干,它們來自某種共同的、但不為人所知的根基,這就是感性和知性,通過前者對象被給予,通過后者對象被思維”[6]21-22。在康德看來,人類知識是感性與知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康德還在其《純粹理性批判》開篇便指出:“一種知識不論以何種方式和通過什么手段與對象發生關系,它借以和對象直接發生關系、并且一切思維作為手段以之為目的的,還是直觀。”[6]25在此,我們又可以看出直觀(感性)對于知識產生的重要作用,以至海德格爾甚至據此認為:認識原本就是直觀,而且思維(知性)也是臣服于直觀的,認知就是思維著的直觀。而神的直觀直接就是知識,就是真理,它是不需要思維的,因此可以說人的認識有限性的一種體現,也就是人類知識的有限性的一種體現。
然而,是否就可以說人的有限性本身是建立在需要思維的直觀的有限性基礎之上呢?恰恰相反,“正因為我們的親在(即:Dasein,又譯此在。筆者加)是有限的,生存在已然存在物之中并被拋向這一已然存在物,所以它才必然而且必須領受已然現存物,也就是說,為此存在物提供呈報自身的可能性”[6]23。也就是說,我們的此在必定首先已經被拋于與存在物打交道之中,我們才可能接受現成物的刺激而產生表象,也就是說存在物(現象)首先并不是有限本質存在人所創造的對象或首先需要由先驗主體(先驗統覺)所概念化地建構的對象,而是有限的本質存在——此在或人在其生存的有限性境域中與之打交道的物。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正是因為我們已經被拋于已然現成物這樣的有限性境域之中,我們才具有接受現成物(對象)刺激的而產生表象的有限性直觀。
在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康德通過設立物自體將人類認識能力限制在現象界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在海德格爾看來,存在(物自體)不是存在者(經驗對象),它是不能像存在者(經驗對象)那樣被知性進行概念化的規定的,它只能通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存在而得到領會,所以,存在論的知識的內在可能性就只能通過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存在領會才是可能的。
如前已述,海德格爾是要通過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解釋為形而上學的一次奠基而來展開一種基礎存在論,而“超越”正是在這種為形而上學奠基過程中展開的存在論知識內在可能性的根基中形象出來的,因此如果我們要完全形象出“超越”的話就需要對存在論知識的根基進行探索。海德格爾認為有限的本質存在(人)的知識原本就是直觀,而且是思維著的直觀——思維本身就表明了有限本質存在的知識的一種限制性(神的直觀是不需要思維的),而這種有限本質存在的直觀自身也是一種接受性的直觀,這就決定存在論知識從根本上具有有限性特征。然而這種思維著的直觀是如何產生存在論知識的呢?
由于直觀(感性)不能思維,思維不能直觀,直觀是接受性的,思維是自發性的,因此二者是完全異質的兩種認識能力,但要產生知識的話,直觀就需要思維來規定,思維也需要直觀提供感性材料,那么它們如何才能結合產生知識呢?為此,康德指出,靈魂除了具有感性和知性兩種認識能力以外還有第三種認識能力,那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種當對象不在場時仍然在直觀中表象對象的能力,而作為一種先驗想象力,它不是經驗性的再生想象力,而是生產性的先驗想象力。
然而,康德在利用先驗想象力溝通感性與知性時候,在進行第一版先驗演繹的時候,隱約感到它并非是與感性和知性并列的兩種認識能力,而毋寧是它們共同的根源。這在海德格爾看來,是由于康德唯恐使知識喪失普遍有效性,而在存在論知識的真正根基面前退縮了。
先驗想象力在康德的先驗哲學中只是起了溝通感性與知性的認識中介的作用,然而以海德格爾的角度來看,這種先驗想象力正是感性與知性兩種能力的共同根源,二者在先驗想象力中相互隸屬,構成先驗想象力這個統一體的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由于直觀(感性)是有限的接受性直觀,而非神的創造性直觀,因此它需要與具有自發性的思維結合才能產生知識,但在海德格爾看來,這種知識不是關于存在者的知識,而應該是存在論的知識,這樣先驗想象力就成了存在論知識的根源。由于先驗想象力是感性與知性的共同根源,因此它同時具有感性的接受性與知性的自發性,但由于存在物(現象)不是它創造的而是在其中顯現出來的,因此,先驗想象力在本質上是一種接受性的自發性,即是說在接受了存在物(現象)的基礎上,知性才可能對其進行綜合、統一以形成知識。所以,先驗想象力就是一個有限性的發生境域,而超越就在存在論知識之中形象出自身。
顯然,在存在論知識中形象出的超越絕非康德那種使對象成為可能的先天條件的超越,簡單地說,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超越,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由于國內普遍將康德認識論稱作先驗哲學,因此為了區分康德與海德格爾的立場,我們將康德的認識論意義上的超越稱作先驗,而把海德格爾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稱作超越,因而海德格爾存在論意義上的先驗想象力,我們按照王慶節先生的譯法,叫做超越論想象力。
我們知道在康德那里,先驗演繹是為了證明知性范疇應用于直觀的合法性,而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型法是要闡明范疇是如何運用于現象的,然而在海德格爾看來,“超越論演繹的基本意圖在于揭露有限理性的超越”,而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型法是《純粹理性批判》全書最核心的一章,它揭示了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形而上學奠基由此也達到了目的,而“超越”也隨著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的發掘而被完全展露出來了。鑒于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型法對于形而上學奠基,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以及超越的揭示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需要深入其中去考察超越是如何在那里得到揭示的,以便對“超越”進行進一步的理解。
由于在海德格爾看來,《純粹理性批判》就是為形而上學奠基,也就是要去發掘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對于這種根基的發掘也正是要揭示一種本源意義上的超越。那么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基礎究竟在何處呢?如前已述,海德格爾認為在康德那里,知識是一種思維著的直觀,是思維與直觀兩種異質的認識能力相互結合而產生的知識,而兩種異質的能力正是通過先驗想象力及其產物——圖型才能結合產生知識。
由于知性范疇與現象是異質的,那么知性范疇如何才能運用于現象呢?康德認為需要一個第三者,“它一方面要與范疇同質,另一方面要與現象同質,并使前者運用于后者成為可能。這個中介的表象必須使純粹的(沒有任何經驗性的東西),但卻一方面是智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這樣一種表象就是先驗圖型”[5]139。這種先驗圖型實際上就是一種先驗的時間規定。就先驗的時間規定以先天的規則為準而言,先驗的時間規定是與范疇同質的,而就經驗性雜多表象都含有時間而言,先驗的時間規定也是與現象同質的,“因此,范疇在現象上的應用借助于先驗的時間規定而成為可能,后者作為知性概念的圖型對于現象被歸攝到范疇之下起了中介作用”[5]139。
可以看出康德是通過“先驗的時間規定”來說明范疇是如何運用于現象的或是如何將現象統攝到概念之下的,而這種“先驗的時間規定”也就是純粹知性概念得以運用于現象的先驗圖型(Schema)。康德把“知性概念在其運用中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這種形式的和純粹的條件稱為知性概念的圖型”[5]140,此外,圖型也是“想象力為一個概念取得它的形象的普遍的處理方式的表象……叫作這個概念的圖型。而把知性對這些圖型的處理方式叫做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型法”[5]140。以海德格爾的角度來看,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型法(或圖式法)就是要將純粹知性概念的規則進行感性化以便運用于現象,這實際上是要將先驗范疇時間化,或者說使范疇按照時間序列進行先驗規定,以便使知性與感性、思維與直觀、范疇與現象統一起來以形成知識。
三、圖型-圖像和作為“我思”與時間統一的超越境域
由于“超越”需要在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處形象出來,而超越論的想象力又正是這個根基, 而“作為‘超越論的時間規定’,圖式‘是想象力的一種超越論的產物’。這一圖式化先天地就形成了超越,因此叫‘超越論的圖式化’”[6]99。因此,超越論的圖式化(或譯圖型化)就集中體現了“超越”,所以我們需要對超越論的圖式進行深入考察,以便完全揭示本源意義上的“超越”。
圖型不同于圖像,它是一種概念(規則)的原象(Urbild),是它的圖像的模型,其他的圖像(Abbild)都是它的特殊形象,這些派生的圖像是通過想象力按照原象這種模型而產生的特殊的形象,可以說圖型作為規則的表象具有普遍性,而圖像則具有特殊性。圖型是先驗想象力的產物,因為它只是先驗的時間規定,而先驗想象力只是在時間中對表象進行綜合,因此圖型不能存在于空間中;而圖像作為空間中的圖形則是先驗想象力和再生想象力共同作用的產物,再生想象力產生出空間圖像;空間圖像必須以先驗的時間規定為基礎,以先驗想象力為基礎才能產生。
但海德格爾認為圖型自身具有圖像的特征,圖型將自身也就是將概念帶入圖像。圖型-圖像則是范疇感性化的進一步表現。海德格爾區分了幾種概念的圖型-圖像:①經驗感性概念的圖型-圖像,如一只狗的概念的圖型-圖像。②純粹感性的數學的概念圖型-圖像,如一個三角形以及一個數字圖型-圖像。③范疇的圖型-圖像。其中,經驗感性概念和純粹感性概念的圖型-圖像都只能通過以先驗想象力為基礎的再生想象力產生出具體的空間圖像,從而為范疇賦予一個客體,賦予意義;而范疇的圖型-圖像則只能由先驗想象力產生出一種“純象”,這種“純象”不為概念帶來任何具體的空間形象,即不形成一個固定的現成對象,但卻為具體的空間形象、現成對象準備了一個得以顯現的時間性的發生境域。“作為‘純粹圖像’,時間是式-像,而不僅僅是站在純粹知性概念對面的直觀形式……因此時間不僅僅是純粹概念之圖式的必然的、純粹的圖像,而且也是其唯一的純粹外觀可能性”[6]98-99。而且“觀念的圖式,通過將自身規整到作為純粹的外觀的時間中去,并從此出發,賦予自身以圖像,這樣觀念的圖式就將唯一的純粹外觀的可能性與純粹圖像的多樣勾連了起來。純粹知性概念的圖式就以這樣的方式‘規定著’時間”[6]99。而“超越在源生性的時間中產生的存在論的知識就是超越論的時間規定”[6]189,且“那形象為超越之境域的東西就是作為超越論的時間規定的純粹圖式”[6]189。由此,可以說為形而上學奠基、對純粹理性的批判以及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最終就在于先驗想象力的產物——圖式,而圖式化作為一種超越論的時間規定先天地形成了超越。由此,海德格爾將傳統哲學中強調邏輯(包括康德強調知性的先驗邏輯的)傳統回溯到了時間這個基礎之上,但這種時間不是現在序列意義上的時間,而是使這種現在序列意義的時間的可能的源生性的時間——時間性,即超越論的(先驗)想象力,前一種意義上的時間仍然只是康德認識論意義上的現象(或存在物)得以被先驗統覺進行統攝的感性直觀的形式條件,而這種認識論意義上的時間卻只有在作為存在論意義上的時間的超越論的想象力為其提供得以被直觀的存在物(現象),提供讓……對象化的境域的基礎上才可能發生,“時間屬于讓……對象化的內在可能性,它……源初地形象為有限的自我性”[6]180。這種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論的想象力不是要去創造一個存在物,而毋寧首先是這種存在物得以顯現的場域,因為這種超越論的想象力是一種有限的本質存在——人的有限的生存境域。這也是海德格爾對于康德認為人只能擁有關于現象的知識而不能有關于物自體的知識的以及人只能有接受性的直觀而不能有創造性的直觀的繼承,因此,存在物(現象)首先只能在一種有限性的直觀或發生境域之中顯現,被遭遇與讓……對象化,而不能被創造。盡管存在物不能在這種有限性的直觀或發生境域中被創造,然而卻就其最初只能在這種有限性的直觀或發生境域中被遭遇而言,這種源初的有限性的直觀就可以叫做源生性的直觀、源生性的時間。
由于先驗自我與時間相互隸屬而統一于先驗想象力,本來無時間性的先驗自我與時間等同起來,先驗自我與時間統一就意味著一種有限性的(接受性的自發性的)主體的發生境域的形成,然而這種源初的有限性的主體首先并不是要去認識一個存在物和概念化一個存在物,而是在其有限的本質存在中同存在物打交道,認識活動只是有限的本質存在(有限的性的主體)的一種衍生性的存在方式而已,也就是說,認識活動只有在有限的本質存在中才是可能的。這種有限的本質存在即人的存在,海德格爾將其稱為此在。最終存在知識的內在可能性就在于此在的存在,超越因此可以說在此在這里得以“形象”出來,即存在通過此在而展現自身。
通過海德格爾對于康德關于存在物的(存在論)知識——人的有限知識根基的追問闡釋,康德的認識論意義上的超越(Transzendenz)就自然地被引回到了更為源始的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關于存在物的知識不再是先驗統覺為主導而以先驗想象力為中介來形成的本質性的現成性的規定的知識,而是以作為感性和知性共同的根源——先驗想象力而形成的存在論的知識,這種知識不是要形成關于存在物的固定的概念,而是要形象出存在物得以顯現的超越境域。
可以說,在這種先驗想象力產生的“純象”中,范疇與直觀(時間)達到了統一,被概念化的對象在其中才得以顯現,這種“純象”也就是范疇感性化的超越境域,在其中,有限的本質存在才能超越自身通達“對象”(存在物)。也就是說人的有限性,即超越的境域乃是對象得以被遭遇、被直觀與被知性規定的源始發生境域,而這恰恰與康德強調知性和強調先驗邏輯的主導作用是相違背的。在海德格爾這里,先驗邏輯、先驗范疇只能按照時間序列來進行規定才可能運用于現象,而不是相反,而這種時間(直觀形式)卻是源于先驗想象力的,因為在海德格爾看來,“一個有限的本質存在必須要在一個存在物作為已然現成的東西公開之際,才能領受那存在物。但領受要成為可能,需要某種像‘轉過來面向’這樣的東西,而且不是一個任意的‘轉過來面向’,而是這樣一種‘轉到對面’,它先行使得那與存在物的相遇成為可能”[6]84。而先行使得那與存在物相遇成為可能的“轉過來面向”正是超越論想象力的作用。某存在物要為我們所直觀、領受,那么它必定先行處于一種能與我們相遇的境域中,而提供這個境域的正是超越論的想象力。由于先驗想象力是感性與知性的統一根源,因而也是一種有限性的存在論知識的根源,所以它是一種有限性的發生境域。
四、超越和超越論的想象力與此在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超越最終體現在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處,而海德格爾對通過康德在追尋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時所產生的疑難進行一種源初的闡釋,而最終認定超越論的想象力才是存在論知識內在可能性的根基。通過海德格爾的闡釋,康德的知識論首先成了一種存在論,而在康德圖型論中最終體現的超越——存在論知識的內在可能性的根基,也由康德認識論意義上的超越轉變成了生存論的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
由于超越論的想象力并非相繼的現在序列的認識論意義上的直觀形式——時間,而是使認識論意義上的時間得以可能的源生性的時間——時間性。超越論的想象力這種源生性的時間,它具有自身內在的時間的結構,海德格爾通過對康德第一版演繹的闡釋認為超越論的想象力作為存在論綜合三種模式——直觀中領會的綜合、想象中再生的綜合與概念中認同的綜合的根基,而這三種綜合模式在經驗性的想象力中分別對應著映像、后像和前像,它們又分別對應現在、過去和將來。海德格爾認為第三種模式——概念中認同的綜合是一種偵查活動,這種“偵查活動作為純粹的偵查活動就是這種預先的粘連(Vorhaften),即將來的源初形象活動。這就表明綜合的第三種模式在本質上就是一種時間性的形象模式……預先的粘連活動就是純粹的前-像活動,這是純粹想象力的行為之一”[6]177。“而且純粹前-像這種模式由于其內在的結構,甚至還顯現出一種比其他兩種在本質上同時共同隸屬的模式更為優先的位置”[6]177。這就表明“將來”對于其他兩種時間模式的優先性,而同于認識論中的“現在”的優先性。而“如果超越論的想象力——作為純粹形象的能力——本身形象為時間,即讓時間得以源生出來的話,那么……超越論的想象力就是源生性的想象力”[6]177。
由于 “時間性最初是由將來來展開自身的,這就是說:時間性的綻出性整體以及這種視域的統一最初是按照將來來規定自身的”[7]273。同樣,超越論想象力具有“將來”優先于“現在”和“過去”這種內在的時間特質,因而超越論想象力作為使存在物得以顯現自身與“讓……對象化”的有限性發生境域也就必然是有限本質存在——此在,人的生存境域。
可以說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中,海德格爾是通過追問存在論知識的本質可能性根基——超越論的想象力來凸顯有限的本質存在——此在的,或者說是通過對康德形而上學的奠基疑難的闡釋來揭示此在形而上學的,進一步講是通過將超越論的想象力闡釋為時間性而揭示此在的。而在《存在與時間》之中海德格爾則是通過對此在的生存論分析來揭示此在的時間性從而通過此在的時間性來展示存在的意義的。在此,我們可以看出超越論的想象力、時間性與此在,甚至存在的意義都可以說只是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談論一個問題而已,這個問題就是“存在的意義是什么?”對此,John Sallis甚至直接認為“就此而言想象力證明自身為存在的意義”[8]135。
在John Sallis 看來,“本質與實存屬于存在者的存在,海德格爾試圖表明這種概念與論點是從古代存在論的存在理解中成長起來的”[8]134。他認為,古希臘哲學中的Eidos與Idea(理念)都是生產制作活動的前瞻圖像(Vorausschauenden Bild),Eidos與Idee作為制作物的預設圖像(Vorausbild),預設外觀(Aussehen),它們只能通過想象力才能獲得。“海德格爾強調,這樣一種在制作過程中的圖像性的預見不是附帶的,而是從本質上屬于制作過程的結構的。想象力從根本上控制著制作過程”[8]135。由此可見,想象力對于存在(理念)的實現的重要意義,正是由于想象力在存在物(理念)的形成建構過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存在物的概念(理念、存在)才能實現、顯現出來。甚至在海德格爾那里,這種由想象力支配的制作過程、制作結構是優先于被制作之物的實現與顯現的,因為只有在這種由想象力支配的被制作物的實現過程中和實現結構中,被制作物(存在者的存在或理念)才是可能的,可以說這與亞里士多德對于事物的運動與實現過程的把握是一脈相承的,簡單說,就是實存(Existential)先于本質(Essentia),因為實存(制作過程,制作結構)是本質(理念,存在)的發生境域,而推動這種制作過程進行就是想象力。而想象力在海德格爾那里就是超越論的想象力,它就是一種源生性的讓存在物顯現源生性的時間或時間性,進一步說它就是操心著的此在,它通過自身的操心結構而讓存在物顯現。同時也可以看到海德格爾所看重的“超越”不在于事物所分有的或事物成其本身的現成在場的理念,而是在于存在物首先得以在其中顯現的發生境域。
此在與存在物的關系不同于認知主體(先驗自我)對于現象的統攝關系,在后一種關系中主體與對象之間是一種概念性的建構被建構的關系(在胡塞爾那里,先驗自我與原初予料之間也是一種意向性的建構關系),而前一種關系——人與物的關系則是一種生存實踐關系,一種在此在的生存活動中打交道的關系,在這里,存在者不是作為被認知建構、被概念化的對象,而是同此在一同處于一種生存實踐的游戲活動中的游戲參與者,可以說此在從本質上就是與他物、他在共在的存在者,而不是一種孤立的認知主體或概念建構的主體,即是說存在物首先只是在人的有限性的生存境域的被接受、被遭遇并與之打著交道的東西,而不是被建構的知識對象。
由于此在不是某種固定不變的現成存在者,而是一種不斷出離自身的存在者,因此在自身的存在-生存(Existenz)中就是一種對于自身的“超越”。而“此在在它的超越之中所超越的東西不是一段距離或它自身與對象之間的界限恰恰隸屬于它的作為實際性的此在的存在者被此在所超越”[7]212。如前已述,超越論的想象力并不是一種創生性的想象力而只是存在物得以被遭遇與“對象化”地考察的接受性的(自發性)有限性境域,而這種有限的境域實際上也就是此在的存在,即人的有限性生存境域。由于人作為一種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它不能像上帝一樣創造存在物,因此它只是在其有限性的生存境域之中接受和遭遇存在物,而且是必然的要和其他存在物打交道,所以它也是被拋于世的,自從此在一開始存在(生存)它便是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而此在的存在本身也就是一種超越,因此最終“超越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7]218。
按照前文,“超越”在存在論知識的根源處——超越論的想象力形象出來了,由于超越論的想象力是一種源生性的時間,并且是一種以“將來”為核心的三位一體的綻出的時間性,“‘綻出的’這個說法與出神狀態毫不相干。Ekstatikon[希:綻出、出離]這個平常的希臘詞意指出-離-自己,它與‘生存’這個術語有關聯。我們便以綻出特征來闡釋生存——從存在論的角度看,生存乃是‘走-向-自己’、‘回歸-自己’、當前化地外在于-自己-存在之本源統一。具有綻出的規定的時間性乃是此在之存在建制之條件”[9]365。作為將來、曾在與當前的統一,時間性在其自身之中便是出離的,因而它在本質上就是人的生存論建制,而人的生存也正是此在。“如果時間性構成了人的此在之存在意義,而存在領悟屬于此在之存在建制,那么這一存在領悟也必須基于時間性才得以可能”[9]19。而此在正是在其存在領悟中展開自身的,甚至“存在的領會就是超越”[7]280。也就是說,此在是在時間性的領會中展現超越的。這樣,“超越”便體現在綻出的時間性中,進一步說就體現在此在的存在或人的有限性生存境域之中。由于時間性本就意味著一種有限性,而此在的存在也是有限性的生存境域,因此可以說超越與有限性又是密切關聯的,海德格爾甚至說“超越同時又是有限性自身”[6]85。可見,通過海德格爾對康德的“先驗想象力”(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的解釋,Transzendenz(超越)便不再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使經驗和經驗對象得以可能的先天條件的“超越”了,不再是一種靜態的本質(Essentia)性的認識主體通過其知性功能——范疇對于現象(存在物)的“超越”,而是一種動態的時間性的生存性的(Eixtentia)綻出,一種有限性的出離-自身的生存境域,并且是“最源始的本真的真理:‘生存的真理’(Wahrheit der Existenz)”[10],因此實存性的或生存論的超越是一種本源性的真理意義上的超越,本質性的超越只有在一種本源性的真理意義上的超越的基礎上是可能的。
五、兩種想象力的區分與翻譯
先驗想象力在康德的兩版先驗演繹中有著前后兩種不同的地位,在第一版演繹中康德將其稱為一種 “靈魂不可或缺的功能”,而在第二版演繹中康德卻將其稱為一種“知性的功能”。海德格爾當然更看重康德的第一版演繹。然而康德之所以做出第二版演繹的原因在于他要強調先驗邏輯(知性范疇)的普遍有效性的優先地位,由此先驗想象力便成了從屬于知性的一種知性的功能,從而先驗想象力的作用也只是在于用先天范疇對純粹直觀——時間進行先驗的規定,從而達到對現象進行統攝以形成概念的目的。
由康德的第二版本演繹,可以看出康德更加注重先驗想象力的認識功能,因此筆者認為按照國內傳統的譯法將康德認識論意義上的想象力譯為先驗想象力是較為合理的,因為Transzendental(先驗的)在康德認識論中表示的正是經驗或經驗對象得以可能的條件,而且由于符合傳統譯法,也不會讓人產生誤解。孫周興先生也認為可以將Transzendental翻譯成“先驗的”,因為也可以指“一種超自然的存在的、超出自然的世界的、超出生活和科學的自然的實證性研究態度”。但孫先生同時也認為將Transzendental翻譯成“先驗的”確實“沒有很好地傳達出‘超’的意義”[11]22,但即使沒有很好地傳達出Transzendental中Transz的意義,“只要用心,仍舊能夠體會其‘邏輯上在先’意義上的‘超’”[11]23。
然而,在海德格爾的《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中,我們是否還能將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 譯作“先驗想象力”呢? 王慶節先生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中將Transzendental 譯作“超越論的”,因為它原本是指“那獨立于經驗,而又使關于對象的經驗知識所以可能的先天性條件……而按照現象學的解釋Transzendental講的首先不是去證明經驗知識如何可能的先天條件,而是去發問和描述,使得經驗知識得以可能的‘超越境域’和事情本身,即作為使得我們關于現象的知識的可能以及不可能之淵源的境域和事情本身,究竟是怎樣以及如何發生的?”[6]12在此,筆者認為王慶節先生在《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中將海德格爾存在論意義上的 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 翻譯為“超越論的”想象力也是較為合理的,因此為了區別二者,筆者認為從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的角度還是應將Transzendental譯作“超越論的”(不能翻譯為“超越的”,若將Transzendental譯為“超越的”的話就與Transzendent混淆了),因為在該著作中,按照前文的論述,海德格爾顯然是在談一種存在論意義上的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超越論想象力),而不是一種使經驗和經驗對象得以可能的康德認識論意義上的先驗想象力或一種從屬于知性的功能或認識能力。王慶節先生認為Transzendental并不是指關于對象的經驗的知識的可能性條件,而是去描述使經驗知識得以可能的“超越”境域或事情本身;王炳文先生也認為胡塞爾以Transzendental來指稱“一種超自然的存在的、超出自然的世界的、超出生活和科學的自然的實證性研究態度”。如果把它翻譯成“先驗的”就有可能將“超越論”的態度與“自然的”態度混淆起來。但是孫周興先生卻認為Transzendental中并無“論”可言,而筆者卻認為將Transzendental翻譯成“超越論的”,并不一定就是意味著Transzendental“超越論的”中有什么“論”或者就會產生好像有一種“學說”的歧義,而只是一種按照Transzendental這個詞在諸如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這樣的詞組內的含義而作出的符合漢語習慣的表達而已,如zeitlich其中也并無“性”可言,而我們通常卻都按照漢語的表達習慣翻譯為“時間性的”。
可以看出,在對待Transzendental這個詞的翻譯上,孫周興認為應該譯作“先驗的”,而王慶節、王炳文等認為應該翻譯為“超越論的”,在此,筆者認為不管哪種譯法,如果只是固守Transzendental的字面含義來進行翻譯而不管它在哲學家的具體語境中的含義,都會有失妥當。因此,筆者結合前文的論述,對Transzendental采取了一種按照哲學家的哲思語境來進行的翻譯方法,即同意孫周興先生的譯法,將康德哲學中的Transzendental翻譯為“先驗的”,因為它表示經驗與經驗對象的可能性條件,是認識得以可能的條件,它主要側重于認識上的超越,它同時也是一種邏輯意義上在先的超越;但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尤其是在海德格爾的基礎存在論意義上應將Transzendental譯作“超越論的”,因為,正如王丙文和王慶節的觀點,Transzendental這個詞表示一種超自然存在、超生活的態度,一種經驗與經驗對象得以可能的發生境域的而非僅僅是一種經驗與經驗對象得以可能的先天條件。而且按照海德格爾對康德先驗想象力的解讀,康德的先驗想象力從根本上講應該是其讓存在物在起來的,讓對象化的綻出式的發生境域,是一種基礎存在論意義上的超越境域,而它首先并不是認識得以可能的條件,而是此在在世的生存境域,并且只有在這種生存境域之中認識才可能發生,可以說認識活動是此在在世的一種衍生樣式。
六、結語
綜上,形而上學的超越(Transzendenz)的兩種基本形式:本質性的(essentia)超越與實存性的(existenia)超越,其中大致可以說柏拉圖、康德的哲學思想屬于前者,而亞里士多德、海德格爾的思想屬于后者。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認為兩種超越哲學或超越追問之間的關系在海德格爾的《康德與形而上學問題》得到了比較集中的體現。進一步說集中體現在海德格爾對于康德的先驗想象力的不同理解上——在康德那里先驗想象力傾向于作為從屬于知性的一種功能,即是說康德的先驗哲學(超越)傾向于本質性的形式上(認識范疇的)超越;而海德格爾卻從康德第一版演繹中得出一個令其“感到陌生”的結論,即先驗想象力作為知識的根基出發認為先驗想象力并非一種“知性功能”,而是一種純粹直觀、一種源生性的時間,是一種讓存在物得以被領受而非創造存在物的境域。而這種時間性的境域正是此在的存在,它是一種實存性的existenia超越,而且也只有在這種實存性的existenia超越的基礎上本質性的超越才是可能的,即是說認識論意義上通過范疇而可能的本質性的essentia超越只有在存在論意義的超越,即實存性的existenia超越上才是可能的。這里我們可以反觀到亞里士多德哲學中第一實體——個體的實存(existenia)高于第二實體——個體的屬性、本質(essential)(或個體的外觀Eidos,Aussehen)的卓越思想。
此外,由于不管是康德的超越追問還是海德格爾的超越追問,都是超越哲學(Transzendenzphilosophie);不管是將康德的哲學稱作先驗哲學還是超越論的哲學,它們都使用的是同一個詞Transzendental。但是如上述,為了區分兩種超越,我們最好將康德哲學中Transzendental譯作先驗的,而且這也符合國內翻譯傳統,而將在海德格爾思想中的Transzendental譯為超越論的,盡管如孫周興先生認識這個詞當中沒有“論”的含義,但我們為了與Transzendent超越的進行區分,而意譯為超越論,就如zeitlich一樣,我們通常譯作“時間性”的,而其中也并無“性”這個含義。由于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是海德格爾與康德爭辯的焦點,因此我們特別建議將康德哲學中的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譯作先驗想象力,這樣既與國內康德哲學研究傳統保持一致又能夠凸顯其認識論、(范疇)本質性的超越的含義;而將海德格爾思想背景下Transzendental Einbildungskraft譯作超越論的想象力以凸顯其實存性超越的含義。
[1] Joachim Ritter.Historisches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e[M].Basel:Schwabe & Co,1971:346.
[2] 海德格爾.形而上學導論[M].熊偉,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3] 馬丁·海德格爾.尼采(下)[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1042.
[4] 康德.未來形而上學導論[M].龐景仁,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172.
[5]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鄧曉芒,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 馬丁·海德格爾.康德與形而上學疑難[M].王慶節,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7] Martin Heidegger.Metaphysiche anfangsgruede der logik(im Ausgang von Leibniz) [M].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0.
[8] John Sallis.Heidegger und der Sinn von Wahrheit[M].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2012.
[9] 馬丁·海德格爾.現象學之基本問題[M].丁耘,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10] Daniel O Dahlstrom.Das logische vorurteil[M].Wien:Passsagen-Verl,1994:300.
[11] 孫周興.后哲學的哲學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