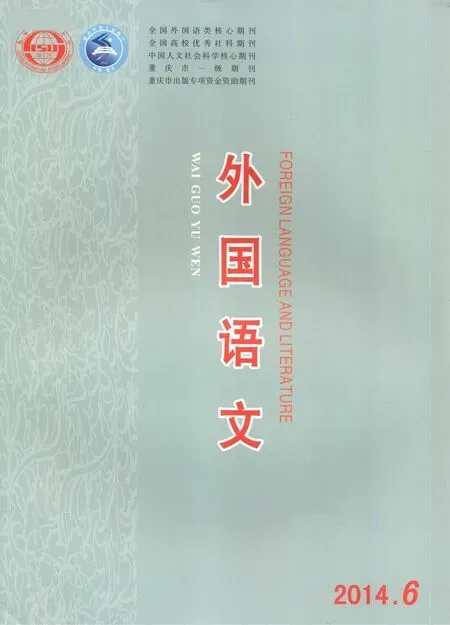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
任虎軍
(四川外國語大學 國際關(guān)系學院,重慶 400031)
晚清時期,美國小說進入中國。1872年,華盛頓·歐文的短篇小說“Rip Van Winkle”被首次譯成中文,發(fā)表在4月22日的《申報》上(謝天振、查建明,2004:1),這是最早進入中國的美國小說。此后將近30年,沒有美國小說進入中國。20世紀開始,美國小說陸續(xù)進入中國。1901年,林紓與魏易合作翻譯了斯托夫人的小說Uncle Tom’s Cabin(1852),取名《黑人吁天錄》(謝天振、查建明,2004:260);190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出版了愛德華·畢拉宓的小說Looking Backward(1888);1907年,林紓與魏易合譯出版了歐文的《見聞札記》(收入《瑞普·凡·溫克爾》與《睡谷傳奇》等短篇小說)(謝天振、查建明,2004:260)。隨后,美國小說開始大量被譯介到中國,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隨之興起并逐漸活躍起來,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不僅出現(xiàn)了大量的美國小說評介、研究論文與專著,而且譯介了很多國外美國小說研究成果,很多評介和研究成果不僅學術(shù)分量頗重,而且歷史價值甚高。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大體經(jīng)歷了日益活躍期(1916-1929)、繁榮發(fā)展期(1930-1939)和深入發(fā)展期(1940-1949)三個階段,每個階段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批評標準、批評觀點以及研究的廣度和深度方面呈現(xiàn)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本文對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做一歷史考察,以突顯這個時期中國美國小說研究的整體面貌和歷史走向,為學界研究美國小說提供歷史參照。
1.1916-1929年:日益活躍的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
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始于1916年。是年,孫毓修編著出版了《歐美小說叢談》,收入三篇評介美國小說家的短文章:《斯拖活夫人》簡單評介了斯托夫人及其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以及她對歐文與霍桑的影響(孫毓修,1916:41-43),《霍桑》簡單評介了霍桑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并比較了他與歐文和庫柏的不同(孫毓修,1916:45-49),《歐文》簡單介紹了歐文(孫毓修,1916:49-51)。嚴格地講,這三篇短文章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美國小說家研究論文,卻是國內(nèi)最早評介美國小說的文字,因此具有比較重要的歷史價值。除此以外,20世紀20年代之前,中國幾乎沒有其他評介美國小說的文字。
進入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開始逐漸活躍起來,評介美國小說的文字頻現(xiàn)于各種文藝期刊。1921年,《小說月報》第12卷第5、11號分別發(fā)表了理白評介杰克·倫敦和沈雁冰評介梅·辛克萊小說《威克的惠林頓先生》的短文章。1922年,《東方雜志》第19卷第20號發(fā)表了幼雄的《美國革命文學與貴族精神的崩潰》,文章以劉易斯《巴比特》為例論述了美國文學中革命精神的興起與貴族精神的衰落,是國內(nèi)最早的美國小說主題研究;《小說月報》第13卷第5號發(fā)表了沈雁冰的短文章《美國文壇近況》,介紹了美國文學的最新情況。1923年,《小說月報》第14卷第6、7、11號分別發(fā)表了沈雁冰的短文章《兩部美國小說》、《美國的短篇小說》與《美國的小說》,分別評介了格特魯?shù)隆ぐ⑸D(Gertrude Atherton)的《黑牛》和安德森的《許多婚姻》、奧·勃林主編的The Best Short Stories of1922:II:American以及1923年上半年美國“關(guān)于歐戰(zhàn)的小說”、“兩性問題小說”、“由近代人的‘望鄉(xiāng)心’產(chǎn)生的憎恨都市的小說”、“描寫異域情調(diào)或古代風化的小說”、“戀愛小說”、“反對結(jié)婚的小說”和“描寫‘新奇跡’的小說”及其代表作(沈雁冰,1923:1-2)。總體上講,20世紀20年代前半期,中國美國小說研究以概論性評介為主,真正意義上的深入研究仍然很少。
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開始,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日益活躍,呈現(xiàn)出蓬勃發(fā)展的態(tài)勢,產(chǎn)生了不少頗有學術(shù)分量的評介和研究成果。1927年4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鄭振鐸的《文學大綱》。該書第43章①該章最早發(fā)表于《小說月報》第17卷第12號(1926年12月)。第二部分介紹了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歐文、庫柏、霍桑、愛倫·坡和斯托夫人等南北戰(zhàn)爭前的美國小說家。作者認為:布朗是“美洲的第一個重要的小說家”(鄭振鐸,1998:357)、文學方面“美國的開國元勛”(鄭振鐸,1998:358);歐文和庫柏與霍桑和愛倫·坡不同:“柯甫[庫柏]和歐文把人生的外面的冒險與奇遇寫成為他們的傳奇”,而“霍桑與愛倫·坡寫的卻是人生的內(nèi)面的事件,他們的心靈的冒險與奇遇”(鄭振鐸,1998:360);霍桑是“美國文學史上第一個寫悲劇的人”(鄭振鐸,1998:362);坡是“美國最偉大的作家,沒有一個美國作家在歐洲文學史上有他那樣之有力的影響的”(鄭振鐸,1998:365)。第43章第三部分介紹了南北戰(zhàn)爭后美國小說界的“三個一等重要的作家及好幾個很有才情的作家”(鄭振鐸,1998:367):馬克·吐溫、豪威爾斯、詹姆斯以及哈特、朱厄特、克萊恩、諾里斯和歐·亨利等12位19世紀后期的美國小說家。作者認為:馬克·吐溫是“最深沉而博大的美國人”,“沒有一個作家比他更適宜于解釋他所住之國的,也沒有一個國家有他那樣的一個作家更適宜的去解釋它的”(鄭振鐸,1998:367);詹姆斯是“十九世紀有數(shù)的藝術(shù)家之一”(鄭振鐸,1998:369)。第46章第三部分簡單介紹了劉易斯、華頓、安德森等14位20世紀初的美國小說家。鄭振鐸《文學大綱》中對美國小說的評介雖然比較簡略,卻是國內(nèi)對美國小說的第一次全面評介。
1929年3月,上海ABC叢書社出版了曾虛白的《美國文學ABC》,這是中國第一部美國文學研究專著。該書“總論”說:“美國人的文學作品是理想的、甜蜜的、織巧的、組織完善的,然而,他們沒有抓住人生的力量[……]他們成功的小說家既不多,又是軟弱。”(曾虛白,1927:7)作者認為:“美國作家的小說自然也有各種不同的好處,然而要找一部完善的,簡直很難:巧妙了不免軟弱,堅強了不免粗糙[……]因此美國作家的小說,雖有驚人的產(chǎn)量,始終不能攀登文壇上第一流的位置。”(曾虛白,1927:9-10)這種觀點表明,20世紀20年代,中國學界對美國小說的認識還比較粗淺。“總論”之后的部分涉及七位小說家:歐文、庫柏、霍桑、愛倫·坡、馬克·吐溫、豪威爾斯和詹姆斯。作者認為:
在歐文的不朽作品里,我們聽不到革命的號角,也找不到開辟荒蕪的偉大事業(yè),只享受他靜悄而舊式的詼諧、溫文的語調(diào)、爾雅的態(tài)度。對于地方性濃厚的熱情,他只有微笑的淡漠。就在自己國家里,他也像是個同情而注意的過客,眼見的雖熟練地了解,可是不會投身到思想的漩渦里去。他不會叫我們感覺到在他那時最占據(jù)人們心靈的是什么,最煩擾人們生活的又是什么。他的確是跳出人群的一個袖手旁觀者。(曾虛白,1927:15)
同樣,“古柏[庫柏]的作品是大刀闊斧粗枝大葉的東西,若拿精細的文學眼光去研究他,可以說毛病百出。什么叫風格,什么叫描寫,他一概不問”(曾虛白,1927:19-20)。因此,“古柏[庫柏]不是藝術(shù)家[……]我們不應把他高高地捧到第一流作家的位置上去[……]他是個曠野里的作家”(曾虛白,1927:21)。但是,霍桑卻不同,雖然“很多美國的批評家說霍桑是一個表現(xiàn)清教精神的作家”,但“這是個重大的錯誤”,因為“霍桑的作品特別顯示給我們看他已經(jīng)完全脫離了清教的色彩。他的作品是純藝術(shù),決沒有受什么黑奴問題或其他重要的政治問題的影響[……]他的目的只注意在藝術(shù)化表現(xiàn)靈魂的形態(tài),決不想開發(fā)什么道德問題”(曾虛白,1927:34)。因此,霍桑“是一個諷詠者,不帶一點兒道德的氣味;他表現(xiàn)的[……]決不是清教的精神,是‘美’的精神,是毀滅靈魂的清教道德所仇視的‘美’的精神”(曾虛白,1927:37)。同樣,愛倫·坡不僅是優(yōu)秀的小說家,而且是“切實的、大膽的、高超的、而且是獨立的”批評家(曾虛白,1927:61)。馬克·吐溫是“穿著小丑衣服的人生哲學家”(曾虛白,1927:92)。豪威爾斯“抱著偉大的志愿,要給美國的文學開一條新的途徑[……]可是他卻不能接受寫實派的根本條件:要講赤裸的真理,并且他始終沒有找到了寫實派的真精神”(曾虛白,1927:100),而他“寫實的失敗是在他根本上沒有了解人生”(曾虛白,1927:103);但是,“在他的范圍里講,他仍舊是個完善的藝術(shù)家。他沒有寫一頁不好的文學,他沒有寫過一句能讓人家修改的句子[……]他的情緒和事實雖不能引人的注意,可是他的作風是有陶醉性的;看他表演英文的藝術(shù)確是種文學家的愉快”(曾虛白,1927:104-105)。詹姆斯是“美國第二個寫實派的領(lǐng)袖,然而他仍舊算不得怎樣偉大的作家”(曾虛白,1927:114),因為“他能深入到每一個單獨的人,卻不能深入到人生中去”(曾虛白,1927:115);然而,“根本上講,詹姆士[詹姆斯]是一個頭腦清晰、理智透開的思想家[……]他是個解析心理的專家”(曾虛白,1927:116-117)。《美國文學ABC》雖然不是美國小說研究專著,但對上述七位小說家的深入評論是前所未有的。
1929年,中國美國小說研究還產(chǎn)生了另一個重要成果。是年8月,《小說月報》第20卷第8號發(fā)表了趙景深的《二十年來的美國小說》,這是中國最早的美國小說斷代研究,介紹了20世紀前20多年美國小說的發(fā)展狀況,重點評介了“較著名的12個人”(趙景深,1929:1247):“羅曼小說家”倫敦、加蘭和阿瑟頓、“神秘小說家”坎貝爾(James Branch Cabell)和赫格西默、“心理小說家”達金頓和華頓與“社會小說家”德萊塞、安德森、辛克萊、劉易斯和凱瑟,文章還簡單總結(jié)了評論界對劉易斯的評價。通過對12位小說家的評介,文章比較全面地勾勒了20世紀前20多年美國小說的面貌,雖然對涉及小說沒有做文本分析,但“卻無疑擴大了美國小說在中國現(xiàn)代文壇的影響”(謝天振、查建明,2004:264)。
2.1930-1939年:繁榮發(fā)展的中國美國小說研究
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呈現(xiàn)出非常繁榮的景象。1930-1931年,《小說月報》第21 卷第1、4、5、8 號和第22 卷第1、2 號分別發(fā)表了趙景深的短文章《最近的美國文壇》、《辛克萊的山城》、《美國文壇在俄國》、《美國文壇雜訊》、《美國文壇短訊》與《劉易士得諾貝爾獎的輿論》,分別簡單介紹了美國文學的最新狀況、辛克萊的小說《山城》、美國文學在俄國的情況、赫格西默的小說《宴會的衣服》、達金頓的小說《歡樂之港》和劉易斯獲諾貝爾文學獎后的輿論反應。1932年,《國聞周報》第9卷第18期發(fā)表了挹珊的《戰(zhàn)后美國小說概況》,介紹了美國批評家Gorham Munson的論文《戰(zhàn)后美國小說》。文章認為,一戰(zhàn)之后,美國小說界沒有越出德萊塞、劉易斯、菲茨杰拉德與海明威的影響(挹珊,1932:1),他們是“當代美國小說界之路標”(挹珊,1932:3),是“美國四領(lǐng)袖小說作家”(挹珊,1932:5),他們“能占據(jù)領(lǐng)袖地位,產(chǎn)生影響者,并非僅只能力使然”,而因“每人均受大數(shù)量讀書界之歡迎,均有極多模仿者”(挹珊,1932:5)。
1933-1937年,中國美國小說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多具有歷史和學術(shù)價值的重要成果。1933年,《文學》第1卷第3號發(fā)表了黃源的《美國新進步作家漢敏威》,詳細評介了海明威及其創(chuàng)作,是中國第一篇專論單個美國小說家的論文。同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張越瑞的《美利堅文學》,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了楊昌溪的《黑人文學》。《美利堅文學》是中國第一部美國文學史,概括介紹了17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文學的歷史發(fā)展,評介了49位美國小說家,包括早期小說家布朗、浪漫主義小說家歐文、庫柏、愛倫·坡和霍桑、19世紀“鄉(xiāng)土派”小說家哈特、馬克·吐溫、朱厄特和加蘭、“寫實派”小說家豪威爾斯、詹姆斯和畢拉宓、19世紀末“自然主義”小說家克萊恩和諾里斯以及華頓、凱瑟、劉易斯和安德森等20世紀初的小說家。作者認為:布朗的小說“不是傷感的,不含道德教訓的,而是高特式[哥特式]的(Gothic)或浪漫的”(張越瑞,1933:40),但他“所寫的恐怖不是高特式[哥特式]的機械的而是心理的。這種寫法影響到日后歐林坡[愛倫·坡]、霍桑的創(chuàng)作”(張越瑞,1933:40);坡是“一位盛世的文宗”,是“在世界文豪隊里顯出偉大金光的”作家(張越瑞,1933:59);霍桑“是靈魂的宣露者,是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張越瑞,1933:83),《紅字》是其“最偉大的悲劇小說”,是“‘美’、道德、詩意三種元素集合成”的“曠世的偉著”(張越瑞,1933:83)。《黑人文學》是中國第一部美國少數(shù)族裔文學史,其“黑人的小說”部分比較詳細地介紹了杜波依斯、拉爾森、休斯等十一位美國黑人小說家。作者認為:1912年之前,黑人小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是很和平的”(楊昌溪,1933:40);1912年之后,“黑人對于美國和宰制亞非利加洲[非洲](Africa)的帝國主義者作了新的控訴。所以,從那時起,小說家在描寫上轉(zhuǎn)變了方向,在意識上已經(jīng)從緩和的領(lǐng)域而到了激烈的階段。不但在黑人文學方面開展了一個新的局面,而同時更為黑人民族解放運動開拓了一個新時代”(楊昌溪,1933:41)。作者指出:“美國的黑人小說家[……]為了[由于]生活的壓迫,好像只有對于[……]短篇小說方面有所貢獻,而對于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造,除了休士[休斯]的長篇小說《不是沒有笑的》外,只有約翰遜(James Weldon Johnson)的《一個有色人的自傳》(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算是好幾部長篇自傳中出色的作品。”(楊昌溪,1933:44-45)
此外,1934年,《現(xiàn)代》第5卷第1號發(fā)表了趙家璧翻譯的Milton Waldmand的《近代美國小說之趨勢》,第5卷第6號推出了“現(xiàn)代美國文學專號”。《近代美國小說之趨勢》分析了美國小說從“英國的”走向“美國的”發(fā)展趨勢,評介了20世紀初以來追求“阿美加主義”的小說家詹姆斯、豪威爾斯、華頓、德萊塞、劉易斯、赫格西默、凱瑟和福克納,認為:前四位盡管有諸多不同,但都在努力回答“怎么樣才是一個美國人”的問題(Waldmand,1934:108),而這些小說家中,福克納是“美國近代小說家中最重要的”,因為他的小說“不但是純粹的藝術(shù)作品,并且是十足美國的”(Waldmand,1934:108)。“現(xiàn)代美國文學專號”收入八篇美國小說研究論文,其中一篇概括論述了美國小說的歷史發(fā)展,其余七篇分別評論了倫敦、辛克萊、劉易斯、德萊塞、海明威、帕索斯和福克納,此外還有一篇短文章介紹了美國第一部小說《同情之力》。如此大規(guī)模地集中評論美國小說,在20世紀30年代前的中國美國文學研究史上尚屬首例。
20世紀30年代正中期,中國美國小說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多重要成果。1935年,《世界文學》第1卷第4號發(fā)表了允懷的《黑人文學在美國》,對黑人小說有一定介紹。《時事類編》第3卷第8、13期分別發(fā)表了高植的《兩本人物正相反的美國小說》與他翻譯的穆爾(Harry Thornton Moore)的《今日之美國小說》,前者評介了威爾特(Thornton Wilder)的《天堂是我的目的地》與阿奇博爾德(Norman Archibald)的《天堂高——地獄深》,后者評介了20世紀30年代前半期美國小說的主要派別:模仿海明威情調(diào)的小說、“普羅小說”、“地方小說”和“城市小說”。文章說:“近來許多小說的情調(diào)是模仿漢敏威(Ernest Hemingway)[……]那些模仿他的體裁的人都慘然失敗了[……]但許多模仿他的情調(diào)而不是他的體裁的人卻有相當?shù)某晒Α!?Moore,1935:78)文章比較詳細地介紹了一些代表性“普羅派作家”、“地方派作家”和“城市文學作家”。《現(xiàn)代文學》第1期發(fā)表了斐丹翻譯的高垣松雄的《美國小說的一側(cè)面》,評介了以福克納為中心的美國現(xiàn)代實驗派小說,分析了詹姆斯、劉易斯、海明威、弗蘭克、帕索斯和福克納小說中的實驗技巧及其影響,認為“文學的技巧,是受作家的世界觀與創(chuàng)作之目的支配的”(高垣松雄,1935:67)。《協(xié)大藝文》第2期發(fā)表了點默的《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介紹了吐溫的生平及其早期作品,認為他“是美國的蕭伯納。他的作品里充滿著獨創(chuàng)的滑稽的筆調(diào),同時還具有最高的藝術(shù)的條件,并不只幽默而已[……]在亞美利加[美國]文壇上占有最高的地位[……]他的作風是奇趣的、豪爽的。他是美國寫實主義文學的先驅(qū)。在他的諷刺的幽默的文章里透露出他底社會主義和德謨克拉西的意識”(點默,1935:7)。此外,中華書局出版的張夢麟與劉杰夫合譯的杰克·倫敦的中短篇小說集《野性的呼喚》前有兩篇文章,介紹了倫敦及其創(chuàng)作。
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中國美國小說研究的重要成果首推1936年出版的趙家璧的《新傳統(tǒng)》,這是中國第一部美國小說研究專著。作者在“序”中說,“美國的文學是素來被人輕視的,不但在歐洲是這樣的,中國也如此”(趙家璧,2013:2),但這種現(xiàn)象不應該出現(xiàn),因為:
現(xiàn)在中國的新文學,在許多地方和現(xiàn)代的美國文學有些相似的:現(xiàn)代美國文學擺脫了英國的舊傳統(tǒng)而獨立起來,像中國的新文學突破了四千年舊文化的束縛而揭起了新幟一樣;至今口頭語的應用,新字匯的創(chuàng)制,各種寫作方法的實驗,彼此都在努力著;而近數(shù)年來,在美國的個人主義沒落以后,從五四時代傳播到中國思想界來的“美國精神”,現(xiàn)在也被別一種東西所淘汰。太平洋兩岸的文藝工作者,大家都向現(xiàn)實主義的大道前進著。他們的成績并不十分驚人,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從他們的作品里認識許多事實,學習許多東西的。(趙家璧,2013:2)
在開篇一章“美國小說之成長”中,作者勾勒了美國小說從馬克·吐溫的“邊疆的現(xiàn)實主義”,經(jīng)過豪威爾斯的“緘默的現(xiàn)實主義”、辛克萊和倫敦所代表的“早期的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凱瑟和華頓等代表的“逃避現(xiàn)實的浪漫主義”、德萊塞、安德森和劉易斯的“個人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海明威和福克納的“悲觀主義”,發(fā)展成帕索斯的“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的成長軌跡。作者認為:馬克·吐溫是“近代的‘美國的’小說的始祖”,因為“在他之前,沒有一本小說能這樣的擺脫殖民地心理而寫得如此獨創(chuàng)而富有邊疆精神過”(趙家璧,2013:8),因此,“馬克·吐溫的‘邊疆的現(xiàn)實主義’(Frontier Realism)或稱‘初民的現(xiàn)實主義’(Primitive Realism),終于替今日的美國現(xiàn)實小說樹了一塊基石”(趙家璧,2013:9)。但是,“霍威耳斯[豪威爾斯]對阿美利加主義[Americanism]和現(xiàn)實主義在美國的成長,和馬克·吐溫是同樣值得紀念的”,因為“雖然他沒有把那時代的生活忠實的記錄下來,并且有許多不徹底的地方,至少他已看到美國作家所應寫的題材比[必]得是美國的事物,而寫小說的基本條件更脫不出對于事物忠實的觀察和熱情的抒寫”(趙家璧,2013:10)。辛克萊和倫敦使美國小說“在寫實的企圖以外,帶上了些社會的意識”,他們的暴露文學“對于二十世紀的美國文學,發(fā)生極大的影響,因為它在現(xiàn)實主義以外,又替美國小說開辟了一條社會主義的道路[……]把美國人的目光,第一次由‘個人的’轉(zhuǎn)變而為‘社會的’了”。(趙家璧,2013:13-14)德萊塞使“美國的現(xiàn)實小說[……]開拓到‘真實的現(xiàn)實主義’的園地里去了”;但是,“德萊塞的現(xiàn)實主義是個人主義的現(xiàn)實主義,他代表了美國農(nóng)村和都市里數(shù)千萬小有資產(chǎn)的個人主義者,為了[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壓迫而難以生活,在替他們吐露著悲觀失望的情緒”(趙家璧,2013:23)。到了福克納,美國小說又深進了一層,因為“福爾克奈[福克納]的小說不但在形式上是美國的產(chǎn)物,他的故事和思想,也是現(xiàn)實地美國的”(趙家璧,2013:32)。帕索斯使美國小說“又深入了一層”(趙家璧,2013:33),因為他“把社會上的實際材料,作者本身的生活經(jīng)驗,和各層社會間的許多男男女女的歷史,完全打成了一片,是馬克吐溫,霍威耳斯[豪威爾斯]一輩人所意想不到的。他替美國的現(xiàn)實主義又開辟了一條新路,不是緘默的寫實主義,也不是個人主義的寫實主義,而是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趙家璧,2013:35)。作者總結(jié)說:
一百五十多年來,為了[由于]思想上,言語上,經(jīng)濟上的落后,停頓在英國殖民地意識上的美國小說,從馬克吐溫起開始掙扎,經(jīng)過霍威耳斯[豪威爾斯]、倫敦、辛克萊的努力,到二十世紀開始,由德萊塞、安特生[安德森]、劉易士[劉易斯]而逐漸建立,如今到了福爾克奈[福克納]、帕索斯,而成為一種純粹的民族產(chǎn)物了。這里,美國的人民活動在美國的天地間,說著美國的話,表露著美國人的思想感情;在美國的散文中,包容著美國的韻調(diào),講述著美國實際社會中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趙家璧,2013:35)
然后,作者分章評論了九位美國現(xiàn)代小說家:德萊塞、安德森、凱瑟、斯坦因、威爾特、海明威、福克納、帕索斯和賽珍珠,認為:“講現(xiàn)代的美國文學,就得從特萊塞[德萊塞]說起”,因為“美國民族文學一開始就在擺脫理想文學而向現(xiàn)實主義的大道前進,但是馬克吐溫、霍威耳斯[豪威爾斯]、諾立斯[諾里斯]、杰克倫敦一群人只替特萊塞[德萊塞]開辟荒蕪,幫助完成特萊塞[德萊塞]的事業(yè)而已”(趙家璧,2013:37);斯坦因“一反過去文藝作品用最華麗的字句和最雕飾的修辭去敘述故事的舊習慣,而模仿小孩子的言語,用最本質(zhì)的字句去表現(xiàn)最本質(zhì)的東西[……]她把所有文字上的裝飾全部剝落掉,而只用了幾根動不得的骨干”(趙家璧,2013:99-100),她的重復“并不是第一種東西的第二次表現(xiàn);而是第一種東西的第二種表現(xiàn)。并不是靜止的反復,而是進展中的變化;不單是空間的,而是空間加上時間了的”(趙家璧,2013:102);海明威是“散文界中偉大的天才”(趙家璧,2013:145),他“用最經(jīng)濟的文字,‘報告’最復雜的情緒”(趙家璧,2013:150);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是“現(xiàn)代文學中最大膽的實驗作品”(趙家璧,2013:159),雖然“題材上已經(jīng)是驚心動魄的戲劇,可怕的故事,和變態(tài)的人物,可是取用了喬也斯[喬伊斯]的形式,所以并沒有獲得廣大的讀者群”,但《圣殿》“利用了偵探小說的方法,他的作品才逐漸被人注意起來了”(趙家璧,2013:165);帕索斯“用新的形式去表現(xiàn)新的社會結(jié)構(gòu)”,因此,“他寫小說所用的方法,和其他小說家根本不同”(趙家璧,2013:181)。
20世紀30年代后半期,中國美國小說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1937年傅東華與于熙儉編譯出版的《美國短篇小說集》譯者《導言》,該文比較詳細地評介了19世紀初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短篇小說的歷史發(fā)展,是中國第一篇全面評介美國短篇小說的論文。文章說:
不但在英語的短篇小說中,就是以全世界的短篇小說而論,美國的短篇小說也占著極重要的地位。因為,我們曉得,美國和法國的短篇小說是近代短篇小說所由發(fā)展的兩個主要的源派,而法國則等到一八五二—六五年間 K.波特萊爾(Baudelaire)翻譯了E.愛倫坡的作品方曉完成了近代短篇小說的藝術(shù),而產(chǎn)生了G.莫泊桑之流的大作手。那么我們即使說美國的短篇小說是近代短篇小說的鼻祖,也不算過分夸張的。(傅東華、于熙儉,1937:1-2)
文章評介了11位短篇小說家,認為其作品雖然“不能代表美國短篇小說的全部”,卻能代表“美國短篇小說對于近代短篇小說所貢獻的各種成分”和“時代潮流”:歐文、霍桑與愛倫·坡的短篇小說體現(xiàn)了“形式與技巧上的完成”,馬克·吐溫與O.亨利的短篇小說體現(xiàn)了“幽默的成分”,哈特的短篇小說代表了“地方色彩即鄉(xiāng)土小說”,安布烈斯·皮爾斯與詹姆斯的短篇小說體現(xiàn)了“心理分析或性格解剖”方法的嫻熟運用,德萊塞的短篇小說展現(xiàn)了“生理的解剖”,凱瑟與劉易斯的短篇小說反映了“大戰(zhàn)后美國生活”;歐文是“前期浪漫主義即初期國民時代(1800-1840)的代表”,霍桑是“后期浪漫主義即后期國民時代(1840-1861)的代表”,愛倫·坡是“南方浪漫主義的代表”,馬克·吐溫是“南北戰(zhàn)爭后所謂鍍金時代(1865-1900)的代表”,哈特、皮爾斯與詹姆斯是“美國寫實主義創(chuàng)始的代表”,O.亨利是“寫實主義確立時代(1900-1920)的代表”,德萊塞是“自然主義的代表”,凱瑟與劉易斯是“大戰(zhàn)后的代表”(傅東華、于熙儉,1937:2-3)。文章認為:歐文在短篇小說里“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特的優(yōu)美動人的情調(diào),就成了短篇小說所不可缺少的一個元素。短篇小說的體裁雖不完成在歐文手里,歐文卻曾給短篇小說打下了一個堅實的精神的基礎(chǔ)”(傅東華、于熙儉,1937:4);霍桑“把道德和藝術(shù)調(diào)和得非常融洽,以致他的作品里雖然包含著深切的教訓,卻使你無論如何不會覺得討厭”(傅東華、于熙儉,1937:5),因此,“他的作品里面一般地充滿著黑暗的陰影,而又流露著閃電一般的光明,使讀者讀了之后自然覺得現(xiàn)實之可唾棄和光明之可追求”(傅東華、于熙儉,1937:6);愛倫·坡“用做詩的方法做小說,他的小說也就同他的詩一般,作風簡潔而能給人以強力的整個印象”(傅東華、于熙儉,1937:8);馬克·吐溫“在體裁上[……]替短篇小說開闖了一條新路”(傅東華、于熙儉,1937:9);哈特“并不怎樣掩飾人們的惡,但他有一種技倆,能夠顯出即使萬惡的敗類也未嘗不包含著幾分的善,而表現(xiàn)時又絲毫不違背自然”(傅東華、于熙儉,1937:10);皮爾斯的短篇小說“非常精細而深刻”(傅東華、于熙儉,1937:10);詹姆斯“常能引起讀者的輕妙的笑和不可及料的淚,把握題材擅長發(fā)明力和布局的技巧,故雖在社會意識上價值不如那些同時代的社會抗議的作家,卻不能不認為都市生活的精密的反映,因而具有了歷史的價值,同時又完成了美國短篇小說最高的技巧”(傅東華、于熙儉,1937:11);德萊塞“大膽打破了從前那種講究布局的作風,而自創(chuàng)一種新風格,因為他已經(jīng)看出現(xiàn)實的人生是并不如小說家意想的那么有結(jié)構(gòu)的”(傅東華、于熙儉,1937:12);凱瑟的短篇小說“寫實的觀察非常忠實,但一般的含著悲劇的情調(diào),往往把現(xiàn)代生活烘托在過去時代的背景上”(傅東華、于熙儉,1937:13);劉易斯是“一個眼光銳利的第一流的諷刺家。他的題材是徹底地現(xiàn)代生活的[……]他對于現(xiàn)世相的各方面表示著深刻的不滿和憤激”(傅東華、于熙儉,1937:13)。
3.1940-1949年:深入發(fā)展的中國美國小說研究
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略有衰退,但有價值的成果仍然很多,不少成果并非簡單評介,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深入研究。這個階段,中國學界更加關(guān)注國外的美國小說研究情況,譯介了不少國外美國小說研究的最新成果。
1940-1948年,中國出現(xiàn)了不少評介美國小說的文章。1940年,《健康生活》第18卷第6期發(fā)表了玉棠的《美國小說家格雷的奮斗經(jīng)過》,介紹了格雷(Zane Grey)成名前的艱辛與出版處女作的曲折經(jīng)歷。1941年,《文學月報》第3卷第1號推出“美國文學專輯”,收入鐵弦的論文《關(guān)于約翰·斯丹貝克》。1943年,《時代生活》第1卷第6期發(fā)表了龍溪的《幾部新翻譯的美國小說》,評論了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人鼠之間》與《月落》和奈埃德的《高于一切》。1946年,《世界知識》第1期介紹了辛克萊及其《龍果》。1948年,秦牧的《世界文學欣賞初步》介紹了辛克萊的《屠場》和倫敦的《馬丁·伊登》與《野性的呼喚》。
1943-1949年,中國美國小說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多重要成果。1943年,《時與潮文藝》第2卷第2號推出“美國當代小說專號”,收入孫晉三的《美國當代小說專號引言》、吳景榮翻譯的《泛論美國小說——離了舊世界的桎梏》和林疑今的《當代美國問題小說》三篇論文。孫文以英國小說為參照評論了美國小說,認為后者比前者健壯,因為:
英國的小說,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和活生生的人生,已是距離漸遠,研究的對象,走向變態(tài)的人生,而不是嶄新活跳的人生,作家的注意,在技巧的實驗,而不在素材。當代英國小說,或探測到了靈魂的深處,或遨游太空,但都沒有一種“活”的感覺,一種“生”的喜悅。而這種“活”的感覺,“生”的喜悅,卻正是當代美國小說所給予我們最醒目的印象。當代的英國小說家,給讀者以一個夢幻世界的感覺,而美國小說家,卻沒有陷得這樣深,也管不了這樣多,只是寫面前有血有肉的人生。因此,美國當代小說,似乎特別的健壯。(孫晉三,1943:1)
因此,美國小說的寫實性比較突出,但“美國的寫實主義和歐洲與英國的寫實主義稍有不同,就是,舊世界的寫實主義作家只是以一種新的態(tài)度來寫舊的題材,而美國作家所寫的卻是嶄新的東西”(孫晉三,1943:3)。文章評介了美國寫實主義小說中代表“本地風光”、“赤裸裸的寫實主義”、“社會批評”和“幻滅破碎的寫實主義”的小說家及其風格。文章還認為,美國的短篇小說比英國的更為興盛,因為“短篇小說在英國只是一種次要的體裁,甚至有些‘不登大雅之堂’,似乎很少受人注意。但是,從最初,美國文學里就以短篇小說為一種主要的類型”(孫晉三,1943:5)。吳文分析了美國小說從“英國式”走向“美國的”歷史嬗變及其脫離英國小說傳統(tǒng)之后的特征,認為美國小說的“歷史雖短,但已經(jīng)與不列顛的現(xiàn)代小說并駕齊驅(qū)”(吳景榮,1943:7),其“蓬勃之氣以及創(chuàng)造性,已勝過出產(chǎn)于大不列顛或其他英語各地的小說”(吳景榮,1943:7)。林文分析了美國問題小說興盛的緣由,評介了“種族問題小說”、“政治問題小說”、“經(jīng)濟問題小說”與“社會問題小說”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認為“自從1929年經(jīng)濟大恐慌后,問題小說逐漸成為美國文學的主流”(林疑今,1943:13)。1944年,重慶新生圖書文具公司出版了胡曦翻譯的加爾·凡·多蘭的《現(xiàn)代美國的小說》,其中介紹了克萊恩、諾里斯、倫敦、歐·亨利、加蘭、德萊塞、華頓、凱瑟、辛克萊、劉易斯、安德森、沃爾夫(Thomas Wolfe)、福克納、海明威、法萊爾和賽珍珠等22位美國小說家。1946年,《西風》第67期發(fā)表了林疑今翻譯的紀德(A.Gide)的《幻想的會晤——談美國小說》①原文為法國作家紀德在美出版的《幻想的會晤》的一部分,由美國《新共和周刊》編輯Malcolm Cowley翻譯成英文,1944年2月7日發(fā)表于該刊。,該文評論了海明威、福克納、帕索斯、斯坦貝克、劉易斯、德萊塞和考德威爾等美國小說家。1947年,《新聞資料》第149期推出“美國文學專輯”,收入大衛(wèi)·鄧普賽(David Dampsey)的《現(xiàn)代美國小說及其背景》以及評介辛克萊、劉易斯、海明威、斯坦貝克、德萊塞和黑人小說家拉愛特的短文章。鄧普賽的文章分析了現(xiàn)代美國小說的特點及其產(chǎn)生背景,認為其主流是寫實主義的(鄧普賽,1947:1652),經(jīng)歷三個發(fā)展階段: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寫實主義“是記錄社會變化的現(xiàn)象、抗議一切的不平”或“嘲笑和分析富有階級”(鄧普賽,1947:1652),其代表是豪威爾斯、諾里斯、倫敦和辛克萊;1917年到1930年的寫實主義“選擇了諷刺形式的文字”,體現(xiàn)了“對于保守政治和大商業(yè)的反感”(鄧普賽,1947:1653),其代表是海明威和劉易斯;1930年以后的寫實主義是社會分析性的,是“對于社會基本問題的探討”和“對于經(jīng)濟崩潰的診斷”(鄧普賽,1947:1653),其代表是考德威爾、法萊爾和福克納。1948年,《時事評論》第1卷第24期發(fā)表了劉夔翻譯的Newton Arvin的《泛論近代美國小說家》①該文最早發(fā)表于《新聞資料》第163期(1947年),第1768-1769頁。,該文分析了二戰(zhàn)之前克萊恩、諾里斯、倫敦、德萊塞、辛克萊、劉易斯、海明威、帕索斯、法萊爾、考德威爾與斯坦貝克等小說家的“外傾主義”與“文件記錄式”自然主義特征,展望了戰(zhàn)后南方作家福克納、安·波特、韋爾蒂、麥卡勒斯、卡波特和亨利·米勒等向“內(nèi)傾主義”與“人情化了的詩化了的自然主義”發(fā)展的趨勢(Arvin,1948:13-14)。同年,《新中華》復刊第21期發(fā)表了陳東林翻譯的 Malcolm Cowley的《第二次大戰(zhàn)的美國小說》②1949年,趙景深將其譯為《美國小說與兩次世界大戰(zhàn)》,發(fā)表于《幸福》第24期,第17-21頁。,該文以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描寫“一戰(zhàn)”的小說為參照,分析了40年代末出版的描寫“二戰(zhàn)”的小說的主要特征,認為描寫“二戰(zhàn)”的小說是“反叛的、現(xiàn)實的、自然派的,同時要比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多數(shù)小說更注重形式的問題”(Cowley,1948:50-51),因為“大多數(shù)的第二次大戰(zhàn)的小說,在動作和對話上是根據(jù)海明威的;在結(jié)構(gòu)上是根據(jù)杜斯派索斯[多斯帕索斯],在氛圍上是根據(jù)菲吉勒特[菲茨杰拉德],在幽默上是根據(jù)史坦培克[斯坦貝克]。同時還有福克納和華爾夫(Wolfe)的痕跡,并且在《裸者與死者》中有法萊爾的氣息”(Cowley,1948:52)。文章說,20世紀20年代的“作家們努力創(chuàng)造美國文學的一種新的傳統(tǒng)”,但40年代末的“美國作家——包括新的戰(zhàn)爭小說作家——努力在發(fā)展已經(jīng)存在的傳統(tǒng)”(Cowley,1948:52)。1949年,《方向文輯》第1期發(fā)表了江森的《試論當代美國小說》,該文以《斯坦貝克蘇聯(lián)行》中的話——“在美國和英國,一位良好的作家是社會的守望犬。他的任務是諷刺社會的病態(tài),攻擊社會的不公,指責社會的過錯”(江森,1949:15)——為引子,認為:
美國的文學,尤其是小說,能夠在世界文學中放出燦爛的光輝,就是因為他們[它們]能大膽地描繪當代美國的真實生活,去接觸社會,體驗生活,狂喜地擁抱現(xiàn)實生活,他們看穿了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中之矛盾與病態(tài),勇敢地揭穿暴露這社會的不合理。因此美國的小說作品中都充滿著積極的背叛者。作家們更以年青的富有幻想的眼睛去觀察,夢想著一種新的改革。因此他們的寫實主義里還有著嶄新的內(nèi)含的浪漫性,這就形成了美國近代小說的基調(diào)。(江森,1949:15)
因此,當代美國小說的主流是“富有批判性的積極性的寫實主義”(江森,1949:15),其代表作家是克萊恩、諾里斯、倫敦、辛克萊、劉易斯、安德森和德萊塞,其中德萊塞是“美國近代文學的開山鼻祖、寫實主義的奠基人”(江森,1949:16)。
4.結(jié)語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相當繁榮,但不同階段的研究具有明顯不同的特點。20世紀20年代之前,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剛剛興起,雖然有一些美國小說評介,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研究。20世紀20-30年代,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呈現(xiàn)出非常繁榮的景象,既有大量的簡單評介,又有不少的深入研究;既有專題論文,又有研究專著;既有很多國內(nèi)研究成果,又有不少國外研究成果的譯介。20世紀40年代,中國的美國小說研究較前一時期略有降溫,但其研究意識卻明顯增強,簡單評介減少了,深入研究增多了,及時譯介國外研究成果也更多了。總體上講,新中國成立前中國美國小說研究有兩個突出特征:其一,研究以概論性批評為主,雖然整體評介和研究美國小說的論文和專著不少,但專門評介和研究單個小說家或單部小說的成果很少;其二,研究以“寫實主義”批評為主,主題研究較多,審美研究較少;主觀性評價較多,共識性結(jié)論較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當時的中國文藝界,特別在專搞外國文學者的圈子里,美國文學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趙家璧,1980:91-92)。
[1]Arvin,Newton.泛論近代美國小說家[J].劉夔,譯.時事評論,1948,(1)24:13-14.
[2]Cowley,Malcolm.第二次大戰(zhàn)的美國小說[J].陳東林,譯.新中華(復刊)1948,21:50-52.
[3]Moore,Harry Thornton.今日之美國小說[J].高植,譯.時事類編,1935,(3)13:78-86.
[4]Waldmand,Milton.近代美國小說之趨勢[J].趙家璧,譯.現(xiàn)代,1934,(5)1:108-115.
[5]曾虛白.美國文學 ABC[M].上海:ABC 從書社,1929.
[6]大衛(wèi)·鄧普賽.現(xiàn)代美國小說及其背景[J].新聞資料,1947,(149):1652-1654.
[7]點默.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J].協(xié)大藝文,1935(2):7-10.
[8]傅東華,于熙儉編譯.美國短篇小說集[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9]高垣松雄.美國小說的一側(cè)面[J].斐丹,譯.現(xiàn)代文學,1935(1):66-71.
[10]江森.試論當代美國小說[J].方向文輯,1949(1):14-15.
[11]林疑今.當代美國問題小說[J].時與潮文藝,1943,(2)2:13-16.
[12]沈雁冰.美國的小說[J].小說月報,1923,(14)11:1-2.
[13]孫晉三.美國當代小說專號引言[J].時與潮文藝,1943,(2)2:1-6.
[14]孫毓修.歐美小說叢談[M].上海:商務印書館,1916.
[15]吳景榮譯.泛論美國小說——離了舊世界的桎梏(原載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副刊)[J].時與潮文藝,1943,(2)2:7-12.
[16]謝天振,查明建.中國現(xiàn)代翻譯文學史:1898-1949[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
[17]楊昌溪.黑人文學[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3.
[18]挹珊.戰(zhàn)后美國小說概況[J].國聞周報,1932,(9)18:1-6.
[19]張越瑞.美利堅文學[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
[20]趙家璧.出版《美國文學叢書》的前前后后——回憶一套標志中美文化交流的叢書[J].讀書,1980(10):87-96.
[21]趙家璧.新傳統(tǒng)[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
[22]趙景深.二十年來的美國小說[J].小說月報,1929(20):1247-1251.
[23]鄭振鐸.《鄭振鐸全集》第12卷·文學大綱(三)[M].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