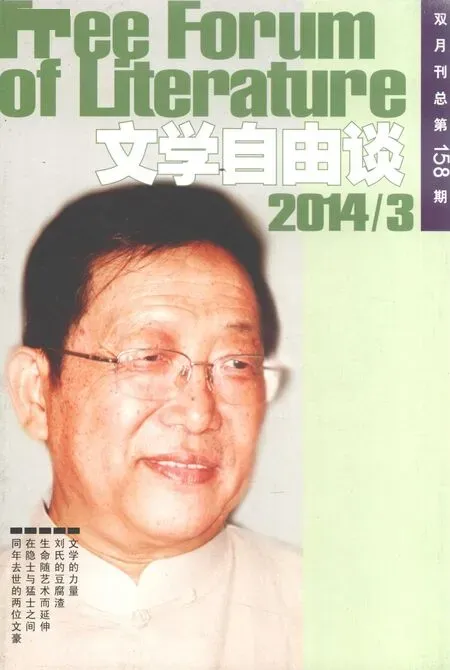好好吃飯,好好喝水
●文/陳 沖
禁不住朋友們的慫恿,終于用了兩天半的時間,把二十一集韓國電視劇《來自星星的你》,一集不拉、一段不跳地看了一遍。這種看法相當累人,可想而知不是為了休閑和娛樂,當然也說不上是鑒賞,大略說,就是一種職業閱讀吧。而我的職業是文學不是影視,所以伴隨那職業閱讀的,也只能是以文本分析為基礎的解讀,只有讀后感,沒有觀后感。即使是這個讀后感,也是圍繞著一個預先設定的目的產生的。直白地說就是,當人們都在問,為什么我們就拍不出這樣讓觀眾愛看的電視劇,而且已經有了某種答案時,我能不能也提供一個我自己的答案?
商業電視劇是大眾文化產品,看重收視率,略相當于看重銷量的通俗讀物,它的文本,自然也必須遵守那三條基本原則:故事的模式化,人物的類型化,價值取向的俗眾化。一個成功的文本,必定是既嚴格遵守了這三條基本原則,又在不違背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有所創新。這個話,說說容易,真做起來卻相當不容易。
《星星》的故事,就是個孤男寡女相鄰而居的故事。這是一個愛情浪漫劇里很常見的模式,因為它是一個很容易演化出成百上千種不同版本的模式。如果編劇想偷懶,發生這種故事的最佳環境就是中國式的大雜院,但任何事物總是會有利亦有弊,大雜院有利于為本來素不相識的孤男寡女提供更多發生交集的機會,但這樣的環境人多眼雜,會使男女主人公很難得到那種必不可少的封閉環境單獨相處。更重要的是,在這樣的大雜院里,必然會產生一種涉及較多人的群體性的人物關系,非常不利于展開只與兩個主人公有關的“純情”。《星星》的編劇走的是另一條捷徑。他讓自己的故事發生在一座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公寓樓里,這使人們猛一看會誤以為他是有意給自己出了一道難題,因為在這樣的公寓樓里,相鄰而居卻老死不相往來的事是經常發生的。然而,編劇解決這道難題的辦法其實仍然是很偷懶的——他讓其中的一位具有超能力,從而使空間的距離,墻壁的阻隔,甚至刻意加強的隔音效果,一舉化解為零,大雜院里那一墻之隔的障礙都不存在了。當然,我們的文本分析也不能抹煞編劇的巧妙之處。首先,兩位主人公的性格截然不同,都教授極其內向,而千明星非常外露,如果具有超能力的是千明星,有了也白搭。然后,編劇對這種不對稱性的利用非常有節制,應該說這一點是相當難能可貴的。在整個劇情的發展中,絲毫沒有讓我們感到兩個人的彼此了解有什么不對稱之處。一直到最后,我們也不覺得都教授對千明星的了解,比千明星對他的了解更多更深。從表面看,這是在說對人的內心的了解不是靠看見什么或聽到什么去完成的;往深處看,這正是主題思想的需要——電視劇的主題是“純情”,本質上與了解不了解無關。
中間插一段,為自己做個不得不做的辨解。我這樣地做文本分析,可能會讓您覺得很突兀,好像頭回見著似的。可是您圣明,這不賴我,因為做批評原本就應該這樣的,只是現在的有些批評家,已經失去了,或者壓根兒就沒有學會做這種最基本的文本分析的能力。越過這種最基本的文本分析直接就說某作品好得不得了或差勁得不得了,好處是說好說賴都隨意,壞處是說賴說好都沒有說服力。我不能不承認這樣做涉嫌泄漏行業機密,但我也確實認為,觀眾有權知道你那些電視劇的故事是怎么編出來的,然后才可能去追問那些不按規矩瞎編出來的故事為什么還會被拍成電視劇。當然,小說也一樣。小說的故事差不多也是這樣編出來的,只是變化更多。現在的有些小說,常可見到作者在那里不停地炫耀“現代”技巧,卻又寫不成那種完全沒有故事的先鋒小說,于是就出現了奇形和怪狀,在一些充滿“現代”技巧但又離不開故事的小說里,講的竟是一個讓人沒法往下看的故事。
話說回來,還是接著講《星星》的故事。相對于二十一集的容量,《星星》的故事稍嫌復雜了些。不在圈內的人們往往有種錯覺,以為故事復雜些才好,其實正相反,像這種不是百八十集,而是只有二三十集的電視劇,講究的是故事要簡單,情節要曲折,細節要豐富,人物關系要富于變化。《星星》在這方面做得很一般。作為故事主線的都千戀,一個大故事里面又套了兩個小故事——一個十二年前的故事,和一個四百年前的故事。這兩個小故事,一度(大略是整個劇情的前一半)讓人覺得是必不可少的,是現在時的大故事的酵母,沒有它們,就不可能有都千戀,可是到了后面,編劇又硬是把這種關系徹底否定了,直稱那兩個人的相愛是在電梯里第一次見面時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跟別的一概無關。您圣明,編劇不得不這樣做,自有他的苦衷。只有把諸如感恩、懷舊之類因素全都排除掉,都千戀才有可能成為一個“純情”故事。至于作為故事副線的那個系列犯罪案件,真有點讓人不知道說什么好。從效果反推,都千戀本身真是沒有多少能抓人的故事,它的幾次轉折,都帶有明顯的人為痕跡,而且來回重復,說白了就是這個熱時那個冷,這個冷了那個又熱了,而弄到最后,兩個人的冷又都是假冷——內熱外冷。那么,我們就有理由猜想,當編劇意識到沒有足夠的想象力把這對孤男寡女的故事編出足夠多的花樣時,就不得不在“相鄰而居”的模式之外,再套上一個“英雄救美”的模式。您不難發現,當都教授和千明星之間的故事不再有來自自身的理由推動其往下發展時,就會有一只魔爪伸向千明星。也真難為了編劇,這魔爪既要來得是時候,還要來得是地方,所以那個犯罪案件也就不能太簡單。但是,是不是非得像現在這樣復雜呢?故事復雜了,就無法三言兩語講明白。因為怕觀眾不明白,竟然出現了同一片段在劇中多次出現的做法。盡管如此,這個犯罪故事還是講得很生硬,不少地方采取的就是“愛信不信,就這樣了”的辦法。
再說人物。《星星》的人物都是類型化的,一望可知,不須多說。好人,壞人,不好不壞的人,亦好亦壞的人,很難說是好人還是壞人的人,都明擺在那兒。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文藝作品中只有好人和壞人,還有一種叫“中間人物”的,屬于好壞兩種人都在爭取的對象,當然最后多半會被好人爭取過來,成為“團結對象”。但這種人無論怎么弄也成不了好人,所以只能站在舞臺的邊邊上,稍微往中間靠了一點,就有被批為“中間人物論”的危險。這樣一來,上面說到的后三種類型,好像就成了“圓形人物”了,其實不是的,它們同樣是類型人物。在《星星》里,這后三種類型的人物多一些,即便算不上大優點,畢竟為作品增加了厚度,給故事增添了張力。編劇在這方面最值得稱道的,還是幾個主要、重要人物,在類型化的前提下,寫得很有個性。其中處理得最好的,是千明星。這個好人身上同時又有很多、很嚴重的缺點,這種缺點嚴重到這種程度,而且如此張揚地表現出來,而最后的效果,不僅不招人討厭,還讓人覺得挺可愛,確實是有難度的。當然這也與演員的出色表演分不開。相比之下,同為藝人的劉世美,也有同樣的缺點,沒那么嚴重,更沒有那么張揚地表現出來,但是卻成了這個亦好亦壞類型的壞的一面。由此可見編劇的駕馭能力。這個人物也很“純情”,“純”得不含任何雜念,且一往情深,但是卻成不了“純情”故事的主人公,這就是類型化的人物在模式化的故事里的必然命運。
文本分析至此,我們對這部電視劇應該已經有了一個基本的估價。當然,鑒于它的巨大成功已是不爭的事實,我們對它的優點長處已經無須多說,所以對不足之處說得多些。合在一起整體來看,這是一個不錯的文本,但遠不完美。那么,以偌大之中國,難道就沒有能把故事編到同樣水平,把人物寫到同樣水平的編劇嗎?當然不是。要找一百個可能不容易,要找三二十個應該不難。那么,問題應該就出在價值取向上了。
一位領導同志就是這樣說的。他閑閑的一句話,實際上狠狠地將了所有電視劇的從業者和管理者一軍。他說:“韓劇走在咱們前頭。韓劇內核和靈魂,恰恰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升華,是用電視劇宣傳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個話一針見血,但終究簡略了些,而咱們中國人里恰恰盛產一種聰明人,特別擅長于在領導者的簡略之處,手腳麻利地塞進自己的私貨。“中國的傳統文化”指什么?“升華”又是什么概念?很快便有人來做這道填空題了。我隨手舉一個例子。就在王岐山說這話之后沒兩天,一位被冠以“電視觀察人、劇評家”頭銜的人士說:“(韓劇)始終有很多反映中華傳統文化痕跡的地方,像韓國人特別重視長幼有序,韓劇中就不止一次地對這種傳統文化進行強調。而在國內影視劇中,一些雷劇不講究禮儀傳統,簡直是一群穿著古裝的現代人,這正說明傳統文化已經不是要靠電視劇來傳承的問題,而是這些優秀的傳統在我們創作者心里,所剩無幾。”這位“觀察人”顯然沒有觀察到,中國在雷劇之外還有正劇,在一些表現好皇帝如何愛民如子的歷史正劇里,大臣見皇帝時如何叩拜,小官見大官時如何行禮,都做得很合規制,如果你照著去做,是不會學錯的。當然里面偶爾也有穿幫的時候,例如張嘴就說“到我府上”如何如何。可是這會造成多么嚴重的后果嗎?穿著今裝的當代人遇到類似情況,說句“請到我家談談”就很失禮嗎?非得說“還請枉駕光臨寒舍一敘”才行嗎?
老實說,我在想這件事兒時,真是十分地糾結,十二分地困惑。小說不行,也就罷了。我們的小說在價值取向上有問題,那是因為我們的多數作家思想資源不夠豐厚,精神資源嚴重短缺。好在讀者都明白,現在的中國,并不是出大思想家的時代,真出了,大家未必就喜歡。可是電視劇是大眾文化,它的價值取向要的本來就是個“俗眾化”呀,這有什么難的?所謂的俗眾化,無非就是絕大多數平民百姓都能接受的東西,日常生活中已經存在東西,說白了,就是它不能玩什么現代、先鋒、前衛、另類、邊緣那一套,只能是傳統的——嚴格地講,還得是傾向于保守的。而且,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分界線,過了界,就不再“大眾”而會變成“小眾”了。難道我們的國產劇是因為玩小眾化才被韓劇“走在前頭”了?
在《星星》的最后一集,都教授在與千明星告別(這一去很可能成為永訣)的時候,給她下達的最后指令是什么?是“不要穿暴露太多的衣服”,“吻戲,背后擁抱戲,這種絕對不行,激情戲,不行”。這話猛一聽真讓人忍不住啞然失笑——這位外星人真是迂腐得夠可以的了。然而,這正是此劇對“傾向于保守”的價值取向的堅守。對于大多數平民百姓來說,別人的老婆怎么樣我管不著,我老婆做這種“絕對不行”。前面還出現過類似的話題,談到吻戲、背后擁抱戲,都教授的建議是“用替身”。替身也是女人呀,但那是別人的老婆。
相比之下,我想起了我們的電游廣告。我從不玩電游,但只要上網,想不看電游廣告絕無可能。看來看去,發現眾多的女俠原來只有一種造型。雖然頂著沉重的頭盔,穿著厚厚的鎧甲,但脖子以下卻必須露出來,裸露的下緣則以“不露點”為限,而且這對一邊各露出多半個的“美胸”必定異常飽滿,其鼓脹的程度也以解剖學的極限為界。她們的腳上穿著高可及膝的長靴,非常穩妥地保護著小腿,但大腿一定是裸露著的——當然是一雙“美腿”。很明顯,女俠們獲得這樣的造型,并不是因為她們的脖子以下或膝蓋以下練過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可以刀槍不入,而是因為制作者們認為潛在的購買者們喜歡這個。真是這樣嗎?看來還真是這樣。不過我仍然有個困惑:到底是因為買家喜歡,這種東西才多起來,還是因為全是這種東西,買家想不喜歡都不可能?畢竟電游里玩的還是打打殺殺,不是襲胸摸腿。這個“掃黃打非”都管不著的灰色地帶,是否有人守土有責?
人們通常把這類情形稱為“社會風氣”。“風”和“氣”都是某種看不見、摸不著但能感覺到的東西,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它好像是“無形中”形成的,是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共同參與的結果,但實際上社會的管理者的作用遠遠大于被管理者的作用,尤其是管理者經常強勢介入的時候。由于現實社會生活的復雜性,管理者介入后所得到的結果,并不一定符合其介入時的初衷。比如“勵志”原本是好事,但是在社會不能給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時,就很可能導致過度競爭和不道德競爭。
但是,至少從直接的因果關系看,這類情況本不應造成拍不出好電視劇的結果。一個很“低級”的問題是:當下中國的電視劇從業者,經常受到的指責恰好有三條,太想賺錢,太看重收視率,又太能跟風,那么,眼見得《星星》那么賺錢那么走紅,為什么不跟著拍幾個呢?我們的編、導、演不缺“大腕”,實際水平也真是不低,比不上美國,起碼不次于韓國。可見問題不是拍不了,而是不去拍。這又是為什么呢?
我們在前面的文本分析中已經分析出一個階段性結論:《星星》里講的不是愛情,是“純情”。那么,如果我們也來拍一部“純情”劇行不行?您圣明——不行。不是說拍了以后必定通不過審查,好像此前也沒有這種案例,而是說我們的制作者們自己就覺得不行。這也是一種“風”或“氣”吧,大家就是這么一種“思想”,而實際上這種“思想”也是“正確”的,因為但凡有點“思想”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純情”這種東西,沒有無緣無故的什么都不為的愛,連魯老都說愛總得有所附麗。假如我們做一番更透徹的文本分析,完全不被制作者們的煽情牽著鼻子走,其實很容易看出,《星星》里的都千戀相當地“不真實”、“不可信”。我愿意如實供述我在觀劇過程中有過的一些猜想。當張律師向都教授報告為他清理資產的情況時,我們了解到都教授身家豐厚。這當然不僅是為了說明他為什么會住上這么好的房子。按通常的編故事的規矩,你在前面提到了有一筆錢,那么后面這筆錢就應該花出去。所以,到了都教授變成了都經紀人,在拍攝現場親眼目睹了他心愛的千明星怎樣被導演折騰,我想花這筆錢的時候到了。以此為基礎,幫千明星實現東山再起,最起碼也會有個相愛的人共同奮斗的勵志效果吧?可是根本沒有這種事兒!那錯過了這個機會,這個都千戀里真是一點兒正能量都沒有了。
我們怎么能拍一部不傳播正能量的電視劇呢?
可是,“韓劇內核和靈魂,恰恰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升華”,難道這不是“正能量”嗎?這不恰恰是很大、或許還是最大的正能量嗎?“正能量”這個詞語是不久以前才出現的,但它的意思,或者說其所指,并不是憑空而來的。在此之前,我們一直都在提倡同樣的或近似的東西,只不過表述的方式有所不同,從積極向上,健康樂觀,向善向美,愛黨愛國,直到“緊緊圍繞”什么什么。這些都很對。不過我覺得我們的“思想”或許還可以更開闊一些,更寬泛一些。我們每天都要吃飯喝水,從而獲得必不可少的能量。這當中要緊的是好好吃好好喝,不一定非得精細計算一個饅頭一碗米飯中含有多少正卡路里或負卡路里。一杯純凈水——類似于“純情”劇的純凈水吧,里面也并不是什么都沒有的。
“星星”說了些什么?好好吃飯,好好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