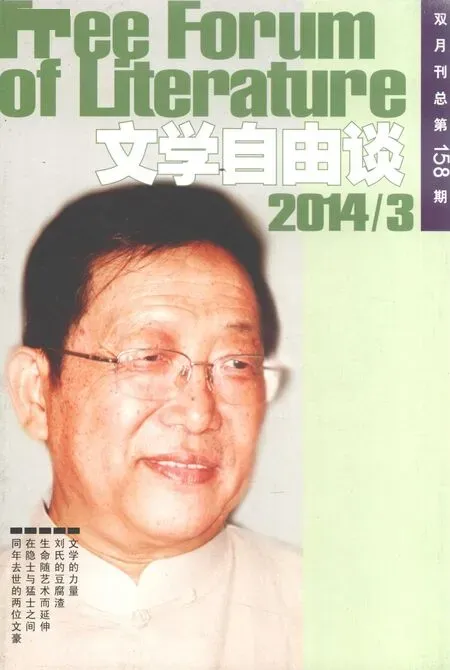山外的青山(外一章)
●文/任芙康
龍山腳下,步入國恩寺,一進一進的院子,緣山套建。且走且看,有種緩緩上攀的感覺。巧合心中所愿的是,香客稀疏,或一二作伴,或三五成行。細水長流般的進香,虔誠而散淡,接續著大殿小殿的輕煙繚繞。
數十年間,曾入廟無數。眼見眾多大牌名剎,生意興隆,尤如街市。絡繹的信眾,讓人行走不順;鼎盛的香燭,使人呼吸不勻;如縷的梵音,令人耳根不靜。如此佛門之旅,往往淺嘗輒止,先自出寺,坐候同伴。到了如今一把年紀,落得個似是而非,常將一些佛家常識,在心中張冠李戴。好在尚能自律,進寺入廟,當會棄絕職業習性,從不多嘴多舌,妄加點評。故而吾雖愚笨,與佛甚遠,隔著無望的高墻;又仿若與佛很近,橫著可視的柵欄。一位相識相知的朋友,自小修行佛法,心得非凡。但恰如俗語所講,彼此只有塵緣,并無佛緣。天馬行空的閑聊,從不牽涉佛事。她是聰明,知道夏蟲不可語冰;我亦不呆,明白班門切忌弄斧。但納悶終究還是有的。常遇某些修身君子,聽其言,高潔清雅,滿嘴隨遇而安;觀其行,自相抵牾,稍有失意,便視為三災八難,訴諸焚香期許。這般心思,落空居多。最終祈福未果,豈不舊恙未除,又添新疾?
聽事先安排,將與住持會面。那位佛道精深的方丈,會為我們講述國恩寺的前世今生,并備有已然“開光”的念珠相贈。因手頭握有此廟簡介,素來浮光掠影的毛病,讓我依舊脫隊獨行。
繼續上走,置身于一片意外的素樸。以往進過的寺廟,多會在氣象森嚴的“大”中,露出煞有介事的“小”來。然此處迥異。俗名喚作慧能的一位少年,成為法名仍叫慧能(佛門罕見)的一位高僧。“高”到何等程度?被供奉至禪宗六祖的圣位。其《六祖壇經》,弘揚人人平等,毛澤東贊譽為“百姓的佛經”。在此之前一千三百年,唐朝女皇武則天,亦有先見之明,御筆賜題匾額。如此皇恩浩蕩,堪屬頂級包裝,國恩寺遂為華廈唯一“國”字號寺廟。寬厚仁愛的慧能,建廟選址,無意掠取他人地盤,奠基在自家故居。廟后坡上,壘有他父母的墳塋。一箭之遙,活著他親手栽下的荔枝。由高處下望,竹木中隱現的屋宇,儼若嶺南民居。輕霧飄忽,仿佛戶戶農舍正啟灶煮飯,裊裊炊煙中,亦有慧能家的幾縷……身邊一草一木,寵幸于六祖的浸潤;眼前一石一瓦,福延著慧能的庇佑。寺廟建而毀,毀而擴,終至眼前規模。古往今來的香客,歷朝歷代的政府,均有貢獻與建樹。同國恩寺相比,輕而易舉就被比下去的,恰是許多虛張聲勢的寺廟,敘說來龍去脈,擅長天花亂墜,而真實、可信的人文脈落,則往往虛無縹緲。
慧能業績光耀千秋,史書記載及民間口碑,皆已洋洋大觀;更有當今學者,殫精竭慮,挖掘新礦無數。而我陋習難改,不肯盡信其真,亦不會全視其偽。環顧龍山四周,山護著水,水繞著山,竟是我自幼習見的南地風物。驚喜之余,放膽揣度,千八百年前的貧鄉僻壤。只要不是土財家的惡少,農家子女的終日功課,不是上山放牛、打柴,便是下河浣衣、洗菜。誕生于斯的慧能,倚重鄉鄰、報孝父母,當屬情理之內。在外弘法多年,暮歲落葉歸根,圓寂于斯,亦非偶然,實有必然之因。六祖的博大,就在于他超常的平易。篤志經學,常行農耕之事;善待信眾,從無欺瞞之心。看如今某些僧侶,袈裟雖裹身,言行卻飄忽。逸出佛門的參禪悟道,盡管裝模作樣,終是裝神弄鬼,引人“普度”之徑,無異夜路一條。何時見天明,只有鬼知道。
因平日循左而行的習慣,進寺出寺,一上一下,方向正相反,等同又逛一座新廟。就在最后一層院子,忽覺廂房有異,好奇中湊近望去,竟是一幅難以置信的景象。返回賓館,幾位見了住持、喜獲佛珠的旅友,原本面露炫意,但聽罷我“最后一瞥”的稀奇,莫不詫異至極,嘖嘖驚羨任某的“獨具只眼”。
且說那間窗欞之內的廂房,大約兩丈見方。首先入眼一屋老嫗,且多在古稀以外。十來位圍坐一桌,大方桌有七張之多。桌面堆積出小山般的錢幣。定晴細瞧,既有伍拾圓、壹佰圓的大鈔,更多是拾圓、伍圓、壹圓乃至伍角、壹角的毛票。佛樂舒緩的陪伴中,老人們的工作,就是將這些面額不等的善款,分門別類,碼齊,點清,再包扎成捆。
我趴在木格窗前,一時有些出神,想不出用什么端莊、隆重的字眼,形容眼前陌生的場面。七十來位老人家,濟濟一堂,平心靜氣地勞作著,動作熟諳,顯然都是常來幫忙的義工。恍惚間,一位老婦對我頷首微笑。心跳頓覺加快,滿頭銀發、一臉慈祥的老人,竟酷似我三年前尚健在的母親。就連動作都像。大媽笑笑,好似打過招呼,又埋頭干活兒。我媽亦如此,兒子跟前,常以微笑替代說話,然后繼續她手中的事情。
國恩寺座落于粵西云浮市境內。離別龍山,起程云游云浮。一連數日,飽覽山連山、山套山的青山。目光所及,無一座梁是荒梁,無一道嶺是禿嶺,無一條河是枯河。薄霧如紗中,無處不在的參天古木,皆是生機蓬勃的“文物”;清風拂面中,村村鎮鎮的古舊建筑,皆是沉郁豐厚的“史書”;秋陽暖身中,數量眾多的百歲壽星,皆是四季錦繡的“人證”。你仰望一棵棵樹齡兩百年、六百年、一千年的香樟、榕樹、荔枝、紅椿、芒果樹、紅豆杉、菩提樹,你穿行一幢幢一百年至七百年間的祠堂、文廟、書院、民居、莊園、炮樓,你挨近一位位清末民初降生于世的安恬、健康、整潔、天真的人瑞……內心浮現高低錯落的顫動,是往昔不曾有過的蕩漾。禪意氤氳,無須刻意營造,這方山水,最是福地洞天。
此番南下之際,我定居的北國,依遵天意,已開始鋪展今冬的水瘦山寒。青山層疊、田疇蒼翠的仙境,雖無福久留,并無遺憾。有得十天半月的清爽、喜悅,已是緣分不淺。朋友相邀的恩惠,自會銘記于心。阿彌陀佛。
2013年11月
舞蹈的懸念
一個頂呱呱的男人,一個好端端的女人,明目張膽,或是偷偷摸摸,進過幾次舞廳,就跳出“不好”的事情來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風水,盛產有關舞場的懸疑故事。尋常的三步、四步,幻化為妖步、狐步,像刀尖上翻轉,又如懸崖邊騰挪。肚皮舞、貼面舞之類,則直通通與高危行為劃上等號。舞蹈本身的屬性,皆被忽略不計,一些伙計津津樂道的,只是空穴來風。兩口子同床異夢,因為跳了;年輕人破罐破摔,因為跳了;老家伙晚節不保,因為跳了……時間、地點、人物、情節,成龍配套,曲里拐彎,有鼻子有眼兒。
一位朋友,迷上跳舞,且只認拉丁。她住美國,從這個州跳到那個州。她去西歐,從倫敦跳到巴黎。回到中國,陀螺般轉戰北京、上海、廣州,會合同道,切蹉技藝。舞者之組合,明白無誤的雇傭關系。通常是有錢有閑的女性中老年做學徒,有藝有貌的年輕小伙子當師傅。虔誠的學徒,一旦上癮,成為生活中的依賴,碰上異地交流、競賽,常會心甘情愿地額外破費,為師傅置辦行頭,包攬旅費。而師傅享有的種種“孝敬”,因由言傳身教的勞動換得,往往受之坦然。朋友曾帶我們實地見識,挑逗而狂放無羈的音樂中,親昵而不可省略的動作中,默契的師徒,舉手投足皆心領神會。但又確乎看不出曖昧與纏綿,看不出誘惑與欲念。散場時分,彼此“拜拜”,扭頭上車,絕塵而去。此種玩法,綿延中外,定有大堆合理之處。但仍有人較真:“我就不信,拉拉扯扯的拉丁,不是姐弟情、師生戀的溫床?”是怎樣,不是又怎樣?單一、武斷的結論往往隔靴搔癢。我不接茬,因這類話題,并非關注所在,最多只是舞蹈帶給生活的懸念。
八年前的五月下旬,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看過紀念舞蹈家米肖爾·佛肯的專場。其中一個章節《輕盈的少女》,誠如舞名,悅目之至。尤物滿臺,輕盈一片,行云流水般變幻出急而高的躍起,輕而穩的落地。目睹過國內同類演出,幾乎多半演員讓人捏把汗的,恰是躍起與落地。終究是舞盲,瞧過熱鬧,漸生疲憊。忽覺周圍出現似有若無的騷動,細看臺上,一位中國姑娘,正居中領舞,一招一式,技壓群芳,盡顯東方柔韌、靜美的內斂,揮灑出同場舞伴難以企及的玄妙。天鵝中飛出金鳳凰的壓軸安排,堪屬顛覆觀眾意料的“包袱”。但此刻提起這段往事,仍舊不屬于舞蹈本身的懸念。
言歸正題吧。清風明月的某晚,走進本市某劇場的舞蹈晚會。落座之后,學習節目單。一行行讀下去,駐目于三個字上。演出過半,終于輪到《青花瓷》。大幕啟開,一個花容月貌的集體,神采奕奕地組合出一尊青花巨瓶。聞聽鄰座幾許驚嘆,不由得生出惋惜,并心下預測,眼前造型必定迅速碎開,歷經一通起承轉合,又重新合攏,恢復原狀,然后收官。接下來的流程,果不其然。但觀眾的新鮮,已提前支付,禮貌的鼓掌,帶出勉強之相。假設,以我外行的想法,避免先聲奪人,服飾一色土素,每個演員自成飄飛的精靈,再有多番分合散聚的回環起舞,宛若陶器制作的揉搓。待到盡興、盡情之際,借助燈光切換,倏忽間眾姑娘青花衫著身,凝固成有形有神的成品……猜想滿堂掌聲,一定經久不息。因為此時的看客,使勁拍手,不是展現教養,而是表達驚喜。
懸念是諸般藝術的支撐。上來就辟出一條岔路,讓人墜入興趣,往下的進展,難以推知,終局的模樣,更無跡可尋,這就叫引人入勝。單說眾多耳熟能詳的舞劇,從皮到瓤,盡管了然于心,人們仍常看不厭,并自欺欺人地“不曉得”尾聲。除了著迷其音樂、布景,著迷其僅靠身體,便能無聲敘說世間的喜怒哀樂,發燒友們享受的(或曰緬懷的),一定還有經典行進過程中,那份非凡的懸念。敞開了說,琢磨藝術的人,輕忽懸念,便近似職業的誤會。無論編舞、編歌、編相聲、編雜技、編戲劇、編影視,甚至包括照相、畫畫、寫毛筆字,如果置懸念于不顧,便會以咫尺天涯的距離,表明閣下,可能入錯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