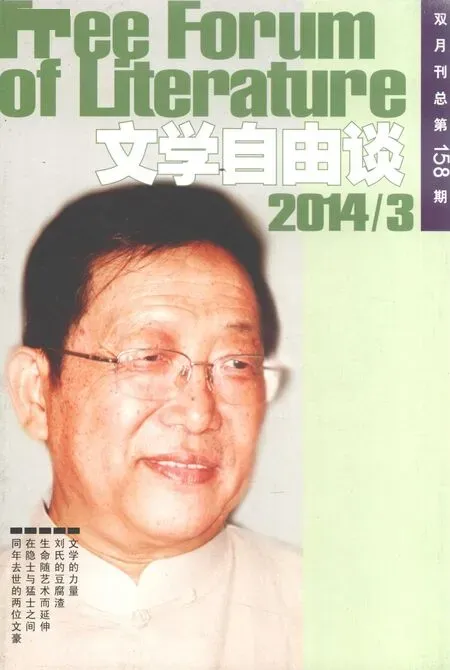蓋棺論定亦不遲
●文/曾紀鑫
這種勸人向善的文章,乃老生常談,本刊其實不愿選用。多數時候,大師等同于騙子。凡欺世盜名得逞于一時者,途徑有三,自己吹出來,機構寵出來,眾生慣出來。大師都命硬,野火燒不盡,邪風吹又生;大師都命薄,夜來風雨聲,泡沫破多少?
·責 編·
“大師”一詞,到處聽到,我是一個不喜湊熱鬧的人,但生活中的兩件事,使我不得不拿起筆來,也來蹚蹚大師這股“渾水”。
第一件,我在編輯一篇稿件時,作者將所寫之人稱為工藝美術大師,于是便跟作者交流商量:是不是可以低調一點,不要隨意命名大師?作者回道:“他可是真正的大師呵,國家頒發了證書的!”大師還有證書?我在網上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驚一跳,這一評審中國工藝美術大師的活動不僅早就開始了,并且弄得風生水起,搞了好幾屆呢。看來我等井底之蛙,實在孤陋寡聞。
再一件,寫作圈中的朋友踫到一塊,大家會互稱大師,比如傅大師、吳大師、張大師、何大師之類,相互調侃,活躍氣氛,以增添一點人生的樂趣。沒想到有人卻當了真,人家叫他大師,他居然“真誠”地聲叫聲應,一時讓人無話可說。
一方面是大師的分量,在許多人眼里是十分神圣的;另一方面是大師的貶值,不管是人是鬼,都可通過各種手段弄一個“大師”的稱號自慰,以至大師“滿天飛”,成為調侃打趣的“味精”。甚至有人撰文說“大師”淪落被毀如同“小姐”一詞,還有人說你想罵對方的話干脆就稱他“大師”。
原本高貴、高雅之物,何以貶得一錢不值甚至走向負面?不外乎兩種情形:一是多且濫。比如詩人、老板、經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風光之時,有人戲言一片樹葉落在大街上,總能“砸”到幾位詩人,后來是一片樹葉掉下來就能“砸”到幾位經理或老板;二是價值錯位,稱呼沒變,而以前所承載的內涵卻變遷移位,由高貴變得庸俗、低俗乃至丑陋。比如小姐一詞便是,以致有人稱呼一聲小姐后,一位男子竟以對方辱罵自己女朋友為由持刀殺人。
現實生活,往往比小說更為荒誕。因為小說無論怎么虛構,作者總得遵循一定的內在邏輯規律,而現實生活則可以穿越超越、毫不講理地亂來一氣。然而,不論現實如何演變,社會如何發展,時代如何變遷,真正的大師,在我等內心深處的地位,是高貴神圣而令人仰慕的。
那么,真正的大師,到底該是一種怎樣的范兒呢?要想描摹大師的本來面目,先得說說大師的“不是”,以洞穿那些所謂的大師嘴臉。
真正的大師不是自封的,也不是炒作、吹噓出來的。凡跳竄出來的大師,都可疑。
大師不是某種職業,與老師、導師、技師、牧師、法師等有著本質的區別。
大師不能以學位職稱、職位崗位來衡量,無法用數量、指標來界定。高職稱高學歷高職位者,不一定就是大師。某一職位、職稱、學位空缺,很快就可填補,而某一大師的離去,留下的也許就是一片永遠無法彌補的空白。
大師不是某些部門機構、專家評委能夠評定授予的。誰也別以為拿著一張證書就是真正的大師。大師自然生成,無法評選。只要想想那些受頒 “大師”稱號的學者或藝術家站成一排或幾排,在不停閃爍的鎂光燈下從顯赫要員手中接過證書或獎牌、獎杯時那副受寵若驚、誠惶誠恐的樣子,就感到頗有幾分滑稽,就覺得此等舉動是在有意貶低“大師”這一稱號。
大師不是“心靈雞湯”。靠一點蠱惑人心的小聰明贏得無數“粉絲”,賺取激情與眼淚,離真正的大師,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之遙。
大師不能貼標簽,也不用貼標簽。別人稱呼是一回事,而自己坦然接受,明碼標示,性質就不同了,至少修煉尚不到家。一旦貼上大師標簽,別人就有了一種敬畏與期待,如果一個動作、表情、細節與人們心中的大師形象不符,那不是自找麻煩給自己難堪嗎?連藏拙都不懂,還算什么大師?
大師不介入權勢,不沾染銅臭,不爭名奪利,不炫耀不夸飾不自我。
大師不裝腔作勢,不拿捏擺譜,始終保持純真質樸的本色。
那么,真正的大師又該是怎樣的呢?首先引用兩位大師論大師的名言,現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錢穆說:“大師者,乃是通方之學,超乎各部專門之上而會通其全部之大義者是也。”法國著名作家、思想家羅曼·羅蘭說:“大師是心靈的偉人,是一支震撼靈魂的歌,是一道破窗而入的陽光,是死水中的一股波濤,是市儈侏儒中的一個巨人。”
據此,我們不妨稍加體會,便可得出真正大師的應有之義。
大師是天才,思維超人,不拘一格。人與人之間,其實是有很大區別的,天才是一種客觀存在,你不承認也得承認。若沒有天份,哪怕再刻苦再勤奮再努力,別說大師,連行當的門檻也難以進入。
大師是創新、創造性人才。大師靠成就說話,如果落入前人窠臼,業績千篇一律,缺乏開創性質,則連大師最起碼的質地也不具備。大師特別有創造力,能拓出一片新的氣象,開出一片新的天地。
大師是開宗立派的人物。當今學科越分越細,最起碼也得是某一領域的專家權威,學科帶頭人。當然,僅有此點是不夠的,大師之所以成為大師,在于能夠超越具體的學科之上,具有全局性眼光,能夠綜合多門學科,融會古今中西,在理論、方法、實踐等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與成就。
大師具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擁有無畏的勇氣與信心,為了真善美,不懼任何權力與壓力,不惜舍棄自身的一切。
大師除了專業成就,必須接地氣,心系民眾,關注公共領域,關心國家社會,具有相當的責任、使命與擔當。
大師是時代的高峰。大師與時代互動,不同的時代土壤,造就不同的大師。大師在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所體現出來的精神與風骨,能夠引領時代潮流,并成為后代繼承的傳統。
大師是一個坐標,是一種象征,是鳳毛麟角的精英,是道德的風范、時代的楷模、學習的榜樣。大師的學術貢獻、藝術成就、思想境界、人格魅力具有示范意義,達到高山仰止的程度。
大師之“大”,顯然與“小”相反。大師須具備正大光明、大度大氣、宏大博大等品格,如果小人小氣、官里官氣、銅臭俗氣的人妄稱大師,只會讓人笑話。
大師須蓋棺論定。一個人是否真正的大師,得經過時間的沉淀與歷史的檢驗。因此,大師不要隨便稱呼,最好不要生前稱呼。
就大師本身而言,應該內心坦蕩、虛懷若谷,不可自我招搖,不必炫耀似的讓人稱為大師,更不會以大師自居。
當下被人稱得最多的似乎是佛教界的一位大師。剛開始在報刊上見其法名后面加有“大師”后綴,以為是信眾、記者所為;后來發現其演講、訪談之時也被人稱為大師,便知得到了他本人的首肯;再后來,見其所有出版的書籍,都要在法名后標注“大師”二字。出版物中類似貼有大師標簽的作者少之又少,哪怕外文翻譯過來的書也沒有,比如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黑格爾、愛因斯坦這些人類的驕傲,足以稱得上大師的作者,也沒有特別標注“大師”二字。對于這位法師所取得的成就,所著書籍的價值,以及能否稱為大師,在此姑且不論,即以佛教界而言,如弘一(李叔同)這樣真正的大師,人們稱得最多的也只是弘一法師。再看那些佛教著作,哪怕流傳千百年的經典,作者要么直署法名,要么在法名之后加上“法師”或“禪師”。即以中國唯一稱為佛經的《壇經》為例,著者也就“慧能”二字,從未署名“慧能大師”。莫非慧能算不上大師?非也!只能說明真正的大師是十分謙遜的,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真大師是不須專門注明“大師”二字的。
在此之所以特別提及這位法師,是擔心此風一開,善于模仿的國人仿效不已,泛濫成災——所出之書,著者爭相標示“大師”這一后綴,于我等喜歡讀書的人來說,將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寫到這里,不禁想到被人稱為“國學大師”、“學術界泰斗”、“國寶”的季羨林,在《病榻雜記》一書中,他對這三頂桂冠一一“請辭”。于“國學大師”這一頭銜,他寫道:“環顧左右,朋友中國學基礎勝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竟獨占‘國學大師’的尊號,豈不折煞老身!我連‘國學小師’都不夠,遑論‘大師’!”
這,才是一個飽學之士應有的風范!
當然,大師是有一定相對性的,所謂“矮子里面拔長子”是也,“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是也。
當下時代,大師陷入尷尬的“悖論”之中,一方面是大師泛濫,什么國學大師、美術大師、工藝大師、中醫大師、養生大師、氣功大師、風水大師、成功學大師等多如牛毛;形形色色的大師充斥于世,說明我們這個時代患上了“大師饑渴癥”,這便是大師悖論的另一方面——真正的大師嚴重匱乏!
四處招搖的大師,說到底,不過一些偽大師、假大師而已。假大師何以泛濫?自然與國民素質、時代環境、歷史傳統密不可分。
官場腐敗,學術腐敗,出偽大師;當事人汲汲于名利,自我認可,出假大師;后生急功近利,為提高身份妄稱老師、導師、師傅為大師,自己便以“大師弟子”、“大師傳人”自居,出半吊子大師;后現代解構一切,大師也在其列,便成調侃之語、罵人之詞……
其實,鑒別假大師、偽大師并不難,只要以大師的“是”與“不是”稍加比照,就可將其外衣戳穿;難的是真正的大師極度匱乏,社會與時代該如何呼喚,使之于蕓蕓眾生中脫穎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