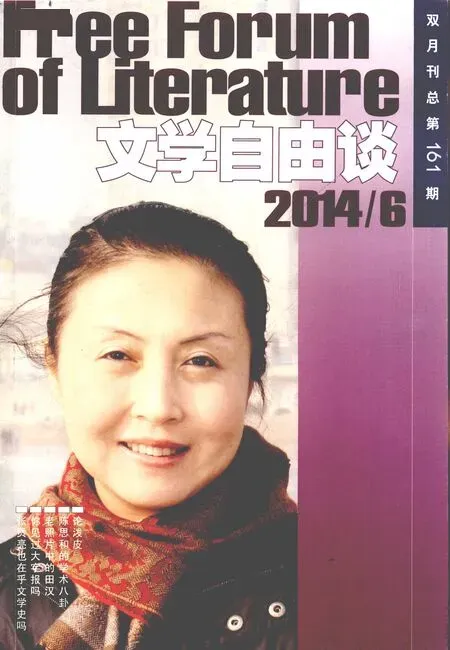徐遲先生紀事
●文/劉益善
徐遲先生紀事
●文/劉益善
徐遲先生1914年10月15生于浙江南潯,1996年12月13日逝于武漢,今年是他的百年誕辰紀念。我有幸與先生在同一單位供職多年,并有多次親密相隨聆聽教誨的機遇,受益終生。這里挑選兩件與先生有關的事情寫出,以示紀念。
這兩件事都發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
夜訪創作室事件
我將這件事說成事件,是因為湖北文藝界在“文革”后期發生這樣的事,確實是一件不小的事。我的日記記載,1976年5月29日晚上,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到湖北省文藝創作室看望徐遲與黃聲孝,我和沈毅參與接待。
朱洪霞原為武漢重型機床廠工人,時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省總工會副主任;夏邦銀原為漢陽軋鋼廠工人,時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中共中央九屆、十屆中央委員;胡厚民原為武漢鑄鋼廠工人,時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常委、省總工會副主任。這三個當時的顯赫人物,沒與省文化局與省文藝創作室兩級領導打招呼,夜訪徐遲與黃聲孝,是要干什么呢?
黃聲孝是宜昌港務局的碼頭工人,也是著名的工人詩人。他寫的“我是一個裝卸工,萬里長江顯威風,左手搬來上海市,右手送走重慶城”是名句,當時的革命樣板戲《海港》中有兩句唱詞“裝卸工,左手高舉萬擔糧,右手托起千噸鋼”,應是蹈襲他的詩句。徐遲在六十年代就親自輔導過黃聲孝寫詩。黃聲孝的文化水平不高,他的詩句有氣魄有奇想,將這些如珍珠般的詩句用蠶豆大的字寫在一張大紙上,得靠別人幫他用線串起來。1962年1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黃聲孝的長篇敘事詩《站起來了的長江主人》,這是徐遲與他一起謀篇布局,告訴他如何用詩句寫人物,如何結構,如何抒情而寫成的。長詩的封面題目,是徐遲親自題寫的。那是徐遲特有的書法,雋秀而柔韌。黃聲孝在“文革”期間,被一些人利用,經常在報紙副刊上發表詩歌,配合形勢,頗有影響。其實黃聲孝當時的許多詩歌,是編輯給他打電話,讓黃聲孝在電話里說幾句,編輯就幫他寫成了,重要的是借“工人詩人黃聲笑”(“文革”中黃聲孝曾更名黃聲笑)這個名頭。后來黃聲孝調到長航創作組,住在漢口的長航招待所,那些要借用他名字來發揮戰斗作用的報刊就更方便了,到招待所給他打個招呼,第二天報紙上就能見到“工人詩人黃聲笑”的詩了。
“文革”開始后,文聯作協遭到解散,人員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1973年,在武昌紫陽路215號掛起了湖北省文藝創作室的牌子。創作室陸續從干校調回一些文藝干部,有《湖北文藝》編輯部,即“文革”前的《長江文藝》編輯部的;有音樂組,即“文革”前的音樂家協會;有美術組,即“文革”前的美術家協會;還有文學組,即文革前的專業作家。創作室相當于“文革”前的文聯,但級別是縣團級,隸屬于省文化局領導。徐遲在“文革”開始后就全家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到他年屆六十歲時,有關部門通知他退休,但后來他又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到湖北省文藝創作室上班。他不知道這是什么原因,但是他高興。
武昌紫陽路215號是個很小的院子,院子里有前后兩幢樓,前幢樓兩層,一正樓帶兩廂樓,呈U字形,辦公;后幢樓三層,住人。徐遲到創作室報到后,在前幢樓一樓的右廂住兩間十幾個平方米的小房子,單位還在二樓辦公室邊騰了一間屋給他做書房。徐遲回來時,除了老伴陳松外,小兒子徐健、小女兒徐音都回來了,和他們住在一起,他們家的廚房在樓梯拐角處。
徐遲回到創作室時,分到文學組。文學組由沈毅負責,當黨支部書記。文學組原來有作家碧野、辛雷、洪洋,現在又增加了徐遲。徐遲到了創作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幫助黃聲孝把《站起來了的長江主人》第二部第三部寫出來。徐遲看到了黃聲孝被某些人利用,把他作為政治的工具,心里很不安。徐遲向創作室黨委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幫助工人作家同時也向工人作家學習,這無疑很適合當時的文藝方向。創作室黨委很支持徐遲,同意了他的方案。于是黃聲孝就從漢口長航招待所搬來了,住在前幢樓二樓右廂的一間客室里。我是1973年10月由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畢業分配到《湖北文藝》編輯部,當時住在二樓一間六平米的水管房里,緊鄰徐遲的書房,離黃聲孝住的客房也很近。徐遲輔導黃聲孝修改長詩時,有時我也在場旁聽,他很細心,肯定黃聲孝的句子,告訴他如何打磨,如何圍繞人物來抒情敘事。具體細致的輔導后,黃聲孝房間的燈光有時徹夜不熄,他趴在稿紙上,精心地創造他的詩句。
1976年5月29日的那個晚上,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到創作室時,還不到九點。我當時正在斗室中看書,沈毅找到我,說朱洪霞等人來拜訪徐遲與黃聲孝,讓我去門房那里提兩瓶開水,到黃聲孝住的客室去幫助招待。我提了開水進客室后,看到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坐在客室里的床沿上,徐遲與黃聲孝坐在椅子上,沈毅洗杯子,我幫沈毅泡茶。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當時都是四十來歲,看上去也并不趾高氣揚。他們在徐遲和黃聲孝面前,倒也謙和平常,大約他們都是工人出身,心里還存有對文學的那份尊敬與熱愛。朱洪霞在武漢重型機床廠當工人時,就是個業余作者,寫過不少詩。現在回憶,他們當時主要是問候徐遲與黃聲孝,問了《站起來了的長江主人》的創作情況,說了下文學要正面歌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并問徐遲與黃聲孝在創作與生活上有什么困難沒有?如果有,告訴他們,他們愿意盡力幫助。徐遲當時回答說,沒有困難,他和黃聲孝一定會把長詩改好,歌頌工人階級。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離開創作室時,大約是十點鐘,他們在創作室呆了近一個小時。
朱洪霞等人夜訪徐遲黃聲孝,知道的人并不多,徐遲黃聲孝也并沒把這件事當做多大個事,那段時間,黃聲孝還是改詩,徐遲有空就去黃聲孝的客室或者到我的斗室里聊天,談詩,談讀書。徐遲說,老黃的筆頭這些年寫壞了,大而空的東西太多,是被某些人引導壞了的。我以前就盯準他,要把他引上扎實的創作之道,你看現在,他變了。我一定要把他拉回來。當時我想,徐遲是在真心地幫助他。自從黃聲孝搬到紫陽路215號后,那些想借用他的名字當工具的人,就很難得逞了。寫什么東西,黃聲孝會給徐遲說,徐遲往往就以要抓緊修改長詩為借口,不讓黃聲孝寫那些配合政治事件的表態詩與戰斗詩。
“文革”結束,全國各地都在清理“四人幫”及其在各地爪牙的反革命罪行。湖北的清理工作也在緊張進行,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也在清理之列。創作室黨委與駐室工宣隊曾找我談話,詢問朱洪霞、夏邦銀、胡厚民五月夜訪創作室的情況。他們來的目的是什么?他們談了些什么?你們受了什么影響?我說,他們好像沒談什么,主要目的是看望徐遲和黃聲孝,他們說要寫文化大革命,寫造反派與走資派的斗爭。我就這么實事求是地很簡單地回答了他們。之后,創作室黨委副書記徐壽基與工宣隊程師傅又把徐遲、沈毅和我(黃聲孝回宜昌去了)找到一起,還是談朱洪霞等人來創作室的事情,我們幾人說的情況是一樣的。徐遲說,我們要實事求是,他們沒談的,我們不能編造,他們說了的,我們也不會隱瞞。最后商討的結果是要寫一篇揭發材料,與“四人幫”聯系起來。徐遲和沈毅要我寫,我是年輕人,又是工農兵大學生出身,他們覺得由我來批判比較合適。當天晚上,我到徐遲的書房找徐遲,問這材料怎么寫?徐遲說,很好寫。就說“四人幫”在文藝創作上鼓吹寫造反派與走資派的斗爭,就是要打倒一大批革命領導干部,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大陰謀,朱洪霞他們夜訪創作室,也鼓吹寫造反派與走資派的斗爭,秉承了“四人幫”的衣缽,我們革命文藝工作者決不答應。我從徐遲書房出來回到斗室,連夜寫了篇材料交上去,第三天即11月10日,湖北省文化局系統在湖北劇場召開全系統批判大會,領導要我上臺代表創作室發言,我就照稿子念了一遍。現在看來,我在徐遲指導下的揭發是蒼白無力的,實際上就是口號,沒有什么具體的東西。第四天,即11月11日,創作室機關召開批判大會,我寫了篇稿子,在會上又發了一通言。我這天的日記寫著:“兩天發了兩個言,昨天的發言稿被文化局的一個什么人拿去了,今天的發言稿做急用的包裝紙。”現在想不起來那是做了什么包裝紙。
這件事情很快就過去了,徐遲對我在這件事情的處置方法是滿意的,我也得到了他的指導。
這件事帶來的唯一后遺癥是,1976年,創作室評選我為湖北省文化局系統的先進工作者,報到省文化局之后,沒有被通過,原因就是朱洪霞等三人夜訪創作室時,我在場。
若干年過去,朱洪霞、夏邦銀在服完了刑期后,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俞正聲同志在一個文件上批示,要有關部門安排好他們的生活問題。而胡厚民則在服刑期間去世了。
《哥德巴赫猜想》前后
作為大作家的徐遲,在文藝圈子里無疑受人尊敬,人人知曉,但在社會各行各業人群中,他們平時不接觸文學,卻不知徐遲是何等人也。徐遲成為那個時候國人盡知的人物或說大師,是在1978年之后。1978年1月號《人民文學》發表了徐遲寫數學家陳景潤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加“編者按”全文轉載,隨即各地方的大小報紙紛紛轉載。一時間,凡能讀書讀報的人,無人不說陳景潤,無人不議1+1那數學上的皇冠,無人不知有個大作家叫徐遲。徐遲火了,徐遲熱了,徐遲創造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奇跡。徐遲受到各方面的重視關注,也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與敬仰,機關團體,大中小學校紛紛請徐遲做報告,報紙雜志找徐遲約稿,出版社爭著出徐遲的書,一些科研部門請徐遲去寫他們的科學家。徐遲忙壞了,徐遲招架不了,徐遲坐飛機在各大城市飛來飛去,徐遲做報告,聽眾擠爆禮堂。
可是徐遲在發表《哥德巴赫猜想》之前,在文藝圈雖說受到尊敬,但在非文藝圈、在社會上,甚至在官場,他受到的是什么樣的待遇呢?
1984年10月,湖北省新聞出版系統在黃石海觀山賓館舉行全省新聞行業的記者編輯職稱培訓考試,通過考試者即可參加職稱評定。參加培訓的報刊社人員有一兩百人,其中有不少年齡較大且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人,為了獲得一個正高副高的職稱,也屈尊參加培訓學習。我當時和一批同事也參加了培訓。11月2日中午,黃石市委市政府舉辦宴會,招待全省各地前來參加培訓的人員。會務組給每人發一張宴會券,粉紅色的紙印成撲克牌般大小,參宴者憑券入席。我那段時間真沒好好學習,寫了一二十首詩,與黃石文學界的朋友李聲高、龔去浮、胡海波等經常聚會,喝酒談詩。反正考個七十分,通過資格絕無問題。這天剛好胡海波到賓館找我聊天,談到憑券參加宴會的事,胡海波給我講了一個故事,繪聲繪色。胡海波當時說這個故事可能是見景而生回憶,隨便說說而已。但我聽后卻哭笑不得,久久無語,而且終生難忘。
大約是1977年七、八月間,徐遲一個人到了黃石,也住在海觀山賓館。徐遲喜歡往下面跑,不愿久呆在城市里,他說下面有新鮮空氣,有新鮮事物,可認識新的朋友,聽到新的故事。徐遲到黃石,時任黃石市文藝創作室主任的李北桂一手接待,胡海波參與陪同。李北桂1949年參加革命,寫了黃石市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賊狼灘》,曾得過徐遲的教誨,后來擔任過黃石市文聯主席、市委宣傳部長、湖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李北桂和胡海波對徐遲尊崇有加,安排徐遲到大冶鋼廠參觀,走訪華新水泥廠和源華煤礦,考察漢冶萍舊址,踏勘古銅礦遺址銅綠山。
那段時間,海觀山賓館正在開一個黃石市的科技大會,那天會議閉幕,中午舉辦宴會。李北桂是會議參與者,離不開身,就讓胡海波陪同徐遲,黃石市創作室司機小張開車,去銅綠山看遺址,并叮囑他們中午趕到賓館參加科技大會的宴會。
但是李北桂沒想到那天中午參加宴會要憑券,當會務組工作人員把他和小張的宴會券給他時,他才想到俆遲和胡海波中午要回賓館吃飯,而且他對他們說過是參加宴會的。李北桂當即就給發宴會券的工作人員說了情況,工作人員說這券是按名單人頭發的,你想多要就去找會務組長,并告訴他會務組長的房間號。這李北桂平時不求人的,身上那種文人的清高是免不了的。但為了徐遲,他決定去求人了。
李北桂找到會務組長,對會務組長說省里來了位老作家,正好住在海觀山賓館,能不能給兩張宴會券,請老作家和陪同人員一起參加宴會。
那會務組長是市委或市政府辦公室的一個副主任,對李北桂也熟,但對文人一貫看不起,不就寫點小說詩歌的么?憑什么那樣清高不愿理人。呵,今天你求到我了,老子就不給券,看你怎么樣?那會務組長臉上皮笑肉不笑地對李北桂說:李主任,按說兩張宴會券,小事一樁,但我不能給你。如果我給了你兩張,張三也來要兩張,李四也來要兩張,那不就亂套了么?這參加宴會的人員名單,是市委領導圈的,我沒權力決定。要不你去找找書記,他在某號房間,讓他批準吧!
會務組長給李北桂碰了個不軟不硬的釘子,李北桂氣得無話可說,扭頭就離開了會務組長的房間,心里罵一句狗東西。他決定不就此罷休,找書記就找書記,不信就弄不來兩張宴會券。
李北桂找到書記的房間,敲了敲門就進去了。書記正在看科技大會的閉幕詞講稿,待會他要在會上念的。書記從講稿上抬起頭,問:北桂同志,有事么?
李北桂說了老作家徐遲來黃石深入生活,住在海觀山賓館,書記能否抽時間見一見,中午順便讓老作家參加宴會,也算是書記對我們創作室工作的支持。
書記站起身,在房間里走動了一下,問:這徐遲是什么人,寫過些什么作品?
李北桂說:徐遲在四十年代就有名了,解放后寫詩寫小說寫報告文學,代表作有《美麗·神奇·豐富》、《祁連山下》、《一橋飛架南北》等,在國內享有名望。“文革”中下放、進“五七”干校,才“解放”不久,正在搜集材料寫新的作品。
李北桂一口氣將徐遲做了介紹,生怕書記不了解。
書記在房間里又走動了幾步,皺了下眉頭說:北桂同志,我看就算了吧,這科技會閉幕忙,我對這位作家也不了解,我就不見了,你接待一下就行了,好么?
李北桂只好從書記的房間里出來,氣得直哼哼。十一點半鐘,司機小張開著車把徐遲和胡海波送回賓館。胡海波陪著徐遲在房間說話,小張到李北桂的房間說:這徐遲老頭了不得。他的風度、談吐、學識的淵博都令小張這個小青年折服了。李北桂不聽小張說徐遲,只說讓他中午到外面找個好酒店請徐遲吃飯。小張問:不是一起參加宴會么?李北桂搖了搖頭,把上午做的努力碰的釘子說給小張聽。小張一聽,大罵這些狗東西,有眼不識泰山,說:李主任,你先去陪陪徐老,將我的宴會券給我,我一定給你弄回兩張券來。注意,我不回來你們不要出房間,你們去吃飯會晚一點。
小張從李北桂手上取了一張宴會券,沒等李北桂說什么,就匆匆走了。李北桂只好到徐遲的房間,和胡海波一起陪徐遲說話。小張果然在半小時后來到徐遲的房間,交給李北桂兩張粉紅色的撲克牌大小的紙券,說,這是徐老和胡老師的宴會券,你們快去吧,現在人不多。
胡海波的故事講到這里,才開始給我揭謎底。原來小張拿了自己的宴會券后,找了一張人不熟的桌子坐下來,把券往桌上一放。別的人也學他樣把券放到桌上,他就把大家的券收到一堆,在收的時候他故意把券散落在地上。他趕忙蹲下撿宴會券,順勢把兩張券塞進了他的涼鞋里。服務員每桌收宴會券,手里抓了一大把,收到小張這桌時,小張主動把一卷宴會券交給服務員。那服務員連說謝謝,哪里還去數哩。小張在半個小時內吃完飯,推說有事先走,趕到房間給徐遲和胡海波送他藏在涼鞋里的兩張宴會券。
半年之后,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隆重發表。黃石的書記想結識一下這位著名作家。便打電話給市文藝創作室的李北桂,要李北桂把徐遲請到黃石來,他要親自作陪。李北桂只能答應,他能說徐遲半年前來黃石他當書記的不愿見的事么?李北桂一直沒請徐遲到黃石,書記后來再問,李北桂就說徐遲太忙,安排不過來。書記只好遺憾了。
徐遲一生寵辱不驚,得意不忘形,失意不自棄,在他生前,我有多次機會可對他講黃石宴會的故事,但我終究沒說,我不想讓他知道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