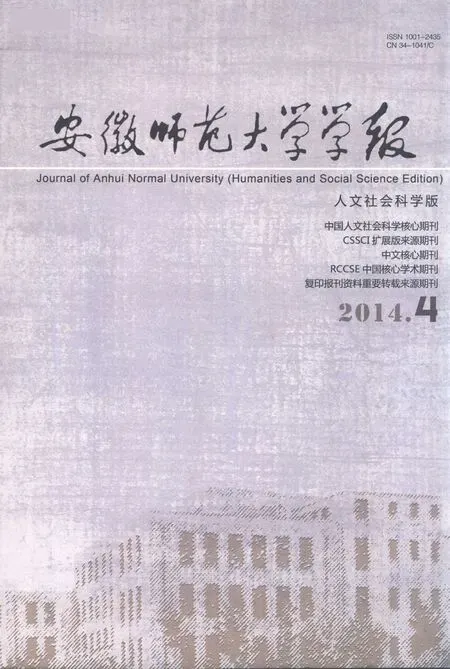中國文學起源問題重議——從甲骨文與中國文字起源發生說起*
木 齋,祖秋陽
(吉林大學 文學院,長春130012)
一、中國文學起源傳統說法的反思及新的理論體系構建
關于中國文學的緣起,有兩種近乎定論的權威說法和寫法:一是就文學體裁而言,幾乎都是說詩歌先于散文,這種說法似乎主要與文學藝術源于勞動的理論有關;二是就文學題材而言,在文學史的寫作中,往往又是以神話為開篇。
其中文學起源詩歌說,詩歌源于勞動說、源于民間說,具有雙向的理論來源。一方面,來自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如 《淮南子·道應訓》云“今夫舉大木者,前呼 ‘邪許’,后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可視為后來 “杭育”說的先聲;又如班固、何休出于儒家民本思想編造,朱熹光大張揚之詩三百 “采詩”說、民歌說等,皆為胡適以來民間說之宗祖。另一方面,源于俄蘇意識形態以及更為上溯的以普列漢諾夫、恩格斯為代表的勞動創造人理論。而這些舶來品又同華夏民族長期以來儒家出于民本思想的需要所產生的采詩說、漢樂府民間說等說法相互呼應,相互之間循環論證。
將神話視為中國文學的起源,則是中國文學史寫作的慣例——在理論上詩歌是中國文學最早的體裁,在文學史實際的寫作中,往往是以散文體裁寫成的神話為開篇,如 “神話的起源正如詩歌的起源,是文學最早的源頭”①林庚 《中國文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如袁行霈本 《中國文學史》等,莫不如是。等。詩歌起源和神話起源這兩種說法看似有別,實則同本同源,都源于一個多世紀以來意識形態領域的勞工神圣、民間創造這同一個意識形態思潮。在中國學者中,魯迅最早借助現代的 “神話”觀念講述中國文學史的起源,其 《中國文學史略》第二篇《神話與傳說》云:“神話不特為宗教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為文章之淵源。”“‘街談巷語’自生于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于神話與傳說。”魯迅之后,敘述中國文學的源頭一自神話,已成為一種中國現代學術的新傳統而為眾多學者所接受。[1]39
如上所述,這兩種說法,幾乎都主要發端于一個多世紀以來新興的意識形態觀念,當然,也和中國本土原有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儒家民本思想異曲同工。但這兩種說法,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圓通的悖論:既然詩歌為文學的起源,就不應該是以神話為起源。迄今為止所見到的中國最早的文獻史料,罕見中國上古以詩歌體裁寫作神話,因為中國文字的特點以及上古時代甲骨文、金文的書寫形式和傳播方式,從根本上制約了神話文學的寫作,華夏民族上古時代漸次形成的廣義上的儒家文化,則更從文化層面制約了神話文學的寫作、接受與傳播。堯舜禹湯文武的儒家道統(無論堯舜禹是否可信,其作為一種道統則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標識了華夏民族在自身民族文化的起源發生階段,就基本奠定了以人為本而非以神為本,以現世為本而非以冥界為本的民族文化特征。這一民族文化特質,必定衍生出重視現世的人倫關系,重視記載歷史等等。宗廟祭祀,祈禱神靈,都是為了現世的存在。中國文學的起源發生,必定也應該主要以上述方面作為主要的書寫內容。而這些內容本身,決定著中國文學在起源發生時期,理應是散文的而非詩歌的,理應是寫實的,而非想象的,理應是記載現世日常必須的應用文字、記載重要的政治文誥,記載對于祖宗神靈的祈禱等。這些理應是起源發生時期主要的書寫內容。當下文學史以神話作為開端,主要是采用 《山海經》 《淮南子》等后來之文獻,是以寫作題材所顯示的所謂遠古內容替代了寫作時間,是以想象替代了中國文學史起源發生的時間次序。其中少量認為出自 《詩經》雅頌關于禹的部分,出自 《尚書·百刑》(成于西周)的上帝、蚩尤故事,楚辭 《天問》等中的后裔故事[1]43,這些都不能說明中國文學最早的題材是神話故事。
總之,不論是詩歌早于散文之說,還是神話為中國文學之起源的說法,都主要是來自于意識形態的臆斷,這是一個時代集體的誤區。以之到歷史文獻中去驗測,必定歸之于推斷,并無實在之根據。筆者認為,中國文學就文學體裁而言,最早起源于散文,即由甲骨文記載的應用性散文,隨后才是詩歌的產生。詩歌的產生和兩大文學藝術文化類型密切相關,即與音樂和散文有關。兩者之間,應該是先與散文有關,詩的因素是從甲骨文的反復記錄和書寫中萌生的,以后到周公制禮作樂的時代,音樂的音律節奏引導了這種原本從散文文體中孕育出來的詩歌雛形,從而成為了中國最早的詩歌。無論是甲骨文還是禮樂制度,皆為帝王宮廷文化的重要組成,與所謂下層民眾并無關系。因此,無論是最早由甲骨文記載的應用體散文,隨后一些的政令性散文、記載歷史的散文 《尚書》,還是與西周禮樂制度密切相關的 《詩經》,都同樣是貴族政治制度的產物。
筆者的這一觀點,其含義主要有:(1)就中國文學的起源的時間而言,筆者斷代在商周之際,甲骨文肇始于武丁時期,因此,即便是廣義的以甲骨文作為載體的中國文學的起源,不能早于武丁之前;而由文字的創造到文學的創造,還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文學的起源,由寬泛概念的文學到狹義的文學的出現,一直到西周初期周公制禮作樂之際,才真正出現。換言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發端于周公時代,是禮樂制度的產物,周公本人即為其中的創造者、始作俑者。(2)如前所述,散文早于詩歌,中國詩歌的起源,來源于禮樂制度的需要,中國詩歌之產生里程,概略而言,先以散文體裁寫出祭祀祖先的文字,然后配樂以合于禮儀,音樂的節奏音律導引了后來祭祀文字的寫法,詩歌體裁遂由散文體裁中借助音樂的載體蛻變而出,從而有了詩歌這種形式。(3)以上是從文學的視角立論,若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而言,則凸現了周公禮樂制度的歷史性變革的偉大地位,再向前追溯,則武丁時代的文字的創造和甲骨文的發端,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文化地位。(4)再進一步作追問性質的思考和研究,則中國文字的產生,也需要給予深一步的研究。以筆者所見,武丁時代的甲骨文,正是中國文字的真正意義上的產生。
這些觀點,構成了一個中國文學起源產生的新的理論體系,其中包括中國散文的起源發生歷程、中國詩歌的起源發生歷程、中國文字的起源發生歷程、《詩經》的寫作歷程、甲骨文化、青銅文化向竹帛文化載體演變歷程等諸多問題的重新認知。幾大問題之間盤根錯節,相互印證,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文學的起源發生史,需要系列篇章將諸多問題逐一論證,此篇為其首篇,著重論證文學的界說、文字的界說等基礎性問題。
二、中國文學的界說
筆者所闡發的這一認知,可以先從任意其他學者的相關論證中辨析與闡發。筆者隨舉手頭正有的材料。如柳存仁認為:“觀乎商代銅器之刻詞多僅記名字、稱號、年月,或某人作之子孫永寶之陳詞,而周代銅器之記載已漸能達情表意,文從字順。”“其后殷周民族之畛域漸泯,文化混合而產生更大之進步。此時期已達成熟之農業社會,生活既較前復雜,而文字之表現亦見典整豐長,有時且用韻律。”[2]17
此段文字,可以歸納幾點含義:(1)中國文學的發端,就現有的文獻記載,大抵在商周之際,也就是柳先生所說 “漁獵社會向農業社會之過渡”之際。柳先生從現有的商周之際的青銅器文字的變化上,已經看出了商、周之間正是從濫觴階段轉型為江河階段本身。(2)有關中國文學的緣起,就柳先生具體論述而言,理應是文早于詩,詩源于文。雖則如此,但中國文學之詩歌早于散文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一種近乎定型的觀念。即便是柳存仁先生隨后也同樣論述:“遠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文學史發源之程序,其韻文之發展,必先于散文者若干年,此為各國文學史之通例。在吾國最早者為 《詩》三百篇,希臘則有著名之史詩,印度則有古梵文之歌唱,均為韻文寫成……韻文之中,復以詩歌一體為最先。蓋詩歌產生于原始人類生活之真實素描,即為自然感發之歌唱,故其所藉以傾吐哀樂心感之節奏韻律,亦無不歸反之于自然。且詩歌多伴音樂歌舞而俱成,而樂舞又咸為舉動中節之表現……”[2]22
上述之理由,并不能說明詩早于文:其一,詩三百的寫作時間,基本為開始于周公時代的作品,殷商時代的甲骨文文獻,遠遠早于詩三百的產生時間;詩三百之前的詩歌作品,可能會有,但迄今為止,尚未出現能證明早于周公時代的原創文獻,因此,都不能確認為早于散文之作。其二,“詩歌產生于原始人類生活之真實素描,即為自然感發之歌唱,故其所藉以傾吐哀樂心感之節奏韻律,亦無不歸反之于自然”的理論,也不能成為詩早于文的內證根據。從情理上來說,功利的、功用的、實用的早于審美的,這才應該是合于人類社會文化包括文學在內的基本起源發生發展規律。
西方的文學起源發生歷程不在本文探討之內,就中國文學的起源發生歷程而言,就現有的文獻史料而言,無疑應該是應用性的、政治性的、記載歷史的文字在先。在經歷漫長歲月的應用文字、政令文字、歷史記載文字的過程中,先民們在這種大量的文字書寫的經驗基礎之上,無意地、有意地發現了在文字書寫中較為整齊的句式,以及句式之間的聲韻節奏,不僅僅能帶給接受者某種快感,而且能在這種富含詩意的書寫方式中,起到容易記誦、容易傳播,并能得到閱讀的快感。于是,在漫長的散文體裁的書寫過程中,發現了詩歌的文學樣式。這應該是中國文學的起源發生歷程之梗概。
先秦詩三百,雖然名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但對詩三百的闡發史,卻始終遵循著漢儒說詩的軌跡,將其視為人倫教化的教材。換言之,就其內在的功用而言,并非是審美的、愉悅的、人性的、情感的產物和存在,而是如同散文體裁最早產生時代的應用的、政治的、歷史記載的載體。此則為詩文之間唐前交互影響史之概要。在漢魏以后的發生發展的歷程中,一直到六朝之際的文筆之辨,實際上,一直是詩體從原本產生之際對文體的依賴、比較中逐漸實現尊體的歷程。
這樣一說,就要涉及到文學的界說。或說是中國文學的界說。因為,反對者可以說,你所說的這種應用的、政治的、歷史的文字,不一定是文學。概括而言,文學有狹義、廣義之不同,狹義而言,文學為訴之于審美、情感的語言藝術,廣義而言,錢基博的界說最為精準:“則述作之總稱也。”[3]3就中國文學史的演變歷程而言,乃先為廣義,逐漸走向狹義之文學。文的本意來自于織,《易·系辭傳》曰: “文相織,故曰文。”《說文·文部》曰:“文錯畫,象交文。”演變成為 “文者,會集眾采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意,如文繡然”(《釋名·釋言語》),“所謂文者,蓋復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3]3。如同“文”字本身有演變過程引申之義,文學在中國歷史文化之中也經歷著由廣義而狹義,由 “述作”而 “美麗而適娛悅者”的演變歷程。仍以柳存仁的界說為基礎進行討論:柳先生例舉 《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語,而后說:
文學為 《詩》、《書》、《禮》、《樂》,同于典籍文獻……迨及兩漢,更以文學泛指一切學術而言……誦經書者眾,當時即美之為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魏晉之后,有倡言文學應自有其特殊之范疇,而與玄、儒、史分稱“四科”者,自宋文帝始。其前,則范曄 《后漢書·文苑傳》贊、陸機 《文賦》已肇其端。其后,則梁昭明太子蕭統嘗舉 “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者……西文之釋 “文學”,最早蓋源于拉丁語之“Litera”,衍變而成 “Literature”,實含有文字、文法及文學等三種意義。西人著述中對 “文學”所下之定義,亦有廣義、狹義之不同,而采用狹義者較多。如美國韓德氏 (Hunt)于其所著《文學原理及其問題》中,闡述其個人對文學之解為:“文學為思想之文字表現,藉想象、感情與趣味為之媒介,使人易于理解及發生興味。”……綜合其定義中所列舉之文學要素,則想象、情緒、思想、形式四者,不可缺一。[2]4-5
以此來衡量中國文學之發軔,其進入到狹義文學的認知,亦為一個長期漸進的歷程。先秦時代,則文學為 《詩》《書》《禮》《樂》,同于典籍文獻;迨及兩漢,更以文學泛指一切學術而言。詩三百之所以列為儒家經典之首,其原因并非由于其為 “詩”,為文學之一種,具有文學的想象、情緒、思想、形式,而是由于其更為典型具有興觀群怨的人倫教化功能,是更好的政治教化教材,它使政治憑藉著文學的翅膀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 (所謂 “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它的立足點在于教化,在于對儒家思想的傳播,而非審美的愉悅。在這一點上來說,詩三百與其說是“詩”,毋寧說是當時最為優美的文,是詩化的散文,是散文化的詩。一直到齊梁時代,才有了狹義文學的認知。當然,這是就理論的層面而言的,就文學創作的實踐來說,早在建安時代,準確的說,是從建安十六年開始的時代,發生了五言詩的游宴詩寫作運動。游宴詩寫作,成為了將詩歌從儒家人倫教化桎梏中解放出來的契機,成為文學自覺的搖籃,成為中國文學從政治化、散文化向審美化、詩歌化轉型的樞紐。
盡管如此,就中國文學的起源發生運動而言,則應該是在先秦兩漢時代完成的。既然在起源發生時期,華夏民族對于文學的理解,尚在文學為詩書禮樂,同于典籍文獻的階段,則當下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起源發生,自當同此標準,一切典籍文獻,一切由文字而形成文章者,即均可化入到廣義的文學大范疇之中。這也就是一向所說的先秦時代文史哲不分的歷史文化現象之所由來,之所存在。
三、甲骨文與中國文字之起源
筆者以為,對于中國文字、文章、文學的起源,自然應該以現有的文獻史料作為依據,而不能脫離這些文獻進行想象判斷。甲骨文不僅僅是華夏民族語言最早的文字,而且是當下所能見到的中國最早歷史文獻,①中國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龜甲、獸骨為載體的文獻,是已知漢語文獻的最早形態。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稱為契文、甲骨刻辭、卜辭、龜版文、殷墟文字等,現通稱甲骨文。商周帝王凡事都要用龜甲 (以龜腹甲為常見)或獸骨 (以牛肩胛骨為常見)進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關事情 (如占卜時間、占卜者、占問內容、視兆結果、驗證情況等)刻在甲骨上,并作為檔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可參見甲骨檔案)。甲骨文獻中還有少數記事刻辭。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飲酒及敬鬼神;也因為如此,這些決定漁撈、征伐、農業諸多事情的龜甲,才能在后世重見天日,成為研究中國文字重要的資料。同時也是最早的華夏民族的散文。
甲骨文,指刻于商周甲骨之文。當下出土的主要為安陽殷墟以及西周初期周原的甲骨文。一向所說的從夏代開始有文字,或是更早的黃帝時代倉頡造字,都僅僅是一種傳說,并無實證。陳夢家對此論證甚為詳切:認為 “倉”是 “商”的聲同相假,商契就是倉頡:《爾雅》《釋鳥》“倉庚商庚”, 《夏小正》 “倉庚者商庚也”,可證“倉”“商”聲同相假,而古音 “頡”和 “契”又非常相近。因為漢字為商人所造,而契不僅僅是商的古王,更因為契字的本意是契刻——最早的文字是契刻于甲骨上的,因此,才有倉頡造字之說。但這一附會,它幫助我們解說:龜甲上的文字是最早的文字,發明文字的地方是契的封地,發明文字的人倉頡實在就是契。總之,最早的文字是商人契于龜甲的卜辭。[4]此論是否準確,驗之以甲骨文的實際情況,便可得知。
1933年,董作賓發表了 《甲骨文斷代例》,在十項標準之下,提出了甲骨文的五個時期:1.盤庚、小辛、小乙、武丁 (二世四王);2.祖庚、祖甲 (一世二王);3.廩辛、康丁 (一世三王);4.武乙、文丁 (二世二王);5.帝乙、帝辛 (二世二王)。[5]以五期斷代來看殷商甲骨文的實際情況,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在商代之前,中國尚未進入到以文字時代,甚至在第一期之前,尚未進入到書寫文獻的時代。在早、中商時期既發現刻劃符號,又發現文字。在鄭州商城出土的大口尊、盆、豆等陶器上,經常發現刻劃符號。一般一器一個符號,個別的刻有相同的兩個符號,或者兩個符號的合文,已經發現的刻符有30多種。[6]關于這些符號的意義,有學者認為是 “陶器容量的符號”[7]。其中,“在大口尊口沿所刻有的有些圖像,則很可能是象形文字”,“商代早中期的文字資料,還見于河北藁城臺西遺址。在該遺址的70多件陶器上,發現了文字和符號。” (參見原書圖57、58)[8]其中止、刀、矢、戈等字,與殷墟甲骨文相似。從這些文字與符號來看,河北藁城臺西出土的4處刻劃符號和河北藁城所出土的文字,顯然有刻劃符號和文字的不同。雖然這些刻劃符號 “與殷墟甲骨文屬于同一個系統”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4-425頁。,但明顯屬于華夏文字的早期雛形形態,河北藁城的4處刻劃尚還屬于圖畫形態。
河北藁城臺西與鄭州商城出土文物,兩者皆被視為是早中商文化的產物,但卻顯示出來由圖畫文字向表意文字轉型的痕跡,可以充分說明在殷商之前尚未進入到文字時代,而在沒有其它商代早中期甲骨文出現的情況下,又可說明鄭州商城出土的這片刻字甲骨,比較接近于當下出土的殷墟甲骨文。“大多數學者認為夏代應當有文字,但在二里頭文化遺址中,只在陶器上發現數十種符號。其形體大多屬于幾何符號,也有象形符號。”[5]迄今為止發現的考古材料,正說明了夏代僅有刻劃符號,尚屬于圖畫階段和幾何符號階段,商代早期的情況,也仍然在夏代的這種刻字符號階段之中。從當下所能見到的第一時期的甲骨文,雖為二世四王,實則主要是武丁時代的作品。筆者前文的判斷,認為發生于武丁時代的甲骨文文獻,基本上就是中國文字的發生期,同時,也是中國最早文獻的發生期以及中國文學的起源期。不僅僅根據前文所征引的出土文物的對比,同時,也根據如下的方面得出判斷:
(一)甲骨文文字,尚還處于文字發明的探索時期
這其中包括一字多樣寫法,如 “舌”字,根據董作賓所掌握的甲骨文字,就有12種之多,除了前1、2種無異 (前兩種也有不同,2種多一枝杈),其余3-12體,兩旁均有小異,示舌上有水、舌下有口、舌在口中等,至于金文中所掌握的 (參見 《董作賓先生文集》,藝文印書館印行)。即便是最為基本的天干地支,其寫法在董作賓為殷商甲骨文的五個分期之中也有變化。其中既有相對穩定的寫法,如甲,寫成+,乙,則與后來的乙字近似,但在武丁時期,方向尚未確定。類似情況還有 “己”字,開口方向一直在變化,在武丁時期兩個方向皆有,并一直延續到文丁時期,到帝乙、帝辛時期方才定型為左開口,如同現在的己字。丙字、丁字大同小異,丙字在帝辛時期略有變化,戊字在武丁時期原本與甲骨文的 “又”字相似,一直到第五期才開始看出后來 “戊”字的形態。癸字則一直到帝辛時期的寫法,仍與后來文字的 “癸”字不似。還有合字現象等。
甲骨文除了作為文字方面的這些特點,說明其時中國的文字尚在早期雛形形態之外,由當下甲骨文所形成的文獻,其本身同樣屬于雛形形態。甲骨文文獻刻寫的目的,是對占卜情況的簡單記錄,也是對商王朝的史的最原始記錄,文獻篇幅短小,尚未具備后來之所謂文章寫作的意識和形態。同時,甲骨文在書寫形式上,也還處于非常原始的狀態,一片甲骨上,或是從左向右,或是從右向左。如 《殷墟文字乙編》第6385片。從右往左為:貞:有疾自,隹又它?右面文字從左向右:貞:有疾自,不隹又它?自,“鼻”之初文,《說文·四上》:“自,鼻也。象鼻形。”隹,語氣詞,經籍通作 “唯”。它, “蛇”之初文。《說文·十三下》:“它,蟲也……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蛇,‘它,或從蟲。’”此處與有災禍意近。該辭句意:貞人問:鼻子有疾病,是否有災禍?
當然,在這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原始記錄中,逐漸也會出現某些文學的因素。譬如,敘事文學的因素,如《甲骨文合集》第14002片正面:
甲申卜, 貞:“帚好冥, ?”王 曰:“其隹丁冥, ;其隹庚冥,引吉。三旬有一日甲寅冥,不 ,隹女。”
甲申卜, 貞:“帚好冥,不其 ?”三旬有一日甲寅冥,允不 ,隹女。
全辭意為:甲申日占卜,貞人 問:婦好將要分娩,是生男的么?王察看卜兆后判斷說:如果在丁日分娩,就生男的;如果在庚日分娩,就永遠吉利。結果過了三十又一天,在甲寅日分娩了,不是男的,而是女的。甲申日占卜,貞人 問:婦好將要分娩,不會生男的吧?結果過了三十又一天,在甲寅日分娩了,果然不是男的,是女的。這是一組對貞卜辭,第一條卜辭的敘辭、命辭、占辭、驗辭齊全,第二條則省去了占辭。婦好是武丁之妻,也就是殷王武丁的后。這組卜辭記錄武丁王后生育男女以及是否吉利的事情,顯示了在殷商時代已經認為生男為吉,生女不吉的風俗。 (音確),為武丁時期貞人之一,冥,通 “娩”,甲骨文原文寫法為 ,為腹中有子之子宮形象; ,通嘉 (參見郭沫若 《殷契粹編》);其、隹皆為語氣詞。這一片卜辭記述婦好生子的占卜,可以視為后來敘事文學的雛形,由貞人和殷王卜辭的記錄,形成了事件發生過程的完整記錄。
(二)重復構成詩歌因素
其中或有重復,成為一種重復美,如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卜辭通纂》第375片)占卜者和刻寫甲骨者,不一定為了詩意的韻律節奏,而僅僅是面對四個方向占卜是否有雨的自然記錄,但卻自然形成了每句只變換一下方位的重復節奏美。與后來 《江南可采蓮》“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有異曲同工之美。有些是對占卜正反定否的自然記錄,偶然出現詩歌因素,如 “自今辛至于來辛又大雨?自今辛至于來辛亡大雨?”(《甲骨文合集》第30048片)雖為甲骨文刻字文獻,仍為文言文系統,這就保持了兩句之間的對仗之美,嘗試比較白話語和原文的不同:從這一個辛日到下一個辛日有大雨么?從這一個辛日到下一個辛日沒有大雨么?這一點,也正解釋了中國文言文的由來,同時見證了中國文言文自其起源發生之日起的演變歷程。
(三)句式構成的文學因素
在殷墟甲骨文前數期中,主要刻寫人為占卜者,也就是貞人,因此,甲骨文文獻所載,也多為占卜者的口吻和視角記錄下的殷商史實,其中也可以看到以后六經時代書寫文字的印痕,如:“壬子卜,爭貞,我其乍邑,帝弗 ,若?三月。”①《殷墟文字丙編》,第147片。其中乍,為 “作”字的初文,“左”字需要造字,去除 “工”字,為左字的初文。“我其乍邑”四字,《詩經·大雅·文王有聲》:“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兩者之間,后者將原先單一出現的四字一句,而為兩個四字句,遂由散文而為詩。此與兩周散文筆法并無太大區別。或說是兩周散文的基本元素并無二致。
四、文字的界說與文學的起源
關于甲骨文在中國文學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高估其地位,因為,不論是中國的文字還是文學,甲骨文均為開辟鴻蒙、從無到有、篳路藍縷的歷史階段,但也不能低估其歷史作用和地位。研究中國文學史的起源發生,很多人雖然談及甲骨金文,但仍然從神話和詩歌的起源談起,這就無視了甲骨文文獻的存在,放著最為可信的最早的文字、文獻記載而不研究,反而以后人所作的神話和傳說中的所謂上古詩歌作為文學的起源,這是不對的。甲骨文文獻所顯示出來的文學因素,既是粗糙的、無序的、胚胎的,但又是極為寶貴的、自然的、美妙的,它們在應用的、功利的、歷史的記載中,放射出了文學審美的異彩,播種了后來文學的、詩歌的種子。
有關中國文字的開始,自古至今,爭論甚大,有學者認為夏代開始就有文字,也有學者認為更早,要往前推到圖畫文字,譬如前文所引的出土文物中的以腳印代表 “止”字等,也有學者更進一步上溯到上古結繩記事,為中國文字之起源發端。之所以爭辯不清,主要是爭論雙方不是用同一個界說標準:文字有廣義狹義之不同,有起源與發生開端之不同,如果說是廣義的起源,則結繩記事有關,圖畫文字有關,刻劃符號有關,周易占卜有關,但這些均非文字本身,而是廣義的文字起源。
作為狹義的文字,需要先行確定其界說范圍,方能指認其產生時間。以 《辭源》對 “文字”界說為例,主要有兩個義項:語言的書寫符號;連綴而成的文章。①《辭源》第1357頁,“文字”條。但這兩個義項,似乎都還不能作為我們想要追究文字發生點這一使命的權衡標準,前者過寬,如前文所引商代早中期的四個畫圖文字,以腳印作為 “止”字,雖然是典型的畫圖表意,但也似乎可以視為一種語言的書寫符號,更何況以河流的正反走向代表 “逆”,則初步具表意的特質,再更進一步,“目”“五”兩字,均已經和后來的文字極為相似。但這些單獨出現的表意符號,無論怎樣接近后來文字的雛形形態,它們均非我們所要尋求的用諸多字來表達完整含義這樣人類特有的功能。后者過窄,因為文章也可以有狹義廣義之分,廣義而言,一切表達出人類思想的連綴文字皆可以稱之為 “文章”,狹義而言,文章在規模上較大,在表達思想上較為復雜,在應用場合上較為正式、莊重。譬如我們常用 “廟堂文章”和宋元之后的 “小品”相對,來指認同樣是散文體的不同樣式和階段。同此,我們平日三言兩語的日記文字和便條文字,一般來說,我們也不稱其為 “文章”,但它們確乎為 “文字”。同此,甲骨文文字,我們也不便稱其為文章,但它們確乎為文字、文獻。
因此,筆者嘗試為 “文字”重新界說:所謂文字,簡單來說,就是 “連綴字以成文”。文的含義較文章更為廣義,這里,“文”或是文學的界說,可以重回 “則述作之總稱也”[3]3的表述。文字可以獨立的表達一個完整的思想,而前舉的四個單獨的字 (如果將圖畫文字也稱之為字的話),并沒有連綴以成為文,這就還沒有達到文字的發生發展階段。
采用筆者的這一界說,重新來審視殷商何時開始產生甲骨文的問題,也就會有了新的認知。從以上對武丁之前,盤庚之后的甲骨卜辭的綜述來看,雖然從提出五期分期說的董作賓,就開始嘗試為之尋找證據,將第一期放寬到 “武丁及其以前 (盤庚、小辛、小乙)”,但這僅僅是為自己的學說留有余地,并無實證;以后,胡厚宣又在《甲骨續存》中,嘗試指認某些甲骨卜辭為盤庚小辛小乙之物,但也僅僅是 “疑皆當”而無實證。以后的出土文物,似乎為這一難題的解決提供了一些線索,但終究尚未得到真正早于武丁的甲骨文。
以筆者的推測來看,一個重大文化現象、文學現象的產生,必定要有著從政治、軍事、經濟、宗教、哲學、文藝、語言文字,到文學等多學科的重大歷史變革作為背景方能得以發生飛躍性的突破,從而成為一個新時代的里程碑。正如以后周公制禮作樂的革命,發生了中國詩歌的飛躍,從而產生詩三百以及中國詩歌;曹操鄴城銅雀臺起,清商樂興起,才有了五言詩體形式的飛躍,從而奠定了中國詩歌美學的發展方向和詩歌史歷程。武丁時代,也一定會有類似的文化變革發生,譬如已經被學者所論述的,至少從武丁時代開始,殷商之間開始發生的軍事沖突。屈原《離騷》記載的 “說操筑于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為我們描述了武丁時代圣君賢相的歷史圖景。此外,占卜制度的確立,貞人群體占卜記錄歷史的確立,政治、宗教等的需要,可能會極大地刺激了文字記載的需要,從而發生了中國文字、文獻、文學鑿空鴻蒙從無到有的歷程。換言之,當下其它地區所出土的甲骨殘字,一鱗半爪,均只能是中國文字史、文獻史、文學史江河發軔之前的涓涓溪流而非江河本身;武丁時代之前之于文字的暗中摸索歷程,似應為漸變的歷程,武丁時代,則為質變的飛躍。
在討論基本完成了武丁時代殷墟甲骨文之后,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對于周原甲骨文的討論。至今有字甲骨共發現300多片,其中周原一地就出土300片左右。西周甲骨的文字一般都比較少,而且,字跡纖小,“在沒有爭議的較為典型的西周卜辭中 (無論是在周原,還是在幾千里外的邢臺),其刻辭行款幾乎都毫無例外地都是自右向左。”[9]相對比殷墟甲骨卜辭,可以明顯地看到,殷墟甲骨卜辭的書寫次序,并無一定,從左到右,從右到左,從上到下和從下到上,無不具備。這可能與殷商甲骨卜辭的記錄,基本都是以甲骨為書寫材料有關,而西周很有可能在文王時代即已經開始有竹簡書寫,而竹簡書寫最大的特點,是可以采用繩等物將其編為策。如果當時已經習慣編在其左,掀動方便,則勢必要由右向左書寫,方能閱讀方便。當然,不排除也會有從左向右的書寫次序。但不論如何,西周時代的甲骨文,已經開始有了書寫次序的規范意識。
曹瑋編著 《周原甲骨文》一書的圖片[10],均為從右向左,從上向下。《周原甲骨文》一書為收集周原甲骨最為全面的一書,可知周原甲骨基本為接近西周之后開始的 《尚書》等的書寫習慣。圖片中的文字,涉及周方伯等的字樣,應為西周早期,近于文王時代的文字。其書寫刻畫的痕跡非常纖細,疑其之地原本慣于竹簡刻寫,與甲骨采用不同的刻畫工具。甲骨貴重于竹簡,也有可能,就是王室用甲骨而非王室則用竹簡。至于周原甲骨字跡纖小是否與竹簡的書寫習慣有關,尚需要進一步研究。
但也有例外,采用自左向右的書寫次序,如來自陳全方摹本的周原甲骨文①均出自陳全方摹本,原載 《四川大學學報》第10輯 《古文字研究論文集》,第381頁。:同樣出現周方伯,但文字的表達,似乎更為接近成熟。在刻寫風格上,同樣纖細。有學者探究了周原甲骨文中“王”字的演變②王宇信等 《商周甲骨文》,第222頁。,嘗試比較殷墟甲骨文中的“王”字,顯然,周原甲骨更為接近后來的寫法,或說是基本完成了 “王”字的定型。這一點,幾乎是具有典型意義概括意義的。中國文字,在西周初期,一方面通過在甲骨刻寫載體內部的變革演變,漸次接近定型,一方面,隨著西周新時代的開始,也漸次完成了由甲骨文字向青銅器金文書寫的變革和定型,以及當下尚未能有出土文物證明,卻在情理之中的竹帛載體以及竹帛書寫文字形式的變革和定型。同此,伴隨著文字書寫載體的變革和日趨穩定,書寫文字、文章變革飛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 趙敏俐,譚家鍵.中國古代文學通論[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
[2] 吳梅,柳存仁,等.中國大文學史[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3]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M].北京:中華書局,1993.
[4] 陳夢家.中國文字學[M].北京:中華書局,2011:11-12.
[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429.
[6] 裴明相.鄭州商代陶文試釋[C]∥河洛文明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7] 安金槐.商代糧食的器量[J].農業考古,1984,(2).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臺西商代遺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0-99.
[9] 王宇信.周原甲骨卜辭行款的再認識和邢臺西周卜辭的行款走向[J].華夏考古,1995,(2).
[10] 曹瑋.周原甲骨文[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