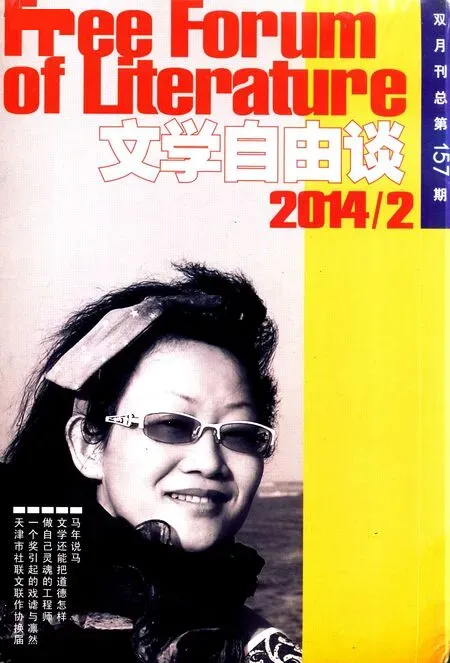文學還能把道德怎么樣?
●文/陳 沖
文學還能把道德怎么樣?
●文/陳 沖
最近出現了一種提法,叫“文學不能消解道德”。這提法對不對呢?我認為太對了。或許正是因為它對得不能更對了,才讓人產生了一點疑惑,由一批權威級專家,來創制出這樣一種無可置疑的提法,是不是哪兒存在著一點不對勁的地方?毫無疑問,道德是不可能被文學消解掉的,因為文學不具備那么強大的惡法,那道理就像敵敵畏不可能被臭蟲毒死同樣一目了然。因此,在做了一些比較具體的考察之后,我們似乎有了一些隱約的發現,大約說來,不是臭蟲把敵敵畏毒死了,是敵敵畏里長臭蟲了。
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或一種類型的專家,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反復探索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很具中國特色的做學問的新方法論。解析一下這種方法論,應該是件饒有興味的工作,不僅可以大大豐富邏輯學的運作方式,還可以對模擬電子計算技術中長期難以解決的“零點漂移”問題做出一定的貢獻。您可能還不了解,當模擬電子計算機還處在分立元器件時代的時候,其中有一種核心的元器件叫“積分器”,這種元器件有個最重要的技術指標就是“零點漂移”。您想啊,所有的計算都是從“零”開始的,可是當你給這個積分器預先設置的“零”點呆著呆著自個兒就“漂移”了,那以后的計算還能準確嗎?當一臺模擬計算機上幾十、幾百個積分器都自行漂移起來,有的往這邊漂出來了0.00001,有的往那邊漂出去了0.00002,它算出來的結果您還敢信嗎?當然,要考察這樣的問題,靠分立元器件的電子技術也是很難實現的。這就也需要一個新的方法論。我這兒采用的新方法論,方法論是新的,方法卻是舊的,大略說來,就是早已有之“高速攝影”技術。說得再通俗一點,回放出來的效果,就是電視里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時最常見的“慢鏡頭”。
您瞧仔細嘍!我們先在論題的兩邊,各放上一個概念。不是要論證“文學不能消解道德”嗎?相應的,這邊放上一個概念叫“文學”,那邊放上一個概念叫“道德”。請注意,到這時為止,它們都只是概念。這是兩個很常見的概念,我們并沒有對其做出任何特別的定義,也就是說,我們就是按它們原來約定俗成的定義來使用它們的,包括它們的已經被約定俗成了的內涵和外延。此外,我們也沒有對它們的“狀態”做出特別的說明,這意思就是說它們都處在通常大家都理解的“正常狀態”。比如,道德正有效地規范著人們的社會行為,道德水平低下的行為會受到人們的批評,道德惡劣的行為會受到人們的譴責。文學呢,也同樣,比如文學的創作正處于正常的狀態,或者說健康的狀態,或者說正在像鄧小平要求的那樣,寫什么和怎么寫,正在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不斷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并沒有什么人會橫加干涉,豎加干涉有一點也不多。在這樣一種“概念化”的狀態下,這兩個概念之間肯定是會有一些交集的,是會相互產生某種影響的,前者會影響后者,后者也會影響前者。那么,如果我們想考察一下它們之間都有哪些影響,乃至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影響,當然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的。不過,有一點必須注意,一旦要進行這種考察,實際上就從靜態轉入了動態,原來放在那兒的那兩個概念,也就不再能繼續保持住“純概念”的狀態,而是立即轉變為兩種具體的社會現象。就像模擬計算機上的積分器,處于關閉狀態時怎么都好,一旦啟動,它原來設定的零點呆著呆著自個兒就漂移了。
第一個漂移,我們先姑且認為是可以容忍的,因為它是由論題本身自動帶來的。既然要討論的只是“文學不能消解道德”,就先不討論道德能不能消解文學吧。當然這個事后面還是不能不提到,因為有時候道德是可以消解文學的,消解起來一點外傷內傷都不留。
然后我們發現“文學”有了漂移。和原來放在這兒的“文學”不一樣了,現在這兒的“文學”已經不再是“純文學”了。從邏輯上說,這個“純”與“不純”,指的不是它的“純凈度”,不是它有沒有包含三聚氰胺一類的雜質,而是指它已經不再是一個概念,不再能用原來約定俗成的定義、內涵、外延來概括了。不過,與積分器零點漂移的隨機性不同,“文學”在此處的漂移是有特定方向性的——它與道德的關系被人為地拴在一起了。本來,“文學”與“道德”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獨立的范疇,它們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產生影響,但是同樣也可以不發生交集。事實上也正是有很多文學作品不正面涉及、甚至完全不涉及道德問題。然而,發生漂移以后的“文學”不再是這樣的了。“個人的創作成果一旦以文學作品的形式發表出來,它就進入了公共空間,具備了公共屬性,就必須承擔道德建設的義務。道德并不是文學的附加,道德與文學密不可分。”“以‘純文學’的名義‘純’掉道德是片面的,是另一種功利。”這真是讓人目瞪口呆的說法啊!專家們都是研究文學的,你們心目中的“文學”真的就是這種樣子的嗎?在你們讀過的大量文學作品中,有幾本是因為作家深感自己“必須承擔道德建設的義務”而寫出來的?
經過這樣的慢鏡頭回放,我們就不難看出發生這種零點漂移的那個原因,或者叫產生漂移的那個驅動力了——專家們是在給文學下達任務。他們顯然認為這正是他們的職責所在,既然痛感當下全社會的整體道德水準如此低下而且每況愈下,且越是每況愈下就越是每下愈況,也就是說,那個“況”越是低下,它日愈低下的原因也就暴露得越清楚,所以身在其位的專家們再不給文學下達這樣的任務,就有玩忽職守之嫌了。當然,他們又都是研究文學的,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文學的功能極限在哪里,誰愛信誰信,反正我不信。文學既不具備能把道德消解掉的惡法,也不具備“承擔道德建設義務”的良法。古往今來,古今中外,從來不曾有過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文學史,記載過某一時期的文學,是造成全社會整體道德水平低下的元兇,或者是承擔了道德建設義務的救星。正常的情況恰恰是,某一時期文學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道德水平的高低,通常都是與當時全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高低大體相當的。道理很簡單,文學活動無非是當時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正好反映了這一類專家們的思維慣性:他們很在意自己的職責,但是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專業。
但是,當我們的慢鏡頭繼續往下回放時,我們緊接著又發現了另一個不對勁的地方:放在“文學”對面的那個“道德”也發生了漂移,而且漂移出來的誤差更大得多!
在我們的慢鏡頭里,出現了一個新的命題:“當文學遭遇色情與暴力。”天哪,這是一下子就漂到哪兒去了?我們不是正在討論文學與道德的關系嗎?色情與暴力跟道德又有什么關系?當然,無論是色情還是暴力,都是一種社會現象,所以如果要把它們當作研究的對象,它們都可以成為一個單獨的研究領域,成為一個獨立的范疇。但有一點,它們都是社會學的范疇,不是道德的范疇;如果用簡單的道德判斷去考察社會生活中的色情問題或暴力問題,那純屬驢唇不對馬嘴。好吧,我們先忍一忍,暫時地離開道德一會兒,看看“當文學遭遇色情與暴力”時,究竟會遇到什么問題?在這種地方,真是用不著專家,只用得著常識。最常見的常識都能告訴我們:這是一個文化市場的管理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對“文學”稍有了解的人,會認為文學作品中絕對不能出現任何一點點色情或暴力的因素。問題僅僅在于要有一個“度”,包括對不同年齡段受眾的不同的度。首先要制定一個具有可操作性的規范,然后就是通過有效的行政管理來實施這個規范。如果在這方面出了問題,那也只有兩種可能,要么是你那個規范制定得不好,要么是你沒有把它執行好。還有別的嗎?沒有了。這個問題就這么簡單。在這個問題上說別的,包括作家的社會責任心也好,文學與市場的關系也好,甚至還說到盲目求新的蠱惑和市場利益的誘惑,全都是扯淡!
這就算是打了一個岔吧。打完這個岔,該回到“道德”上來了吧?沒有。很難判斷專家們是有意還是故意,反正他們從這兒漂出去以后,就再也沒有漂回來。
不過,得承認,這兒的一漂,是漂得相當專業的。要看明白專家們在這把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光靠常識確實不夠用了。
慢鏡頭接著往下放,出現了這樣一個命題:“道德是一個發展的概念,具有鮮明的時代性。”這樣講對不對呢?要做出判斷,就是一個專業性很強的判斷了。從表面上看,它講的是道德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隨著時代的前進有所變化,從這一點上講,它是對的。但我讀到這里時想到的卻不是這個。關于“道德”的這種本質,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有過一個經典的表述:“道德說到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兩種表述一比,巨大的差距一目了然,前者的不確切之處更是立刻凸現。什么叫“鮮明的時代性”?“狠斗私字一閃念”就是個有鮮明時代性的說法,但它根本不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只是某一階段權力對草民們的訓誡,表面上好像是某種道德訓誡,實際上跟道德沒有一毛錢關系,只是對人民群眾正當權利的無理剝奪。正是這種剝奪,這種凌空蹈虛、違悖天理人情的所謂道德訓誡,長時間地侵蝕了人們賴以培育道德涵養的人性基礎,才造成了當下道德水準日益低下的局面。那么,我們的專家,為什么放著現成的經典表述不用,非要自己生造出一個似是而非的表述來?若說以他們的地位所理應擁有的學養,竟然不知道恩格斯說過這樣的話,實在是有太過不敬之嫌,所以我寧愿猜想另有原因。而且,慢鏡頭接著往下放,那答案也就真的呈現出來了:“對舊有的道德觀念的突破,……不會(能)觸碰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底線。這種‘底線道德’在歷史的發展流變中具有穩定性,是人之為人的根本特征,也是人類社會得以維系的重要保障。”您瞧,這就明白了,原來我們的專家所說的道德,并不全都是歷史的范疇,而是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不是。那么,我們應該相信誰呢?您信誰您自個兒拿主意,反正我寧愿信恩格斯的。而一旦信了恩格斯,下一個合乎邏輯的推理必然是也只能是:我們的專家在這兒談論的既然不是歷史的范疇里所具有的內容,那么他談論的就不是道德。
這個零點漂移漂得實在太遠啦!
不是道德,又是什么呢?
我們都知道,道德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一種非剛性的約束,更多地依靠人們自己的主動、自覺的追求,而由于人與人必然會有的差別,這種追求也就必然會有層次、水準的不同,不需要也不應該存在某種整齊劃一的要求,而不同的層次、水準之間,也不存在排他性。能夠舍己為人固然很好,能夠利己達人也很不錯,用不著只把前者奉為正能量,并因此就把后者貶為負能量。總體來說,道德倫理是個容許多元共存的空間,不像價值倫理往往會有一元化的訴求,因為從本質上說,道德倫理是一種個體的修養,價值倫理則是一種群體的信仰。不幸的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具有一種喜歡追求整齊劃一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又被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不斷強化。宋開慶元年,即公元1259年,蒙古親王忽必烈攻打鄂州,南宋皇帝理宗亦不怠慢,調兵遣將準備守城。偏偏宋朝有個宦官叫董宋臣的,覺得萬一鄂州有失,蒙軍即可沿江而下,則朝廷所在的臨安就比較危險,所以建議“南遷行在以避敵鋒”,對與不對,也就是那么一說吧,連皇上都沒怎么當回事兒,不料卻有個芝麻大的小官寧海節度使判官,名叫文天祥,上疏請斬董宋臣,“以一人心”,也就是以此保持人心的一致。據我讀史的印象,這位文天祥應該是歷史上頭一位把腦袋和思想聯系在一起的人,凡是里面的思想不能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腦袋,就不能再讓其長在脖子上了。這個悠久的文化傳統綿延至今,究竟去掉了多少,還剩下多少,官方尚未見有權威的統計數字公布,但從一系列的慢鏡頭回放來看,它至少仍是產生各種零點漂移的原因之一。
“文學”漂移了,“道德”也漂移了,在這個“文學不能消解道德”的命題之下,還能剩下什么東西呢?恐怕只能說句大白話:誰也不能把誰怎么樣了。但是,在把一大段洋洋灑灑的文字唏哩嘩啦硬給拆巴成一片白地之后,卻也不能不有點兒心有戚戚焉者。不錯,文學是壓根兒沒那個能耐把道德消解掉的,反過來,道德要把文學消解掉,雖然不是絕無可能,怕是也并不那么容易。正像網友們嘲笑的那樣,當一次次表彰道德楷模的會每次都不知不覺開得像追悼會之后,道德其實也成了某種軟啦巴嘰的東西,得靠著不斷地煽情,才能勉強給自己找到一塊立錐之地。但是,社會整體道德水準的低下,卻很容易影響到文學從業者的整體道德水準,因為每個文學從業者也都是這個社會的組成部分。當我們看到這個群體中有越來越多的人正歡騰雀躍前赴后繼地參與到搖尾里去的時候,也確實可以為道德松一口氣了。這樣的文學,還能把道德怎么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