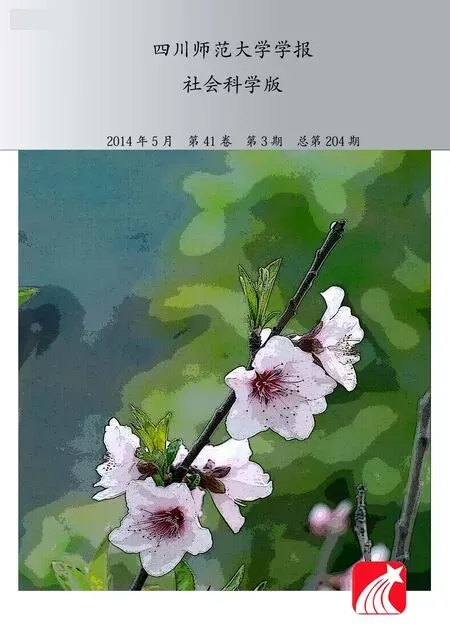邛崍《竹麻號子》研究的賦學意義
(溫州大學 人文學院,溫州 325035)
邛崍古稱臨邛,是著名的巴蜀古城,也是西漢人司馬相如、卓文君愛情故事的發生地。2013年8月,中國賦學會和四川師范大學聯合在邛崍舉辦賦學討論會。與會者不僅重新談起2100多年前的浪漫故事,而且討論了賦的性質和起源等問題。會議之所以在邛崍召開,是因為這里提供了地點、人、主題的因緣際會。這是頗讓人感到興趣的。為此,今想把這幾個元素結合起來:通過邛崍的名片——《竹麻號子》,來談談四川師范大學的一個研究特色,進而討論中國賦史上的重要問題——賦的性質和起源問題。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的關鍵是賦和風的關系問題。
一 邛崍《竹麻號子》和對它的考察
《竹麻號子》可以說是邛崍的驕傲。它于2008年列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它的傳承人名叫楊祚欽。
早在2006年7月,四川師范大學西部民歌研究所萬光治教授就從學術角度對《竹麻號子》作了考察。這個月中旬,萬光治團隊到達邛崍,對邛崍民歌進行全面采錄,在天臺鎮、平樂鎮、夾關鎮共采錄了40首民歌(編號1536-1575)。其中有5首同造紙相關聯的民歌,也就是由宋樂攀(1946年生)等二人演唱的《竹麻號子》(編號1539)、由楊祚欽(1942年生)等五人演唱的《竹麻號子》(編號1559),以及由楊祚欽演唱的《造紙山歌》(編號1560、1561)和《壩區竹麻號子》(編號1566)。
考察表明:《竹麻號子》是造紙工人在打竹麻時所唱的一種勞動號子,主要保留在邛崍境內的平樂鎮。它唱腔質樸、粗放、高亢,具有濃郁的川西地方特色。
和其它勞動號子一樣,《竹麻號子》的歌唱方式是一領眾和。當鉤子手手執長釘耙,把需要捶打的竹麻交給工人時,工人們就配合勞動節奏唱起了《竹麻號子》。竹麻號子的唱腔富于節奏和變化。唱詞的內容比較豐富,樂段的伸縮性也比較強,段落之間常用“嗦咿”、“喂”、“喲嗬”等襯詞,并且采用一種“數十二月”的傳統唱法。比如,《竹麻號子》包括《上工號子》、《中午號子》、《收工號子》等段落。據楊祚欽公布的資料,其中《上工號子》的歌詞是:
正月里晨花齊開放,喲啊,二呀月燕子上高梁羅;
三月里陽雀叫頭上,喲啊,四呀月農忙正栽秧羅;
五月里端陽鬧龍舟,喲啊,六呀月家家曬衣裳羅;
七月里荷花滿池塘,喲啊,八呀月十五桂花香羅;
九月里重陽蹬山上,喲啊,十呀月豐收把酒嘗羅;
冬月里家家把火烤,喲啊,臘呀月過年人人忙羅。
喲嗬,喲嗬,喲嗬喲嗬嘿,哩喲嗬喲嗬哩呀。
考察人員注意到:《竹麻號子》有很深厚的歷史背景。它同從宋代開始繁榮的造紙業密切關聯。在宋代,成都地區有一半草紙產于古鎮平樂,所以古有“成都草紙半平落”的說法。據說平樂的造紙作坊來源于浙江,現在保存得比較完整的是平樂鎮同樂村的蘆溝——這里有74處造紙遺址①。另外,制作手工竹紙總共有72道工序,包括砍竹、浸泡、捶竹、選料、漿灰、蒸頭鍋(篁鍋蒸煮,一層竹麻一層石灰)、打竹(用6米長的木桿把竹料搗碎)、洗料、蒸二鍋、洗料、發酵、打堆、擇料、搗料、淘料、漂白、打槽、加滑水、撈紙、壓水、掀紙、打吊子、貼紙、曬紙、清點、包裝等等[1]231。
在以上這些環節中,造紙工人有很多機會歌唱,比如砍竹的時候可以唱山歌,撈紙的時候可以唱小曲。而當竹料經過浸泡、初步捶打、篩選、漿灰、蒸煮等工序后,工人要借著篁鍋里的高溫把竹麻纖維進一步搗碎。這就是打竹麻的環節。這時,工人要站在熱氣騰騰的篁鍋上用力捶打,也用力呼吸(圖1)。出于協調勞動的需要,人們便唱起了《竹麻號子》。

圖1.平樂工人打竹麻的勞動場景
二邛崍《竹麻號子》和夾江《竹麻號子》、邛崍《造紙山歌》的比較
萬光治團隊對《竹麻號子》的調查并未止于邛崍。事實上,從邛崍往南走120公里,在峨眉山下的夾江縣,也有豐富的手工造紙的歷史遺跡。據推測,夾江的造紙史超過了500年。在這里,同樣流傳《竹麻號子》等造紙民歌[2]。
萬光治團隊是在2008年9月24日到達夾江縣的。這一天,在夾江縣迎江鄉大橋村四組,他們向一位名叫鄭文均的老人(73歲)采錄了6首民歌,其中4首是《竹麻號子》,另外2首是山歌。
鄭文均所唱的4首《竹麻號子》,分別屬于平腔(編號4227)、高腔(編號4230)、銀絲調(編號4229)、胡琴調(編號4231)。一般來說,平腔指的是旋律平緩的歌唱,用真聲演唱,富于詠述性,其音區不高,接近通常的朗誦調。高腔指的是高亢、響亮的歌唱,曲調音域寬廣,旋律有較大的起伏。銀絲調、胡琴調則是由于唱詞中的襯詞而得名的,比如胡琴調的襯詞中有模仿胡琴的擬聲詞。有人說:邛崍的《竹麻號子》也和夾江《竹麻號子》一樣,有高腔、平腔、連環扣、銀絲調、扯麻花之分。既然如此,這兩者之間便可能有傳承上的關聯。
但是,據四川師范大學西部民歌研究所周翔分析,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簡單。周翔認為,以上這些造紙民歌,音樂形態上的特征是頗不相同的。
1.邛崍平樂鎮宋樂攀、李永林演唱的《竹麻號子》(編號1539)。這首號子歌的音樂有一定的當代特點,感覺是在保留《竹麻號子》勞動音樂節奏的基礎上,由現代人進行了整理。演唱者的狀態比較舞臺化、歌唱化,與勞動場景的結合不夠密切。
2.邛崍平樂鎮楊祚欽等五人演唱的《竹麻號子》(編號1559)。這首歌的音樂可分為兩部分:前部是引子,旋律既和以上一首(編號1539)相同,也和網上視頻中的《竹麻號子》相同,估計應表演要求進行過組合。后部是主體,以《十二個月》為唱詞,采用傳統唱腔。其音樂特征是:四分之二拍,節拍規整,音樂律動強,與勞動節奏配合較密切;音域較窄,在5度內,級進加小跳;采用一領眾和的歌唱方式,演唱時再現了勞動場景;音樂旋律為單句的循環反復,和部對領部尾句加以重復,尾聲則較為歌曲化。
3.邛崍平樂鎮楊祚欽演唱的《壩區竹麻號子》(編號1566)。從音樂角度看,這首歌和以上1559號是同一首歌。
4.楊祚欽演唱的《造紙山歌》(編號1560、1561)。這兩首歌旋律相同,只是唱詞不同。曲名稱“悲調”,大概指音樂具有抒情特點——整段速度較慢,情緒較《竹麻號子》更為緩和;句幅被拉開,音域也加寬,多大跳與旋律的回旋;音樂多起伏,表達出情緒的起落。
5.夾江《竹麻號子》,四首歌雖然分屬平腔、高腔、銀絲調、胡琴調,但它們有共同點,即演唱形式都是一領眾和,節拍都是四分之二拍。

高腔號子的特點是:和部唱腔相對長一些,一拍一字或兩拍一字。旋律中的骨架音是2、5,多級進和3度音程的組合。

以上說的是音樂學角度的觀察。如果從文化傳承的角度看待以上情況,那么,它們應該說明了這樣一些事實。
1.在邛崍,楊祚欽所傳承的《竹麻號子》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因為它保留了較多的傳統音樂成分,反映了打竹麻勞動對歌唱的制約。但是,其旋律資源卻不豐富,采錄時的歌唱往往重復。由此可見,隨著手工造紙這種傳統工藝的消失,即使在有上千年造紙歷史的邛崍,《竹麻號子》也不免于衰變,亦即被新的歌唱風尚所侵蝕。《竹麻號子》一旦走上舞臺,成為宣傳工具,這種衰變就更加明顯了。
2.相比之下,夾江《竹麻號子》的表現要更為生動一些。在唱腔上,它有平腔、高腔之分;在曲調上,它有銀絲調、胡琴調、扯麻花、連環扣之分。為著同勞動節奏相配合,它采用一領眾和的演唱形式,節奏規整,強弱分明。它的和部詞生動活潑,富于生活情趣,音樂的色彩也很豐富。另外,據統計,它遺留下來的歌詞有150多首[3]463。它和邛崍的《竹麻號子》很不一樣,兩者之間并不存在同源關系。
3.通過邛崍、夾江兩地《竹麻號子》的比較,可以看到勞動方式對于勞動音樂的積極作用。據考察,夾江的手工造紙傳統比邛崍保存得完好。夾江手工造紙最盛于清朝,曾是清代科考的專用紙,稱“文闈卷紙”,后來又被定為“貢紙”。民國年間有記載說:“四川造紙區域為夾江、銅梁、合川、廣安四縣,而以夾江所產為最多。”[4]305可見夾江造紙業遠盛于邛崍。1949年以后,盡管受國家經濟體制影響,個體經營的手工紙業舉步維艱,但在1978年以后,夾江造紙業得到改善,其書畫紙產量一度(1990年)達到全國的40%[5]36。2003年,文化部啟動“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夾江竹紙制作技藝受到重視,遂于2006年列為中國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樣一來,制作手工竹紙的全部工序便在夾江得到恢復,竹紙制作技藝保護點也得以一一建成[3]16-18。圖2便是對夾江工人打竹麻的勞動場景的反映。夾江《竹麻號子》的豐富性、原始性,應該是以這種對勞動方式的保護為條件的。

圖2.夾江工人打麻的勞動場景
4.從另一方面看,在勞動號子的傳承過程中,歌手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歌手離開勞動方式,勞動方式遺失歌手,這兩種情況都會造成號子音樂的散失。比如自貢的《鹽工號子》、隆昌的《麻布神歌》,都是勞動方式尚存而歌曲失傳的例子。而楊祚欽所演唱的《竹麻號子》和《造紙山歌》,則反映了歌手的歌唱風格對音樂的影響:盡管號子、山歌是兩個不同的民歌種類,號子強調律動,山歌則節奏自由;但楊祚欽演唱的《竹麻號子》和《造紙山歌》,卻有很多相同——它們的切分音節奏是相同的,旋律骨架系統是相同的,宮音也一樣。這一點也意味著,《竹麻號子》和《造紙山歌》,乃用于造紙勞動的不同工序。
三 作為“風”的《竹麻號子》
萬光治的民歌調查工作已經進行了十年。2004年,當他卸去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職務之時,就建立了西部民歌搶救小組,并且購置了一部豐田越野作為座駕。他采用“先打游擊后攻城”的策略,先是前往甘肅、新疆等地進行資源調查,然后有計劃地進行四川民歌的采錄。他走遍四川省181個縣,像卷地毯一樣,收集到各種民歌約4000首。2011年,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羌山采風錄》;2013年年底,多卷本的《四川民歌采風錄》也已結集。
“采風”是萬光治對自己的工作方式的評價,也是他對這幾千首西部民歌之性質的認定。據此,我們可以把他看作現代的“輶軒使者”。就這一名稱而言,他是當之無愧的,因為他不僅有名牌“輶軒”,而且有進口的“木鐸”——有很高級的錄音錄像設備。
從古代留存的資料看,“風”、“采風”、“采風之官”是三個相關聯的詞語。歷經兩周而至秦漢,由于社會時尚和政治需要,“采風”的功能和范圍有一個發展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虞夏以來,諷謠始作,采風者是“樂師”,主要采集“歌謠之言”。此即《左傳·襄公十四年》引《夏書》所說(亦見于《尚書·胤征》[6]151下):“遒人以木鐸徇于路。”杜預注:“遒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謠之言。”[7]1958
第二階段:兩周之時,歌謠用于禮樂詩頌,并用于制訂雅言、勸諫君王,采風者是“遒人使者”,兼采“代語、童謠、歌戲”和“怨刺之詩”。此即劉歆《與揚雄書》所說(又見于應劭《風俗通義序》[8]11):“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9]518
第三階段:到了兩漢,禮儀殘缺,武帝追慕周秦,興禮制樂,采風者稱“風俗使者”,所采偏重“風俗”。此即《漢書·藝文志》所說:“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10]1756從《漢書·藝文志》看,采風之官中還有一種叫“稗官”,主要采集街談巷說。
那么,萬光治是哪一種采風者呢?我看比較像夏周之時的樂師。他有三個身份:一是文化傳承者,因為他有搶救遺產的責任心;二是藝術家,因為他有對民歌資源的珍愛;三是研究者,因為他有辨別真偽的敏感,也有記錄風俗的自覺。事實上,從西周開始,就有一種虛飾頌聲的詐偽歌謠;這種偽“風”到漢代更盛,以致“謠言”成了一種貶詞②。現代的采風之人,要在沙里淘金,就必須具備以上三個身份。
從這一角度看,《竹麻號子》是現代的“風”詩。如果把民歌分為號子、山歌、小調三類,那么號子便是民歌中同勞動生產關系最密切的類型。如果按勞動的類別,把號子分為搬運號子、工程號子、農事號子、船漁號子、作坊號子等五類,那么,由于地理環境多樣,四川是號子形態特別豐富的地區,擁有作坊號子這一較特殊的類別③。隨著社會發展,傳統的手工業勞動往往被現代機械所取代,很多作坊號子失去了生存土壤,瀕臨消亡。《竹麻號子》集中反映了以上特點,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當作現存“風”詩的代表。
四 從《竹麻號子》看“賦”和“風”的關聯
不過,以上這些《竹麻號子》卻是彼此有別的,按其性質可以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夾江《竹麻號子》,第二種是邛崍《竹麻號子》,第三種是出現在媒體上的《竹麻號子》。夾江《竹麻號子》是作為勞動號子而存在的,一直未離開孕育它的生活土壤,可以說是本色的“風”。邛崍《竹麻號子》有歌手而無勞動,可以說是勞動號子的遺存。而當《竹麻號子》變成“《竹麻號子》藝術團”的保留節目,進而登上中央電視臺“歡樂中國行”的節目之時,它顯然就不再是“風”了——這時它在功能上被賦予“藝術”(而非生產手段)和“歡樂”(而非勞動情感)的定義。據媒體報道,《竹麻號子》藝術團成立于2005年,其藝術表演由中央電視臺播出于2009年6月13日。我認為,若用古代的文體名來作類比,那么,這里有從“風”到“賦”的跨越。
本文所說的“風”和“賦”,是《周官》時代的概念,即《周禮·大司樂》所說的“風、賦、比、興、雅、頌”[11]796上。盡管《周禮》成書于戰國到漢代初年,但從《漢書·藝文志》的記載看,《大司樂》這份文獻直接來自“六國之君魏文侯”[10]1712,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兩周。而若把《周禮》和西周時期的可靠文獻相比證——比如拿《周禮》和西周金文相比證——那么,《周禮》所載職官,四分之一以上可以在西周金文中找到根據。這就說明,《周禮》一書保存了許多西周時期的職官制度史料④。在《大司樂》中有兩個相互對應的課程組合:一是大師教瞽矇的“風、賦、比、興、雅、頌”;二是“以樂語教國子”的“興、道、諷、誦、言、語”。這兩組課程便是同關于儀式用樂、諷諫用詩的早期記錄相吻合的,可以相信是周代的制度。
以上所說也意味著,“風”和“賦”代表了樂師時代兩種傳述“詩”的方式:“風”是按其本來面目采錄民間語言、童謠、歌戲,并進行傳述;“賦”則是用雅言的方式或“以聲節之”的方式進行傳述。關于這一點,我在《詩六義原始》一文中作過詳細論證[12]222-229。這一論證可以支持關于“賦”的一個經典的定義,即《漢書·藝文志》引先秦之《傳》語所說:“不歌而誦謂之賦。”[10]1755這句話說的就是風俗歌謠和“賦”的關系。
同“六詩”之“風”與“賦”相對應,國子所學“樂語”中有“諷”與“誦”。鄭玄注《大司樂》說:“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賈公彥疏:“云‘倍文曰諷’者,謂不開讀之;云‘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皆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為吟詠,以聲節之為異。”[11]787下所謂“樂語”,指的是儀式用語。因此,作為“風”的通假字,“諷”應該是對儀式上所歌“風”詩的復述。《周禮·春官》說:大師須于“大祭祀帥瞽登歌”,瞽矇則要“諷誦詩世、奠系,鼓琴瑟”[11]797中。可見“諷”和“誦”的主要內容是古歌(“詩世”)和黃帝以來的世系傳承(“帝系”)。一方面,為尊重詩世、帝系的原貌,須采用“諷”的方式,即“背文”、“不開讀”;另一方面,為適合儀式要求,須采“吟詠,以聲節之”的方式,即富于儀式性的朗誦。
“賦”“誦”等方式,意味著對“風”的改造有其必然性。因為采風主要有兩個目的:其一用于儀式,其二用于勸諫。這兩個目的都要求對“風”進行改制。除掉儀式要求外,《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記的一件事,可以解釋這種改制的必要性。《左傳》說:衛樂師師曹受命以歌款待孫蒯,師曹“恐孫蒯不解”詞意,于是改而“誦之”[7]1957上。這件事說明,同歌相比,“賦”和“誦”是更加明白易解的。這就印證了上面的判斷:“賦”和“誦”是兩種不同的朗誦方式,賦是雅言誦或保留了歌詩音節的韻誦,而誦則是離開“風”的儀式性誦讀。
有必要指出,“賦”、“誦”等方式都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因為“六詩”是瞽矇受教的科目,“樂語”是國子受教的科目,既然稱“教”,則這些科目便各有其專門性。具體說來,只有具備極好的辨音能力,才可能“風”;只有兼通方言和雅言,才可能“賦”;而對于國子來說,只有習得各地方言、土歌,才可能“倍文”;而一旦按儀式的要求來對“諷”加以轉換,就必須學會“吟詠,以聲節之”,也就是“誦”的方法。正因為這樣,《左傳·文公四年》說賦是“肄業”(習歌)之人所長,是一種專門伎藝[7]1841上。
關于“風”、“賦”、“誦”之法的專門性,《國語·周語》還有一段涵義豐富的記錄,云:
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13]9-10
這段話說的是“天子聽政”,但從中可以窺見儀式活動的一般。這段話記錄了聽政過程,其中有獻詩、獻曲、獻書、箴、賦、誦、諫等項目;記錄了聽政對象,其中除公卿至于列士外,有瞽、史、師、瞍、矇、工等技術人材。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出現了三種盲樂官:一為“瞽”,即雖然有眼球,但眼皮天然閉合因而無所見的樂官;二為“瞍”,即眼球縮壞的樂官;三為“矇”,即有眼球而無見的樂官,亦即俗所謂“睜眼瞎”⑤。他們恰好分別承擔了“風”、“賦”、“誦”的職責。這件事是富于社會生理學內涵的。因為,根據“目無明則耳聰”的道理,“瞽”、“瞍”、“矇”三者的順序是有規則的:既是失明程度之強弱的順序,又是辨音能力之強弱的順序,而且是某種職務的順序。“獻曲”者須精于記音,以識別曲調,所以由瞽這種天生的盲人承擔;“賦”者須有較強的記音能力,以識記“風”歌,所以由瞍這種未必天生失明,但卻完全失明盲人承擔;“誦”者須聽懂“風”和“賦”的內容,所以由“矇”這種稍有光感的盲人承擔。
關于“瞽”、“瞍”、“矇”等樂官的分別和分工,頗多資料作了記載。盡管有些文獻會把這幾種盲人的名稱彼此混淆,但有一個基本判斷卻很明確:瞽是盲樂官中最具技術能力的人物,承擔掌管原始史料的職責⑥。這些原始史料或稱作“詩”,或稱作“史”,或稱作“曲”,從文體分類的角度看,其實都可以歸入“風”的范疇。因此,所謂“賦”和“誦”,可以看作對這些史料的加工。前文說到,這種加工是祭祀儀式和外交活動的需要;現在可以補充的是,這也是王者聽政的需要。《國語·楚語》說:“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13]551這段記載表明:正因為“風”是方言土語,王者難以聽懂,所以要用兩種方式來對它加以傳達:其一是“導”或“書”的方式,由瞽史實行,主要傳達大義;其二是“賦”和“誦”的方式,由矇工實行,主要傳達辭意。“詩”、“史”、“曲”等同樣需要這種轉達。總之,改“風”為“賦”、為“導”、為“書”,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現在,聯系《竹麻號子》,我們對“風”和“賦”的古老關系,又可以有新的理解了。《竹麻號子》表明:真正的民歌,不僅是同方言土語相聯系,而且是同民眾的勞動和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生存的土壤。一旦脫離土壤,任何民歌都不免會變質。所以,《周禮·春官》介紹“六詩”和“樂語”時,使用了兩個涵義相近的詞:一是“風、賦、比、興、雅、頌”的“風”,用以指原生態的民間謠言、歌戲,以及對它們的忠實記錄;二是“興、道、諷、誦、言、語”的“諷”,用以指對“風”的樸素傳述,以及它所采用的“背文”、“直言”的方式。這說明,任何形式的“采風”,都不可避免要使用“諷”和“賦”的手段,作為“風”的補充。我們在很多場合看到過萬光治教授的民歌演唱,同時也看到過他的民歌辭朗誦,其實,前者就是所謂“獻曲”,后者則是“登高能賦”。
關于民歌變質的原因,前文還指出了另外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喪失了歌手,二是喪失了承擔它的社會組織。比如自貢的《鹽工號子》、隆昌的《麻布神歌》,都是因歌手喪失而失傳的例子。而古樂脫離其社會組織,較明顯的例子是《漢書·藝文志》所說:“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10]1712“鏗鏘鼓舞”是說音樂尚存,“不能言其義”則是說由于喪失了承擔儀式的隊伍而遺忘了其儀式涵義。如果要究其更深一層的原因,當然,應該歸咎于養育歌手及其隊伍的社會條件的喪失。所謂“禮壞樂崩”,便是因為這些喪失而形成的。但正是由于這些喪失,“賦”這一文體卻得以產生了。
“賦”體的產生,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一是根據《周禮·春官·大司樂》的記載,大司樂實施的國子之教,有樂德、樂語、樂舞三個系列課程,目的是培養能致鬼神、和邦國、諧萬民、安賓客、悅遠人、作動物的儀式人材和行政人材[11]787下。這些人材已掌握“賦”“誦”之法。二是根據《左傳》、《國語》的記錄,由于經過了“樂語”教育,所以公卿士大夫往往能夠“賦政于外”,并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13]258-264。三是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載,這種“賦”的才能,在春秋以后最終結晶成了賦體:
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10]1756
這就是說:賦產生于“學詩之士”把他們所專長的“聘問歌詠”變成了新文體,亦即賦。而若追蹤其源頭,則這種作為新詩的辭賦乃來源于古老的“不歌而誦”。這件事啟發我們:包括《竹麻號子》在內的那數千首四川民歌,一旦出版,便提供了造就一種新詩體的可能。
(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由四川師范大學西部民歌研究所周翔、張科成提供。特表感謝!)
注釋:
①據四川師范大學西部民歌研究所2006年7月20日調查筆記。
②參見以下資料:《楚辭·離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王逸注:“謠,謂毀也。”洪興祖補注:“言眾女競為謠言,以譖愬我。”(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頁14-15。)《后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李賢注:“謠言,謂聽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版,頁1851。)
③參見:張亞初、劉雨《兩周金文官制研究》,中華書局1986年版;李晶《春秋官制與〈周禮〉職官系統比較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04年碩士學位論文。
④參見:杜亞雄《漢族民歌音樂形態分類芻議》,《樂府新聲》2011年第1期;彭子華《漢族民歌分類研究的思考》,《交響》1998年第2期;戢祖義《中國勞動號子》,《云嶺歌聲》2004年第9期。
⑤許慎《說文解字·目部》:“矇,童矇也,一曰不明也,從目蒙聲。”“瞍,無目也,從目叜聲。”“瞽,目但有眹也,從目鼓聲。”段玉裁注:“無目與無眸子別。無眸子者,黑白不分;無目者,其中空洞無物。”劉熙《釋名·釋疾病》:“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蒙,有眸子而失明,蒙蒙無所別也。瞍,縮壞也。”
⑥例如《詩經·大雅·靈臺》說“矇瞍奏公”;《國語·楚語》說“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蒙不失誦”;《左傳·襄公十四年》說“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呂氏春秋·達郁篇》說“矇箴,師誦”;《淮南子·主術》說“瞽箴,師誦”;《賈子新書·保傅篇》說“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從這些文獻中可以概括出如下一種二分關系:

典據關于瞽史掌詩關于矇瞍掌誦《詩經·大雅·靈臺》矇瞍奏公《國語·楚語》臨事有瞽史之導/史不失書宴居有師工之誦/蒙不失誦《左傳·襄公十四年》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呂氏春秋·達郁篇》矇箴,師誦《賈子新書·保傅篇》瞽史誦詩工誦箴諫
他們的主要區別是:瞽的地位較高,掌歌詩,用于“導”、“書”,有“瞽史”之稱;“矇瞍”的地位較低,掌誦諫,稱“工”或“師工”。
參考文獻:
[1]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2]李盈盈.歌唱與勞動:四川夾江馬村鄉竹麻號子調查研究[D].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2011.
[3]夾江縣志[M].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
[4]楊大金.現代中國實業志·制紙業[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8.
[5]劉少泉.夾江手工紙與中外經濟文化[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
[6]尚書正義[G]//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7]春秋左傳正義[G]//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8]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M].2版.北京:中華書局,2010.
[9]錢繹.方言箋疏[M].李發舜,黃建中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1.
[10]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11]周禮注疏[G]//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
[12]王小盾.詩六義原始[M]//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
[13]國語[M].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