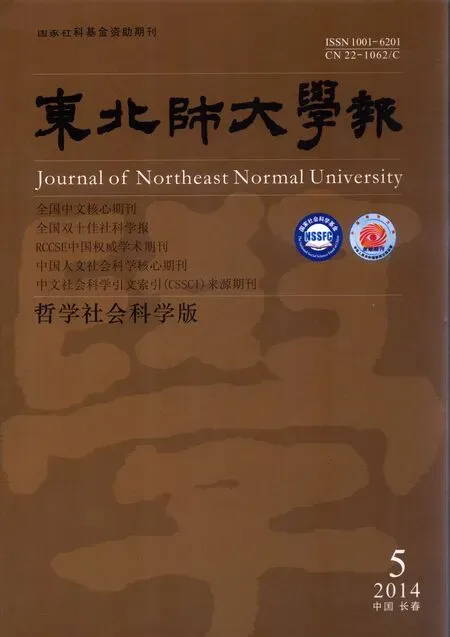中歐氣候變化治理利益格局比較及對策分析
張麗華,王 樂
(吉林大學 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中歐氣候變化治理利益格局比較及對策分析
張麗華,王 樂
(吉林大學 行政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全球氣候治理關系到世界各國和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國家利益決定一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立場,成本與收益的激勵決定一國在氣候治理的國際合作中的態度。歐盟與中國在氣候治理中的不同表現是基于各自在發展階段、能源結構、貿易結構等方面的國情不同導致的不同的節能減排成本與激勵水平。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需要有效的國際合作,應加強氣候問題的科學研究,促進節能減排的技術推廣,避免國際合作中的泛道德化和目標過高等傾向。
國家利益;氣候治理;歐盟;中國;合作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9次締約方會議在華沙經歷近18個小時的延時后,于2013年11月23日晚終于打破僵局,達成三項主要共識:最終就德班平臺決議、氣候資金和損失損害補償機制等焦點議題簽署了協議。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發表聲明說:華沙氣候大會通過的決定,將成為在2015年達成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普遍協議的重要基石。眾所周知,世界各國為應對氣候變化所進行的努力與博弈已然成為當前國際社會最為復雜的全球性議題之一,這一議題也成了學界研究國際合作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最熱門案例。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復雜性體現在雖然各國已就該問題的重要性達成政治上的共識,但在如何承擔減排責任的談判和實際行動方面卻各有各的主張,可謂“空談”多而“實干”少。本次華沙氣候大會三個議題的實質性爭議都沒有解決。發達國家只是答應要出資,但是什么時候出、出多少都沒有明確;也沒有對何時以及如何建立補償機制做出任何承諾。本文將運用國際關系學中國家利益的概念和理論,結合中國和歐盟在氣候問題中的具體情況,分析造成這種局面的深層原因,并嘗試為促進各國在這一領域中的合作、積極提供全球公共產品提供一些對策和建議。
一、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
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彼此間的聯系日益緊密,機遇共享,風險共擔,每個人的安全、健康和幸福都與所在國家參與國際合作的質量息息相關。正是為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才會有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也正是出于對本國利益的考慮,才使得這項有益的合作充滿了阻礙和挑戰。要想分析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出現諸多困難的根源,并且希望提出推進這項合作的方法,就有必要對氣候變化中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及其關系進行考察。
(一)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是指“主權國家全體人民的物質和精神需要”[1],按性質可分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幾大類。國家的決策者無一不是按照本國的國家利益,至少是打著維護本國利益的旗號來制定和執行對外政策。如果判斷什么是國家利益比較簡單,那么判斷何種國家利益更為重要,更應該得到政策的優先考慮就比較困難了。這就是世界各國都知道控制氣候變化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也即符合各國自身的利益,但各國又都在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具體指標上討價還價的根本原因。要想理解各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中的立場和行為模式,并為推動這項國際合作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深入了解國家利益的層次、排序與實現的標準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政策制定時一般按照重要性和緊迫性對不同的國家利益進行排序。不同類型的國家利益具有不同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涉及民族生存的安全利益,然后依次為維護本國基本制度與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政治利益,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的經濟利益,擴大本國影響力與美譽度的文化利益。各種類型的國家利益在不同條件下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還要受到實現國家利益的緊迫程度的影響,所謂緊迫程度即實現國家利益的時間。如此一來,為了給國家利益排序,可以將國家利益分為以下四種基本類型:當前重要的國家利益、當前次要的國家利益、未來重要的國家利益、未來次要的國家利益[2]。
制定政策時,當前重要的國家利益要優先于未來次要的國家利益,這一點是毫無爭議且容易做到的,但要在當前的次要利益與未來的重要利益之間做出選擇就比較困難了,人們往往對近期可實現的利益有較強的偏好,會放大當前利益的效用,最終傾向于選擇當前的次要利益而放棄未來的重要利益。人類工業化的生產生活方式導致的氣候變化,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方式正是這種偏好的典型體現。
其次,處于不同發展階段,擁有不同國情的國家的利益排序是不同的。冷戰結束以來,世界的安全形勢大大改善,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在大力發展本國經濟,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在把握由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發展機遇的同時,努力擴大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甚至一度以單邊主義的姿態向別國推廣自由、民主等西方價值觀。而朝鮮則走上了先軍政治的道路,大力發展核武器和遠程導彈,顯然是將安全利益擺在了第一位。面對全球氣候變化這一事實,海島國家與俄羅斯所處的環境與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全球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將直接威脅到海島國家的生存,而俄羅斯將獲得更加溫暖宜人的氣候和開辟北冰洋航線的利益。對于中東產油國來說,作為收入主要來源的石油出口帶來的經濟利益顯然遠遠大于節能減排帶來的環境利益。由此不難理解各國在氣候問題上存在態度差異。
最后,國家利益的實現需要考慮政策的成本與收益。任何能滿足一國生存與發展需要的東西都可以成為國家的利益,但國家利益不等于主觀愿望,更不可能存在無須任何成本就可獲得的國家利益。如果不計成本地去追求某種國家利益,實際上是以損害國家的其他利益的方式去滿足國家的某種需要,本質上是對國家利益的傷害。即使是涉及國家存亡的安全利益的戰爭也不是不計成本的,冒著人類毀滅的危險,或者至少是全國大部分人口和城市被摧毀的危險去打一場核戰爭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即使贏得了戰爭,這樣的勝利也是沒有意義的。對氣候變化問題的不同態度恰好反映了各國對各自成本與收益的不同考量。減排成本低,技術條件好,減緩氣候變化獲益最大的歐盟國家積極性最高;石油出口大國俄羅斯和化石能源消費大國美國則由于減排成本高而對制定減排義務標準持消極態度。
(二)國際利益
“保護我們共同的家園”這一口號反映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盡管仍有不少科學家持不同看法,但至少鮮見一國公開反對節能減排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這說明各國政府至少表面上認可應對氣候變化符合國際利益。既然符合國際利益,為何各國又各有主張,甚至一些國家對該項事業持消極態度呢?這就必須分析國際利益內在的復雜性。
首先,國際利益具有多樣性與對立性。不僅不同國家和國家集團之間的利益可能是對立的,即使是看似符合全人類利益的全球性國際利益也可能彼此發生矛盾和沖突。維護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與尊重民族自決權之間,維護自由貿易原則與實現貿易公平之間都存在著不能完全調和的矛盾。拯救人類的生命一定是符合國際利益的,節能減排防止氣候變化可能可以減少自然災害,從而挽救人的生命,同時發展中國家利用化石燃料發展經濟減少饑荒,同樣是挽救人的生命。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消除貧困都符合人類的共同利益,但在同一時間不可兼得,必須做出取舍。
其次,國際利益與國家利益是對立統一的。國際利益不等于集團利益,某種利益只有符合所有國家的根本利益才能稱為國際利益。和平的國際環境,公正的國際秩序,良好的自然生態都是典型的國際利益,這種利益實現時世界各國都能從中受益。另外,國家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產生的負外部性很可能損害國際利益,即使這種行為是完全正當的。例如某國發展防御性的先進軍備維護國家安全,這可能會引起鄰國的擔心從而引發軍備競賽,惡化地區和世界的安全環境,但我們不能說任何國家維護國家安全的努力都是不利于國際利益的。
最后,國際利益并不天然具有道德優先性。國家的道德不等于個人的道德,個人為了他人利益犧牲自身利益是道德高尚的表現,而國家為了所謂的國際利益而放棄對本國利益的維護則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強迫他國做出自我犧牲以換取所謂的共同利益則更加是不道德的行為。當今國際社會討論全球性議題,尤其是氣候變化的議題時有一種樂觀主義的人類共同體意識,似乎只要事關全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各國就應該無條件地服從甚至于不惜犧牲本國的利益來實現這一崇高的目標。這種傾向反而大大阻礙了問題的真正解決。國際利益的實現不應以損害具體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既然工業化國家使用化石燃料造成海平面上升危及島國的生存是不道德且應該承擔責任的,那么為了挽救島國而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大量的失業和貧困則同樣是不道德的。
二、歐盟、中國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的利益格局
歐盟和中國同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關鍵參與者。在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歷史上,歐盟始終扮演著積極推動者的角色,2011年德班會議后,歐盟更是確立了在此一議題上的領導者地位。據歐盟委員會研究報告預測,歐盟15國在2008—2012年的年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相比基準年將減少14.2%,大大高于《京都議定書》中承諾的目標[3]。歐盟早在2007年就單方面承諾了自愿減排目標:到2020年時,在1990年排放水平基礎上減排20%,并將可再生能源比例提高到20%,節能20%[4]。在氣候變化治理問題中,中國“是積極而又謹慎的參與者”[5],“中國在堅持不承擔量化減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的同時”,“以比過去靈活、更合作的態度參與國際氣候變化談判”[6]。雖然都積極參與全球氣候變化的治理,但在具體措施特別是減排義務量化指標方面,中國和歐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可以從歐盟與中國在治理氣候變化中的利益差異中獲得解釋。
(一)歐盟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的利益格局
歐盟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的積極態度反映出其背后特定的利益格局,這種格局的基本特征是相對于其他國家和地區,歐盟節能減排的收益較大而成本較低。這種所謂的收益主要體現在如果不這么做將要承擔的代價上,盡可能地降低損失就是獲得了最大的收益。
一方面,歐盟國家的環境脆弱性高。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二工作組的評估報告[7],如果不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到2080年,歐洲可能發生嚴重的生態災難,某些地區的物種損失可能高達60%。氣候變暖將大大增加南歐地區熱浪和火災的發生的機率,增加中東歐地區夏季干旱發生的概率,從而影響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歐盟國家屬于經濟發達人口密度高的地區,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現象增加造成的損失將比給人口少經濟欠發達地區造成的損失大得多。
另一方面,歐盟國家能源安全面臨挑戰。歐盟是和中國、美國并列的能源消耗大戶,預計到2020年,其對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對外依存度將達到70%,不僅受到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更面臨不能得到穩定供應的風險。歐盟國家消費的天然氣主要來自俄羅斯,自從2009年俄羅斯與烏克蘭就天然氣價格與過境費用發生爭執之后,曾數次切斷鄰國的天然氣供應,這使得歐盟受到極大震動。為此,歐盟國家將轉變能源消費結構與保障能源安全進行綜合考慮,以期同時達到減緩氣候變化與確保能源安全的雙重目標。
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過程中,歐盟不僅有較大的收益,而且相對其他國家和地區只需支付較低的成本。
首先,歐盟有節能環保的優勢。作為發達經濟體的歐盟歷史上高度依賴化石能源,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迫使并不具有美國那種保證石油供應能力的西歐走上了節約使用能源,降低進口能源依存度的道路。根據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的統計,1990年,每使用1噸標準油的能源,歐盟僅排放2.36噸二氧化碳,美國和日本則分別排放2.53噸和2.38噸二氧化碳。到了2005年,歐盟15國的對應指標則降低為2.11噸,下降了0.25噸,美國和日本的對應指標后期僅分別下降了0.04噸和0.08噸。1990年,每創造1 000美元的GDP,歐盟15國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為0.36噸二氧化碳,遠低于美國的0.61噸。到2005年,歐盟15國的對應指標下降為0.28噸,低于日本的0.31噸[8]。歐盟的這種優勢還反映在其能源結構上,清潔能源所占比重較大。在法國,50%以上的能源來自于幾乎沒有碳排放的水能與核能。即使煤炭使用較多的德國,其煤炭也僅占全部能源的23.6%。
其次,歐盟具有新能源技術的優勢。據OECD的統計,2005年,歐盟擁有的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技術專利占全球份額的36.7%,高于美國的20.2%和日本的19.8%。在核能技術方面,歐盟占相關專利總數的34.8%,高于美國的27.2%和日本的22.7%[9]。歐盟在可再生能源產業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優勢,以風能為例,在2000年的世界風電設備市場中,僅丹麥、西班牙和德國三國的出口就占了3/4以上的份額[10]。這種技術優勢不僅能降低歐盟自身節能減排的成本,還可以通過技術和設備的出口賺取大量的利潤。
最后,歐盟有對外貿易中的低碳優勢。雖然引起了世界各國的巨大爭議,歐盟仍在積極推動航空業碳關稅的征收,并試圖將其擴展到進出口貿易領域。征收碳關稅的確是推動各國節能減排的有效激勵措施,歐盟的積極推動的行為反映了其在國際貿易中對發展中國家的低碳優勢。2001年,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為1.55億噸,而與此同時,歐盟對中國的出口僅產生1 600萬噸二氧化碳[11]。以上事實表明歐盟的出口越來越低碳化,能源密集型產品更多依賴進口,這使得歐盟在低碳競爭中處于優勢地位。
(二)中國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的利益格局
相較于歐盟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積極推動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中國雖然也積極參與這項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仍然有所保留。2009年,中國宣布了自愿減排指標,決定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但同時拒絕接受歐盟等發達國家提出的長期量化減排目標,也不承擔具有約束力的國際減排義務而是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對人類共同事業和國際利益的關注與承擔責任的意愿不如歐盟,而是因為中國在氣候變化治理中具有和歐盟不同的利益格局。
中國同歐盟一樣屬于環境脆弱型的國家,農業生產和人民的生命健康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引起的極端天氣現象的侵害。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與石油進口國,和歐盟一樣面臨能源安全的巨大挑戰。以上事實表明中國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的收益是巨大的,至少和歐盟處于同一水平上,如此一來,中國和歐盟在氣候變化治理問題上的主張差異就反映在了兩者不同的治理成本上。
首先,中國屬于人均收入較低的發展中國家。2011年中國的人均GDP為5 432美元,全球排名100位以后。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統計,以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 300元人民幣/年計算,中國還有1.28億的貧困人口。而相當于歐盟平均水平的意大利與西班牙2010年的人均GDP為30 000美元左右,遠遠高于中國的水平。中國沒有條件立刻實現歐盟那種高標準的碳排放指標,因為與節能減排相比,發展經濟消除貧困對于中國是更為緊迫的國家利益。
其次,中國的能源結構屬于高排放型。2009年中國的一次能源消費中煤炭占到70%,石油占20%,天然氣、水電、核電分別僅占3.9%、7.5%和0.8%[12]。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需要大量廉價的能源,煤炭的資源和價格優勢使其成為首選。煤炭相對來講最便宜,但是,它的二氧化碳排放也最多。以發電為例,單位發電燃燒煤炭產生的二氧化碳是石油的1.3倍[13]。中國一直致力于改善自身的能源結構,到“十二五”末,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從2009年的70%下降到63%左右,非化石能源到2020年提升到占能源消耗總量15%[12]。由此可見,中國在能源結構上高碳高排放這一國情導致在節能減排、治理氣候變化上的成本遠遠高于歐盟等發達國家,甚至高于印度等發展中國家。
最后,中國的貿易結構屬于高能耗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迅猛增長,中國制造的產品遍布全球,使中國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稱號。2010年我國的出口總額為15 779.3億美元,其中初級產品出口額為817.17億美元,工業制成品的出口額14 962.16億美元,工業制成品占全部出口額的94.82%[14]。中國出口的工業產品中以高能耗的能源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僅機械與運輸設備產品2010年出口就達7 803.30億美元,占當年出口總額的49.45%。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保護本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在貿易中加入能源效率和碳排放等新標準,這將大大提高中國出口產品的成本,使其降低競爭力。與此同時,作為出口導向型經濟的中國,對外出口不僅關系到貿易收入,更牽涉到國內大量勞動力就業的問題。當節能低碳與解決就業這一目標發生沖突時,中國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成本將是非常高的。
三、提供公共產品的激勵:對策與建議
比較歐盟與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利益格局,分析各自的收益與成本,不難發現兩者對節能減排目標與期限持不同立場背后的深層原因,而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態度也取決于各自基于成本與收益的利益結構。全球氣候治理本質上是一項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國際合作,要使理性自利的國家積極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選擇“搭便車”政策,就需要適當的激勵:提高收益或者降低成本。
首先,應加強全球氣候變化的科學研究。到目前為止,在減緩全球氣候變化方面各國采取的實際行動較少,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氣候變化尚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只是有部分研究表明存在這種風險與可能性。氣候變化是一個緩慢過程,對自然生態和人類的影響是漸變式的,所產生的風險也是某種程度上的而非決定人類生存或者毀滅的二選一。國家和人一樣是理性自利的,會愿意支付一定的成本去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但支付的意愿取決于這種風險危害的大小以及出現的概率。這就像一個人很可能愿意傾家蕩產去治療已經診斷出的疾病,卻未必愿意花很少的錢買一份30年后若患上某種疾病就能得到賠款的保險。
國家的利益分為很多層次,不同的國家利益的緊迫性不同,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當前的發展經濟消除貧困改善民生的緊迫性顯然要高于避免未來因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的緊迫性。要想提高這些國家參與氣候治理的積極性,就必須提高其收益,至少使其確定本國在這一國際合作中的收益究竟有多大,而非泛泛告知其這么做的好處。這就需要加強氣候變化方面的科學研究,對具體的國家和地區在具體的時間內可能受到的具體損失做出評估,并證明先期為此付出的成本比如果不這么做將要付出的代價小。
其次,應加強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與推廣。氣候變化治理的一個基本假定是進入工業化時代以后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所依賴的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是導致氣候變化的重要原因。顯然人類不可能為了防止氣候變化退回到農業文明時代,節能減排的要義在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發展和使用清潔的可再生能源,降低單位GDP的碳排放,而絕不是要求人類在總量上減少對能源的使用。高能耗高排放的生活方式是技術革命的產物,也只能靠新的技術革命去解決。目前已經有許多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新能源的技術,例如太陽能、核能、風能等,制約其推廣的因素在于成本和安全性,這同樣需要靠技術的進步來解決。
在節能減排的技術和設備方面,發達國家擁有巨大的優勢,但氣候治理是一個全球性的工程,沒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參與不可能取得有意義的成果。發展中國家由于科技和經濟實力的制約,其采購與使用這些技術和設備的成本是巨大的,這導致其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激勵不足。如果發達國家能夠為人類的共同利益同時也是自身的國家利益做出長遠考慮,低價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關技術和設備,至少兌現其在各種國際會議和文件上的承諾,那么將大大推動治理全球氣候變化這項事業的發展。
最后,應展開基于國家利益的務實的國際合作。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關鍵在于激勵各國積極提供公共產品,而不是采取“搭便車”的政策,要做到這一點,應避免實踐中經常出現的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技術問題政治化,利益問題道德化。當前的國際氣候問題談判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互指責:歐盟國家認為發展中國家應該為全人類利益著想,做出有約束力的減排承諾,同時將一國在氣候治理中的立場與該國是否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國家聯系在一起,試圖形成一種道德壓力。發展中國家則強調發達國家在碳排放中的歷史責任,主張應由其承擔節能減排的主要義務,同樣打出了公平正義的道德旗號。這種傾向也許在理論上是有道理的,在政治談判中也是必要的,但不可避免地擠占了國際會議中討論務實合作的空間。
另一種傾向是將減排標準定得過高,不夠務實。2009年,中國就宣布了量化的、清晰的自愿減排指標,決定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15]。中國之所以不肯接受具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就是因為該指標定得過高,沒有體現出“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如果全球氣候治理能按照循序漸進的原則,先達成一個有約束力,但低標準的國際協議,則可以吸引盡可能多的國家參與到這一進程中來,然后再依據各國的實際負擔能力逐漸提高標準。
全球氣候治理事關人類的共同利益,需要世界各國的努力與合作。在這次華沙氣候大會上,盡管發展中國家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沒有得到全部滿足,但中國代表團表示,無論談判進展如何,中國都將堅定不移地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同時這項事業也是一場全球范圍內的利益博弈,各國都將在自身利益與國際利益,當前利益與未來利益之間做出艱難但必要的選擇。要繼續推動全球氣候治理的國際合作,就必須充分考慮各國不同的基于成本與收益的制約條件與激勵機制。只有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協調統一,全球氣候治理這項有益的事業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上。
[1] 閻學通,閻梁.國際關系分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6.
[2] 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72.
[3] European Union.Climate Change: European Union Making Deeper Emission Cuts than Promised[EB/OL].http://europa.eu /rapid /pressReleasesAction.do? reference = IP /10 /1315.
[4] 謝來輝.為什么歐盟積極領導應對氣候變化?[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8):72-91.
[5] 薄燕,陳志敏.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的中國與歐盟[J].現代國際關系,2009(2)44-50.
[6] 張海濱.中國與國際氣候變化談判[J].國際政治研究,2007(1):21-36.
[7]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第二工作組報告(中文版)[EB/OL]. http: // www. ipcc.ch pdf/assessment-report /ar4/syr/ar4_syr_cn.pdf, 2010-01-28.
[8]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J].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2010:362.
[9] OECD.Compendium of Patent Statistics,2008,Paris: OECD,p.21[EB/OL].http://www.oecd.org/sti/ipr-statistics.
[10] Urs Steiner Brandt,and Gert Tinggaard Svendsen.Fighting Windmills: The Coalition of Industrialists and Environmentalists i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M].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2004,4(4):331.
[11] John Kornerup Bang,Eivind Hoff and Glen Peters,“EU Consumption,Global Pollution,”WWF Report,2008,p.12,Figure 4[EB/OL].http://assets. Panda.org /downloads /eu_consumption_global_Pollution.pdf.
[12] 李慧,馮蕾.透視“十二五”能源結構變局[J].光明日報,2010-08-01(06).
[13] 林伯強,姚昕,劉希穎.節能和碳排放約束下的中國能源結構戰略調整[J].中國社會科學,2010(1):58-71.
[14] 王玲莉.低碳經濟背景下中國貿易結構轉型研究[J].社會科學輯刊,2012(2):119-122.
[15] 薄燕.合作意愿與合作能力——一種分析中國參與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新框架[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1):135-155.
[責任編輯:秦衛波]
The Interests Structure of Climate Change Governance Between Sino-EU and the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China
ZHANG Li-hua,WANG Le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is related to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human society. A country’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depends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state,and calculation of costs and benefits determines the attitude of a country o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climate governance. Th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climate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the energy structure,the trad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needs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n climate change,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technologies. At the same time,all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avoid the tendency of moralistic and have unrealistic goals.
National Interests;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European Union;China;Cooperation
2014-03-28
吉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012B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13ZZ032)。
張麗華(1964-),女,遼寧彰武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樂(1987-),男,湖南湘潭人,吉林大學行政學院博士研究生。
X16
A
1001-6201(2014)05-009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