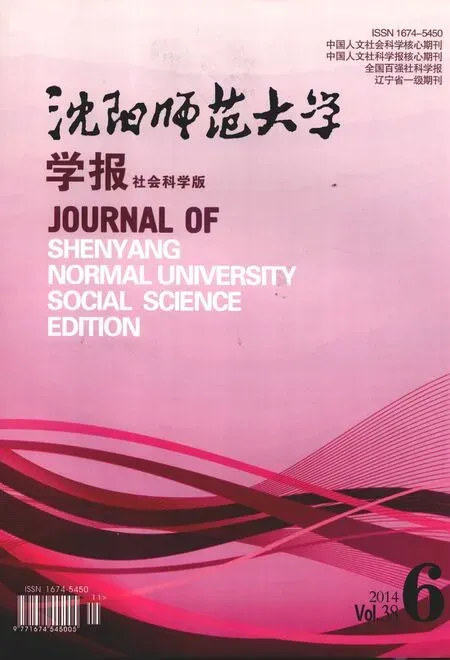廣告的倫理困惑與路徑抉擇
李闖
(中國計量學院 藝術與傳播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廣告的倫理困惑與路徑抉擇
李闖
(中國計量學院 藝術與傳播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廣告傳播過程涉及四類利益相關者,其所處的道德立場各不相同,由此產生了四種類型的廣告倫理困惑。規避廣告倫理問題,必須充分考量四類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道德義務,以“善惡差等定律”為參照坐標,以“為己利他”為路徑抉擇,而不是選擇難以操作執行的“無私利他”原則。這有助于消除各方的道德立場分歧,為廣告倫理規范的日常操作提供現實可能。
廣告倫理;倫理困惑;道德立場;路徑抉擇
自產生之日起,廣告就伴隨著人們的道德評價。在廣告行為還難以從經商或銷售活動中分離出來并成為一種職業之前,人們對廣告的道德評價往往包含在對商人或其商業活動的評價之中。早在1919年,徐寶璜在其撰寫的中國第一本新聞學專著《新聞學》中就曾指出,廣告應該“所說者為事實,而又無礙風紀”[1]。他對廣告道德提出了三個方面的要求:一是廣告必須與新聞分開;二是禁載不正當廣告;三是要樹立廣告信用[2]。
即便從中國改革開放后廣告業開始與市場經濟接軌算起,中國廣告的倫理研究也走過了30多個年頭。然而,廣告倫理研究似乎始終在古老的道德二元對立當中:一方面,廣告倫理研究追隨傳媒技術和廣告形態的革新,日益走向深入;另一方面,面對日益復雜的媒介生態環境和廣告日常實踐,廣告倫理的規范訴求似乎未能真正實現其應用價值,未能有效地回應人們對廣告愈演愈烈的抱怨與憤怒。
一、廣告倫理問題的產生
“倫理和道德,不論是學術研究還是生活觀念當中,這兩個概念通常在一個意義上使用”[3],指的是處理人與人關系的一系列準則和規范,用于評判人們的行為是否合范。無論從概念上還是從實踐上看,廣告均涉及一系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互動,其中涉及的各方均持有相應的道德目的和立場。
下圖顯示了廣告信息生成和流動的過程,虛線箭頭代表可選。從圖中可以看出,廣告傳播活動的四大相關主體形成了兩兩相對的六種道德關系,即廣告主/廣告人、廣告主/廣告媒體、廣告主/廣告受眾、廣告人/廣告媒體、廣告人/廣告受眾、廣告媒體/廣告受眾。由于廣告人和廣告媒體均從廣告主的廣告費支出中獲益,三者天然地具有“結盟”的傾向,因此,廣告活動中最核心的道德沖突是廣告信息的傳者與廣告受眾之間矛盾。

與其他領域的應用倫理學研究一樣,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道德立場沖突導致了倫理問題的產生。因此,要解決廣告的倫理困惑,不能只直陳違德失范現象的不合理性,還必須檢視并協調各方的道德立場。
二、廣告的倫理困惑
(一)廣告倫理規范的可操作性
在廣告倫理的研究文獻中,一個最重要的主題就是對廣告倫理規范的探討。“廣告道德原則和規范是處理廣告人在面臨價值和利益沖突時的行動指南,因此向來都是廣告職業道德研究探討的重點問題。”[4]盡管眾多的研究者提出了林林總總的道德規范,甚至建立
了相對完整的道德規范體系[5],然而,諸如誠信守法、真實健康、公平正義、服務社會之類的道德規范在面對廣告實踐的日常運作時,往往顯得蒼白無力,難以為道德抉擇者提供行動指南。
“到目前為止,在廣告倫理的研究中存在著兩個誤區:第一,大多數研究者把廣告倫理或是廣告道德滯留在一種簡單的規范訴求層面,而沒有上升到一種內在文化價值的層面。第二,與大多數應用倫理學的研究一樣,廣告倫理還沒有解決其價值體系的實踐可操作性問題。倫理學界如果不切實解決這兩個問題,廣告在面對功利與公正的‘道德兩難’時就將仍然不知所措,廣告業也就將長久地陷在經濟發展與道德失范二元對立的古老悖論之中。”[6]實際上,這些道德規范是社會普適性的,能廣泛應用于其他行業或領域,但并未真正考量廣告活動的特殊性和各參與方的道德立場。
(二)廣告傳者的道德價值判斷
站在理想的道德高地對廣告傳者提出應該遵守的規范是容易但卻難以奏效的。研究者習慣于從受眾的立場或優良道德的目標愿景出發,為廣告活動制定倫理規則,這忽略了被評判者的道德抉擇情境和價值判斷。因此,許多倫理規則已經超出了廣告本身所“必須”承載的道德義務和社會責任,而是在更高的道德水平上提出的價值期許。
顯然,廣告不應該惡俗(不道德),廣告能夠高雅(更高的道德要求),但廣告不一定必須要高雅,它可以處在兩者之間的中庸狀態,忠實地傳達基本信息。廣告應該對消費者負責,但不一定由此將企業與消費者對立起來,要求廣告“更重要的是對消費者負責”[7]。這種道德訴求只會將廣告置于揭企業短處的境地,不僅難以奏效,而且不符合廣告自身的存在邏輯。
廣告“應該如何”的道德規范的提出涉及到價值判斷。廣告之于傳者的道德價值是什么呢?廣告企業通過廣告擴大銷售、實現利潤;廣告公司通過廣告獲得制作費和傭金;廣告媒體通過廣告來補貼其他節目的開支;三者都不是慈善機構或公益組織,維持各自公司/機構的正常運轉、對員工負責是它們最優先考慮的道德命題。因此,三者的道德價值判斷首先是“利己的”,要求它們遵從“無私利他”式的道德訴求是不現實的。
永樂十八年(1420)七月,因功被赦復職,留于遼東都指揮使司(簡稱遼東都司)任都指揮使。當時,明廷正積極經營奴兒干都司,為了給京師、遼東都司與奴兒干都司之間提供運兵運糧、轉輸賞賚與貢品的船只,劉清奉命統兵來到荒涼之地——船廠。
由“利己”的立場出發而產生的廣告信息一定會導致道德問題嗎?這是廣告面對的另一個倫理困惑。
(三)廣告信息意義的不確定性
廣告是科學和藝術的統一體,這在學界和業界早已達成共識。用精確的數字和言辭傳達樸實準確的意義固然可取,但長期以來,廣告更喜歡追求“創意”,追求情感化的敘事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廣告人奉行“做爛廣告是不道德,沒有好創意是不道德的”[8]的信條。
一方面,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廣告主、廣告人和廣告媒體應該為企業或產品進行鼓吹,搖旗吶喊。否則,它們就是不道德的,因為它們要么沒有對雇主負責,要么沒有對企業員工負責(經營不善,成為社會負擔),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他們還將這種不對稱的信息進行藝術化的修飾,以一種“務虛”的手法(如夸張、比喻、象征等)表達出來。這使得廣告信息往往呈現出模糊多義性。
另一種趨勢加劇了廣告信息意義的不確定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和成熟,人們越來越從具體的實物和功能消費走向符號和意義的消費。廣告信息也越來越致力于塑造意境和氛圍、挖掘符號的象征意義,訴諸于消費者的心理和情感。于是,廣告信息從物質走向精神體驗,意義更加模糊。
撒謊、色情、暴力、歧視、騷擾等明顯的廣告道德淪喪現象是毋庸諱言的,它們甚至稱不上倫理困惑,社會的道德標桿已經將它們釘在了恥辱柱上。現在的問題是,那些“務虛”的藝術化的廣告信息,諸如“今年二十、明年十八”“1:1:1”等,也將被推上道德審判臺嗎?這取決于廣告受眾的道德立場。
(四)廣告受眾的道德價值判斷
受眾是廣告信息的傳播對象。在面對強大的廣告企業、廣告公司和廣告媒體時,個體受眾是弱勢的。正因為這個原因,廣告倫理研究往往將廣告受眾視為“受害者”,忽略了其主動性和應該承擔的道德義務。在面對道德危害時,研究者往往寄希望于法律法規。然而,“法是道德的最低限度”[9],它的應用并未發揮道德應有的約束力量。
廣告受眾的道德價值判斷取決于廣告是否符合其道德目的。也就是說,他也是站在利己的立場上,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作出的道德評判。從整體上看,受眾群體龐大,媒介素養和道德水平各異,對同一廣告活動的道德評價也經常呈現出差異。但不能忽視的是,廣告受眾不是廣告倫理的旁觀者,其覺悟高低和能動性水平對廣告倫理的實現具有重要影響。
陳正輝指出:“消費者覺悟程度的高低決定道德素質的高低,影響廣告倫理缺失的成本,決定廣告監督的水平。”[10]這意味著,廣告受眾不僅作出道德評判,還要積極行動起來,以抵制、罷買、投訴、抗議等行動來表達道德判斷,真正發揮道德的輿論影響力。
三、道德立場的分歧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廣告傳受雙方各自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去評判廣告行為和廣告信息是否符合自身的道德價值,似乎形成了難以逾越的道德鴻溝。
廣告主作為企業公民出資做廣告,自然希望廣告能有利產品銷售、實現企業擴大再生產,因而盡量宣揚產品和企業美好的方面。企業的經濟屬性決定了將企業經營好、提供就業崗位、促進經濟發展、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等目標是其所承擔的最大社會責任。否則,它就違背了企業的本質屬性,也就違背了它對員工和社會的道德義務,因而是不道德的。“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
謀求利潤最大化是市場營銷的出發點,合法并滿足公司利潤最大化的行為便是合乎倫理道德的。它排除了不合法的行為,例如賄賂和欺騙性廣告等。”[11]
同理,廣告人受雇于廣告主,兩者是一種經濟契約關系,從而形成了相應的道德權利和義務。由是觀之,廣告人與廣告媒體、廣告主與廣告媒體也是如此。“在信息傳遞過程中,當廣告主的利益和消費者的利益發生沖突時,廣告媒體和廣告代理會毫不猶豫地維護廣告主的利益,廣告主、廣告媒體和廣告代理就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同盟。”[12]
從廣告受眾的道德立場看,處于強勢群體的廣告主、廣告人和廣告媒體“理應”更多更好地服務消費者、承擔社會責任、傳播高尚文化,這是個人與社會組織之間締結的隱形的社會契約。否則,維系社會的基本的心理信任將會崩潰。在要求廣告傳者遵守道德規范時,廣告受眾是否為營造一個更好的、更適宜的廣告倫理環境而承擔了應有的道德義務呢?廣告受眾不僅需要具有較高的媒介素養和廣告認知能力,免于自己遭受廣告道德的負面影響;還需要維護優良道德的行動力,免于他人遭受廣告道德的負面影響。試想,面對欺騙性廣告,一個人因為自己不會上當而聽之任之,無異于在別人上當時未能施以援手。這同樣是不道德的。現實情況往往是道德評判大于道德行動。
從“利己”的立場出發,廣告傳者傳播于己有利的信息天經地義;廣告受眾要求廣告傳者承擔社會責任和道德義務也無可非議。要彌合二者的分析,必須尋求一種在“利己”的同時能夠兼顧“利他”的道德立場,這就要借助“善惡差等定律”。
四、廣告倫理的路徑抉擇
根據“善惡差等定律”,道德善惡原則是有差等的。“利己與利他(它)都是善,但它們的善惡的高低大小等級有所不同。”[13]178王海明通過對道德目的、道德終極標準、人類全部倫理行為事實的客觀本性的分析,推導出了善惡六大原則,其差等關系如下圖所示[13]186。善惡六大原則的差等關系圖顯示,廣告倫理的路徑抉擇只能是“為己利他(基本善)”。原因有三。

第一,就廣告活動而言,在道德惡的三大原則中,純粹害己幾乎可能,而損人利己和純粹害他的行為則全無道德可言,屬于嚴重的道德淪喪,是任何倫理規范所不容許的,它主要依靠“最低限度的道德”——法規——來進行管制和規約。
第二,無私利他雖然是道德善的最高境界,但卻難以在廣告領域“落地”。要求廣告主、廣告人、廣告媒體承擔無私利他的至善行為是不符合其經濟法人的本質屬性的,這恰是廣告倫理研究長久以來存在的誤區。許多被視為真理的道德規范在面對廣告的功利性日常運作時,操作性不足,就是這個原因。
第三,單純利己作為最低的善已經超出了法規的管制范圍,進入到倫理考量的層面。從道德善的原則上看,單純利己并無可厚非。但在廣告的運作過程中,它難以彌合廣告傳者和廣告受眾之間道德訴求的鴻溝。單純利己既不符合廣告在整體上為社會道德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現實,也不能為處于道德抉擇困境的人提供決策指南。在利益沖突中,單純利己往往導致錯誤的道德抉擇,從而走向道德惡。
因此,唯有為己利他打通了廣告傳者與廣告受眾之間的道德立場隔閡,把握了“廣告信息的經濟價值、社會權力和市場權力的平衡點”這一廣告倫理學的核心問題[14],也只有在為己利他這一道德原則之下,廣告活動的倫理評價才具有統一的尺度。
結語
通過對廣告的倫理困惑和廣告相關各方的道德判斷及立場的分析,我們發現廣告倫理只能在為己利他的基本善的層面上展開,既不能好高騖遠地追求道德至善境界,也不能囿于最低限度的單純利己。為己利他是廣告倫理唯一合理科學的路徑抉擇。只有在這一道德善的原則之下,探討諸如誠信、公平、高雅、健康向上之類的倫理規范訴求才具有現實意義。
[1]蘇士梅等.廣告倫理學[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3.
[2]孫瑞祥.以德治國與廣告倫理[J].新聞戰線,2001(5):29.
[3]陳正輝.廣告倫理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3.
[4]黃娟娟.廣告人職業道德研究述評[J].科學大眾:科學教育,2009(11):135.
[5]張金花等.廣告道德研究[M].北京:中國物價出版社,2003.
[6]鄭根成.論廣告道德及其建設[J].株洲工學院學報,2004(3):47.
[7]易昌泰.廣告與道德[J].贛江經濟,1981(11):44.
[8]何敏.沒有好創意是不道德的[J].成功營銷,2008(9):22.
[9]王海明.倫理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9.
[10]陳正輝.廣告倫理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252-253.
[11]李小勤.廣告倫理——面對難以躲避的誘導[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12]楊海軍.廣告倫理與廣告文明締構[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7(3):21.
[13]王海明.倫理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78.
[14]程士安.廣告符號的道德判斷——談廣告倫理學研究的意義及方法[J].廣告大觀:理論版,2005(5):23-25.
【責任編輯 詹 麗】
B829
A
1674-5450(2014)06-0190-03
2014-06-12
浙江省社科聯課題(20130085)
李闖,男,山東單縣人,中國計量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