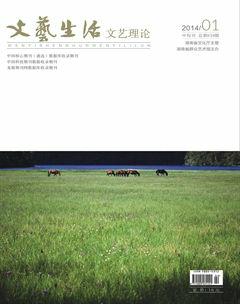試論攝影藝術與文學相結合的藝術特點及魅力
——以《光影瞬間——吳赤鋒攝影散文集》為例
向梅芳
(廣東省信宜市文化館,廣東 茂名 525300)
試論攝影藝術與文學相結合的藝術特點及魅力
——以《光影瞬間——吳赤鋒攝影散文集》為例
向梅芳
(廣東省信宜市文化館,廣東 茂名 525300)
有了文學,攝影才有了生命和靈魂。是文學讓攝影真正完成了從技術到藝術的飛越過程。攝影文學的最高境界,不是攝影,也不是文學,而是兩者共同呈示的藝術精神。雖然攝影、電影、電視誕生在國外,但是攝影文學卻誕生在中國。對這門全新的藝術樣式進行學理研究的也是在我們中國。
攝影;文學;攝影文學;藝術魅力
自從法國人達蓋爾在1839年發明了攝影術,人類從此便有了現代的影像記錄技術,可以將遠逝的或者必須離開的風景,借助相機和攝影技術永遠地留在自己的記憶中。而伴隨著數碼影像時代的到來,攝影又從人們的職業技能逐漸演變成了人人都會操作的生活技能,攝影真的是已經普及了。相機不僅記錄我們的生活,記錄時代的變遷,記錄美麗的大自然,也記錄著我們的情感。
攝影術發明一個半世紀后,攝影才有了相攜同行的伴侶:攝影文學。1990年,一個叫成東方的攝影愛好者在距離法國遙遠的中國,最早提出了“攝影文學”這個概念。迄今為止,攝影文學已經走過二十多年,她的百花園中終于開出了一朵奇葩:《光影瞬間——吳赤鋒攝影散文集》。
如果說攝影文學是中國獻給人類文明的玫瑰,那么我手上的這部百讀不厭的《光影瞬間》,就是其中最亮麗芬芳的一朵。為了讓這個類比具有說服力,我想從三個方面對這部攝影散文集進行淺顯的賞析和解讀。
一、攝影:光與影的瞬間交匯,人與自然的奇妙契合
《光影瞬間》里收錄的圖片總共250多幅,隨手翻閱,給人的總體印象是:構圖大氣磅礴,色彩豐富明麗,意境幽遠深邃。這些特點是吳赤鋒作品中非常吸引人的東西。在大家習以為常的印象和思維里,草原多是“風吹草低見牛羊”的一望無際的綠,但吳赤鋒鏡頭里的《美麗的呼倫貝爾草原》,卻是五彩繽紛的。他拍的根河濕地,一望無際的原野就像一塊巨大的調色板:黃的明艷,紅的濃烈,紫的妖冶,橙的絢爛,與濕地本來的綠色交匯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讓人感覺有些夢幻迷離。也正因此,吳赤鋒為他的那組根河圖片命名為《夢幻迷離的根河濕地》。還有他鏡頭下的冰川和石林,也是被秋天的白樺林襯托得姹紫嫣紅,那遠而又遠的梅里雪山,也成了《日照金山》,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沒有人會相信那斑斕耀眼的金色的山,會是原本潔白晶瑩透著寒光的冰峰。
除了色彩,還有故事和情緒。他拍的《北疆牧歌》《金帳汗的遐想》《歷盡滄桑的居延海》等等都能讓讀者聯想到“故事”。甚至他拍的水都是千姿百態的:《九寨歸來不看水》中的水是歡呼雀躍的;《銀河飛瀉諾日朗》中的水是國畫大師用畫筆渲染出來的,透明得可以看見瀑布后面的五彩山石;《九寨溝的海子》里的水,是晶瑩剔透的秀美,安靜得讓人心生憐憫;《扎噶瀑布》中的水呢,卻是隨遇而安的……
那些光影瞬間交匯的準確把握,天人合一的和諧境界,在這些絕美的風光圖片里被體現得淋漓盡致。宏觀的場景,畫面的構圖、線條、色彩、明暗等一切作為藝術審美的因素,水乳交融地展現在《光影瞬間》的每一幅圖片里,雄渾,沉厚,又空靈悠遠,多方面體現出作者的藝術修養和智慧。
祖國的大好河山,透過他的相機有了別樣的風采,有了凝重純粹的生命,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二、文學:對自然和歷史的獨特言說
也許,喜愛攝影的吳赤鋒應該感謝文學,感謝文學造就了他敏感的心靈和深邃的思想,還有博大的胸懷。
也許,攝影也應該感謝文學,感謝文學詮釋了她的靈魂,破譯了她背后的故事。
如果沒有文學的詮釋與表達,那些美得驚心動魄的胡楊,就只是胡楊。就不會有沙漠曾經的歷史,也不會有關于胡楊與大漠的愛情想象,更不會有對西域古文明的緬懷;如果沒有文學,那淺淺的弱水河,又怎么會擁有千回百轉的生命與情懷?那被拍過千萬次的瘦西湖,又怎么會給人妖嬈嫵媚的綺麗聯想?
當攝影遇見文學,攝影才有了新的生命和靈魂。
吳赤鋒的文字,跟他的攝影作品一樣大氣磅礴。《碧波萬頃呼倫湖》《大美祁連山》《天子山雄姿》……單看這些配圖短文的標題,就可以感受到非一般的氣勢。
然而《光影瞬間》的獨特言說,絕不僅僅體現在大氣上。文學的本質是至情至性,是發自內心,吳赤鋒的文學情懷也不例外。《光影瞬間》的每一篇文字,都有著作者個人獨特的感觸與領悟,都是對自然和歷史的獨特言說。
在《胡楊對大漠的戀情》那一組圖片的配文中,作者有一番不可遏制的激情言說:
“在漫漫黃沙里,面對亙古的荒漠蒼穹,一萬年癡心不改的守護。
那是胡楊對大漠深深的戀情。
……為了和大漠長相廝守,胡楊頂著烈日,耐著嚴寒,忍著饑渴,把根深深的扎進地底,一毫厘一毫厘地掙扎著生長。終于長大成林,橫空出世屹立于大漠之中。
……有了胡楊,大漠從此不再孤獨,不再單調,不再冷漠。生而一千年,胡楊為大漠唱歌、跳舞,增添五彩繽紛的色彩;死而一千年,胡楊始終巍然屹立,頑強不屈地守護著大漠;倒而一千年,胡楊更親昵地躺在大漠懷中,情話綿綿,直至最終融于大漠之中。”
多么美好纏綿的想象啊,作者對大漠和胡楊賦予了連人類都嫉妒的生命和情感。
每一處風景都有其歷史和底蘊。《光影瞬間》的配文中較長一些的短文,多有對圖片背后的人文歷史故事的解說,和作者對人生的感悟。比如在《美麗的呼倫貝爾》里,作者這樣寫道:
“……這里有中國最美的大草原,有中國北方幾千里內唯一的大澤呼倫湖,有數不清的蜿蜒流淌的河流,有龐大的濕地生態系統。
這里的魚群曾多到阻礙船只的行進,鳥的種屬占了全國的五分之一,野生的黃羊曾經在這片草原上如非洲大陸上的角馬般壯觀地遷徙……
這里是北方游牧民族成長的搖籃,鮮卑人、契丹人、女貞人、蒙古人都曾經是這里的主人。
……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就是從這里起步,統一了蒙古高原……事實上,這里豐富的歷史文化和生物資源,都歸因于亞洲這片最肥美的草原。”
這樣的文字融匯古今縱橫捭闔,讓讀者在獲得攝影作品直觀的美感同時,增長了知識,開闊了視野。配文中短的如《青海秋色》:“大美青海,接天秋色,醉了多少山川。”這類干凈、洗練,卻讓人浮想聯翩的妙文比比皆是。
三、攝影與文學的藝術邂逅,指向的是精神的遠方與靈魂的高處
就像一場美麗的邂逅,攝影文學,是攝影邂逅文學的“愛情結晶”。攝影文學把攝影與文學融合起來,創造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二者融合,互滲互動,相得益彰,把藝術推進到一個新的審美境界,讓那些有意味的東西永遠留在世間。
攝影文學的最高境界,不是攝影,也不是文學,而是兩者共同呈現的藝術精神。《光影瞬間》的魅力,在于她的可觀和可讀,在于畫面與文字的完美結合所形成的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讓讀者在欣賞之后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并引發無盡地思索。這里僅以《情牽日月山》為例,據吳赤鋒說他選編那兩幅圖片的目的,是為表述中國歷史上不容忽略的“和親”主題——
“日月山聞名遐邇,卻是因為一位傳奇美人的動人故事。”作者在講述了日月山的來歷之后,很自然地引入關于“和親”的話題。
“‘和親’,早在漢朝就有了先例。在唐朝作為一種重要的外交手段,被演繹得淋漓盡致。唐朝先后送出21位公主遠嫁番邦國王,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文成公主,她創造了一女可抵十萬雄兵的神話,不僅為兩國帶來了和洽的邊關,更把中原的文明遠播到鄰邦。其后,從唐蕃古道走出去的另一位偉大女性是金城公主。到了唐玄宗時,永樂公主、燕郡公主。東華公主、宜芳公主、固安公主、靜樂公主、東光公主……都陸續走上了和親的道路。她們不僅用柔弱的身軀化解著男人間的戰爭風云,還用美麗和智慧推動著鄰邦的發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日月山下高聳入云的文成公主雕像,應該是所有和親女兒的紀念碑。”
這兩幅作品,以最短的瞬間爭取最長的敘事,展示了定格的歷史細節,將讀者的情感和思緒帶進了歷史,以及對那些歷史隱痛的反思中。
其它諸如《老城的水巷——蘇州山塘》《怒江,英雄的江》等,也都是攝影與文學缺一不可才擁有獨特的藝術魅力的。
我們常常說及的所謂藝術的魅力,更多的體現在內在的深刻。藝術家的創作不該是對世界的簡單描摹,而是通過感性的創造表達對自然、歷史及人生的深度詮釋與意義重建。正因為如此,我們欣賞這些攝影文學作品時,不僅可以看到作者的個性與文化修養,還可以看到作者對社會、政治及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對宇宙、自然萬物及人生的體驗與感悟!
愿《光影瞬間》的藝術魅力和藝術精神引起更多人的心靈共鳴。
愿攝影文學重塑的審美時空越來越精彩紛呈。
[1]成東方,與攝影文學同行.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年10月30日第七版.
[2]成東方.攝影文學有著廣闊前景.人民日報,1990年3月3日發表.
[3]大眾攝影,2012.01A期,p2,P28—P38.
[4]大眾攝影,2012.04A期,p2.
[5]中國名家學者詮釋成東方創立的攝影文學.搜狐文化2011年12月31日發表.
J405
A
1005-5312(2014)02-0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