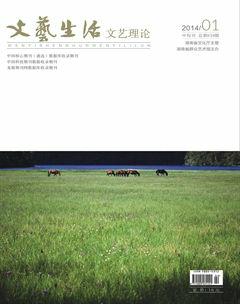談滕守堯先生的“生態式教育”理論對藝術教育的啟示
孫丹青
(江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談滕守堯先生的“生態式教育”理論對藝術教育的啟示
孫丹青
(江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江西 南昌 330000)
當今中國的教育體制處于一種非常態的模式下,體制的刻板單一化,學生只學主課輕視副課的學習模式以及以“分數”論英雄的評判標準,都制約著學生的天性和創造力,因此,學生藝術素養的匱乏和學校藝術教育的不完善就成了當今中國藝術教育的現狀。滕守堯先生在《藝術與創生——生態式教育理論》中提出的“生態式教育”理論對中國的藝術教育有所啟示。
生態式教育;藝術教育
對于一個擁有五千年之久歷史的國家來說,濃厚的文化藝術氛圍理因傳承至今,并發揚光大,但由于當今中國的教育體制處于一種非常態的模式下,體制的刻板單一化,學生只學主課輕視副課的學習模式以及以“分數”論英雄的評判標準,都制約著學生的天性和創造力,因此,學生藝術素養的匱乏和學校藝術教育的不完善就成了當今中國藝術教育的現狀。滕守堯先生在《藝術與創生——生態式教育理論》中提出寫這些關于藝術教育的書籍和文章其意圖在于糾正和改善當今中國藝術教育現狀,并給中國的藝術教育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藝術與創生——滕守堯先生生態理論之路》從多角度解釋和分析了滕守堯先生提出的“生態式教育”理論。何為生態,為什么要把生態觀運用到教育領域中。生態是指人以及其他一切生物存在的狀態,我們常說生態系統,教育同樣作為一種系統,各環節就是有聯系的,如果斷了其中一個環節,這個系統就不完整,重則垮塌或毀滅,固然也就不能稱之為系統了。因此,滕守堯先生把當今藝術教育的改革理論用“生態”二字詮釋,就再好不過了,教育的系統猶如生態的系統,少了某一門課或某一教學環節,都會使學生的成長與發展有所缺失。
滕守堯先生通過長期對古今中外藝術、美學、教育、哲學、和心理學的潛心研究意識到在原始智慧(野性智慧)、現實人文智慧(圣賢智慧和)和神性智慧(超然智慧)這三種主要人類智慧中,唯有神性智慧可以詮釋生態式教育中的“對話”精神。藝術不同門類需要對話、藝術與文化、生活、情感以及科技需要對話、教師與學生需要對話,教學與環境需要對話,學科與學科間需要對話等等。這些對話可以使人回到生命的本源,找到智慧的源泉并重新認識自我的存在價值。
文中歸納總結了八個生態式教育的特征,師生平等、對話精神、開放態度、人的可持續發展、不分主副、主題單元式教學、鼓勵活動式教學和融通文理,我想這些生態式教育的方法或許對當今中國的藝術教育有將所啟示。
一、師生平等,和諧育人
在中國傳統教育模式中,課堂方式不外乎是老師說,學生聽;老師說一,學生不敢說二;老師是主,學生是賓,諸如此類。教師一直以來都是高高在上的形象,學生處于被動接受的低位,在被教訓、被灌輸、被征服的對立關系中學習和成長,這樣一來,學生本來的天性和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必定被抹殺。因此滕先生提出平等的師生關系是教育者教書育人的最高原則,即“生態中心平等主義”。所謂和諧育人,是要求教師和學生在知識的海洋里平等對待、互促互補、共同發展。和諧是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和諧,同時也是知識之間的和諧。教師和學生作為教育關系中的主要兩方,都有權利展示自己的知識觀點,知識的獲取與分享不分高低,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同樣可以同學生身上完善自我的知識體系結構。
二、以“對話”為中心
“對話”作為生態式理論的核心,其真正意義是在兩級邊緣地帶舉行人與人之間的對話(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家長、學生與學生、教師與家長之間的對話)、人與事物的對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教育之間的對話)、事物與事物之間的對話(主科與副科、文科與理科、技與理之間的對話)。繼而滕先生也指出:“這種對話不是形式上的面對面說話,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相遇,一種靈魂上的溝通。”
課堂上,教師常說:“請同學們互相討論下這個問題。”“討論”作為課堂的常態教學模式,已經沿用很多年。在滕先生看來,討論是有規則的、有主題的,不能激發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也不能碰撞出知識的火花,因此僅僅有“討論”的教學模式是不夠,我們要“討論”更要“對話”。“對話”與“討論“的區別之處在于,“對話”是不確定、隨意的,是不分身份等級、學位高低的。學生和老師在這樣一種不限制的、放松的狀態下,通過真誠的“對話”,
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在提出師生平等、要討論更要對話兩點之后,滕先生繼而提出生態教育需要開放的態度,對學識、對他人、對自然、對社會的開放態度。人們常說“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顧名思義,大海的寬廣可以容納眾多的河流,就如心胸寬廣的人可以包容一切。做人做事需要一顆寬廣的心,學知識又何嘗不是呢?滕先生認為,以“對話”為核心的生態式教育其目的在于徹底消除以“我”為圓心的封閉意識。一個人,精力是有限的,時間是有限的,同樣學識是有限的,每個人的知識結構層面都不一樣,每個人感興趣和擅長的知識面也有所不同,正因如此,我們應通過開放的“對話”方式不斷提高自我,完善自我,那些以自我為中心,認為“天下老子最大”的思想都是狹隘的,也是不可取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更何況是在廣闊無限的知識海洋里。
四、人的可持續發展
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于1987年在《我們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一文中明確了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即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觀作為近幾十年世界和社會共同倡導的議題,一直廣受關注,在自然、社會、以及經濟領域都有所建樹,而人作為可持續發展體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自身的發展是不是也應該被重視起來,所以,人要發展必然要接受教育,學習知識,將學習轉化為智慧,學以致用,完善自我的人生價值和目標。滕先生認為:“一個人的素質高低的標志是看其是否具有不斷創新和持續發展的能力,而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絕不僅僅通過分數來表現”。在這個“以分數論英雄”的時代,分數的高低似乎論定了一個學生的未來發展和潛力,從高考到考研、考公務員等,“無處不是考,無處不見分”,分數的過分重視往往會模糊了人們對教育目的認識,教育的目的是替年輕人的終生自修做準備,而學習知識意在運用智慧指導人的發展。當然,分數是考核一個人所學知識多少、好壞的客觀標準,但卻非唯一標準。園金斯曾說過:“教育不在于使人知其所未知,而在于按其所未行而行。”另一方面滕先生也明確了“人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在智慧而非知識”,知識與智慧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知識指人類認知的成果,如經驗知識、科學成果等;智慧指的是一個人的決斷力,兩者區別在于智慧可以產生知識,但知識卻未必能夠產生智慧,有時還可能蒙蔽你的智慧。
五、不分主副,融通文理
滕先生指出,除了教師與學生、孩子與家長之間力求一種生態關系,學校教育在學科、文理之間也應建立一種平等的生態關系。讀書多年,我們潛意識里都會對學科的主副有著很明確的概念,語文、數學、英語是主課,我要好好學;美術、音樂、體育是副課,我可學可不可學。循環往復,就形成了大多數中小學的課堂里只見主課未見副課的場面,課堂失衡,學生的發展同樣失衡。音體美等課程作為一門課程,必然有他存在的價值,音樂陶冶情操,體育強身健體,美術提高審美,這些都是使一個學生認識自我、完善自我的必備因素。所以不管是主科還是副科都是同樣重要的。同樣道理,人文學科與理工科之間建立的生態關系也是如此,人文學科具有人文本性,讓學生認識自己,我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理工科作為自然、科學的統稱,意在讓人變的睿智和理性,滕先生就認為:“人文與科學的相融合可以相互促進、相互支持。”因此,學科、文理之間無論偏向哪一方,都會使學生的發展失衡,使其得到平衡與統一是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由此看來,滕守堯先生的“生態式教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藝術教育的發展指明了道路。作為一名學者,滕先生對藝術教育的發展一直是親力親為的,從其諸多理論著作中,我們可以找到中國藝術教育正在尋求進步和完善的影子。當然,藝術教育改革發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邁出“生態教育”之路實屬不易。因此,作為一名即將從事藝術教育工作的我來說,把“生態教育”這一理念付諸于實踐,更深層次的挖掘“生態教育”理念的價值,發揚光大,都是將來我們要做且必須做的。
G 42
A
1005-5312(2014)02-022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