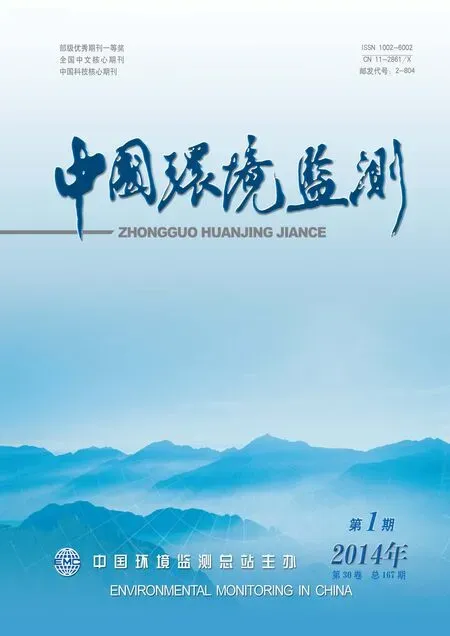松花江下游底棲動物組成及其環境指示作用
李中宇,胡顯安,劉錄三
1.黑龍江省環境監測中心站,黑龍江 哈爾濱 150056
2.佳木斯市環境保護監測站,黑龍江 佳木斯 154002
3.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北京 100012
大型底棲動物是水質生物評價中應用最為廣泛的一類生物,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非常重視利用大型無脊椎動物進行水質生物評價[1-8],美國環保局在2000年制定的5個水質生物快速評價條例中,前3個均與大型底棲動物有關,后2個則是關于魚類的。大型底棲動物對外界脅迫的響應比較敏感,其在河流中的豐富度、群落組成結構、耐污類群和敏感類群的比例以及不同功能攝食類群的結構特征等都可以從不同側面反映水質的好壞,從而可以有效地指示水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近年來,國內研究者們也越來越多地使用大型底棲動物來進行水質生物學評價[9-14]。
松花江是東北人民的母親河,其水質狀況因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備受關注[15-16],“十一五”期間松花江流域落實休養生息政策,加大了環境治理力度。該研究旨在以2005—2010年在松花江下游佳木斯江段開展的底棲生態調查結果為依據,分析大型底棲動物群落在松花江干流的空間差異以及演化趨勢,并通過大型底棲動物指數對水質進行了生物學評價,探討大型底棲動物對松花江水質狀況的反映程度,評估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規劃實施效果,科學驗證“讓松花江休養生息”政策措施的績效。
1 實驗部分
1.1樣品的采集與處理
為了解松花江匯入黑龍江前的總體生態環境狀況,在松花江佳木斯江段干流分別進行大型底棲動物野外樣品采集。如圖1所示,共設置3個采樣斷面,6個采樣點位,分別是佳木斯上斷面的左、右,佳木斯下斷面的左、右,江南屯斷面的左、右。佳木斯上斷面(入境斷面)位于郊區大來鎮境內,距湯旺河口上游500 m左右位置,距離市區江上距離約為53 km;佳木斯下斷面(控制斷面)位于樺川縣城上游,距離市區江上距離約為37 km;江南屯斷面(出境斷面)位于江川農場界內,距離市區江上距離約為61 km。選擇水深1.0~1.5 m處設置采樣點。

注:底圖源自國家測繪局地理信息局下載,網址為http://www.sbsm.gov.cn/公共服務/地圖服務/地圖下載頁面/河流水系版/400萬河流水質版,審圖號為GS(2008)1304號。
采樣方法根據原國家環保總局關于《水環境(生物部分)監測技術規范》的要求并結合松花江的實際水文狀況,使用人工基質采樣器,即掛籠法[18]。鐵籠為圓柱形,直徑18 cm,高20 cm,籠底鋪1層0.38 mm孔徑尼龍篩絹,籠內放滿約5 cm×7 cm的鵝卵石,每個采樣點放置2個鐵籠,在河底放置時間為14 d。樣品取出用孔徑為0.38 mm的分樣篩去除泥砂,之后撿出篩上的大型底棲動物,現場用30%酒精固定,回實驗室后換用70%酒精保存,并進行大型底棲動物鏡檢、分類鑒定。
1.2數據處理與分析
對固定的大型底棲動物進行分類鑒定后,把每個采樣點所采集到的大型底棲動物按不同種類準確統計個體數,并計算每一種類的密度(個/籠)。通過分析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組成和結構的變化,結合調查區域內大型底棲動物的種類組成特點,采用生物學污染指數(BPI)[19]、Chandler生物指數(CBI)[20]以及多樣性指數來分析大型底棲動物對水質狀況的指示作用。
1.2.1生物學污染指數
鑒于各種大型底棲動物對環境污染的耐受性不同,敏感種類將隨著污染加重而快速減少以至消失,而耐受性物種在一定污染程度內仍能存活,甚至數量會出現大幅度上升。根據2類物種隨污染變化而出現的不同反映,通過對搖蚊幼蟲、寡毛類等耐污種與多毛類、甲殼類等敏感種的多度進行數據轉換,計算BPI以評價水質污染程度。
BPI=lg(N1+2)/[lg(N2+2)+lg(N3+2)]
(1)
式中:N1為寡毛類、蛭類和搖蚊幼蟲個體數,個/籠;N2為多毛類、甲殼類、除搖蚊幼蟲以外的其他水生昆蟲的個體數,個/籠;N3為軟體類個體數,個/籠。BPI< 0.1表示清潔,0.1≤BPI<0.5表示輕污染,0.5≤BPI<1.5表示α-中污染,1.5≤BPI<5表示β-中污染,BPI> 5表示重污染,無生物存在為嚴重污染。
1.2.2Chandler 生物指數
CBI依據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類群對水體污染的敏感性及各類群出現的多度分別給予記分[21],按得分對污染狀況進行評價:CBI≤45表示重污染,45
1.2.3多樣性指數
Margalef 豐富度指數[22]:
d=(S-1)/lnN
(2)
式中,d為豐富度指數,N為底棲動物總個體數,S為底棲動物總種類數。評價標準:d>3,表示輕或無污染;1≤d≤3,表示中污染;d<1,表示重污染。
Shannon-Wienner多樣性指數[23]:
(3)
式中H′為多樣性指數,Ni為i種底棲動物個體數。評價標準:H′>3.5表示清潔,2.5 2.1大型底棲動物種類組成 調查期間在采樣區域共觀察到大型底棲動物51種,其中水生昆蟲33種,占總數的64.7%;軟體動物9種,占17.6%;甲殼動物3種,占5.9%,環節動物6種,占11.8%,觀察到的種類數情況具體見表1。 表1 采樣斷面大型底棲動物監測結果統計表 各斷面均以水生昆蟲的種類數最多,其次為軟體動物,該2類物種在各斷面的年度監測中均能被觀測到,且出現頻率較高;而環節動物與甲殼動物的種類數較少,且出現頻率較低。在佳木斯上斷面的監測中,僅在2006、2007年采集到環節動物,甲殼動物也只在2006、2008年被觀測到,如圖2所示。在佳木斯下斷面的監測中,僅在2009年觀測到甲殼動物,在2006年的監測中未發現環節動物,如圖3所示。在江南屯斷面的監測中,環節動物在2007、2008、2010年均被監測到,甲殼動物在2009、2010年被觀測到,如圖4所示。 圖2 佳木斯上斷面的群落結構圖 圖3 佳木斯下斷面的群落結構圖 圖4 江南屯斷面的群落結構圖 自2007年以后生物種類有所增加,增加的種類多為水生昆蟲,其中多為指示輕污染的種類,尤其是指示輕污染的翅目幼蟲(如石蠅)在整個江段均有發現(2006年前從未發現過),因其對生存環境要求較高,所以該幼蟲的出現表明水質發生了明顯的改善。大型底棲動物的部分種類組成及分布見表2。 表2 采樣斷面部分大型底棲動物的種類組成及分布 2005—2010年監測的生物密度年均值為11~513個/籠,單次采樣最多856個/籠,發生在2007年的江南屯斷面右,各年度各斷面生物密度年平均值見表1。生物密度的增加除了表現在優勢種增加外,還主要表現在水生昆蟲密度的增加,次優勢種多為水生昆蟲,表明水體現狀已經適應對水質要求較高的種類生存。 如表1、表2所示,2005—2006年各斷面的優勢種多為指示中污染的搖蚊或軟體動物,而自2007年起,優勢種多轉變為指示輕-中污染的種類,如紋石蠶、多距石蛾科的幼蟲,且占總數的比例較高,最高可分別達到78.6%和86.4%,指示輕污染的扁蜉和小蜉等蜉蝣目稚蟲在2007—2010年也都作為優勢種多次出現。各斷面次優勢種多為指示輕污染的種類,包括各種蜉蝣目稚蟲。可見,2007—2010年松花江佳木斯江段的水質逐漸從中污染向輕污染(或未污染)轉變,水質得到明顯改善。 2.2水質生物學評價 結合松花江的實際情況,根據已有的評價標準,采用BPI、CBI以及生物多樣性指數分析2005—2010年大型底棲動物對調查區域水質狀況的指示作用。由表3可知:2005—2010年的BPI僅有一項對水質的評價為中污染,其余均評價為輕污染狀態,對于輕污染的評價范圍較大,大型底棲動物優勢種、生物多樣性等群落結構的變化不能得到很好體現,對水質的年間變化指示作用相對較弱,與其他3種評價結果差異較大;CBI、d和H′對各監測斷面的評價結果差異較小,部分d和H′的評價結果優于CBI,這可能是由于多樣性指數僅考慮了物種群落結構和種類組成,沒有兼顧底棲動物自身的耐污水平,可能使得部分評價結果優于實際水質狀況。然而,從整體上來看,3種方法的評價結果在各監測斷面的水質年間變化趨勢上基本保持一致,能夠充分體現大型底棲動物的優勢種、生物多樣性等群落結構的變化,較靈敏地反映出年間水環境質量的變化情況。 表3 調查區域水質生物學評價結果 2005—2006年各監測點基本處于中污染狀態,2007—2010年各監測點中已有近1/3的評價結果屬于輕或輕-中污染水平,部分被評價為中污染的監測點的最終CBI也接近于輕污染水平的指數值(300)。其中,佳木斯上斷面在2007—2008年的生物評價指數值明顯上升,但水環境質量不穩定,2009年該斷面的生物評價指數值有所下降,2010年又有明顯上升,雖有波動,但總體上水質處于不斷改善狀態,說明上游來水水質經過多年的治理已初見成效。作為佳木斯市出境的江南屯斷面,2005—2010年的評價指數值雖然也曾出現一定的波動,但整體呈現上升的趨勢,表明該斷面水質正逐漸得到改善。可見,整個佳木斯江段在2007—2010年較2005—2006年的水質評價結果呈現整體上升趨勢,水質狀況正逐漸得到改善。 2.3水質理化指標與生物學評價的相關性分析 參考3個斷面8項與生物生存有關系的指標進行相關性分析,年均值見表4。各采樣斷面的pH均大于7,呈現一定的弱堿性,2010年各斷面的pH較往年有所下降;溶解氧含量2005—2007年達到地表水II類水質標準,2008年接近和達到I類水質標準,2009、2010年全江段達到I類水質標準,這在物種的分布上也得到了充分體現,對氧含量要求極高的翅目幼蟲近年來在整個江段均有出現,而2006年前的歷次監測中不曾有過,說明水質已經能夠滿足敏感生物的生存;高錳酸鹽指數在2005、2006年均維持在IV類水質標準,2007—2010年已有42%的數據滿足III類水質標準;佳木斯上斷面的生化需氧量年間波動較小且逐年降低,有從III類水向II類水轉變的趨勢,而佳木斯下斷面和江南屯斷面的生化需氧量調查期間變化較大,2008—2010年該指標明顯下降,已從滿足這種III類水質標準升至滿足I類水質標準;氨氮及總磷含量除2009年出現較大波動外,各監測斷面的含量多呈現逐年遞減趨勢,氨氮有從III類水向II類水轉變的趨勢;化學需氧量各斷面的年際間差異較小,維持在IV類水質標準;各斷面的總氮含量超標嚴重,年間波動范圍不大,但均達到V類甚至劣V類水質標準。 表4 調查斷面水質指標年均值 結合3個斷面的水質生物學評價結果可以看出,氨氮含量、總磷含量與水質生物學評價結果存在較為一致的波動方式。另外,生物學評價指數與理化指標間的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表明,在8項水質理化指標中,只有氨氮、總磷與生物評價指數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相關系數均大于或等于0.70(P<0.01)。由此可見,佳木斯江段的水生生態質量改善與溶解氧、氨氮以及總磷等指標的不斷改善有著直接的關系。 2.4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特征及水質響應分析 采樣結果表明,水質狀況與大型底棲動物的群落結構、優勢種類、種類數和棲息密度有密切關系。多年來,松花江佳木斯江段大型底棲動物的群落結構比較穩定,但群落組成有所變化,優勢種也由中污染的指示種向輕污染的指示種轉變,敏感的翅目稚蟲在整個江段的出現,傳遞出以溶解氧為代表的重要水質指標好轉;群落特征的變化與水質生物學評價結果相符,充分反映了水質狀況的變化趨勢,說明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特征與水質狀況存在一定的響應關系。 調查期間在采樣區域共觀察到大型底棲動物51個種,其中水生昆蟲33種,占總數的64.7%;軟體動物9種,占17.6%;甲殼動物3種,占5.9%,環節動物6種,占11.8%。水質生物學評價顯示,2007—2010年,佳木斯江段水質雖呈波動狀態,但整體呈不斷改善趨勢。 松花江佳木斯江段調查期間,氨氮、總磷濃度與水質生物學評價結果存在顯著的相關性,佳木斯江段的水生生態質量改善與溶解氧、氨氮以及總磷等指標的不斷改善直接相關。 不同種類的大型底棲動物對水體中污染的耐受能力各不相同,今后應根據松花江的實際情況,通過開展系統的生態調查與數據分析,篩選更為合適的指示生物、評價指標,構建符合客觀實際的評價方法與評價標準,對松花江的水質進行綜合生物評價,從而更準確地反映水環境狀況。目前,沿江的大型底棲動物監測網絡還不夠完善,站點設置過于稀疏;大型底棲動物的采樣頻次也有待提高,以便準確反映水體環境的時空變化。 參考文獻: [1]Growns J E, Chessman B C, Jackson J E, et al. Rapid assessment of Australian rivers using macroinvertebrates: cost and efficiency of 6 methods of sample processing[J]. J N Am Benthol Soc, 1997, 16(3): 682-693. [2]Clarke R T, Wright J F, Furse M T. RIVPACS models for predicting the expected macroinvertebrate fauna and assessing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rivers[J]. Ecol Modell, 2003, 160(3): 219-233. [3]Hering D, Buffagni A, Moog O,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a system to assess the ecological quality of streams based on macroinvertebrates-design of the sampling programme within the AQEM project[J]. Internat Rev Hydrobiol, 2003, 88(3): 345-361. [4]Klemm D J, Blocksom K A, Fulk F A, et al.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macroinvertebrate biotic integrity index (MBII) for regionally assessing mid-Atlantic highlands streams[J]. Environ Management, 2003, 31(5): 656-669. [5]Gerhardt A, Bisthoven L J, Soares A M V M. Macroinvertebrate response to acid mine drainage: community metrics and on-line behavioural toxicity bioassay[J]. Environ Pollut, 2004,130(2): 263-274. [6]Oberholster P J, Botha A M, Cloete T E. Using a battery of bioassays, benthic phytoplankton and the AUSRIVAS method to monitor long-term coal tar contaminated sediment in the Cache la Poudre River, Colorado[J]. Water Res, 2005, 39(20): 4 913-4 924. [7]Maloney K O, Feminella J W. Evaluation of single- and multi-metric benthic macroinvertebrate indicators of catchment disturbance over time at the Fort Benning Military Installation, Georgia, USA[J]. Ecol Indicators, 2006, 6(3): 469-484. [8]Hargett E G, ZumBerge J R, Hawkins C P, et al. Development of a RIVPACS-type predictive model for bioassessment of wadeable streams in Wyoming[J]. Ecol Indicators, 2007, 7(4): 807-826. [9]戴友芝, 唐受印, 張建波. 洞庭湖大型底棲動物種類分布及水質生物學評價[J]. 生態學報, 2000, 20(2): 277-282. [10]王備新, 楊蓮芳. 大型底棲無脊椎動物水質快速生物評價的研究進展[J].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 2001, 24 (4): 107-111. [11]黃恢柏, 王建國, 唐振華, 等. 兩種指數對廬山水體環境質量狀況的評價[J]. 中國環境科學, 2002, 22(5): 416-420. [12]王建國, 黃恢柏, 楊明旭, 等. 廬山地區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耐污值與水質生物學評價[J]. 應用與環境生物學報, 2003, 9(3): 279-284. [13]楊榮金, 舒儉民, 孟偉, 等. 空難對濕地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的影響[J]. 環境科學研究, 2006, 19(2): 104-107. [14]張敏, 邵美玲, 蔡慶華, 等. 丹江口水庫大型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及其水質生物學評價[J]. 湖泊科學, 2010, 22(2): 281-290. [15]陸光華, 王超, 包國章. 江中有機污染物結構與生物降解性定量關系研究[J]. 河海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3, 31(2): 200-202. [16]李平. 松花江水環境問題剖析與污染防治對策研究[J]. 環境科學與管理, 2005, 30(3): 5-8. [17]李再培, 程英, 呂琳. 松花江(哈爾濱段)底棲無脊椎動物群落構成與水質狀況的研究[J]. 黑龍江環境通報, 2000, 24(2): 114-116. [18]郝衛民, 王士達, 王德銘. 洪湖大型底棲動物群落結構及其對水質的初步評價[J]. 水生生物學報, 1995, 19(2): 124-134. [19]尤平, 任輝. 大型底棲動物及其在水質評價和監測上的應用[J]. 淮北煤師院學報:自然科學版, 2001, 22(4): 44-48. [20]Chandler J R. Applying a new score system of zoobenthos for assessing water quality[J]. Water Pollut Control, 1970, 69: 415-421. [21]房英春, 田春, 肖友紅. 蘇子河浮游藻類多樣性與水質的生物評價[J]. 水利漁業, 2007, 27(1): 57-58. [22]許木啟. 從浮游動物群落結構與功能的變化看府河-白洋淀水體的自凈效果[J]. 水生生物學報, 1996, 20(3) : 212-219.2 結果與討論







3 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