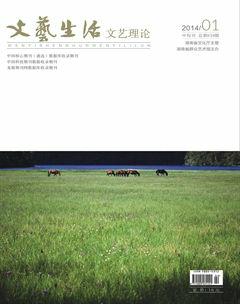小議肌理
——肌理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與發(fā)展應(yīng)用
陳師嘉
(汕頭工藝美術(shù)學(xué)校,廣東 汕頭 515041)
小議肌理
——肌理在藝術(shù)領(lǐng)域的體現(xiàn)與發(fā)展應(yīng)用
陳師嘉
(汕頭工藝美術(shù)學(xué)校,廣東 汕頭 515041)
在繪畫技術(shù)被剖析得如此透徹的當(dāng)下,尤其是高科技的引入,傳統(tǒng)的繪畫技巧技法很難再找到突破的空間,而借助于肌理的制作和處理,我們能找到更多的偶然性和可能性。在我的理解中,藝術(shù)追求的境界之一,便是它的不可預(yù)知性、不可復(fù)制性和唯一性,這是藝術(shù)品的價(jià)值所在。
肌理;應(yīng)用;制作
肌理這個(gè)詞在現(xiàn)代繪畫中被提到并不陌生,因?yàn)樵诟鳟嫹N,不管是油畫、水彩、中國畫這些主流畫種,或是丙烯、甚至延伸到版畫和雕塑,都對(duì)肌理作過探索性的應(yīng)用。肌理如何定義?肌理是指物體表面的組織紋理結(jié)構(gòu),即各種縱橫交錯(cuò)、高低不平、粗糙平滑的紋理變化。肌理還分自然肌理和人造肌理,所謂自然肌理即自然界中自然形成的紋理變化,如木紋、石紋等;人造肌理即人工制作或設(shè)計(jì)的紋理表現(xiàn),將原有材料的表面經(jīng)過加工改造,與原來視觸覺不一樣的一種肌理形式,通過雕刻、壓揉后進(jìn)行再排列、再疊加出現(xiàn)的紋理變化。如鞋印、布紋等。
一、被動(dòng)導(dǎo)入到主觀帶入
肌理的概念伴隨著繪畫的產(chǎn)生而出現(xiàn),隨著繪畫的成熟而具體,特別是繪畫技術(shù)和繪畫材料空前發(fā)展的當(dāng)代,對(duì)肌理的運(yùn)用和對(duì)肌理的開發(fā)進(jìn)入一個(gè)繁榮的階段。
二、時(shí)間分段角度切入
如此一說,并不是空穴來風(fēng),縱觀繪畫史,公認(rèn)最早的繪畫形式是“巖畫”,而能查閱到的資料中最早的巖畫出現(xiàn)在法國拉斯科洞窟中的動(dòng)物畫,這是能考證到的最早的繪畫記錄,距今已有約15000年。而所謂的這些巖畫,經(jīng)過科學(xué)家的研究發(fā)現(xiàn)其功能類似于我們今天的日記。天然巖塊自帶自然肌理,這是一個(gè)不爭的事實(shí),所以史前人類在完成這些圖案記錄的過程中,已經(jīng)無意識(shí)的把肌理的元素融入了畫面之中,而這個(gè)行為是史前人類無法操控的,因此,肌理塑造是無意識(shí)的被動(dòng)導(dǎo)入。這種無意識(shí)的導(dǎo)入在一段漫長的時(shí)間內(nèi)并不為人察覺,而當(dāng)繪畫藝術(shù)慢慢成熟,并衍生出多個(gè)畫種后,藝術(shù)家們才開始意識(shí)到肌理對(duì)畫面效果的影響。
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之前的時(shí)代,繪畫多以宗教題材為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所以藝術(shù)家在這個(gè)題材下發(fā)揮的空間不多。一直到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人文主義精神的星火開始從歐洲點(diǎn)燃,人們開始從以神為中心的思想體系轉(zhuǎn)向以人為中心的思想體系。在這個(gè)時(shí)代里除了世界聞名的藝術(shù)三杰“列奧納多·迪·瑟·皮耶羅·達(dá)·芬奇、拉斐爾·桑西、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以外,還有很多出類拔萃的藝術(shù)家,如喬托、波提切利、提香、丟勒等,在這個(gè)時(shí)期的眾多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肌理的效果已經(jīng)體現(xiàn),至于那是藝術(shù)家的神來之筆還是無心之作,我們也無從考證了,但是很明顯的一個(gè)現(xiàn)象就是在這個(gè)時(shí)期的作品的畫面中肌理的體現(xiàn)已越來越明顯,這無疑跟思想和個(gè)性的解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思想和個(gè)性的解放,對(duì)于追求自由個(gè)性的藝術(shù)家群體來說,猶如一馬平川,可以任意馳騁,在作畫的自由度上變得隨“意”而安,這里的“意”指的是意境,也就是說意境到了即可,不再拘泥于之前傳統(tǒng)封建的繪畫形式。
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思想洗禮為接下來的風(fēng)格主義做了一個(gè)很好的鋪墊,繼而開啟了17世紀(jì)巴洛克風(fēng)格和18世紀(jì)的洛可可風(fēng)格的盛世。在十七世紀(jì)眾多巴洛克風(fēng)格的名畫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作畫者對(duì)于物體的表面的質(zhì)感、材質(zhì)的刻畫已經(jīng)到了一定程度,這種對(duì)物體表面質(zhì)感的追求,其實(shí)就是作畫者在對(duì)肌理效果的一種自我要求,為表現(xiàn)出真實(shí)的材質(zhì)而深入刻畫。這一時(shí)期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倫勃朗,他的作品《帶金盔的人》對(duì)于金屬質(zhì)感的表現(xiàn)大量用了顏料堆砌的手法,而這種對(duì)這種意識(shí)在接下來的洛可可風(fēng)格的畫作中得以更加淋漓的體現(xiàn),細(xì)致觀察洛可可風(fēng)格的眾多名畫,我們又可以從中發(fā)現(xiàn)某些新的表現(xiàn)手法,在追求對(duì)材質(zhì)、質(zhì)感的表現(xiàn)之外,作畫者開始刻意放松筆觸的拘束度,在描畫質(zhì)感效果的同時(shí),柔和度和虛實(shí)感開始躍然于畫面。
從19世紀(jì)到近代,各種主義畫派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而肌理在這一時(shí)期的眾多畫種中得到了充分的拓展,發(fā)揮到了淋漓盡致,法國點(diǎn)彩派代表畫家修拉、荷蘭后印象派畫家梵高、法國野獸派創(chuàng)始人、畫家馬蒂斯,都是運(yùn)用肌理的大師級(jí)人物。
到了近現(xiàn)代,波普藝術(shù)更是與肌理效果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直到當(dāng)代,作為藝術(shù)類從業(yè)者的我們也不忘利用肌理來創(chuàng)作更多更美好更有視覺沖擊力的作品。因?yàn)樵诶L畫技術(shù)被剖析得如此透徹的當(dāng)下,尤其是高科技的引入,傳統(tǒng)的技巧技法很難再找到突破的空間,而借助于肌理的制作和處理,我們能找到更多的偶然性和可能性。
三、從繪畫領(lǐng)域向外延伸
肌理效果的應(yīng)用也不是繪畫領(lǐng)域的專屬,在各種藝術(shù)門類都能找到它的印跡,如陶藝、琉璃藝術(shù)、漆藝,乃至各種設(shè)計(jì)行業(yè),也開始在做肌理的文章了。
四、結(jié)論
由此可鑒,肌理在藝術(shù)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對(duì)于肌理的運(yùn)用在藝術(shù)的各個(gè)領(lǐng)域有著深遠(yuǎn)的影響,而且可以推斷出在未來的藝術(shù)領(lǐng)域發(fā)展道路中,肌理有著深不可測(cè)的潛力和生命力,而且蘊(yùn)藏著強(qiáng)大的爆發(fā)力。善加利用肌理,不失是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尋求突破的一個(gè)著眼點(diǎn)。
[1][英]維多利亞.查爾斯、[美]約瑟夫.曼卡、[美]梅根.麥克舍恩、[美]唐納德、維戈?duì)栔?何清新、趙克、黃藝平、韋秀玉、劉廣濱譯.大師名作1000幅.廣西:美術(shù)出版社.2006.
J205
A
1005-5312(2014)02-018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