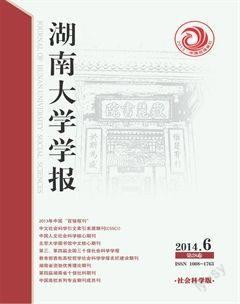從龍場悟道至天泉證道
[摘 要] 王陽明經典詮釋的歷程,主要分經典詮釋奠基時期、經典詮釋發展時期、經典詮釋成熟時期、經典詮釋的總結幾個時期,概括起來可以稱之為從龍場悟道到天泉證道的過程,其間在批評朱熹經學的基礎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無等一系列觀點與主張,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
[關鍵詞] 王陽明;經典詮釋;歷程
[中圖分類號] B248.2[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4)06—0025—09
From Comprehension in Longchang to Prove Dao in Tianquan
The process of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WANG Xuequn
(Institute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Wang Yangming’s intellectual thought, especially his thinking on Classics, and its development, by using hermeneutics as the way. I divide his thought on Classics into three phrases that includes the initial, developing, mature, and summarize stages. Hope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research on Wang Yangming’s thought about Classics would be pushed ahead.
Key words: Wang Yangming;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process
王陽明經典詮釋的歷程指他對儒家經典研究的經歷。經典詮釋的前提是熟讀或熟悉經典之后才開始,如果尋找帶有指標意義的事件,那么應該以龍場悟道開始,到天泉證道結束,這一段大體代表經典詮釋的時期。他的主要經學思想都在此時通過詮釋經典提出并展開加以系統化。
一 經典詮釋奠基時期
王陽明經典詮釋時期始于龍場,龍場悟道是理解其經典詮釋時期的關鍵,它開啟了經典詮釋,也可視為經典詮釋的奠基時期。
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時任兵部主事的王陽明因替戴銑洗冤而批評時政,得罪明武宗、宦官劉瑾,被貶為貴州龍場驛(今貴州修文縣)驛丞。在赴謫途中,歷盡險阻,占卜筮得《易經》“明夷”,有詩云:“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云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王陽明:《泛海》,《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22頁。表現了不畏艱危的胸懷。他在決意去貴州之前回南京省親,又至錢塘與徐愛等三友道別,向他們道出自己的期許:“天將降大任于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于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
王陽明:《別三子序》,《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42頁。到達龍場后,他面對現實,引《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王陽明:《與王純甫書》,《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67頁。以為君子只求就現在所處的地位,來做他應該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既來之則安之,在此地安于現狀,自有一番作為。對于當地的艱苦條件,他表現得十分達觀,引《論語》言:“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王陽明:《何陋軒記》,《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933頁。自比君子,君子所居住自然條件雖然簡陋或生活艱苦,但精神上有所追求有所發明,卻是富麗輝煌的。又作詩云:“投荒萬里入炎州,卻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雖吏隱未忘憂。”
王陽明:《龍岡漫興五首之一》,《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741頁。雖然身居遙遠的蠻荒之地,但樂觀自由,雖受不白之冤,仍憂國憂民。
王陽明早年困于格竹子,又迷于佛老二氏,帶著困惑與迷茫踏上了去龍場的道路,而“后至龍場,又覺二氏之學未盡。履險處危,困心衡慮,又豁然見出這頭腦來,真是痛快,不知手舞足蹈。此學數千百年,想是天機到此,也該發明出來了。此必非某之思慮所能及也。”
王陽明:《陽明先生遺言錄》,《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606頁。他在龍場如此痛快是因為悟道,即體悟儒家經典之道,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第一,心即理與格物致知。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在貴陽龍場,王陽明始悟格物致知。正如《年譜》載:龍場地處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鳥夬舌難語,可用語言交流的大都是中土亡命之士。當地人沒有居所,他開始教他們蓋房而居。宦官劉瑾當政,他雖然能超脫得失榮辱,但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于是為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郁,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圣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于是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經臆說》。
錢德洪:《年譜》成化十八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34頁。
他在《朱子晚年定論序》中講“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致王純甫寫道:“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后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于憂患’之言非欺我也。”
王陽明:《與王純甫書(壬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66-167頁。又致希淵:“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最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
王陽明:《寄希淵(己卯)》,《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72頁。王陽明就是那個天將降大任于斯之人,歷史賦予他創造使命,要肩負起這一使命就必須在艱苦的環境中磨煉體魄與心志。在貴州龍場條件艱苦,他體悟到格物致知的宗旨,就是“吾性自足”,即不是舍心求事物之理,而是求事物之理于心中,這就是心即理之說。可以說他是在心即理基礎上談論格物,格物是心中之物,由此來看,“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誤也”,把心與理一分為二是錯誤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吾心自足,所謂心即理,理不在事物之中而在心中,天賦人之本性即所謂的善,對于人來說是與生俱來而且充足,無需向外苦苦求索,反身本心即可。這里講的“忽中夜”并非突然,而是他長期困于格物或者說思索的結果,是量積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質變。當然他對此忽然悟道還不放心,取儒家經典試圖獲得理論證明,所謂道在經中,這一發明是對經典的詮釋。
第二,道在經中,以經求道,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五經臆說》之作。他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寫序說:“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圣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于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于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為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于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為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于曲糵,而非誠旨于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
王陽明:《五經臆說序(戊辰)》,《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917-918頁。用他的話說,此書共四十六卷,《五經》各為十卷,而《禮》說尚多缺,僅六卷。遺憾的是此書亡佚,只留下若干條,由弟子收入遺書中。
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他在給弟子書信就對經典離道而流于訓詁、辭章之學予以批評,“六經分裂于訓詁,支離蕪蔓于辭章舉業之習,圣學幾于息矣。”
王陽明:《別三子序(丁卯)》,《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41頁。《五經臆說序》中的“得魚而忘筌”源自《莊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醪糟用盡之后被當成糟粕扔掉,喻指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來依靠的東西,但事未成則不應舍棄所依靠的東西。以此比喻儒家的經典與道的關系,儒家經典對于掌握圣人之道來說也不過是醪糟,但他不贊同把作為醪糟的經典僅當成糟粕,醪糟與糟粕有所不同,前者是達于圣人之道的工具,后者則無用。這說明道在經中,但也不能教條化或墨守陳規,即所謂的“求魚于筌”,局限于經注,這樣經是經道是道,彼此離開更遠。他的基本主張是經道合一,道在經中,以經求道。基于此,在當時的條件下,無經書可讀,他則通過回憶把握以前所學經書要旨,有所得后加以詮釋,成《五經臆說》。此書并不完全符合先賢的經注,但卻有創見。
第三,始論知行合一。關于這方面的記載,《年譜》有兩條。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條載: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圣人之學復睹于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錢德洪:《年譜》正德四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35頁。陳榮捷認為,此條載《年譜》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四月,詞句稍異,而意旨全同。但明謂“后”徐愛因未會知行合一之訓,請決于陽明。非謂此對語錄為是年是月之事也。陳來說:“《年譜》以徐愛所錄知行合一之論為在壬申冬南下舟中論學語,然錄中言‘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于先生’,則所錄亦非皆是舟中所論。”《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107頁。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條載:“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
錢德洪:《年譜》正德五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36頁。 陽明自己也曾回憶說:“吾居龍場時,夷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亡命之流。與論知行之說,更無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拍挌不入。”
王陽明:《傳習錄拾遺》,《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550頁。錢德洪《刻文錄敘說》引陽明的話說:“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捍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六冊,第2088頁。綜上所述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其一,王陽明在貴陽龍場始揭知行合一之教,但未能得到積極響應,反而遭到質疑。他當時與土人相處似很融洽,與士大夫反而有距離。他與當地土人講知行之說得到認同,可能因為那里的人閉塞,不知有異說,而與士大夫講知行之說卻建議不統一,議論紛紛,其原因是“意見先入”,這里雖未說明,恐朱熹的知行之說有影響,而這成為他創發知行合一說的動機。后來在北京,知行話頭也不常提起,因為當時始悟格物致知之旨,發明吾性自足,靜坐收心而非知行合一,真正系統研究知行合一是在以后。其二,知行合一的重點是知行本體,即知行合一是知行本身或內在的需要,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又“征之五經諸子”,尤其是五經,再次說明他依據經典發明圣道。其三,他所理解的知行合一屬于道德倫理范圍,主要講道德說教與實踐的關系,涉及心理活動與行為等。
第四,萌發良知思想。良知及致良知雖然是以后明確提出來的,但龍場的經驗至關重要,此一時王陽明心中已經蘊育,只是沒有論述。如他所說:“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于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于聞見障蔽,無人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王陽明:《傳習錄拾遺》,《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548-1549頁。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陽明被貶至貴州龍場,從百死千難中悟得良知之說,即經歷了龍場所謂“居夷處困”之后才悟得來,良知在龍場之后萌發,經不斷錘煉,愈來愈完善。揭示良知可謂洞見心體,為陽明貢獻所在,他毫不掩飾自己發現良知的喜悅之情。良知即是心之本體,屬于內在,無需外在工夫,或直下或當下,反省內尋,自然悟得,借用禪語把良知視為究竟話頭,說話的端緒,也即一切都要從良知談起。如果埋沒良知,則無從談起,良知是王陽明經學思想的基礎。錢德洪說:“謫居龍場,衡困拂郁,萬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
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序》,《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372頁。又說:先師“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
錢德洪:《答論年譜書》,《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394頁。誠意格物之教的系統闡釋是在發明良知之后。
二 經典詮釋發展時期
所謂經典詮釋發展時期,指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后,其經學思想在此時全面鋪陳開來,多度發展。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十二月,王陽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歸省,與徐愛論《大學》宗旨。聽了王陽明一番議論,徐愛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各有不同,宗旨一致。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七月,刻古本《大學》。至是他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他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圣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圣人之學本來簡易明白。《大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于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致知格物之功。至是錄刻成書,“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
王陽明:《大學古本序(戊寅)》,《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59頁。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論《大學》輒持舊見,稱“《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
王陽明:《答方叔賢(己卯)》,《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88頁。湛若水寄示《學庸測》,叔賢寄《大學》、《洪范》。王陽明分別致信若水、叔賢,說:“‘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厘未協,然亦終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
王陽明:《答甘泉(辛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94頁。又“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學》而已。”
王陽明:《答方叔賢(辛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97頁。 強調格物及《大學》古本的重要性。
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王陽明升文選清吏司員外郎,送湛若水奉出使安南。王陽明升遷南京時,湛若水與黃綰言于楊一清,改留吏部。職事閑暇,他們開始在一起討論,甚至吃住在一起,相互期待對學術有所促進。至此,湛若水出使安南封國,王陽明唯恐圣學難明而容易產生遺惑,人生分別容易而相會困難,因此作文以相贈。在此,他提出儒家道統說:“顏子沒而圣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后,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尊孔、孟,賤楊、墨,擯釋、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從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見之矣”,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夸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圣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于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為者,雖其陷于楊、墨、釋之偏,吾獨且以為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與之言學圣人之道。”
王陽明:《別湛甘泉序(壬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45-246頁。并自以為肩負著弘揚儒學的使命,自謂幼不問學,陷溺于邪僻多年,后又究心于佛老二氏之學,再次誤入歧途。賴天之靈,因有所覺,開始沿著周、程之說求孔門正學,如果有所得,愿與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尤其愿與湛若水復興儒學而共同努力。
王陽明經典詮釋的思想形成離不開朱熹,科舉時期系統學習過朱熹的學說,后來在實踐中對其產生質疑,有所反思,對于理學史上的朱陸異同發表己見。早在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時,他就討論過朱熹、陸九淵之學,其學術路數明顯傾向陸九淵,為其打抱不平。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七月,他把撰成的《朱子晚年定論》付梓,此書的宗旨在于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對于陸九淵,他予以推崇。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他為陸象山文集寫序,稱“圣人之學,心學也”
王陽明:《象山文集序(庚辰)》,《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60頁。。孟子之學即是心學,而陸九淵為孟子正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正月,他以為陸九淵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牌行撫府金溪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仿各處圣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錢德洪認為,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于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顯。《年譜》辛巳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88頁。
王陽明在龍場對心即理、吾性(心)自足等都有發明,作為本體的性體、心體的認識大體確立,而這些離不開功夫。在他看來,本體由功夫顯現,功夫是他經學思想的重要內容,既重本體又注意到功夫,這與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說是一致的。
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末,王陽明從貴陽回歸途中在湖南辰州教人靜坐功夫。他說:“前在寺中所去靜坐之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拿,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又引程顥語:“才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著力處。”
王陽明:《與辰中諸生(己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56頁。靜坐并非如佛家坐禪入定,而是補小學收放心功夫而已。又告誡諸友應從此處著力才能有進步。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三月,他升江西廬陵縣知縣,主張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注重功夫,試圖以靜坐自悟性體。他后來回憶說:我昔居滁(正德八年在滁陽)時,見學者往往口耳異同之辯,無益于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亦漸有喜靜厭動之弊。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15頁。多就高明一路以求時弊。與滁陽諸生問答:或患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個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
王陽明:《與滁陽諸生并問答語》,《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1030頁。陽明在南都說:“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污,引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
錢德洪:《年譜》正德九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43頁。錢德洪說他“在金陵時(公元1514-1516年)已心切憂焉,故居贛時(公元1517-1518年)則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實功。”
錢德洪:《與滁陽諸生問答按語》,《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1030-1031頁。在南京任鴻臚至平定江西暴動,注重功夫。正德十五年(1520),他又論動靜說:“心無動靜者也,故君子之學,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又“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五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89,1290頁。。 注重動靜工夫是這一時期的學術特色。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十二月,王陽明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論實踐之功。他與黃綰、應良論圣學久不明,學者想要做圣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認為這很困難。錢德洪按語認為,“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后,吾黨又覺領悟太易,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里著己之功矣。故吾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憂也。”
錢德洪: 《年譜》正德五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37—1238頁。本體由功夫顯或通過功夫達于本體,實踐是其中重要的環節。
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十月,王陽明舉鄉約。他認為,自大征后,以為民雖格面而未知格心,于是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同年,他致信仕德,謂“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錢德洪: 《年譜》正德十三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55頁。只有格心才能破心中賊。正德十五(公元1520年)年六月,他與羅欽順討論《大學》,稱格物為“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王陽明:《傳習錄中·答羅整庵少宰書》,《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83頁。。九月,他與泰州王艮論致知格物,王艮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他易其名為“艮”,字以“汝止”。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五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86頁。格物建立在心即理基礎之上,格物即格心,此為陽明格物的正解。格物立足于心,樂何嘗不由心發。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同月,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王陽明問律呂。陽明不答,又問元聲。回答:“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密室經試耳。”王陽明說:“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氣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舒芬遂躍然拜弟子。
同上,第1286頁。
王陽明強調功夫為其經學思想的特色,其核心是本體與工夫的一致,本體即工夫的本體,工夫即本體的工夫,側重工夫實際上是告誡本體要由工夫顯現,側重本體實際上是告誡工夫也要在本體上下,二者并沒有輕重,只有角度不同而已。
三 經典詮釋成熟時期
王陽明盡管自龍場回來以后已經悟得良知,但并沒有想好如何論述。自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開始,他就意識到僅憑靜坐不能解決在成圣成賢修養中所遇到的問題,龍場以來一直潛藏在心中的良知思想開始涌動萌發。正德十四(公元1519年)年起,他比較系統地公布及闡釋自己的良知學說。王陽明經學思想的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之學,良知之學的系統化標志著其經典詮釋進入成熟時期。
據《年譜》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十月,王陽明到滁州督馬政。此時諸生大都通過靜坐來抵御口耳異同,但他發現專以靜坐為工夫容易陷入喜靜厭動枯槁之病,這為后來提出以致良知精神試圖扭轉此弊創造前提條件。他認為,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悟或事上磨練,良知本體原無動靜,這便是學問頭腦。致良知是實踐中得來,以此為主軸藥到病除。這里明確指出“自滁州至今”經反復思慮,此后“致良知”是他經學思想的不二宗旨。滁州以后陽明有變化。《傳習錄》載: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王陽明回答:“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于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練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15頁。《傳習錄拾遺》也有類似的說法:“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為口耳同異之辯,無益于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可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
王陽明:《傳習錄拾遺》,《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555-1556頁。居滁期間,他已經意識到專以靜坐非但不能克服口耳同異之辯,而且還患上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正是此時致良知工夫蓄勢待發了。
王陽明自謂:“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王陽明:《傳習錄拾遺》,《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556頁。揭示良知在他任南京鴻臚寺卿之后,但具體的時間沒有說。黃綰則直接說:“甲戌,升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
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428頁。但缺乏其他材料作為佐證,不過這時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良知之學,但其已教人遵循良知精神。
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以平寧藩為標志,王陽明開始明確闡釋良知致良知學說。錢德洪在論述王陽明平寧藩之后寫道,陽明“始教學者悟從靜入,恐其或病于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之下,洞見全體。”
錢德洪:《陽明先生年譜序》,《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372頁。這里的“至是”指征藩,從這時起他明確提出“致良知”,以此為標志,良知之學成為這一時期思想詮釋的主軸。錢德洪說:“辛巳以后,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
錢德洪:《答論年譜書》,《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394頁。又說:“蓋師學靜入于陽明洞,得悟于龍場,大徹于征寧藩。”
錢德洪:《續編四序》,《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1089頁。平寧藩以后開始明確良知宗旨,至辛巳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則進一步深化,似乎一切問題都從良知角度來理解,或者說從良知出發處理或詮釋問題。
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九月,王陽明至南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銳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徹講擇交相勸。王陽明回答道:“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得啟悟,故甘隨俗習非。今茍以是心至,吾又為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87頁。良知人皆同然或人人都有良知,只是尚未發現,因此才為習俗所困。良知自在人心,發明本心,開啟良知才能超脫習俗。王陽明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致書陸元靜:“致知之說,向與惟浚及崇一諸友極論于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
王陽明:《與陸原靜(壬午)》,《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02頁。惟浚即陳九川字,崇一為歐陽德字,二人庚辰(正德十五年)在江西侍陽明。此時陽明與陳九川、歐陽德諸弟子談論致良知。陽明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致書薛尚謙再論良知后說:“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
王陽明:《寄薛尚謙(癸未)》,《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13頁。 兩封信皆說明在虔州(贛州)就曾講致良知之說。
《傳習錄》載: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陳九川去虔州見王陽明,師生兩人談話涉及良知。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答:“爾卻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問:“請問如何?”答:“只是致知。”問:“如何致?”答:“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01-102頁。在虔州陳九川與于中、謙之同侍陽明,陽明說:“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02頁。陳九川自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良知何事系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為圣學,將迎無處是乾元。”陽明說:“若未來此講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個什么?”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04頁。在一旁的敷英則認為,發明致良知后,看《大學古本序》才知大意。
《年譜》載: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在江西。正月,居南昌,王陽明始揭致良知之教。陽明聞前月十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后圣,無弗同者。同年致友人、弟子書信多次提及致良知,如他在與楊仕鳴書寫道:“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于此見得真的,真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王陽明:《與楊仕鳴(辛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98頁。對湛若水說:“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圣學傳心之要,于此既明,其余皆洞然矣。”
王陽明:《與甘泉(辛巳)》,《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94頁。遺書鄒守益說:“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門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矣。”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六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1287頁。此信未查到,疑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致信鄒守益有“近時四方來游之士頗眾,其間雖甚魯純,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掇,無不即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真吾圣門正法眼藏。”王陽明:《與鄒謙之(乙酉)》,《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91-192頁。錢德洪刻陽明文錄引此段并肯定的說:“‘良知’之說發于正德辛巳年(1521——引者)。”
錢德洪:《刻文錄敘說》,《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六冊,第2089頁。
《年譜》同條載:一日,陽明喟然發嘆。陳九川問:“先生何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百年。”九川曰:“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陽明說:“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對相傳一點滴骨血也。”又說:“某于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六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87-1288頁。《傳習錄拾遺》四十四條有相同的記載:一天,陽明喟然發嘆。陳惟浚問:您為何發嘆?陽明答:此理簡易明白如此,卻一經沉埋數百年。陳說:“亦為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為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陽明說:“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為祖墓者,何以為辨?只得開壙,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圣賢相傳一點骨血也。”
王陽明:《傳習錄拾遺》,《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557頁。良知本來既簡易又明白,可是后來為人們所忽略,尤其是宋儒指朱熹從知解上入手,即重視感覺聞見而忽視心性本體,阻礙圣道。他以為自揭出良知才真正體認心體即天理,良知才是圣賢相傳的精髓。
《年譜》同條又載:“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為本”,“今經變后,始有良知之說。”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六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88頁。 “今經變”指經歷了宸濠、忠、泰之變以后,明確闡釋“致良知”之說。《傳習錄拾遺》載:陽明對友人說:“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含諸口,莫能相度。”久乃說:“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此更無余矣。”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說:“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后,始有良知之說。”
王陽明:《傳習錄拾遺》,《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五冊,第1549頁。經歷居夷處困后,陽明發現良知,在此之前似有所得,但似處在一種朦朧狀態,“這些子”,給人以模糊之感。良知得圣賢之真傳。 同年九月,王陽明歸余姚省祖墓,此間與宗族親友宴游,隨地指示良知。
錢德洪:《年譜》正德十六年條,《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91頁。
自龍場起,王陽明就已知意識到良知,開啟了良知萌發的過程,只是不成熟,出于謹慎沒有明確提出并加以闡釋。此后的一段時間,在良知萌發過程中發生了一些帶有標志性的變化,分別是在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滁陽開始思考良知,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任南京鴻臚寺卿以前后的思想轉變隱含著從此后以良知宗旨。而平寧藩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虔州(公元1520年)、辛巳即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這三年則明確確立以良知為學宗旨并以此教人。思想不是事件,不必確定在某個時間點上而是一個過程,如果把正德八年至正德十六年這八年連成一條線來考察,可以得出王陽明良知學說由隱到顯、潛至伏,也即由不明確逐漸到明確的演進過程。
嘉靖改元,王陽明居越講學,專提致良知。在此期間與諸友及弟子通信中反復闡發良知學說。相關論述擇要如下:
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王陽明致陸原靜書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
王陽明:《與陸原靜二(壬午)》,《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02頁。以是非之心詮釋良知。
嘉慶二年(公元1523年),二月。王陽明針對別人的各種誹謗說:“吾自南京已前,尚有鄉愿意思。在今只有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無掩藏回護,才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
王陽明:《年譜》,《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96—1297頁。鄉愿無是非觀念,而良知辨明是非,以良知來實踐。同年王陽明與薛尚謙書回憶在虔州時刻討論致知,只是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于古本序中改數語,頗尤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
王陽明:《寄薛尚謙(癸未)》,《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13頁。點出致良知為孔門的精髓。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正月。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稱門生,然性豪曠不拘小節,陽明與論學有悟。大吉說:“良知。”陽明說:“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于是辟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陽明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
錢德洪:《年譜》,《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四冊,第1299頁。
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王陽明說:“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啟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
王陽明:《書魏師孟卷(乙酉)》,《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98頁。自詡其致良知之學傳承孔子、孟子,以良知開啟同志。他與王公弼書說:“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
王陽明:《與王公弼(乙酉)》,《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11頁。良知是自知之明,是知的最高層次。
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王陽明致鄒守益,稱:“比遭家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又“除卻良知,還有甚么說得?”
王陽明:《寄鄒謙之(丙戊)》,《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14,218頁。在工夫的實踐中,對于“良知”的體認更為親切。致鄒守益第五書:“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
王陽明:《寄鄒謙之五(丙戊)》,《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20頁。良知已經闡釋得十分明確,希望弟子們各盡所能,共同推進。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王陽明病中仍草書諸友及弟子。得聶豹來書,見聶豹近來所學進步如此之快,王陽明欣慰之情難以用語言表達。致魏師說:“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
王陽明:《答魏師說(丁亥)》,《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31頁。以意做參照定義良知為意之是非者,遵循良知則不會犯錯。與馬子莘說:“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為贅疣,今之朋友以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
王陽明:《與馬子莘(丁亥)》,《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32,233頁。把良知與天理看成一致的,天理并非外而屬內,天理即良知。至黃宗賢書:“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
王陽明:《與黃宗賢(丁亥)》,《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34頁。與以乘書:“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
王陽明:《答以乘憲副(丁亥)》,《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35頁。對良知之說雖然有所懷疑,但人心所有之良知,則永恒存在,人們應善于發現它。與陳惟浚說:“圣賢論學,無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
王陽明:《與陳惟浚(丁亥)》,《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236頁。致良知簡易明白,便于實踐。征思、田途中示兒:“吾平生講學,只是致良知三字。”
王陽明:《寄正憲男手墨二卷》,《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三冊,第1039頁。這是對平生學問的高度概括。王陽明于嘉靖七年病故,可見他生前一直關心良知之學,為弘揚良知之學而不遺余力,可謂殫精竭慮,死而后已。
良知之學是王陽明經學思想的核心,自其系統闡發良知之后,其他范疇或概念納入到良知系統中,或者說都可以從良知角度加以詮釋,他以良知為基軸構建起自己的經學思想體系。
四 經典詮釋的總結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王陽明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廣西思恩田州二地,臨行前與兩位弟子錢德洪與王畿在天泉橋上討論所謂“四無”、“四有”,所論包括心性及格物、良知,或者說涉及他經學思想的核心,學者稱此為“天泉證道”,可以說是王陽明經典詮釋的總結。
《傳習錄》記載:王畿提到王陽明的教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
毛奇齡《王文成公傳本》載四句教說:“良知”作“致知”。自注“或作良知,誤。” 為善去惡是格物。”錢德洪問道:“此意如何?”王畿說:“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錢德洪說:“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28頁。關于“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這四句話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次為首句,意思是說心之本體無所謂善惡,也可以視為超越善惡,在這里心與性合一,性與天道合一,是最原發之性存在于心中,相對而言屬于形而上,是先天或超驗的。第二個層次是后三句則有了善惡,這已經不是心體,心與性、性與天道一分為二,相對而言屬于形而下,進入后天或經驗的氣化階段。惡的出現就需要工夫,使之回歸本體,達到本體與工夫的一致。后三句第一句,意念的萌動才有善或惡,對于善惡的態度二分步,首先要以良知來知曉善惡即區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惡,其次才是為善去惡,而這便是格物的工夫。在這里,本體與工夫從原初一致到可能不一致再通過工夫回歸一致。錢德洪反問王畿這四句話意思如何?王畿認為這四句話恐不符合王陽明之教,于是王畿提出“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另外四句話與之對立。在他看來,既然心體是無善無惡的,那么與此相關,意知物這三者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因此反對意有善有惡,心體卻無善無惡之說。錢德洪又認為,心體指的是天命之性,所謂心與性、性與天道合一,原本無所謂善惡或超越善惡,而心內在于人在后天受習染影響,意念萌發之中必然表現出善惡,因此才需要《大學》所謂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等工夫以恢復其本心即原發之性,倘若沒有惡,功夫則變得無意義。錢德洪和王畿各持己見且爭執不下,就教于王陽明。
王陽明對他們說:“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 我里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里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執一邊,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體各有未盡。”
王陽明:《傳習錄下》,《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第128-129頁。他區分錢德洪與王畿說法的適應范圍,認為“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與“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并不矛盾,可以“相資為用”,所謂并行不悖。于是分別以兩種人為例闡釋自己的主張:利根之人即天性伶俐的人,屬于“四無”,這種人天賦人性本原處悟入人心,在未發時便是中,心與性、性與天道一致,本體與工夫統一。利根以下之人即一般人,屬于“四有”,這種人本體受習染等遮蔽,心與性、性與天道一分為二,因此要下功夫,在意念上為善去惡,功夫盡到本體自然顯現,也就是說通過工夫復歸本體,達到本體與工夫的一致。王畿強調“四無”指的是天性伶俐之人,錢德洪重視“四有”指的是一般人,兩人的意見互補,一般人雖然有程度上的差異,但經過努力皆可回歸本體,所謂殊途而同歸。因此,他反對把“四無”與“四有”片面甚至走向極端。天泉證道的核心是強調本體與工夫的一致,是良知之學的精髓,也可視為其經典詮釋思想的總結。
王陽明的經典詮釋歷程,概括起來可以稱之為從龍場悟道到天泉證道的過程,其間在批評朱熹經學的基礎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無等一系列觀點與主張,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他的良知學說可以說是以道德為本體、以修養為工夫的道德形而上學,其最大特色是對道德主體的高揚與道德自覺的肯定,從正面或積極角度闡釋人成圣成賢的潛能及其實踐的價值,使其超越時空而具有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