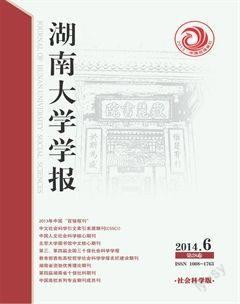何休《公羊解詁》的君主論思想
[摘 要] 何休在《公羊解詁》中,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視域,闡發了其有關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論。其君主論,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定為核心,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養,以孝、廉、信表率天下;主張“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提倡重民用賢的德政;在君臣關系上強調“以道事君”,甚至提出君臣之間存在“朋友之道”;在君位傳承上則堅持以嫡長繼承制為正道。
[關鍵詞] 社會秩序;君德;為政;君臣關系;君位傳承
[中圖分類號] B234.99[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1763(2014)06—0005—09
He Xiu’s Monarch Theory in “Gongyang Jiegu”
ZHENG Renzhao
(Institute of History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He Xiu presented his theory of monarchs and monarchy politics in Gongyang Jiegu,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ongyang School. His theory focuses on the maintaining of social order and peace, urging monarchs to improve their own morality, and exhibit themselves as the models of filial piety, honesty, and credibility before their people. His theory also advocates the political order of “Great Unity”, and the “Benevolent Ruling”,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aking care of common people and appointing righteous men in government positions. On the issue of monarchminister relationship, he holds the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Monarch according to the Truth.” He even claims that there are genuin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ministers. On the issue of throne succession, he respects the lineal primogeniture.
Key words: social order; monarch morality; government ruling; monarchminister relationship; throne succession
何休(129—182)是漢代春秋公羊學大師,他殫精竭慮注疏《春秋公羊傳》,花費十七年的時間寫下《春秋公羊解詁》。《公羊解詁》是后世《公羊傳》的標準注本,在經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何休所處的東漢末年,是與春秋時代一樣的亂世。桓靈時期,“主荒政繆”[1](黨錮列傳),外戚和宦官交替專權,政治極為黑暗,人民生活極為困苦。何休本人也被宦官集團禁錮十幾年。面對黑暗的政治現實,何休苦苦思索“撥亂反正”的濟世良方,期待清明的君主政治的出現,渴望恢復社會的有序狀態。《春秋公羊傳》本身具有強烈的追求社會秩序的傾向,[2] 何休在注解《公羊傳》的時候,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視域,以維護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定為核心,闡發了許多有關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論,對為君之德、為政之道、君臣關系及君位傳承等問題都有深入的思考。
一 為君之德
儒家向來重視君德。在君主專制之下,君主的圣明與否直接決定國家的治理與否。東漢末年的桓、靈二帝就是驕奢淫逸之主的典型代表,他們的統治使東漢王朝直接走向崩潰的邊緣。何休在《公羊解詁》里非常鮮明地指出:“不肖之君為國尤危。”[3](桓公三年)
在闡述君權的合法性時,何休說:
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3](成公八年)
王者的合法性雖然是來自于天,但其落腳點顯然在于“德”,強調的是“德合元者”,“德合天者”,“仁義合者”,實際上是將君德置于核心地位,最終君權的合法性來自于以德贏取民心而天下歸往。
何休強調君主身先天下的表率作用,指出“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于辟雝,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3](桓公四年),認為君主的德行對民眾具有非常巨大的感召力,對社會風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何休繼承了孔子“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4](顏淵)的思想,主張君主應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于人”[3](隱公二年),又說:“王者起當先自正,內無大惡,然后乃可治諸夏大惡,……內有小惡,適可治諸夏大惡,未可治諸夏小惡,明當先自正然后正人。”即要求君主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在各方面都要為民之先。
具體而言,君主首先要做到“躬行孝道以先天下”[3](桓公十四年)。
何休在《解詁》自序里稱:“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圣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孝經》以孝為“德之本”[5](開宗明義),孝道是何休在君德中最為重視的內容之一。孝是何休評價君主的一大標準。如他盛贊“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3](桓公八年),指責周襄王“出居于鄭”是“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3](僖公二十四年)。
[3](閔公二年),三年之中“孝子疾痛,吉事皆不當為”[3](文公二年)。對君主的不守喪行為,何休都予以指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為魯文公聘婦,何休譴責文公“喪娶”[3](文公七年),指出“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先納采、問名、納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僖公九年,宋桓公去世不久,剛即位的宋襄公就赴葵丘會諸侯,何休指責宋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
何休對孝的推崇與漢代標榜以孝治天下是分不開的。他在《莊公二十五年》借《孝經》之文明確提出了君主“以孝治天下”的主張:“禮,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禮之。《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是也。”以孝治天下,孝不僅限于事親,更擴展為社會倫理、政治倫理,要求君主推其愛敬之心及于臣民百姓。他提出:“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為其近于道也;貴臣,為其近于君也;貴老,為其近于父也;敬長,為其近于兄也;慈幼,為其近于子弟也。”[3](桓公四年)何休這里提出了王者治理天下的五大原則:貴有德、貴臣、貴老、敬長、慈幼,就是要以愛敬之心對待臣民百姓。于是貴有德、貴臣、貴老、敬長、慈幼,“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也都經由孝道貫穿起來。
其次,君主要做到“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廉而不貪、儉約輕利也是何休在君德中非常重視的內容,《公羊解詁》中再三致意。何休評論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一事說:
王者千里,畿內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3](桓公十五年)
君主一旦貪利,上行下效,最終就會使人人唯利是圖,吏治腐敗,民間盜賊橫行,造成整個社會貪鄙成風、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惡果,必然會導致社會危機的產生。因此何休主張,君主有正常的租稅和貢品足以滿足需求,除此之外不應該再索取財物。何休非常強調儉約的重要性,其稱“約儉之衛,甚于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3](宣公六年)。層層防衛,還是難以完全防止盜賊,而上下儉約,卻可以從根本上斬斷貪利之欲。所以他奉勸君主要“厚于禮義,而薄于財利”[3](宣公十二年),尤其不要與百姓爭利,強調“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當與百姓共之”[3](桓公十六年),不要把君權變成牟取私利的工具。
隱公五年“公觀魚于棠”,對魯隱公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張網捕價值不菲的魚,何休痛斥隱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文公七年,魯文公伐邾婁,取須朐,何休指責文公“貪利取邑,為諸侯所薄賤”。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靈王以蔡靈公弒父為由,誘殺蔡靈公,進而滅蔡,何休揭露楚靈王“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讬討賊”,聲明“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宣公十五年“初稅畝”,何休譏諷魯宣公“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成公十八年“筑鹿囿”,何休也都責之以“奢泰”。
第三,君主“當以至信先天下”[3](桓公十四年)。
文公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楚師圍江國,晉軍伐楚以救江,卻遇楚師不敢戰即撤還,次年江國被滅。就此何休認為:“救人之道,當指其所之,實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為其勢必當引圍江兵當還自救也。故云爾。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何休認為,晉國說是救江實質上卻沒有救江,這是一種欺詐,于是他借孔子之言提出了“信”的重要性。
何休將宋襄公樹立為君主守信的典范。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水之戰,宋襄公堅持等楚軍列陣完畢之后再發動攻擊,結果大敗。何休稱贊宋襄公“得正道尤美”,“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認為這是“王德”的表現,并感傷宋襄公“有王德而無王佐也”[3](僖公二十二年),“守正履信,屬為楚所敗”[3](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與楚成王盟會,宋公守信而來,楚王卻執宋公以伐宋,何休以宋公“守信見執”而直斥楚王“無恥”。
對諸侯的背信失信,何休也都給予了貶斥。成公三年“及孫良夫盟”,何休說:“《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3](成公三年)指出諸侯之間屢屢盟會,恰恰反映了當時諸侯屢屢失信,互相之間不信任的現實。成公六年“取專阝”,專阝乃邾婁之邑,而上年十二月魯剛與邾婁有蟲牢之盟,何休譴責魯成公“背信亟也,屬相與為蟲牢之盟,旋取其邑”[3](成公六年)。襄公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魚專出奔晉”。衛獻公讓公子魚專與甯喜締約,甯喜迎獻公回國,獻公復位后卻殺了甯喜,何休一再譴責“獻公無信”、“衛侯衎不信”[3](襄公二十七年)。
此外,君主還應有納諫和自省之德。
何休要求君主要善于納諫,他批評宋襄公“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3](僖公十六年),惋惜魯昭公不從子家駒所諫“當先去以自正”之言,“卒為季氏所逐”[3](定公二年)。君主還應當保持自省,經常自我檢視“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3](桓公五年)還要善于悔過。何休夸贊秦繆公說:“秦繆公自傷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變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國,善而與之,使有大夫。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謂也。”[3](文公十二年)又夸贊魯僖公說:“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眾,比致三年,即能退辟正殿,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余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善其應變改政。”[3](僖公三年)
在何休那里,國家的盛衰安危首先就維系在君德上。僖公元年“邢遷于陳儀”,何休認為:“時邢創畏狄兵,更欲依險阻。……王者封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貢賦者均,在德不在險。”德比險阻更可憑恃,這里更有一種“德者天下無敵”的意味。他提醒君主在日常生活中“當修文德”[3](僖公二十八年),注重自身道德修養,崇禮樂、養仁義。他說:“禮樂接于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觀其色而民不敢爭,故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須臾離也。君子須臾離禮,則暴慢襲之;須臾離樂,則奸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曾離于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離于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辟也。”[3](隱公五年)
二 為政之道
穩定有序的政治秩序,何休認為這是為政的首要問題。他說:“統者始也,總系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3](隱公元年)天下一統于王,王擁有統理一切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又說:“一國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3](隱公元年)王者上承天命而統領天下,諸侯上承王命而統領一國,“王者以天下為家”[3](隱公元年),諸侯“以一國為家”[3](定公十二年),諸侯尊王,大夫尊君,上下各安其位,各守其禮,這也就是何休所提的“大一統”的政治秩序。
東漢末年皇權旁落,外戚、宦官兩大集團血雨腥風爭權不止,政治昏亂,社會動蕩,民變四起,統一的國家面臨著分崩離析,這也是何休汲汲于“大一統”的現實原因。他強調“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3](隱公元年),主張強化君主集權。
襄公十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梁之盟,雖然各國諸侯都與會,但主盟者實質上卻是各國的大夫。何休評論說:“諸侯委任大夫交會強夷,臣日以強,……君若贅旒然。”[3](襄公十四年)又說:“諸侯勞倦,莫肯復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權,大夫故得信任,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3](襄公十六年)當時君權旁落,各國大夫專政,國君就好像掛在旌旗上的飾物一樣,徒有其表,就此何休強調君權絕對不能由他人代行。
何休借《春秋》史事對外戚和宦官的專權也多有指斥。文公八年“宋司城來奔”,何休說:“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3](文公八年)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休說:“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強,威權下流,政分三門,卒生篡弒,親親出奔。”[3](僖公二十五年)妃黨也就是外戚,何休將宋國的一系列禍亂都歸于外戚爭權所生。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馀祭”,何休說:“以刑人為閽,非其人。……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為所殺,故以為戒。”[3](襄公二十九年)指出以刑余之人充當閽寺,近君左右的危險性。
何休要求強化君主集權,但他強調君主不要事必躬親,以為“天下之君,海內之主,當秉綱撮要”[3](桓公五年),要君主注意掌控全局,把持關鍵,避免舍本逐末。在何休那里,君主所要專注的主要就是“德治”。強調君德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落實到社會政治上。
他明確提出了“貴教化而賤刑罰”[3](定公元年)的德治主張,認為統治者如果不注重德治,而試圖一味依靠刑罰治理天下,那就會刑愈繁而世愈亂,法愈多而治愈惡。他說:“古者,肉刑:墨、劓、擯、宮,與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應世黠巧奸偽多。’”[3](襄公二十九年)三皇、五帝根本不用刑罰而天下太平,后世刑罰繁多卻仍是“黠巧奸偽多”,孰優孰劣,一目了然。何休譴責魯隱公“設苛令急法以禁民”[3](隱公五年),將僖公十九年梁“魚爛而亡”說成是“隆刑峻法”的后果。他說:“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當絕者。”君主治國當以道德感召百姓,嚴刑峻法只能使民心背離,使國家陷于危機,這與孔子所說的“子為政,焉用殺”[4](顏淵)的“德治”主張是相當一致的。
以德治國,首在“重愛民命”[3](僖公四年)。何休把民眾看成是國家興亡的根本力量和治國的關鍵所在,提出了“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士民為肌膚”[3](僖公七年)的思想,表明了“惡國家不重民命”[3](僖公二十五年)的態度。他譴責君主“無惻痛于民之心”[3](桓公十四年)、“視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3](僖公二十六年),認為君主有“懷保其民”[3](桓公十一年)和使“百姓安土樂業”[3](桓公三年)的政治責任,民心向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興衰存亡,一旦“民人將去,國喪無日”[3](桓公三年)。因此君主應當多為百姓著想,要“憂民之急”[3](桓公五年),不要一味只顧自己享樂。莊公三十一年“筑臺于郎”,何休說:“登高遠望,人情所樂,動而無益于民者,雖樂不為也。”他告誡君主不要“奢泰妨民”[3](成公十八年)和“動擾不恤民”[3](襄公八年)、“費重不恤民”[3](定公七年)。
何休提出了“民食最重”[3](莊公七年)的政策主張,以民食為國家安定的根本要素。他指出:“民以食為本也。夫饑寒并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3](宣公十五年)又說:“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3](宣公十年)民以食為天,民食出了問題,國家必亂。他呼吁君主“當奉順四時之正”[3](隱公六年),不奪農時;同時注意分別土地,教民因地制宜地耕稼,所謂“地勢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麥,當教民所宜,因以制貢賦”[3](昭公元年),保證和促進農業生產。在保證農業生產的同時,還要關注糧食儲備和荒政。他說:“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3](宣公十五年)國家有充足的糧食儲備,有能力抵御災害,同時統治者再“當自省減,開倉庫,贍振之” [3](宣公十年),這樣“雖遇兇災,民不饑乏”[3](莊公二十八年),民眾仍然可以安居樂業;而如果沒有儲備,像魯莊公那樣“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國家則必然“危亡切近”[3](莊公二十八年)。
何休還要求君主“薄賦斂”,減輕人民負擔,主張“稅民公田,不過什一”[3](哀公十二年)。他譏刺魯宣公“初稅畝”超出什一是“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3](宣公十五年),批評魯哀公“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他說:“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3](哀公十二年)可見,說的是魯國的事情,矛頭卻直指東漢之世。他引《論語》“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3](宣公十年)之言,提醒君主,減輕對人民的賦稅搜刮,只有百姓富足了,君主之用才能有保證。對正常的賦稅,何休還是予以肯定的,他認為“賦斂不足,國家遂虛”[3](宣公十三年),是“社稷宗廟百官制度之費”[3](宣公十五年)所必需的。
此外,君主還要關心民眾疾苦,傾聽下層意見,懂得“芻蕘之言不可廢”[3](成公二年)。何休主張君主為了解民情,應該親自巡守:“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雖平,自不親見,猶恐遠方獨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絀陟,五年親自巡守。”[3](隱公八年)他甚至還為君主設計了一個體察民情的機制:“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3](宣公十五年)
桓靈之時,“天下饑謹,帑藏虛盡”[1](馮緄傳),國庫空虛,連年災荒,國家無力賑濟,餓殍遍地,而統治者不顧百姓死活,依舊揮霍無度,竭澤而漁地搜刮百姓,“百姓莫不空單”,又“告冤無所”,紛紛“聚為盜賊”[1](賈琮傳),一場全國性的農民起義已經暗流涌動。何休這一系列建議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德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尊賢、用賢,無德小人當道政治也不會穩定。何休強烈主張“達賢者之心”[3](襄公七年)、“通賢者之心,不使壅塞”[3](僖公二十八年)和“深抑小人”[3](桓公二年)。他提出,君主應當禮敬賢者,為人才提供寬松的環境,這樣才能吸引各種賢才,使天下誠心歸附。他說:“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3](宣公元年)又說:“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為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3](宣公十七年)
東漢末年,“正直廢放,邪枉熾結”[2](黨錮列傳),包括何休本人在內的正直賢臣紛紛遭到禁錮,不得進用,而佞幸小人卻竊踞高位,朋比為奸擅權禍國。對此何休有著切膚之痛,他說:“春秋時,廢選舉之務,置不肖于位,輒退絕之,以生過失。至于君臣忿爭出奔,國家之所以昏亂,社稷之所以危亡。”[3](隱公元年)何休極言不選賢舉能、“置不肖于位”的危害,強調這是導致國家昏亂、社稷危亡的禍根。
何休大力宣揚選舉制,提倡“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3](隱公三年)和“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3](宣公十五年)。他還提出:“諸侯三年一貢士于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兩人,小國舉一人。”[3](莊公元年)
對于那種父子相承官職的世卿現象,何休非常痛恨,認為這造成了“賢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親榮”[3](桓公二年)的惡性局面。他對世卿現象進行了激烈的抨擊:“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為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3](隱公三年)認為世卿必然導致君權衰落,最終引發臣子擅立君上乃至篡弒君上之禍。他還彰顯世卿的危害說:“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強莫大于齊國,世卿尤能危之。”[3](宣公十年)
何休指出,世卿之所以能在春秋之時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主要就在于當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3](文公元年)。我們注意到,何休提出的王者治理天下的五大原則:貴有德、貴臣、貴老、敬長、慈幼,實際上原本為曾子之說,其原始面貌為“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6](孝行)。何休把曾子原先所說的“貴貴”轉換成了“貴臣”,抽離了其中愛敬貴戚的內容,由此也突顯出何休對血緣貴族政治的警惕。
三 君臣關系
何休認為孔子作《春秋》是要“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3](隱公元年),就是要通過處理好各種人倫問題,使社會回歸秩序。君臣關系是君主政治結構的核心,又居于“五倫”之首位,這注定君臣之大倫是維護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的問題。因此何休對“別君臣之義”[3](莊公二十九年)尤為加意,提出“君臣之義正,則天下定矣”[3](莊公二十九年),“君臣和則天下治”[3](隱公二年),認為君臣關系關乎國家的盛衰、社會的穩定,渴望一種良性、和諧的君臣關系。
別君臣首先就是“別尊卑,理嫌疑”[3](閔公二年),明確君臣的上下分際,確立君尊臣卑的政治倫理。東漢末年臣強君弱,皇帝受制于權臣,甚至有弒君之禍,漢質帝即為梁冀毒殺。感于時局,何休對“君道微,臣道強”[3](宣公十七年)極為警惕,疾呼“國君當強”[3](莊公十年)和“抑臣道”[3](襄公三十年),有針對性地提出“臣順君命”[3](宣公元年),“君不可見挈于臣”[3](僖公二十五年),“臣不得壅塞君命”[3](僖公二十八年),甚至“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3](宣公六年),主張為人臣者應該盡忠君主,不得心懷異志。他表彰荀息“一受君命,終身死之”[3](僖公十年);稱贊公孫歸父在宣公死后,“不以家見逐怨懟”,還盡臣子哭君之禮,“終臣子之道”[3](宣公十八年);稱贊蔡季在蔡侯封人死后,“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對蔡侯封人曾欲疾害自己“卒無怨心” [3](桓公十七年)。
何休繼承《公羊傳》“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仇,非子也”[3](公羊傳·隱公十一年)的主張,以復君父之仇為臣子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隱公四年“衛州吁弒其君完”,而后“衛人殺州吁于濮”,何休說:“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隱公十一年“公薨”,何休說:“臣子不討賊當絕,以君喪無所系也。”宣公五年“孫叔得臣卒”,何休說:“知公子遂欲弒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非但弒君,作為臣子知道有弒君的事情要發生而不揭發檢舉的,即與弒君同罪。
何休之時,“三綱”之義已確立兩百多年,且東漢末年皇帝時見挈于外戚、宦官,何休宣揚“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之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也是他“大一統”政治模式的要求。但何休并沒有像董仲舒那樣認為“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于君,惡皆歸于臣” [7](陽尊陰卑),完全取消臣子的獨立人格,他還是主張君臣之間能建立起一種較為平等的關系。從這個方面來講,何休的倫理思想更接近于原始儒家。如他提出君主要“貴臣”、“尊賢”,強調“臣拜然后君答拜”、“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幾”[3](宣公六年)以及“臣于君而不名者有五”[3](桓公四年)等先秦君臣古禮,都是要求君主對臣子尊重和禮敬的一種體現。他提出“君臣相與言不可負”[3](僖公十年),也或多或少地把君臣關系擺在相對平等的位置上。
何休明確地主張,臣子對待君主的態度以君主對待臣子的態度為前提,以為“君敬臣則臣自重,君愛臣則臣自盡”[3](隱公元年)。這明顯保留了孟子的“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8](離婁下)的君臣觀念,只是沒有孟子那般激烈。
何休還非常可貴地提到了君臣之間的“朋友之道”。《公羊傳》在講伍子胥復仇時有“復仇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之文,本來講的是先秦時期人們復仇的一條規則,即復仇的對象只能限于仇人本身,而且復仇的主體也只能是被害者的兒子,朋友可以幫忙但卻不能搶在孝子的前面。而何休卻由此做了發揮:“時子胥因仕于吳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闔盧本以朋友之道為子胥復仇。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3](定公四年)伍子胥為臣,闔盧為君,闔盧為伍子胥出兵楚國居然是為了幫朋友復仇。也就是說,君臣之間是可以像朋友一樣相處的。何休還引述孔子的朋友交往之道做注腳,更烘托了闔盧與伍子胥君臣之間的朋友關系。將君臣與朋友相提并論,這即使在先秦也是相當罕見的,唯有埋藏地下兩千多年的郭店楚簡中有“君臣,朋友其擇者”、“友,君臣之道也”[9](語叢一)這樣的說法。這無疑是何休君主論中的一大閃光點。
何休更堅持了孔子“以道事君”的觀念,以道義來統攝君臣之間的關系,提出“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也就是臣子事君是為了實踐儒家的道義,是以君講道義為前提的,如果君不講道義,那臣就可以選擇結束彼此之間的君臣關系,棄君而去。莊公二十四年曹羈“三諫不從,遂去之”[3](莊公二十四年》,何休說:“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之謂也。諫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從得去者,仕為行道,道不行,義不可素餐,所以申賢者之志,孤惡君也。”[3](莊公二十四年)認為對待惡君,臣子三次進諫就盡到了臣子的責任,然后可以“諫不從而去之”[3](定公八年)。
宣公十七年“公弟叔肸卒”,何休說:“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對于無道之君,可以選擇保持距離,不合作,隱居不仕。
何休進而提出,對于無道之君,臣民甚至可以奮起反抗,肯定了人民誅除“失眾”的無道之君的正義性和合理性。如他評論魯桓公的所作所為時說:“若桓公之行,諸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3](桓公三年),所謂“百姓所當叛”,就是承認臣民有革命的權力。何休評論晉靈公之死是“靈公無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3](宣公六年),評論莒紀公之死是“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也”[3](文公十八年),評論薛伯比之死是“失眾見弒,危社稷宗廟”[3](定公十二年),評論莒犁比公密州之死是“密州為君惡,民所賤,故稱國以弒之”[3](襄公三十一年)。“無道”、“為君惡”、“危社稷宗廟”、“民眾不悅”、“民所賤”的君主必定“失眾”,喪失民心支持,也就失去了統治的合法性,這樣的君主被弒,結果是“國中人人盡喜”。可見,何休把無道之君排除在了臣子盡忠的范圍之外。對于禍國殃民的無道之君,何休認為人人得而誅之,這與孟子的“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 [8](梁惠王下)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
此外,在“國重君輕”[3](桓公十一年)思想的指導下,何休主張臣子對國家的責任要高于對君主的責任。桓公十一年,鄭國權臣祭仲受宋國脅迫,擁立厲公突,逼走昭公忽。何休贊賞祭仲“雖病逐君之罪”,但“保有鄭國,猶愈于國亡”,是“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為賢也”,存國之功大于逐君之罪。何休還將祭仲逐昭公比作伊尹放太甲,他說:“湯孫大甲驕蹇亂德,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負,后有安天下之功,猶祭仲逐君存鄭之權是也。”可見,在何休的考量中,國家利益、天下的安定,遠在君位和君主個人的安危榮辱之上。
毋庸置疑,作為公羊學大師的何休,其君臣觀念很多是承襲自《公羊傳》的。《公羊傳》的君臣觀念大體上反映的還是先秦儒家的觀念。[10]而隨著君主專制的逐漸強化,到了何休那里,顯然已經無法完全秉持《公羊傳》的君臣觀念了。我們知道,《公羊傳》有一個很特異的主張就是臣可向君復仇,明確對伍子胥向楚王報殺父之仇表示贊同,表示“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3](公羊傳·定公四年)。而何休在這個問題上明顯與《公羊傳》產生了距離,何休在解釋《公羊傳》這句話時說:“諸侯之君與王者異,于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3](定公四年)把臣可對君復仇限定為了諸侯君臣間的特例。由此我們也看出,何休所說的臣子于義可去的對象實際上是不包括天子在內的。與天子的君臣關系既然是不可解除的,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想見,在何休那里,臣民革命的對象實際上也是不包括天子在內的,而只是限于諸侯之君。
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紂就是天子;《公羊傳》講“子復仇可也”,也是沒有區分天子、諸侯。何休自己也曾說:“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于王者。”[3](隱公元年)但他在君臣關系問題上卻編織了一道防護網,將作為天子的君主與作為諸侯的君主做了區隔。這是何休在歷史條件已經改變的情況下,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精心設計。藉由這道防護網,何休可以不用顧慮太多政治束縛,繼續闡述先秦儒家的那種君臣觀念,又不會對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產生沖擊,為理想在現實之中找到棲身之所。
四 君位傳承
君位傳承是君主政治的一項重要內容,直接關系到政局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定。很多王朝到了末年,都會在君位傳承方面出現問題,引發政局動蕩,惡化本已經弊亂叢生的政治環境。東漢末年亦是如此,質帝、桓帝、靈帝皆為外戚所擅立,以支庶而登帝位,從而母后稱制、權奸秉政伴隨東漢王朝走向衰亡。
何休目睹東漢末年的這一亂局,非常渴望能建立起一套運行良好的君位傳承制度。首先,他認為最理想的君位傳承應該是堅持嫡長繼承制。在解釋《公羊傳》“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時,他說:
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侄娣;嫡侄娣無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無子,立左媵侄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愛爭。[3](隱公元年)
何休詳細敘述了君位繼承人的順位,最為關鍵的是他深刻地指出了這套制度背后的意義所在——“皆所以防愛爭”,就是為了防止君位繼承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紛爭,消弭可能引發的政治動亂,使權力能夠順利傳承,維護統治秩序。正如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所指出的:“所謂‘立子以貴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者,乃傳子法之精髓。……蓋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爭。任天者定,任人者爭。定之以天,爭乃不生。……所以求定而息爭也。”王國維還指出何休敘述的這套制度過于詳密,“顧皆后儒立類之說,當立法之初,未必窮其變至此”。[11] 也就是說,何休所說的很可能并非真是古禮,他這種幾乎窮盡各種可能的繼承人身份的敘述,更突顯了他對一套嚴密的傳承制度的渴望。越嚴密的制度,可以越明確地把繼承人限制在一個人的身上。
他還在解釋“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侄娣從”[3](公羊傳·莊公十九年)的制度的時候說:“必以侄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繼嗣也。”[3](莊公十九年)認為這也是從維護繼嗣穩定的角度所做的安排。
當然,最好狀況是“國有正嗣”[3](桓公六年),即存在嫡長子。這樣依據“立嫡以長”[3](昭公二十年),可以非常明確大位所屬,一步就解決傳承過程。桓公六年,“子同生”,何休說:“本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于無正,故喜有正。……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寢門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當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負朝于廟,以名徧告之。”魯惠公沒有嫡子,這埋下了后來桓公弒隱公的禍根,因此桓公的嫡長子公子同(莊公)的誕生,使魯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避免了因君位傳承引發的動蕩。何休強調這對魯國來說是非常大的喜事,也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其次,君主應該在生前盡早確立儲嗣,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因名分不定產生的紛爭。文公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何休認為:“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指出商人弒舍篡位,就是因為齊昭公潘在立嗣問題上猶疑不決,未能在生前確立儲嗣。
尤其很多時候潛在的繼承人之間尊卑貴賤的身份差異很小,先后次序并不好確定,則會更容易引起紛爭。文公十三年,邾婁文公薨,其二子玃且、接菑爭位。何休指出,玃且、接菑“俱不得天之正性”,皆非嫡子,而“二子母尊同體敵”,難分貴賤。最后雖然以“以年長故”[3](文公十四年)玃且獲立,但邾婁還是經歷了一場動蕩,晉國甚至出兵逼邾婁納接菑,國家一度陷于危機之中。
魯隱公和魯桓公兄弟之間也屬于這種“尊卑也微”[3](公羊傳·隱公元年)的情況,他們的母親只是左、右媵的區別,尊卑并不明顯。按制度是桓公應繼位,但他們的父親魯惠公死的時候,桓公尚年幼,于是諸大夫“廢桓立隱”,終致十幾年后桓公弒隱公之禍。何休指出,真正的禍根即在于“惠公不早分別也”,是惠公沒有在生前確立嗣君。他提出:“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3](隱公元年)在沒有當然的嫡長子的情況下,君主必須在年滿六十歲或臨終之時指定好嗣君。
君主如果生前未能指定嗣君,除了潛在的繼承人爭位的危險,往往還會使君位廢立之權淪于臣子之手,進而造成君權旁落等一系列更大的政治禍亂,而這也是何休更為警惕的。他評論衛襄公說:“世子輒有惡疾,不早廢之,臨死乃命臣下廢之。自下廢上,鮮不為亂。”[3](昭公七年)“自下廢上,鮮不為亂”,這是何休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同時也是對現實政治的憂憤感慨。
我們從何休對隱公四年“衛人立晉”的態度更可以發現他對“自下廢上”的防范。何休說:“晉得眾,國中人人欲立之。凡立君為眾,眾皆欲立之,嫌得立無惡,故使稱人,見眾。言立也,明下無廢上之義,聽眾立之,為立篡也。”[3](隱公四年)州吁被誅后,衛人迎立公子晉。何休認為,雖然公子晉有民意,被立為君沒有什么過惡,但臣子立君從根本上講是不能允許的,即便是人心所向,也跟篡位一樣是沒有合法性的。
最后,君主立嗣一定要遵循正當、正道。君主早定儲嗣,固然可以減少紛爭,但如果不堅持“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的原則,一樣會招來禍患。何休指出:“廢正當有后患。” [3](僖公十年)君主如果背離嫡長子繼承制的正道,一定會后患無窮。僖公五年,晉獻公為立驪姬之子,殺世子申生,庶子重耳、夷吾逃亡。獻公死后,晉國大亂,驪姬之子奚齊、卓子雖先后得立,但先后被弒,于是惠公夷吾立,惠公死后文公重耳又返國與侄子懷公圉爭位。晉國禍亂一直延續到十幾年后,晉獻公殺嫡立庶真可謂后患無窮。
宋國之亂也是一個典型的事例。宋宣公以其弟繆公賢能,于是不傳子而傳弟。繆公又感念兄恩,也不傳子而傳給了宣公之子與夷,最終繆公的兒子莊公馮弒殤公與夷。何休評論說:“言死而讓,開爭原也”,“死乃反國,非至賢之君不能不爭也”。他認為,繆公雖賢,但宣公破壞了傳承制度,不傳子而傳弟,相當于開啟了一個紛爭的開關,繆公又遞相沿襲,以至釀成了宋國的禍亂。被剝奪了繼承權的嗣子,除非是圣賢,很難不會去奪回本屬于自己的位置,這樣禍亂也就終難避免。據此何休極力強調:“修法守正,最計之要者。”[3](隱公三年)這也就是《公羊傳》“大居正”之說,即尊尚守正,強調正當、正道的重要性。
五 結 語
維護政治穩定和社會秩序,總結治亂盛衰之由,一直是歷代公羊學家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何休生當末世,天下板蕩,因此他對社會安定用意尤深。而在君主專制社會中,君主是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君主的德行、施政方略、君臣關系以及君位傳承等與君主相關的問題,都會對國家能否實現長治久安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在《公羊解詁》中,何休借助經典資源,總結《春秋》史事的歷史經驗教訓,闡發了一套具有公羊學特色的君主論思想。他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養,以道德感召和安定天下,尤其注重君主在孝、廉、信等方面表率天下的德行。他呼喚“大一統”的政治秩序,警惕君權旁落和權臣專政的風險,提倡德政,反對暴政,強調重民恤民和選賢舉能。他渴望君臣之間能建立一種良性和諧的關系,在明確君臣上下分際的前提下,主張“以道事君”,強調君臣之間互相的責任與義務,甚至提出君臣之間存在“朋友之道”。他堅持以嫡長繼承制為君位傳承的正道,主張早定名分消弭紛爭,反對“自下廢上”。他的君主論思想飽含了深沉的歷史責任感和強烈的現實關懷。
[參 考 文 獻]
[1] 范曄. 后漢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65.
[2] 鄭任釗. 論《春秋公羊傳》對社會秩序的追求[J]. 炎黃文化研究,2013,(15):110-125.
[3] 何休解詁 徐彥疏. 春秋公羊傳注疏[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4] 何晏集解.邢昺疏. 論語注疏[M]. 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 1980.
[5] 唐玄宗注 邢昺疏. 孝經注疏[M]. 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 1980.
[6] 張雙棣等. 呂氏春秋譯注[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8] 趙岐注 孫奭疏. 孟子注疏[M]. 十三經注疏. 北京:中華書局, 1980.
[9] 荊門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墓竹簡[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0]鄭任釗.《春秋公羊傳》的君臣觀念[J]. 前沿,2010,(22):24-27.
[11]王國維. 殷周制度論[A]. 觀堂集林[C].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