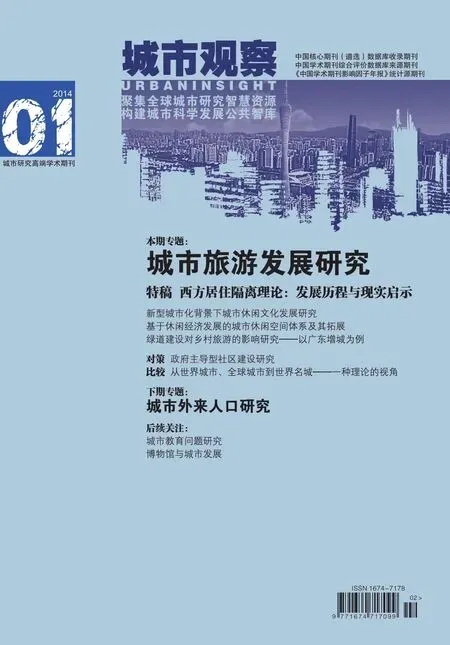城市旅游開發和旅游城市建設的思考
◎ 張凌云
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說過,“人們為了活著而聚集到城市,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在城市”;無獨有偶,2010年中國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題就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由此可以發現,古希臘先哲與我們現代人的思想竟如此契合,或許是人類對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亙古未變、一脈相承的。從古代城邦、封建皇城到近代工業城市,城市是一個區域的行政中心、貿易中心、生產中心、經濟中心、消費中心和財富中心。但工業化和全球化也使“城市病”蔓延。十九世紀末英國人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在其名著《明日的田園城市》中提出的“社會城市”是一個宜居有足夠鄉村田野所包圍的城鎮體系,但現代城市離霍華德的理想漸行漸遠,城市成了追逐財富和炫富的名利場。
一、城市旅游的起源
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對于“旅游”的定義是,人們為了消遣、商業和其他目的離開“慣常環境”(usual environment),連續逗留不超過一年的活動。換句話說,旅游環境就是旅游者的“非慣常環境”(unusual environment),但同時也是旅游地居民的“慣常環境”。旅游環境類似于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66)所說的“他者空間”(Des espacesautres),為此,福柯創造了一個新詞“異托邦”(Heterotopia),顯然,“異托邦”這一名詞是從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516)“烏托邦”(Utopia)的概念轉化而來。烏托邦是“不在場”的空想,而異托邦則是現實存在的,是一種不同于自我文化的“他者空間”,具有想象和真實的雙重空間。旅游環境就是這個真實空間的一種存在方式。人們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對于其他城市或域外城市充滿著想象和向往,期望能增加和體驗與在慣常環境下的慣常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閱歷和經歷。但由于城市功能的日趨多元,城市旅游也變得更加綜合、更加多樣。正如張欽楠在他的《閱讀城市》一書中寫道:“城市是人類所創造的最美妙、最高級、最復雜,而又最深刻的產物”。
早期的城市旅游(urban tourism)可以追溯到17至18世紀歐洲的“大旅行”(Grand Tour),英國和歐陸國家的貴族和有錢人家的子弟在其踏入社會前,往往要做一次以開闊眼界、增長知識為目的的旅行,目的地一般都是當時的文化中心——城市,如法國的巴黎、意大利的熱亞那、米蘭、佛羅倫薩、羅馬和威尼斯等。但對于城市旅游進行系統研究則要晚得多。一般認為,最早對于城市旅游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斯坦斯菲爾德(Stansfield,1964),他在《美國旅游研究中的城鄉不平衡》中提出了對于城市旅游研究的命題。上世紀70年代,霍爾(Hall,1970)曾經預言:20世紀的最后30年,對于歐洲主要的首都城市和眾多的歷史小城鎮而言,最大的轉變是大旅游時代的來臨。據布蘭克和彼特科維奇(Blank &Petkovich,1987)的研究,旅游者選擇城市作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原因是:
(1)城市人口密集,使到城市探親訪友的密度也大;
(2)城市往往是旅游交通中轉、樞紐或終點站;
(3)商業、金融、工業、生產服務的功能都集中于城市,產生了會議、展覽和商務旅游;
(4)城市提供了大量的文化、藝術和娛樂方面的體驗。
總之,城市對外交通和工商業發達程度對于城市旅游起著重要作用,一些國際性旅游大都市往往是交通樞紐或區域中心城市。
二、城市空間系統、功能和文化演進
城市是非農業人口的集聚地,是人類社會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早期西方的城市空間概念比較簡單,可以約略概括為屬于統治者的“紀念性空間”和屬于廣大居民的“生活性空間”。拉波波特和意大利的阿爾多·羅西都持這樣的二元分法。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國際現代建筑協會發表《雅典憲章》提出了關于“功能城市”的概念,首次將城市分為居住、工作、休閑游覽和交通四大功能空間:居住空間、工作空間、游憩空間、交通空間。當代學者將城市的四大空間進一步細化為如下十種類型:
(1)城市道路空間;
(2)廣場空間;
(3)帶形、環形、半環形的游憩空間;
(4)生活小區空間;
(5)文體科技展覽中心的活動空間;
(6)商業娛樂空間;
(7)園林名勝空間;
(8)標志性建筑物及其周圍的空間;
(9)生產運輸集散等工業交通空間;
(10)鳥瞰城區的綜合視野空間。
依據功能原則劃分并安排城市空間是現代城市規劃的基本原理,然而幾十年的實踐表明,絕對化的功能分類容易割裂城市的有機聯系。
1977年的《馬丘比丘憲章》對城市空間的簡單分化傾向做出了修正:“不應當把城市當作一系列孤立的組成部分拼在一起,而必須努力創造一個綜合的、多功能的環境。”正像這次會議指出的那樣,“馬丘比丘代表的都是理性派所沒有包括的、單憑邏輯所不能分類的一切”,肯定了城市及其空間使用的混沌性,這就牽涉到城市空間功能復合化的問題。
《雅典憲章》的城市空間分類原則和《馬丘比丘憲章》的城市空間功能復合要求共同指明了未來的趨向:城市空間功能分化與復合的結合。
由于受自然條件、歷史文化和居民習俗等因素的影響,每個城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個性”,也就是自有的文化特征,其最為直觀的、可識別的外在表現就是由城市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筑風格以及建筑作為重大歷史事件的見證物所形成的可觸摸的“肌理”和“文脈”,尤其是文化旅游城市,建筑成為城市景觀的主要元素,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偉大的城市規劃師和建筑師就是一個城市旅游資源的創造者。如路西奧·科斯塔和奧斯卡·尼邁亞之于巴西的巴西利亞,安東尼奧·高迪之于西班牙的巴塞羅那,查爾斯·倫尼爾·麥金托什之于英國的格拉斯哥,奧托·瓦格納之于奧地利的維也納,多納托·布拉曼特和簡羅倫佐·貝尼尼之于意大利的羅馬等等。西方的城市建筑一般包括教堂、博物館、名人故居、文化遺址、影劇院、體育場館、廣場、噴水池、街心花園、城市園林、橋梁、碼頭、特色飯店、地標性建筑物、商業街區以及一些紀念性建筑。
城市空間還是一個文化有機體(沙里寧曾在1942年寫的《城市,它的生長、衰退和將來》一書中提出過有機疏散論),是一個有歷史記憶,有自己獨特文化基因的有機體。而城市的文化基因是隱藏在一個個城市細胞和元素中的,這些細胞組成了一個個“城市空間”,我們可以通過對這些小空間的考察看到城市間的區別,并進而反映出文化的差異。例如,在老北京,這種細胞就是四合院,它原來是以一家一戶為單元的,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封閉性。老上海的石庫門,組成了弄堂,是半封閉的。美國洛杉磯等城市成片的帶小綠地的獨戶住宅又可算是開放型的。巴黎的小空間,是以社區為單元的,并且通過不同的空間形態顯示了多樣的意境,而具有突出的魅力。離開了這些“細胞”,城市就沒有生氣和特色,就喪失了其個性特征的身份符號。也正是因為這些身份符號,才構成了不同城市之間的文化差異。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看,這些基因通過編碼(約定俗成的歷史的概念)隱含在“敘事”的深層結構中,并產生一種獨特的“語境”,也就是一種歷時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制度。
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書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看來,科技進步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平,城市變得越來越千篇一律。但從文化地方性看,世界并不是平的,每個城市都有著她獨特的個性和色彩,吸引著不同的人群。
三、旅游城市的空間系統和功能特征
城市是近代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區域性文化中心,現代城市和歷史城鎮成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是文化旅游的主要載體和現代旅游的綜合載體。其中城市建筑構成旅游景觀的主體,有些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景區,歐洲的歷史文化城市大多是旅游城市。
與中世紀的城堡和城邦不同,今天的城市已經是一個開放的、多元和包容的共享空間,既是當地居民生活起居的家園,也是外來游客尋求體驗的樂園,城市是這兩種環境的有機組成和空間疊加。事實上,目前許多國際化大都市接待的旅游者規模遠遠大于本市居民人口,尤其是一些著名國際旅游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本地居民僅30萬人左右,而全市接待的過夜旅游者超過本地居民人口的10倍以上。這就是說,城市建設已經不只是解決本地居民的工作、學習、生活和休閑的需要,還要考慮到外來游客的旅游需要。一般而言,一座旅游城市除了特有的歷史文化、博物館、紀念地、名人故居等單體吸引物外,旅游城市在空間系統和功能上具有下列顯著特征:
(一)城市標志性景觀
一般來說,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標性建筑景觀,教堂是歐洲城市建筑的主要景觀內容,從羅馬、拜占庭、哥特、文藝復興、巴洛克到新古典主義、新建筑和后現代等各式教堂密布于歐洲各大城市,其中中世紀的哥特式教堂以其空間的宏偉高大和光怪陸離的玫瑰窗而引人注目。如法國的巴黎圣母院、德國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米蘭大教堂、英國的索爾茲伯里大教堂等都是著名的旅游景區。
這些地標性建筑不僅外形具有較強的觀賞性,而且具有登高遠眺俯瞰城市全貌的功能。為了滿足游客登高遠眺的需要,一些高層和超高層現代建筑往往也增加了觀光功能,尤其是電視發射塔都將其建成觀光塔。19世紀末期由于建筑材料和工程技術的發展,個別西方國家開始嘗試建造超高層(高于300米)建筑,但真正大規模建造還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上世紀90年代后,亞洲國家和地區一些大城市的超高層建筑如雨后春筍般的拔地而起,紛紛加入到爭奪世界最高建筑物桂冠的城市行列。電視塔本身也成為城市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個城市的地標,對城市景觀起著重要的裝飾作用而成為觀光塔,它一般是由混凝土或鋼鐵建造,在較高位置設有觀景臺,供游客登上俯瞰城市全景和城市天際線。
許多國際旅游城市借市內的河流、湖泊、濕地和海灣等水體開發成城市觀光帶,這些城市的水體及其沿岸和水上離島一般都是風景優美,建筑較為密集,可以讓游客在游船上游覽沿岸建筑和城市景觀,也往往成為一座城市的標志性景觀。
(二)城市休閑與旅游綜合體
城市是居民和外來游客的共享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不同的人群能夠各得其所。這些人群集聚的場所在空間上看是一種商業、文化和休閑消費的多要素綜合體。斯坦斯菲爾德和里克特(Stansfield & Rickert,1970)借用了城市地理學中的中心商務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的概念提出了游憩商務區(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RBD),而伯滕肖等(Burtenshaw et al.,1991)在對歐洲城市旅游業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心旅游區”(Central Tourism District,CTD)概念,指出“中心旅游區”是城市旅游的集中區域。蓋茨(Gatz,1993)則做了旅游商業區(Tourism Business District,TBD)與中心商務區(CBD)之間的關系比較研究,認為兩者可能是相鄰的,甚至是重疊的。詹森-弗比克(Jansen-Verbeke,1991)對于在游憩商務區(RBD)中,商業與旅游業之間如何協調發展問題做過專門的研究,她認為,零售業與旅游業是難以區分開的,零售業發達、種類、檔次齊全,可以成為旅游城市的一個重要吸引力。
城市休閑與旅游綜合體一般以街區形式呈現如商業街區(如shopping mall、步行街)、歷史文化街區(如傳統民居社區)、休閑街區(如酒吧街)等。這些街區布局可分為敞開式(完全露天的)、遮蓋式(采用拱廊等形式連接街道兩側建筑,形成不受自然氣候條件影響的步行空間)和半遮式(街道兩側建筑采用柱廊、聯拱廊等形式連成一體,形成室內外空間的過渡空間,它兼具開敞式和遮蓋式商業街的優點)。此外,公共廣場往往也是一個城市的休閑和旅游中心區,這些廣場或莊嚴雄偉,或親切溫馨,有些廣場設有供游人休憩的座椅,栽有鮮花和綠色植物,有紀念碑(柱)、雕塑、噴泉、各色建筑以及購物商店等。
(三)旅游城市設施和服務
在許多國際旅游城市中,市容觀光(city tour)往往是游客的必游項目,散客可以搭乘專為觀光客準備的觀光游覽車,這些觀光游覽車車身顏色艷麗醒目,一般都采用雙層敞篷巴士,行車線路和停靠站點主要是市內主要旅游景區,游客憑當日車票,可多次上下車,車上一般設有人員導游(雙語種)或電子導游(多語種)。此外,旅游咨詢中心(information center)也專為外來游客提供設施和服務。旅游咨詢中心通常設在游客聚集的地方如機場、火車站、碼頭、城市入口、商業街區、大型旅游景區等,并且使用統一的標識“i”(英文信息information的第一個字母)。主要提供該城市的飲食、住宿、出行、游覽、購物、娛樂以及救援、電信、銀行等服務行業的相關信息,有些還代理車船機票、景區門票、旅游地圖、旅游小冊子、旅行用品和旅游紀念品等。
由于城市是工業、服務業的集聚地,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功能。因此,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場結構中,除觀光、度假、休閑外,購物、商務和會展占有相當的比例。因此,會議展覽設施也是旅游城市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
四、中國旅游城市建設的反思
在封建時代,我國城市建設體現的是以皇權至上的社會等級秩序。近代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一些沿海港口相繼開埠,成為對外通商口岸,奠定了現代工商城市的基礎。建國之初,百廢待興,為了急于改變舊中國積貧積弱的局面,盡快實現工業化是新政府的首要執政目標,當時的一些政治口號和流行語如“趕英超美”、“大躍進”、“先生產,后生活”等多多少少反映了這種執政理念和治國策略。那個年代高聳林立的煙囪、嘈雜的機器聲、隨處可見的政治標語成為城市的標志性景觀和主旋律。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城市建設的進程加快,城市建設開始向西方化的“宏大敘事”轉向,商業化彌漫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各大城市紛紛借一些重大題材的節事活動更新建造“地標性”建筑,各類摩天大樓、巨型廣場、城市CBD等“形象工程”拔地而起,競相斗奇。拼錢炫富,城市間競爭成為一場暴發戶們的燒錢競賽。
當“現代化”與“國際化”成為一種模式,成為一種時尚,城市建設非但會在能源消耗、環境污染等方面付出重大代價,更讓人擔憂的是,我們的城市也將日益喪失自己的個性,喪失自己的文化基因。張欽楠在《閱讀城市》中說:“人類歷史始終是前進的,但又從來不是一切從頭開始的。每一代人都要能判斷自己對過去的歷史保留哪些,改革哪些,更新哪些。對一棟建筑物是如此,一個鄰里是如此,一座城市也是如此,大而言之,對一個國家的文化也是如此。”全球化有一種消弭差異的意欲力,但人類精神發展的本質在于統一性和差異性的互滲,全球化也意味著它將參與控制地方化的建構過程,使文化形成越來越失去固定空間的限制,并很難集合為整體的地方傳統。荷蘭發展合作部部長簡·普蘭克曾發表過一個令人深思的觀點:“全球化是盲目的。由于經濟利益的驅動,全球化沖破了疆界,幾乎不顧任何道德規范。假如我們今天不加警惕的話,全球化可以摧毀我們的心理防線和民主觀念。”這是西方國家對全球化作出的深刻反思。
《北京憲章》(1999)認為:建筑是地區的產物,其形式的意義來源于地方文脈,并使地方文脈發揚光大。可是,這并不是說地區建筑僅僅是地區歷史的產物,一成不變;恰恰相反,地區的建筑更與地區的未來相連。不同國度和地區之間的交流,并不是方法與手段的簡單轉讓,而是激發各自想象力的一種途徑。
吳良鏞院士曾呼吁:“面臨席卷而來的‘強勢’文化,處于‘劣勢’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內在的活力,沒有明確的發展方向和自強意識,不自覺地保護與發展,就會顯得被動,有可能喪失自我的創造力與競爭力,淹沒在世界‘文化趨同’的大潮中。”一位荷蘭建筑教授亞歷山大·楚尼斯指出,“近年來在國際設計領域廣為流傳的兩種傾向,即崇尚雜亂無章的非形式主義和推崇權力至上的現實主義。”這股思潮已經由境外建筑師引入中國,中國已經成為他們設計思想的試驗場,甚至奇思怪想的試驗場。今天的許多建筑追求新穎,超乎現實的“完美”,激動人心的奇特,紀念性,宏大,愉悅,媚俗等等,形式在追逐利潤中得到張揚。城市終究是我們人類的家園,是以適宜人的生存和生活為主旨,而不是以物的存在為核心,建筑是為人服務的。無論是西方后現代追求的“詩意地棲居”,還是中國古人崇尚的“采菊東籬下”,都是對身心解放、廓然無累、優雅從容的生活方式的憧憬。從這個意義上講,中西方城市文明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一致的,對美的精神需求是一致的。城市也應該是我們今天提倡的和諧社會的空間載體。但是,目前的城市建筑正從過去“千篇一律”的極端,走向“千奇百怪”的另一個極端;從“仿古一條街”走向“萬國租界”,從“小橋流水人家”走向“宏構巨筑”,從對人的漠視到對物的崇拜。唯獨缺乏當下的屬于我們這個民族、這個時代的城市和建筑風格,一個城市歷史記憶的喪失和文化沉積的斷裂是后世無法用經濟救贖的。對于人道關懷和人文情懷的匱乏不僅體現在城市建筑上,也同樣反映在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方面,在擠壓和局促的空間下,現代城市的發展,被商業的力量所控制,日益脫離了人的生活世界。機械論和規劃的“技術制定”模式消弭了生活的多樣性。汽車則提供了進一步分散的可能。因此,流動不再受步行距離的限制,由此,導致了郊區的蔓延。郊區化造成社區崩潰、場所消失、建筑彼此隔離、土地浪費、環境惡化、人的情感紐帶被割斷。
現在國內許多城市都口口聲聲“以人為本”,但事實上,時時處處“與人為敵”。在追求城市發展“高大全”、“高大上”的同時,漠視了與最大多數人的需要息息相關的細微之處。在道路越修越寬的同時,自行車道、步行道、坡道和盲道不是建成迷宮,就是變成斷頭,甚至干脆消失。靜謐的林蔭道也只能永遠地成為兒時的集體記憶。公共交通系統雖然發達,但換乘不便。身份歧視性的公共政策,低效率的公共服務隨處可見。對于外來游客的不友好環境,城市標識系統的混亂和缺失,而正是這些細節,才決定了城市的品質。
旅游城市建設應該達成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本地居民和外來游客之間的和諧;各類族群之間的和諧;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和諧等等。充分體現對于有特殊需要人群(如殘障人士、老人、孕婦和兒童等)的人道關懷;對于低收入人群的利益關切;對于宗教信仰人士的理解尊重;對于邊緣性人群(如同性戀者、艾滋病患者、乙肝患者等)的寬厚包容。
五、結語
城市旅游仍然是目前大眾旅游的主要方式,旅游城市也是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但旅游城市還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和各相關利益方共存共享的空間綜合體,未來的城市發展既不應是西方中世紀城邦城堡的升級版,更不應成為富人俱樂部的擴大版,而是“為最大多數人提供最大、最持久的幸福”,讓各相關利益方各得其所,各享其樂。
美國著名城市規劃學家、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伊利爾·沙里寧曾說過一句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界流傳甚廣的名言:“城市是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負。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說出這個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什么。”但是,在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居民的文化追求是無足輕重的,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城市建設一直是由政府主導和政策推動的。但在全球現代化的浪潮下,我們的城市究竟要以什么文化基調和底色來吸引旅游者,未來旅游城市的建設應向何處去?旅游城市如何才能在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多個方面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是城市決策者在新型城鎮化建設時,面臨的一系列世紀難題。
[1][比利時]亨利·皮雷納,陳國樑譯.中世紀的城市[M].商務印書館,1985.
[2]古詩韻,保繼剛.城市旅游研究進展[J].旅游學刊,1999(2):15-20.
[3]田銀生,劉韶軍.建筑設計與城市空間[M].天津大學出版社,2000.
[4][英]埃比尼澤·霍華德,侯鯤譯.明日的田園城市[M].商務印書館,2000.
[5]魏小安,張凌云.共同的聲音:世界旅游宣言[M].旅游教育出版社,2003.
[6]張欽楠.閱讀城市[M].三聯書店,2004.
[7]許學強,周一星,寧越敏.城市地理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8][美]理查德·弗羅里達,侯鯤譯.你屬于哪座城市?[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9]魯勇等.旅游思辨[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10]呂超.從“烏托邦”到“異托邦”[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12,27(B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