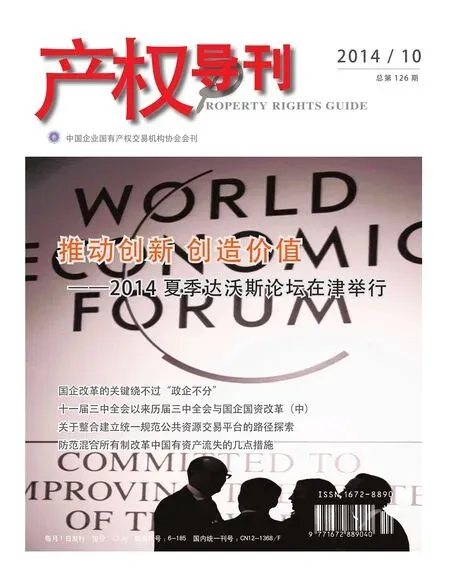亞洲經濟一體化:半是風雨 半是彩虹
◎ 蔡玉梅
亞洲經濟一體化:半是風雨 半是彩虹
◎ 蔡玉梅
亞洲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基礎和重要動力。雖然亞洲經濟一體化如今依然關山阻隔,步履維艱,但貿易依存度和互相直接投資水平提升、三家金磚國家成員領導力增強、區域性經濟組織活躍、地緣政治氣氛緩和等利好都將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早日迎來艷陽天。
當下,世界經濟已進入大變革時代,亞洲地區正面臨著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等重大挑戰。在這一背景下,亞洲各國清醒地認識到,經濟一體化是亞洲新一輪增長的基礎和重要動力。而實際上,亞洲經濟一體化也是伴隨著風雨和彩虹,一路走來。
歷史進程
亞洲經濟一體化始于中國加入東南亞國家聯盟(以下簡稱“東盟”)。東盟涵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文萊、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在內的整個東南亞十國。東盟的前身是馬來亞(現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東南亞聯盟。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四國外長和馬來西亞副總理在曼谷舉行會議,發表了《曼谷宣言》,即《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立。東南亞國家聯盟成為政府間、區域性、一般性的國家組織。1967年8月28-29日,馬、泰、菲三國在吉隆坡舉行部長級會議,決定由東南亞國家聯盟取代東南亞聯盟。2002年1月1日,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這六個老成員國于2002年將絕大多數產品的關稅降至0~5%。越南、老撾、緬甸和柬埔寨四個新成員國將于2015年實現這一目標。
2003年,隨著中國與東盟的關系發展為戰略協作伙伴關系,中國成為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非東盟國家。2004年11月,中國-東盟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規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獲產品和少量敏感產品外,雙方將對其他約7000個稅目的產品實施降稅。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涵蓋18億人口,GDP超過2萬億美元,貿易額達1.23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有著鮮明的地區特征:
第一,亞洲是經濟一體化先行,政治上的保留、防范一直存在,甚至有時還發展成對抗。而歐洲、北美經濟一體化及政治上的融合是同步的,其經濟一體化有政治一體化作支撐。如何使亞洲有關國家把對外關系處理好,經濟一體化先行開道,同時又要防止政治上的摩擦、紛爭影響經濟一體化的深化;反過來,又通過經濟一體化增強雙方互信,求同存異,并加強溝通和對話,使分歧逐步得到解決。這個共同的問題一直在考量亞洲各國領導人的智慧。
第二,從一開始,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就有著濃厚的對抗發達地區強大經濟體的色彩,這與亞洲各國歷史和近代經濟發展趨勢有著密切的關系。平心而論,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是由日本經濟起飛帶動的。在其醞釀期,日本作為地區經濟的領頭羊,在產業結構升級的驅動下,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轉移夕陽產業,促進了亞洲國家、地區在經濟合作上的相互認同。盡管目前日本的國際形象比較差,但它對亞洲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確是不可否認的。在日本之后,中國經濟的崛起對亞洲大陸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有著極強的示范作用,成為亞洲經濟一體化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的穩定器。
第三,多樣性突出。亞洲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現有49個國家和地區。亞洲的多樣性在全球首屈一指,從地理角度來看,分為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中亞和北亞。各國社會制度、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宗教、文化、種族等千差萬別,像土耳其這樣帶有濃郁的歐洲色彩的國家甚至有“脫亞”的念頭。這種多樣性對于亞洲經濟一體化來說是“弊多利少”。
步履維艱
相比風生水起的歐洲經濟、北美經濟一體化,亞洲經濟一體化如今卻關山阻隔,步履維艱。
首先,經濟基礎薄弱。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顯著標志是“互聯互通”。亞洲地區多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薄弱,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金融機制,抑或能源供給,離互聯互通的要求差距還很大。當全球金融危機來襲時,亞洲脆弱的經濟便遭受摧殘。美國的第三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3)又將亞洲經濟套上流動性的絞索,一旦QE3退場,亞洲經濟又將被大量“抽血”。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也阻礙了亞洲經濟一體化進一步發展。而歐洲經濟一體化不僅有密如蛛網的鐵路相聯通,還有成熟的金融體系作為保障,而且一條輸油管道覆蓋歐洲大地保證了能源共享。至于北美,則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大洲,其最主要的兩個國家——美國和加拿大均為發達國家,人類發展指數較高,經濟一體化水平也很高。
其次,缺失大國核心引領作用。從人口、國土面積和經濟實力綜合起來看,亞洲有4個大國,即中國、俄羅斯、印度和日本。但這4個大國在亞洲地區卻都缺失大國核心引領作用。中國因經濟轉型,眼下無力挑頭搞亞洲經濟一體化,一個尷尬的現實是,中國至今尚被排斥在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之外,很難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上有所作為。俄羅斯正遭到歐美經濟制裁,自顧不暇。印度雖然GDP已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但依然有超過3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有著巨大的貧富差距和政府腐敗。日本經濟實力雖然雄厚,但“國家德行”很差,在國際經濟舞臺難有號召力。反觀,歐洲經濟一體化有德、法兩國雙軸心支撐,有強大的向心力,北美經濟一體化有美國無與倫比的國力作后盾,大國核心早已確立,號召力強,正主宰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趨勢。
再次,地緣政治阻遏。亞洲雖不是火藥桶,但從未平靜過,地緣政治復雜。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朝核危機、印巴領土爭奪、菲律賓和越南的“小國鬧騰”等狀況讓亞洲不得安寧。而美國的戰略東移,戰略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太地區,像一根攪水棒,攪得亞洲難得消停。美國時不時地在中國與鄰國之間制造摩擦,企圖孤立中國。歐洲經濟一體化之所以高歌猛進是因為地緣政治相對和睦,國與國之間政治上相互摩擦較少,所以經濟一體化也需要“人和”。即便英國有“脫歐”的想法,但真的離開歐盟這個大家庭,它也會感到孤單。
又次,區域性經濟組織作用有限。歐洲經濟一體化有歐盟這個緊密型的經濟組織作平臺,運作順暢。北美經濟一體化則有泛美自由貿易區作載體,運轉靈活。在亞洲,比較有影響力的區域性經濟組織是東盟,但其作用只局限于東南亞。近幾年,在美國插手TPP合作之后,原來以東盟為中心的“10+3”、“10+6”合作框架受到沖擊,被邊緣化。而亞太經合組織(APEC)雖說權威性遠超過東盟,但其目前還只限于反恐方面的合作,經濟方面的合作還沒有實質性進展。唯有促使APEC回歸作為地區經濟一體化平臺的功能,才能逐步重新凝聚共識,推動亞太合作邁向深入,從而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
最后,亞洲地區缺乏強大的最終消費品市場。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都蘊藏著巨大的購買力,高福利的國家消費政策積蓄著龐大的消費需求,這也促使兩個地區經濟一體化建設。而亞洲由于多為發展中國家,購買力有限,缺少最終消費品高度集中的市場,也就制約著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有利條件
亞洲經濟這幾年的發展成績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倍受全球矚目的,特別在是金融危機中,作為新興市場,亞洲經濟的成長有目共睹。亞洲各國在經濟發展中的相互依存度越來越大,走向一體化實屬大勢所趨。而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改變不了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總趨勢,因為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優勢是軍事而非經濟。作為后來者,美國對亞洲經濟的滲透和擴張還需要假以時日。
其實,亞洲地區也有實現經濟一體化的有利條件,不可等閑視之。
亞洲的貿易依存度已處于較高水平,域內經濟體間的相互直接投資水平也在提升,為地區經濟一體化提供了基礎。截至2013年,亞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從2002年的36個增至109個,另有148個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談判之中,將會使亞洲經濟一體化明顯加速。
亞洲地區的中國、印度和俄羅斯都是“金磚國家”成員,而目前金磚國家正從松散型向密集型轉變,以成立金磚銀行為標志,金磚國家在亞洲經濟一體化中可發揮大國核心引領作用。
亞洲地區內區域性經濟組織正在活躍著顯露自己。急于做大做強的東盟充當領軍角色,彌漫著樂觀情緒的東亞經濟整合的熱潮一波接著一波,原本異想天開的包括中國東北、朝鮮、韓國、日本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東北亞經濟圈”正緊鑼密鼓地籌備。而以東盟一體化、東亞“10+3”及南亞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為代表的諸多“碎片式”努力在不同程度地推進,從未因世界經濟復蘇緩慢而懈怠,正匯集成亞洲一體化的洪流。
亞洲地緣政治的緊張氣氛近來有所緩和。近來,越南派出特使訪問中國,日本也有與中國高層政治接觸愿望的跡象,一些小國在中國周邊的地緣摩擦正趨緩,這些都有利于亞洲經濟一體化沖破政治藩籬。而美國對亞洲崛起的遏制充其量也是搞小動作,阻擋不了亞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潮流。
亞洲國家普遍重視內需市場的培植,特別是中國,正在擴大內需,為最終消費市場擴大購買力。須知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和美歐債務危機可能是一次全球性的經濟洗牌。美國國內市場已趨向飽和,貿易政策也越來越保守,正倒逼全球特別是亞太產業重組。今后亞洲經濟增長將主要依靠區域內的資源配置和產品消費能力(這就是經濟一體化),而不再像二戰后相當長時期那樣依賴對美國的出口。
風雨過后是彩虹,亞洲經濟一體化的艷陽天一定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