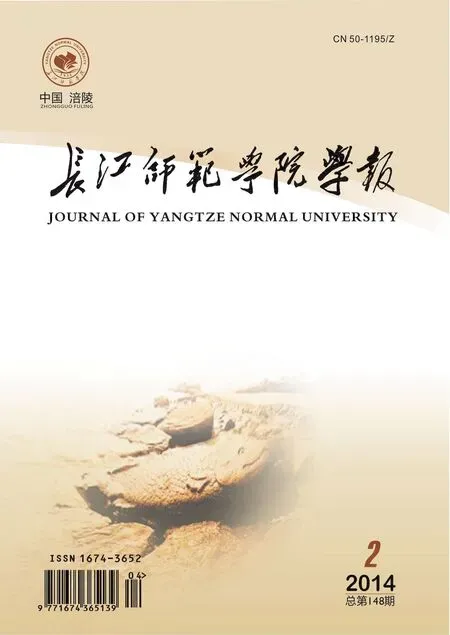牛郎織女起源追尋
楊德春
(邯鄲學院 中文系,河北 邯鄲 056005)
牛郎織女起源追尋
楊德春
(邯鄲學院 中文系,河北 邯鄲 056005)
就現(xiàn)有材料來看,《詩經(jīng)·周南·漢廣》是牛郎織女傳說的原始形態(tài);今陜西西部和甘肅東部不是有關(guān)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產(chǎn)生的地域,而只是其流傳地域,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產(chǎn)生的地域當是 《詩經(jīng)·周南·漢廣》所涉及之漢水中下游流域;湖北云夢縣睡虎地出土之秦簡《日書》如果可靠或可信,即不存在偽造、摻假或其他作偽情況,則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在戰(zhàn)國時期有了新的發(fā)展,并且已經(jīng)基本定型。叔均、女脩與牛郎織女起源無關(guān)。《秦風·蒹葭》與牛郎織女起源無關(guān)。
牛郎,織女,起源
一、《詩經(jīng)·周南·漢廣》中有關(guān)牛郎織女起源的新材料
《詩經(jīng)·周南·漢廣》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1]53—56第一段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起興,男方貧窮,難以在女方家樹下休息。第二、四、六段皆言漢之廣、江之永,重章疊句,強調(diào)被河分開。第三、五段言結(jié)婚。婚后即被分開。
毛 《序》稱:“《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1]52依照毛 《序》,《漢廣》是文王時期的詩歌,當時漢水流域并未進入農(nóng)耕開發(fā)時代,從 《漢廣》的內(nèi)容來看也無農(nóng)耕跡象。故牛郎織女并不是反映男耕女織,而是反映統(tǒng)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致使男性勞動者娶妻困難。依照毛《序》,《詩經(jīng)·小雅·大東》是西周末期的作品,詩中 “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所反映的是牛郎竭盡全力牽牛拉車的情景,牛郎是牽牛郎或曰牽牛拉車的人,與男耕無關(guān);放牛是牛在前而放牛郎在后,也與牽牛的情景不合,可見,“牛郎織女”傳說在 《詩經(jīng)·小雅·大東》所反映的時期里和階段上也與男耕無關(guān)。
《詩經(jīng)·周南·漢廣》開篇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起興,實隱喻女方地位高,而男方地位低且不能及之。《毛傳》云:“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1]53則喬木指高聳而枝條向上之樹木。“息”與 “思”通用,孔穎達 《疏》云:“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為義,故為辭也。經(jīng) ‘求思’之文在 ‘游女’之下,傳解 ‘喬木’之下,先言 ‘思,辭’,然后始言 ‘漢上’,疑經(jīng) ‘休息’之字作 ‘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為韻,二字俱作 ‘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1]54孔穎達之說是。又惠棟 《九經(jīng)古義》卷五云:“案 《韓詩外傳》息作思,《樂記》云:‘使其文足論而不息。’《荀卿子》息作諰。 《說文》云:‘諰,思之意,從言從思。’《禮記》多古文,或思、息通也。”[2]故作息與作思完全一樣,完全可以通用。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之 “游女”大可玩味,此 “游”字當是 “游泳”之 “游”,這就是牛郎織女故事織女游水衣服被牛郎拿走的雛形。
關(guān)于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含義。朱熹《詩集傳》:“興而比也。”[3]6朱熹此說為誤,朱熹以 《漢廣》通篇為興而比也[3]6,此說與 《漢廣》之實際不相符合,“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就是賦,“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雖然是興,但也有賦的因素,可謂興而賦也。比照第一章,第二章之首二句之手法當與第一章同,否則結(jié)構(gòu)不一致。另外,《詩經(jīng)》之詩為現(xiàn)實主義作品,賦之使用大于比興之使用。朱熹云:“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6]1所詠之詞是賦,朱熹以 《漢廣》通篇為興而比也,沒有引起所詠之詞,如此則興之目的何在?故可認為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是賦或興而賦也。
既然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是賦或興而賦也,那么,“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就是實寫抒情主人公之生活,即刈草是抒情主人公之生活內(nèi)容或曰工作。 《漢廣》接言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與第一章相同,這也是賦。 《漢廣》的抒情主人公是男性下層勞動者,他在新娘嫁給他時為新娘喂馬,則其工作當是與喂馬相近之工作,與喂馬最相近的工作就是刈草以喂牛,《漢廣》的抒情主人公當是放牛郎。
《漢廣》詩中的 “漢”為地上的漢水,反映的是牛郎織女傳說的原始形態(tài)。漢之本意當是地上漢水之名,隨著牛郎織女傳說的發(fā)展,牛郎織女傳說由地上發(fā)展到天上,天上的銀河也被稱為漢、銀漢、天漢。如 《小雅·大東》云:“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1]786就稱銀河為漢。《大雅·云漢》云: “倬彼云漢, 昭回于天。”[1]1193則稱銀河為云漢。
揚之水 《詩經(jīng)別裁》云:“‘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古詩十九首》之句由 《漢廣》脫胎,但 《漢廣》卻沒有如此之感傷。”[4]17其實,《古詩十九首》第十首 “迢迢牽牛星”前半部分脫胎于 《大東》,后半部分脫胎于 《漢廣》,這是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稍有一點修養(yǎng)者都能看出的不爭事實,這也就證明了 《漢廣》是牛郎織女傳說的原始形態(tài)。
二、關(guān)于牛郎織女起源的時間和地域
《小雅·大東》稱: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獲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1]779—789
毛 《序》云:“《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1]779跂,《說文解字》引作一個其左邊為匕、其右邊為支的字,該字 “頃也,從匕支聲。”[5]168跂彼織女乃織女身體頃身 (織機),以此言織女竭盡全力紡織。《玉篇》云: “睆,華綰切,目出皃。”[6]83睆彼牽牛乃牽牛眼睛突出,以此言牽牛竭盡全力牽牛拉車。“終日七襄。”《毛傳》云:“襄,反也。”[1]786《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1]786如此解釋 “七襄”,則“七襄”與 “不成報章”失去關(guān)聯(lián)。 《說文解字》云:“漢令解衣耕謂之襄”[5]172。襄的本義為解衣耕,即解開衣服拼命干活。“七襄”之意就是七個人解開衣服拼命干紡織活,織女或被稱為七仙女,“七襄”是牛郎織女傳說中七仙女的現(xiàn)存最早之來源。七仙女和前來幫忙的六位姐姐拼命紡織,還是織不成章。如此則 “雖則七襄”與 “不成報章”在意義上才能形成關(guān)聯(lián),故也只有如此解釋才是正確的解釋。
毛 《序》稱:“《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1]52根據(jù)詩序,《漢廣》為周文王時期之作品。
由人類認識水平的發(fā)展來看,人類必是先認識距離自身較近之事物,然后才可能認識距離自身較遠之事物。人類必然是先認識了身邊之地上之漢水,然后才可能認識遙遠天空中之天漢。故 《詩經(jīng)·周南·漢廣》產(chǎn)生之時間要早于 《詩經(jīng)·小雅·大東》產(chǎn)生之時間。毛 《序》稱:“《大東》,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1]779《大東》之作時當在西周末期,如此則 《詩經(jīng)·周南·漢廣》之作時當在西周初期,詩序以 《漢廣》為周文王時期之作品當可信。
由以上分析可知,《詩經(jīng)·周南·漢廣》是現(xiàn)存最早的有關(guān)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的文獻。如此則《詩經(jīng)·周南·漢廣》所記載之漢水中下游流域是有關(guān)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產(chǎn)生的地域。《小雅·大東》是京畿之音,鎬京只能是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的流傳地域,而絕不是有關(guān)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產(chǎn)生的地域。秦遠在豐鎬以西,平王東遷秦始有豐鎬之地,而此時 《詩經(jīng)·周南·漢廣》《小雅·大東》早已寫成,故今陜西西部和甘肅東部絕不是有關(guān)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產(chǎn)生的地域,而只能是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的流傳地域。
1975年在湖北云夢縣睡虎地出土秦簡 《日書》中有兩簡寫到牽牛織女的情節(jié)。《日書》甲種155簡正面云 “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不果,三棄。”[7]206第3簡簡背云:“戊申、己酉,牽牛以取織女而不果,不出三歲,棄若亡。”[7]208看來 《三輔黃圖》中載秦始皇并天下以后 “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8]是可信的。《日書》所謂 “不果”不是沒有娶成之意,而是沒有結(jié)果,即牽牛以取織女而未能白頭偕老之意。“牽牛以取織女”之 “以”通 “已”,是 “已經(jīng)”之意。《戰(zhàn)國策·楚策一·五國約以伐齊章》云:“五國以破齊,秦必南圖。”[9]484其中之 “以”通 “已”,是 “已經(jīng)”之意,可作為 “牽牛以取織女”之 “以”通 “已”、是 “已經(jīng)”之意的訓詁依據(jù)。由此可見,《日書》所記載之牛郎織女的故事已經(jīng)相對成熟,《日書》所記載之牛郎織女故事之結(jié)局與現(xiàn)今流傳之牛郎織女故事之結(jié)局已經(jīng)基本一致,而 《詩經(jīng)·周南·漢廣》和 《詩經(jīng)·小雅·大東》中之牛郎織女故事均無結(jié)局。湖北云夢縣睡虎地出土之秦簡 《日書》如果可靠或可信,即不存在偽造、摻假或其他作偽情況,則可證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在戰(zhàn)國時期又有了新的發(fā)展,并且牛郎織女故事或曰傳說在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基本定型。
三、叔均、女脩與牛郎織女起源無關(guān)
《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記載:“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xiāng)。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10]430田祖是主管田地之神,《山海經(jīng)·大荒北經(jīng)》明確記載叔均乃為田祖。
《山海經(jīng)·大荒南經(jīng)》記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10]364叔均,又叫商均,傳說是帝舜之子。帝舜南巡至蒼梧之野而死,就葬于蒼梧之野,叔均死后也葬于蒼梧之野。
《山海經(jīng)·大荒西經(jīng)》記載,“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臺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10]392—393帝俊,這里指帝嚳,名叫俊。傳說他的第二個妃子生了后稷。后稷,古史傳說他是周朝王室的祖先,姓姬氏,號后稷,善于種莊稼,死后被奉祀為農(nóng)神。叔均,《山海經(jīng)》曾說叔均是后稷的孫子,又說是帝舜的兒子,這里卻說是后稷之弟臺璽的兒子,諸說不同,實屬神話傳說之分歧。
《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載:“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10]469帝俊,這里也是指帝舜。義均就是上文所說的叔均,但說是帝舜的兒子,這里卻說是帝舜的孫子,此屬于神話傳說的不同。關(guān)于叔均,上文曾說叔均是后稷之弟臺璽的兒子,這里又說是后稷的孫子,而且和前面說的義均也分成了二人,神話傳說分歧,往往有所不同。
《史記·五帝本紀》載:“帝顓頊高陽者,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11]11《史記·五帝本紀》又記載:“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為族子。”[11]13《史記·五帝本紀》又記載:“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勛立,是為帝堯。”[11]14《史記·五帝本紀》又記載:“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2]31顓頊為黃帝之孫,帝嚳為黃帝之曾孫,顓頊之侄子,生堯,黃帝至堯為五代,至堯之二女為六代,舜據(jù) 《史記》為第七代,故堯之二女當為舜之姑母。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yè)。大業(yè)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后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diào)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11]173
秦始祖女脩乃顓頊苗裔孫,苗裔現(xiàn)在多譯作后代子孫,誤。《史記·秦本紀》記載:“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yè)。大業(yè)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大費與禹平水土,則大費必與禹為同時代之人,則大費之父大業(yè)之母女脩必為與堯大致同時代之人。堯為帝嚳之子、顓頊之孫,則女脩與堯同時,即女脩與堯一樣,也為顓頊之孫。顓頊為黃帝之孫,帝嚳為黃帝之曾孫,顓頊之侄子,生堯,黃帝至堯為五代,至堯之二女為六代,舜據(jù)《史記》為第七代,故堯之二女當為舜之姑母。但六代、七代俱出五服,可婚配。黃帝至女脩為五代,未出五服,叔均為后稷侄,后稷為姜嫄生,姜嫄為帝嚳嫡妃,即后稷為帝嚳子,與堯同輩。
可見,由黃帝至叔均為六代,但叔均稱女脩為姑母,一個剛出五服之人與一個未出五服之人,豈可戀愛?又豈可侄子與姑母戀愛?且女脩與堯為同時代之人,而叔均與舜為同時代之人,或曰:叔均為舜子商均。如此則商均稱女脩為姑奶奶,孫子與姑奶奶豈可戀愛?叔均為舜或舜后之人,女脩為堯時之人,兩人年齡相差懸殊,且女比男大一代或兩代人的年齡,豈可戀愛?
秦部族是勇武之部族,秦人性情剛烈,民風彪悍,繼周而有岐豐之地,周為失敗者,而秦為勝利者,秦地人民豈可流行以勝利者之秦人為女性而以失敗者之周人為男性,以勝利者之秦人所化作之女性而委身于以失敗者之周人所化作之男性之傳說?
周之始祖活動于岐豐之地,秦之始祖活動于西戎之地,兩個部族或民族,未聯(lián)合為一個部族或民族,風馬牛不相及,周之始祖與秦之始祖豈可戀愛?
司馬遷只記女脩吞卵生子,未記女脩有夫叔均或牛郎,可證司馬遷之前未將女脩與織女相聯(lián)系。
四、《秦風·蒹葭》與牛郎織女起源無關(guān)
《詩經(jīng)·秦風·蒹葭》云:“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1]422—424
方玉潤 《詩經(jīng)原始》云:“右 《蒹葭》三章,章八句。此詩在 《秦風》中氣味絕不相類。以好戰(zhàn)樂斗之邦,忽遇高超遠舉之作,可謂鶴立雞群,翛然自異者矣。”[12]273可見,《秦風·蒹葭》根本就不是產(chǎn)生于秦人原所居之西垂之地的作品。《秦風·蒹葭》的風格與 《周南·漢廣》的風格完全一致,這說明 《秦風·蒹葭》的產(chǎn)生地域在漢水流域,應當與 《周南·漢廣》一起編入 《周南》。
既然 《秦風·蒹葭》的產(chǎn)生地域在漢水流域,應當與 《周南·漢廣》一起編入 《周南》,那么,《秦風·蒹葭》何以竟然編入 《秦風》? 《史記·秦本紀》記載:“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zhàn)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緌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11]179秦襄公遂有周地,因周南之地處于南方,遠離戎地,周平王東遷后,秦不戰(zhàn)而周南之地即歸于秦。產(chǎn)生地域在漢水流域的 《蒹葭》由此而編入 《秦風》。由此可見,由產(chǎn)生地域來看,《秦風·蒹葭》與秦人始祖無關(guān)。
關(guān)于 《秦風·蒹葭》的詩旨,毛 《序》云:“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1]422”。鄭玄 《箋》云:“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1]422甚是。 《秦風·蒹葭》一詩詩序以為秦襄公時之作,而產(chǎn)生于秦文公時之石鼓詩第二首云:“于水一方”。此指文公初遷至汧、渭之間所見情景,與 《秦風·蒹葭》中 “在水一方”句型和句意完全一致,石鼓詩第二首是襲用了 《秦風·蒹葭》之成句。平王東遷,以其地贈秦襄公,秦襄公與其子秦文公始可得見周南風光。
《秦風·蒹葭》云:“所謂伊人,在水一方。”[1]422首先,毛 《傳》云:“伊,維也。一方,難至矣。”[1]422鄭玄 《箋》云:“伊當作繄,繄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1]422現(xiàn)根據(jù)鄭玄 《箋》,伊人乃指那個知周禮之賢人,該人斷不會是一個女人,伊人不是女人,則 《秦風·蒹葭》與織女傳說斷然無關(guān)。伊人不是女人則必為男性。既然伊人為男性,一般不可能存在女追男還追不上之情況,則 《秦風·蒹葭》斷不會是愛情詩。如此則 《秦風·蒹葭》與牛郎織女傳說也就根本不沾邊了,即 《秦風·蒹葭》與牛郎織女傳說無關(guān)。其次,伊人,即彼人,所謂伊人即所說的那個人,當指別人告訴的那個人,自己連自己的戀愛對象都不知道,若說 《秦風·蒹葭》是愛情詩,則這種愛情詩古今中外絕無僅有啊!
既然伊人斷不會是女人,那么,伊人究竟指什么呢?漢水流域之人民原不屬周南管轄,周昭王南征,始有其地,平王東遷,以其地贈秦襄公,不肖子孫不知祖先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秦風·蒹葭》所思之人斷不會是周平王。秦襄公以治秦之法治宗周故地,棄文治而尚勇武,國人或慕文、武、成、康之治而思文、武、成、康其人,但文、武、成、康之時,漢水流域未入周土,故國人或思文、武、成、康之時,兼及使?jié)h水流域并入周土之人。周昭王南征,漢水流域始入周土,其地始行文、武、成、康之治,故國人所思之伊人系周昭王。
伊人,明言人,不是神。既然是人,于如此尋找之下,當可找到,此詩未找到當為其人溺水而死,且死尸未找到。沿河找人,一般是可以找到的,若未找到,考慮到與河有關(guān)之因素,一般未能找到則必死于河。秦襄公初入周地,以戎法治周,周人之賢者思周昭王,所謂伊人,即為周昭王諱,在水一方,在水中一地方,周昭王溺水而死,且死尸未找到,其必在水中一地方,宛在水中央乃好像在水中,其為幻覺無疑。湄、涘皆為水邊,水中坻、水中沚皆為水中小渚,宛在,是幻覺,好像看到周昭王的死尸在水邊或水中小渚。
由此可見,《秦風·蒹葭》與牛郎織女傳說無關(guān),《秦風·蒹葭》與牛郎織女起源更是無關(guān)。
[1][唐]孔穎達.毛詩正義[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2][清]惠 棟.九經(jīng)古義[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宋]朱 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8.
[4]揚之水.詩經(jīng)別裁[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5][漢]許 慎.說文解字[M].北京:中華書局,1963.
[6]宋 本.玉篇[M].北京:中國書店,1983.
[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8]佚 名.三輔黃圖[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9]何建章.戰(zhàn)國策注釋[M].北京:中華書局,1990.
[10]袁 珂.山海經(jīng)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1][漢]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2][清]方玉潤.詩經(jīng)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3]張開焱.混沌創(chuàng)世神話研究述評[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2).
[責任編輯:田 野]
K828.9
A
1674-3652(2014)02-0093-05
2013-12-15
楊德春,男,河北遵化人,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先秦兩漢文學與文獻研究。